
▲ 2019年4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芬太尼类物质管制进展及下步工作情况,图为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与记者交流。(人民视觉/图)
“您相不相信?有那么一种人,人很好、很简单,从来不惹事,突然有一天,在人生一切都有可能的年纪,所有的可能都被掐灭了……”王丽是一个“制毒者”的妻子,其夫刘迪森是2016年武汉“8·25走私贩卖毒品”案主犯之一。案发半年前,刘迪森与前同事一起创业,因生产毒品芬太尼,公司被“一锅端”,警方在现场查获芬太尼二十多公斤,刘迪森等5人被捕。芬太尼是一种麻醉药品,但它也可以被认定为毒品,根据法律规定,制造、贩卖125克以上,就可判处死刑。然而,作为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刘迪森等人均表示,自己不知道芬太尼是毒品。5人案发时都不到30岁,其中只有两人成家。刘迪森被抓时,妻子王丽怀孕仅两个月,8个月后出生的孩子,至今未见过父亲。2019年12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作为涉案芬太尼生产工艺的研发者,刘迪森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4人分获有期、无期徒刑,以及死缓。刘迪森等人随后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刘迪森早年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曾出具证明,称刘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为人善良。另有138人联名向二审法院“请愿”,称刘因年少无知而误入歧途,并无危害社会的本心,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宽处理。“请愿书”未能起到作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在王丽眼中,刘迪森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男”: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两点一线,惟一嗜好就是打游戏。刘迪森读高中时就对化学感兴趣,获过全国化学竞赛三等奖。2011年,他从南昌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后,先去上海一家药业公司工作,2013年去武汉,成为武汉赛狮药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狮公司”)研发部的一名技术员。据案卷资料,2016年4月,前同事伍敏、程生祥找到刘迪森,向他了解芬太尼的制作工艺。刘迪森当时在赛狮公司就负责这类产品的研发。相关论文显示,芬太尼是一种麻醉药品,但其药理作用和毒品海洛因相似,滥用后会带来愉悦、欣快等精神感受,并具有成瘾性,联合国早在1964年就将其纳入相关公约进行管制。在中国,芬太尼最早于1996年就被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这意味着它从那时起即被作为毒品严格管制。辞职之前,程生祥也是赛狮公司的一名技术员。他所负责研发的是另一种物质——“U-47700”。根据伍敏等人的供述,“U-47700”和芬太尼都属于“医药中间体”,是公司销售的主产品。“医药中间体”是指用于药品合成的化工原料或化工产品,由于所生产的不是药品本身,所以并不需要药品生产许可证,普通化工厂即可生产。不过,“U-47700”和芬太尼并不是普通的“医药中间体”,这两种产品还有一个更为专业的名称——“新精神活性物质”,它是指管制毒品化学结构经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毒品相似的效果,属于新型毒品。不过,只有被列入管制目录之后,“新精神活性物质”才会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掌握“U-47700”的生产技术之后,伍敏和程生祥决定跳出赛狮公司单干。2015年11月,两人注册了一家名叫“格润康捷”的小公司,由于武汉市对本地大学生创业有优惠政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程生祥做了法定代表人。在生产“U-47700”的过程中,伍敏和程生祥了解到客户对芬太尼有需求。但他们不会做,于是找到刘迪森,刘迪森此时正想换工作,便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格润康捷,之后刘迪森介绍了前同事郭彬加入,程生祥则介绍孔令曦加入。孔令曦与郭彬均是公司操作工,每个月拿5000元工资。2016年7月,为“扩大生产”,伍敏等人将公司迁到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某产业园,他们在那里租了一家公司约500平方米的闲置厂房,作为实验室和生产场地。东湖高新区俗称武汉“光谷”。按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8·25案”之前,武汉做“医药中间体”生意的公司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因为“光谷”有许多高校,科研人员集中,不少生产商入驻于此。2016年11月,赛狮公司也将其“研发中心”迁入光谷,相关简介显示,该公司声称“可独立进行从公斤级到吨级的工艺验证与规模生产”。格润康捷则仅能完成“从克级到公斤级产品的定制需求”。在伍敏的供述中,他将列管的芬太尼称作“违禁品”,但对于什么叫“违禁品”,他却表示不知道。刘迪森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以为生产违禁品“最多是行政违规”。根据伍敏的供述,他们生产和销售芬太尼几乎是公开的,并没有“藏着掖着”:制作工具来自一位合作供货商,原料是网购来的,在各类化工产品网站上推广产品,用自己的银行账号收款……仅有的掩饰之处,是公司白天关着门,根据伍敏等人的说法,这是因为生产过程中会有气味产生,他们怕被人投诉。另外,芬太尼的快递单上填的产品名是“食品添加剂”,伍敏向警方交代,这是因为化工品不让邮寄,发货人写的是“张先生”,伍敏说,是客户让他这样写的。据刘迪森供述,他们刚开始做的并不是芬太尼药品本身,而是一种叫“呋喃芬太尼”的衍生物。而当时“呋喃芬太尼”尚未列入管制目录。按刘迪森的说法,“呋喃芬太尼”的效果与芬太尼差不多,制作工艺也类似。至于后来为什么生产起了被列管的芬太尼,刘迪森的解释是:因为有客户“出价比较高”,当时他认为还是打“擦边球”。据“8·25”案一涉案中间商交代,当时贩卖芬太尼的背景是:管制的产品(新精神活性物质)越来越多,替代品的效果越来越差,“老客户还想用原来的产品”。刘迪森还曾研发出“卡芬太尼”的制作工艺。这是一种镇痛效果比芬太尼高出100倍的麻醉药品,2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伍敏的舅舅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听伍敏的母亲说,外甥的公司是做麻药的,“麻醉大象的”。2017年3月,武汉8·25案告破后不久,呋喃芬太尼与卡芬太尼也被国家列管。2017年7月,U-47700被列管。伍敏等人没想到,早在2016年6月份,他们还没做第一批“违禁品”的时候,就已被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盯上”。警方的线索来自一次日常网上巡查。当时,根据国家禁毒办要求,湖北公安禁毒部门对网上发布销售芬太尼类物质信息的公司开展核查。警方最先查到的是格润康捷的客户——武汉一个做医药中间体生意的“中间商”,该中间商“在网上发布新精神活性物质信息,寻求买家”,警方突击检查,发现其涉嫌向境外销售芬太尼。武汉市公安局遂成立专班,将该案命名为“8·25走私贩卖毒品”案。按一位办案民警所说,警方通过中间商查到格润康捷之后,正要采取措施时,发现它已经停止生产芬太尼了,只生产不受管制的产品,当发现格润康捷12月份再度生产芬太尼时,公安机关方才动手。此举后来受到多名被告人家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如果警方在发现格润康捷生产呋喃芬太尼时就查,那么几个年轻人就不至于犯罪。不过,一位办理过芬太尼毒品案的民警认为武汉警方的做法没有问题,因为呋喃芬太尼在那时没有列管,生产并不犯法,警方不能抓人;后来伍敏等人“以身试法”,生产起了芬太尼,警方必须抓人。2016年12月23日,武汉市公安局收网。民警以物业维修的名义敲开了格润康捷公司的大门,将在场的5人全部抓获,现场查获二十多公斤芬太尼,后经鉴定,芬太尼含量在50%以上,无论是数量还是纯度,均堪称国内罕见的一起芬太尼制毒大案。“整个抓捕过程嫌疑人均无反抗行为,未使用武器、警械。”一份8·25案办案材料中这样写道。警方还查明,除了芬太尼,格润康捷还生产过一种名叫α-PVP的违禁品,2015年10月,α-PVP作为新精神活性物质也被纳入管制目录。据伍敏交代,他们生产芬太尼和α-PVP总利润不过17.5万元。破获“8·25案”后,警方根据伍敏、程生祥、刘迪森的检举揭发,抓获了赛狮公司3名涉毒人员,其中包括公司老板张某某,伍敏等人因此被法院认定为立功。武汉警方最初查的那位中间商则逃过一劫。经鉴定,他两次从格润康捷所买的产品分别是“卡芬太尼”和“呋喃芬太尼”,而这两种物质在当时还没列管。时隔4年,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此事时,这位中间商仍后怕不已。他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卖的究竟是哪种芬太尼。警方对格润康捷采取行动的当晚,芬太尼买家之一王道化也在南京被抓,王道化的下家、直接与国外客户联系的王盈波于2017年1月12日在广州落网,替王盈波收发货的季学拯在江西被抓。季学拯自称是王盈波的一个“木偶”,王怎么牵他便怎么动。除了帮王盈波收发货,他还用自己的银行账号代王收取国外买家打来的货款。季学拯对警方说,自己帮王盈波倒卖毒品仅能“赚点烟钱”,一共才挣了1500元。2019年5月1日起,中国对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ICphoto/图)
“8·25案”案发之前,格润康捷曾一度打算不再生产芬太尼。刘迪森、程生祥接受讯问时说,2016年10月,格润康捷在生产卡芬太尼时,曾发生过一次中毒事件,在场5人都出现了呕吐、头晕等症状。他们本来打算不做了,但是伍敏说客户要,不做就会失去这个大客户,于是买了防护服和防毒面具,还找到了一种解毒药,“冒着风险”继续生产。刘迪森出现身体不适后,王丽曾专门在百度上搜过芬太尼。她说,当时只是搜出来一个药盒,这让她认为芬太尼是一种药品,完全没有想过它会是毒品。格润康捷的另一次“刹车”机会是在2016年10月底。那次,程生祥在大学同学微信群里看到了黄冈“名校毕业生制毒案”的报道,他觉得芬太尼可能也是管制的,就在办公室和刘迪森、伍敏都说了。刘迪森在网上下载了一份管制目录,确定芬太尼是管制品。不过,根据他的供述,即便如此,也仅以为就是“类似处方药”的那种管制。知道芬太尼是“违禁品”之后,格润康捷一度停产。但是,根据刘迪森的供述,因为南京客户要得紧,公司又剩下一些上次生产芬太尼的原料,伍敏说“别浪费了”,就决定12月生产最后一批,他和程生祥也没反对。这批芬太尼成为“8·25案”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根据伍敏的供述,他们前后生产过三批芬太尼,总共四十多公斤,但办案机关认定的毒品数量,只是现场查获的二十多公斤和后来查获的已经寄出的一公斤,伍敏之前交代生产的没有计算进去。审讯视频显示,刘迪森对生产芬太尼类物质的各种复杂化学反应式脱口而出,但是被问及国家对精神药品的管制问题时,却经常一脸茫然。他说,在网上看到过相关列管“清单”,但“不知道以哪个为准”。他还说,有客户要甲苯丙胺(冰毒)、美沙酮、麻黄碱,他其实都会制作,但因为知道是毒品,所以都不做。他还问办案人员,如果把这些毒品的制作方法提供出来,能否算立功?警方问他:是不是也做过这些东西?他否认了。程生祥的父亲程连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事前他与程生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11月底,那时,他已经看到过媒体对武汉“绝命毒师”张正波案的报道,担心儿子公司所生产的东西也有问题,还专门叮嘱过程生祥不要制毒,程生祥非常反感,说他怎么可能制毒,父子俩还为此吵了一架。张正波曾是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专业副教授,因研发和生产一种被称作“丧尸药”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媒体称作“绝命毒师”。不过,在出事之前,张正波也没料到自己涉毒。审讯视频显示,被抓之初,刘迪森没想到自己会被判重刑,他更在意的是这事传出去会让家人丢脸,此外,他很关心自己还能不能报考公务员。王丽说,家人一直希望刘迪森考公务员,他报过一次名,但没去考。相比之下,程生祥则显得有些激动。因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一度拒绝在批准逮捕书上签字。郭彬和孔令曦也都认为事情不大,他们开始甚至不要求家人为自己找律师。5人当中,只有伍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被抓之后的首次审讯中,他不时把头伏在审讯椅上,显得非常沮丧。他在审讯中问办案人员:自己会不会被判死刑?办案人员没有正面回答他。2019年1月17日,“8·25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伍敏、程生祥、刘迪森、孔令曦、郭彬5人均表示不知道芬太尼是毒品。刘迪森的一审辩护律师王士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主观明知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只有证明刘迪森等人是在主观明知芬太尼是毒品的情况下制造和贩卖,他们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王士永认为,芬太尼是毒品,这是一个法律专业判断,而不是化学专业判断,伍敏、刘迪森等人虽然学化学,不等于就懂芬太尼相关法律知识。正是由于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芬太尼是毒品,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生产、销售,才会仅以一万元的价格卖给下家。如果知道是毒品,不可能这样做。郭彬读大学时的有机化学课老师向警方作证时表示,对于有些化工产品能不能随便生产,他更多从安全方面而不是从违法犯罪的角度给学生讲解。这位老师还表示,没有讲过药品行业所涉及的相关国家法律和规范。不过,审理该案的武汉市中院没有采信被告人及律师的说法,法院认为伍敏、刘迪森等人都具有大学文化,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还有在其他药物、化学公司工作的经历,比普通人对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有更多的认知,应推定他们明知芬太尼是国家管制的精麻药品,是故意实施毒品犯罪。2019年12月,武汉市中院对“8·25案”作出一审判决,伍敏被判处死缓,刘迪森和程生祥被判处无期徒刑,孔令曦和郭彬均被判有期徒刑13年。5人均上诉。2020年12月,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湖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迪森的父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得知二审结果时已经是2021年2月下旬。伍敏的二审辩护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官通知他二审结果时也已是2月下旬,并告知此前已经委托一审法院将裁定书送达伍敏。王丽是刘迪森的大学同班同学,她后来考取了某重点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研究生。自丈夫出事以来,王丽一直处于自责中:“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学化学的,应该知道(芬太尼是毒品),作为妻子应该给他提出建议,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芬太尼列管史:
1996年,芬太尼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
2013年,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太尼等13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新版《麻醉药品品种目录》
2015年10月,奥芬太尼、异丁酰芬太尼等6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2017年3月,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4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2018年9月,4-氟异丁酰芬太尼和四氢呋喃芬太尼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2019年5月1日起,对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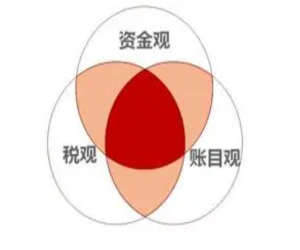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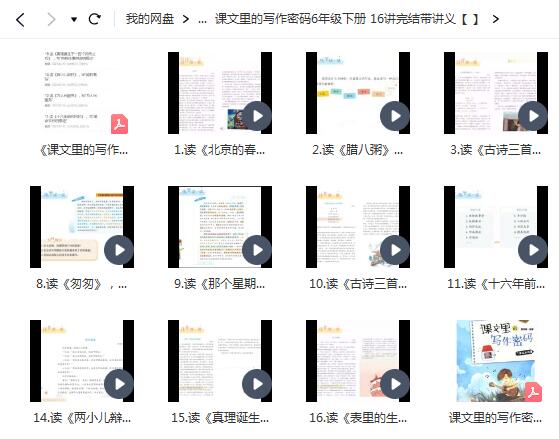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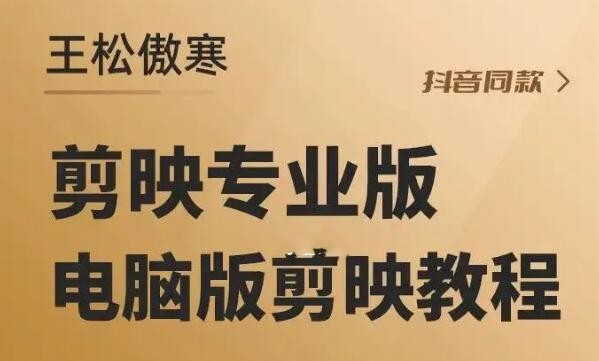
![[Android] 黑马 android 6.0编程者 开发者大会发布新特性 精华版](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e81e6de8dbd24b280383bcbff47efa9d.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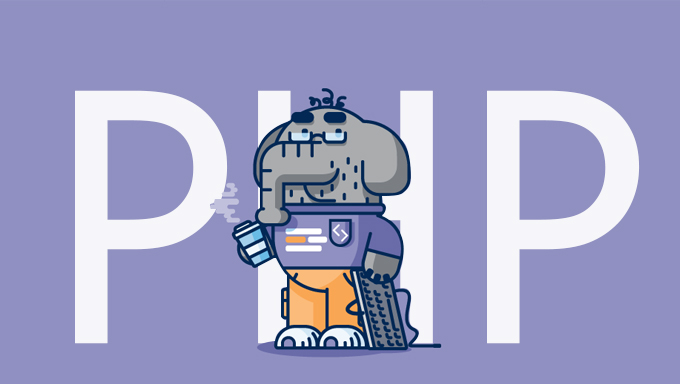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