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潮》第154期|张秀云:春日笔记
发布于 2021-04-26 01:35 ,所属分类:知识学习综合资讯
 点击上方"同步悦读"免费订阅
点击上方"同步悦读"免费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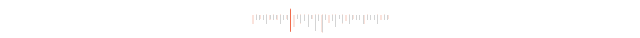

力 匕
■ 张秀云
阝 勹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天的信息,确切地说,还是新鸟告知的。淮北的春天来得迟,立春节气余寒犹厉,尽管梅花顶着寒冷开放了,但天地还是一派冷硬,东风还压不倒北风,节气一过雨水,东风渐渐立住了脚跟,山水慢慢温软了,河里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岸边有了柳色,天空中,可以看到大雁从南方归来了。那些秋天迁徙到南方的鸟,黄雀啦黄鹂啦柳莺啦燕子啦,也都纷纷地返回来,久别重逢,它们激动地看着故园故友,打开的话匣子就没法合上,早晨的梦,常常被它们闹醒,你听听,就在窗台上,或者窗外的树梢上,它们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平平仄仄,滴滴溜溜,软语吴哝,娇声缭乱,兴奋地聊着天唱着歌,就把你喊起来了,就让你恍然察觉,啊,春天来了!整个冬天,院子里都只有几只灰头土脸的麻雀,只有它们破锣般的嗓子喳喳闹闹,春天一来,鸟声就换了,就灵动了。
出门一看,果然,已经是春天的模样。杏花开得一树一树,谁家院子里的樱桃,仿佛一夜间就绽放了满枝繁花,小院的色调一下子被提得明亮起来。这时候,从大转盘往东,在淮河路上走,会被小叶李惊艳到。这条路的两旁种满小叶李,它们碎叨叨的满梢花朵,坠得花枝沉甸甸的,整个树冠堆锦叠绣,粉白细嫩,云一样轻软,雪一样缤纷,真让人有梦幻之感,让你记不起冬天里它们枯瘦的模样。锅灶边尘头土脸的灰姑娘,突然间穿上水晶鞋,华衣美服靓丽起来,她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魔幻和惊艳。小叶李落的时候也惊艳,哗地一阵风来,落红飘扬,雪瓣满地,真是惊人心魂。小叶李一年的好,就在这一开一谢的光景,等到叶子长出来,一树绛紫,脏兮兮的颜色,就不堪看了。何况又长在路旁,落得一身灰尘,更入不得眼了,行人望着它,真会恍惚,曾经,它也有过那般华美的春天?

每年每年,小叶李总会惹我一番感慨,如果把竹林七贤用一种花树来命名,那么,嵇康是一树春梅的孤绝,王戎就是这紫叶李的善变,他后来的贪生、吝啬、恋恋功名,种种不堪,几乎让你记不起,曾经也是个风神秀朗的聪慧少年,有过人人赞美的锦绣时光。郦波说他是个双重人格的人,照此思路,小叶李也是,人生路上,只浅浅一程明媚,惊艳之后,余生秽浊。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杏花李花开过,桃花又开了,油菜又开了,梨花和海棠也开了,田野里的种种野花,也都登场亮相,到处蜂飞蝶绕,五彩斑斓。春事最盛大的日子,当在此时,当在清明时节。此时天暖了,河水柔波轻漾,燕子在拂拂绿柳中穿梭来去,衔湿泥啄落花,筑巢补窝。人也从困顿一冬的水泥笼子里走出来,这时节千里莺啼,万里锦绣,从北向南,万里江山车啸马嘶,到处观者如堵。阳光那么亮,花海那么明媚,亮堂堂的阳光和亮堂堂的花朵,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甚至要把墨镜拿出来戴上了。天也确实暖了,走一程,身上涔涔地起了汗,要脱下外套来扛着。那些年轻的姑娘,干脆穿起纱裙来,看梨花的衣着鲜艳,看海棠的白裙飘飘,时代,都要把美照往朋友圈里传呢。一时间,满世界都是花,满屏都是春天。
这个晴好的周日,我们去三角洲看海棠。海棠开得正好,未开的玫红,新绽的胭脂色,盛开的水粉一般,远望去,一团团一片片,红云缭绕。孩子小的时候,宿州市政府的后院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垂丝海棠,每年花开,我们都去那儿游赏,那时孩儿只有三四岁,披着青色的披风,兴奋地在粉红林子里钻来钻去,我们在那拍过许多照片,前几天还在电脑的旧文件夹里翻出几张来,看来看去,感慨良久。一转眼,近十年的光阴就过去了,她已经是十二岁的大姑娘,当初陪我们看花的宋姨和汪叔,如今已有明显老态,又逢花季,他们很难出门了,汪叔耳朵背得戴上了助听器,宋姨的腿,也不堪行路了。而当初政府后院的海棠林,也早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食堂,还有一片停车场。

看过多少次海棠,我总忘记闻一闻它是否真的不香。张爱玲说她此生有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海棠真的不香吗?每年,被那云涌海啸般的盛大花事震撼,总忘记验证它到底香不香,今年,在三角洲,一进那片云团似的花海,我就留心了,——天哪,海棠是香的!一米开外就有袭人的暗香,把鼻子贴进柔软光滑的花枝里,天,真香,真醉人!这个香,不是汪曾祺形容栀子花的那种“碰鼻子”香,是袅袅的,淡淡的,雅致清爽的,按沈从文的表述习惯,是“格高”的香!沈老喜欢用“格”表述许多东西,形容茨菇好吃,就说它“格高”,“格比土豆高”。海棠的气味,格也是高的,“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高风格高格调的海棠,常常被画家搬上宣纸,成就一幅幅“海棠春睡图”,以后,纸上看花,也当是满鼻清香了。可为什么,张爱玲说海棠无香呢,是不是,她说的是另一个品种的海棠?或者海棠经过一代代改良后,才有了今天的格调?不管怎么说,海棠有香,卿可略去一恨,马上就是清明,我当焚纸告知,以慰泉下。
比海棠花事更加盛大的,是梨花。我的故乡砀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连片果园,春天一来,黄河故道两岸近百万亩梨花绵延无尽,引得五湖四海的游人纷至沓来,争相观赏。试想想,晴光下梨花雪海一样铺展,间或夹杂着桃园的粉红,油菜的金黄,新柳的青绿,如此春光,如此气势,“盛大”一词都显得狭小了,要用“浩瀚”“浩荡”形容,方才差可比拟吧。
但我从来不去观赏梨花。砀山的梨园,最早种植在黄河故道沿岸,后来种植面积慢慢扩大,我十几岁的时候,村庄内外,已经遍是梨树了,上学要从花枝下过,抱柴要从花枝下过,挖个野菜放个羊,都要拂开挡眼的花枝,梨花熟悉得像自己的掌纹一般,早已经与肉身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梨花盛开的时候,我和所有的小伙伴一样,都要爬到树上给梨花“授粉”。所谓授粉,也就是把黄梨树、紫梨树的花蕊摘下来,烤成粉,用橡皮尖蘸着,点在酥梨的花芯里,哪一朵花照顾不到,它就拒绝成长,拒绝变成亮黄的果实。所以,对果农而言,梨花不是用来观赏的,是用来劳动的。整个花期,梨农们昂着头,站在树上或者树下,一朵一朵地问候花蕊,那种辛苦,没经过的你们,不懂。

我更怀念小时候的春天,那个时候,果树还少,周边尽是庄稼,小麦、豆子、棉花、油菜,原野平平展展一望无际。“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天一来,村庄就沸腾了,耕牛遍地,满耳都是鞭花炸响的声音,是喝号子的声音,是牛“哞哞”的歌唱。酥软的土地被雪亮的犁铧尖儿翻起来,一道一道排列着,肥沃的土壤油黑发亮,如一张张翻开的光滑的书页。长长的钉耙齿朝下放入新耕的泥土,我和哥哥姐姐都蹲在耙上压着,祖父牵着牛缓缓前进,一趟一趟,把一面面书页耙得平整光滑,而后,就可以种豆了,可以种棉花了。父亲手持镢头,在前面刨出一个个小坑,母亲把几颗豆种丢进坑里,我则在后面负责掩土。刨起的小土堆又松又软,把左脚的鞋底微微往上斜立起来,把土往前一推,豆子就被掩在里面了,一行一行的脚迹写在大地上,宛如诗歌。春雨贵如油,淮北的春天多旱,点豆时如果逢一场小雨,大家都是兴奋的,都不会停止手头的劳作,细雨悄悄地,湿着头发,湿着新土,湿着意杨金黄的新叶,湿着村庄整齐的青瓦,春意在蒙蒙雨雾中,层层洇开。有了春雨的滋润,过不了几日,豆们就破土而出,一簇一簇,怯怯地,弓着腰,低着脑袋,几天的东风一吹,就昂起首挺起胸来,大胆地抽叶了,忽啦一声,很快满地新绿。这时候,黄昏里放学归来,站在如血的残阳里检阅它们,轻风拂拂,鸡鸣声声,新泥的香和新叶的香在辽阔平原上缭绕浮动,此时忆来,杳如云烟。
父母而今已经七十多岁,这两年,算是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但每逢春天,父亲还是要回故乡一趟,给祖父上过坟,就把门口的那块地挖一挖,刨一刨,这儿点几颗眉豆,那儿种几茎茄子,即使不会在收获季节里赶几百里路回去采摘果实,也不能让土地闲着,不能让春天荒着。早年那片土地上的梨园,我们都哄着父亲砍了。人渐老迈,我们都不在身边,打药剪枝的,料理起来,太吃力了。砍掉大部分果树,留下的几棵,也不管理了,就看看花而已。园子里还有几棵杏树,几棵柿子树,还有几丛月季和牡丹,整个春天,也是花事不断。前几天,父亲又回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他正在“种瓜点豆”呢。久困城里,在乡下小住几天,左把花枝右把锄,也算是调剂吧。父亲不说思乡,但我们知道,他是眷恋故土的,尤其是故土上曾经热火朝天的春日。

我们都爱吃韭菜。父亲每年清明回乡归来,一定会把故园的韭菜割来。没有荠菜的春天不算春天,没有杨槐花、榆钱和香椿的春天不算春天,没有韭菜的春天更不算春天。一冬里,那肥肥胖胖的大棚韭菜,不能算得上韭菜,沐过月浴过风的野地春韭才是真正的韭菜。“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秋末的大白菜,怎能与春韭相提并论?母亲常常说,“早春的韭,佛开口”,春韭之香,神仙也拒绝不了诱惑的。小时候,母亲常拿一把镰刀,把细得跟毛线一样的嫩韭菜割两刀下来,坐在春光里择,一根根撕掉韭菜根部粉红的薄皮,洗净,用刀抹碎,配几只刚从鸡窝里摸出来的笨鸡蛋,炒着吃。白瓷盘里金黄碧绿,那种鲜香滋味,惹得我们还没及放下书包,就先要用脏手去捏一块放嘴里了。上中学时,学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人家招待他的那盘韭菜,一定也是炒鸡蛋吃的,夹一筷子鸡蛋抱韭菜,吃一口小黄米饭,这顿饭,就是今天拿来招待客人,也不寒碜。有一回心血来潮,跟母亲讲这首诗,没料到母亲却说,“下雨咋能割韭菜呢,会沤根的!”天!不假,下雨天不割韭菜,新鲜的刀口被雨水一浸,韭菜是容易烂根的,这是农业常识!可是,卫八处士却在雨夜里剪了韭菜,他是常识缺乏吗?恐怕非也。二十年未见,又于乱世中重逢,即使会沤根,他也要把韭菜割下来,给故人炒一盘鸡蛋抱韭菜,春天还早,韭菜先发,也许,他的菜园里只有那么两行韭菜。卫八处士到底是谁,已不可考,我只一直记得,他是杜甫的故人,一个在春天的雨夜里割韭菜的人。
远离了少年,远离了故园,现如今的春天,已经与农事无关了,装在心里的多是花事。每年就想着,去哪儿看花,去哪儿赏春。那年暮春,宿州到洛阳的高铁还没有开通,我坐一整天的火车,跑洛阳去看牡丹。王城公园里,牡丹热闹,人也热闹,一大早赶去,已经有不少人架着相机,在那拍晨曦里的牡丹,还拿着喷水壶往花朵上喷水,制造露珠。支着画架的写生者,已经画了半纸繁花。我坐在公园里的一池碧水边休息,旁边是几株老柳,柳絮漫天飘着,绿水上毛茸茸地落了一层。一个中年男人立在旁边吹唢呐,他吹得很好,悠扬、嘹亮、婉转,那声音穿过密匝匝的花丛,穿过飘拂的柳絮,向城市上空飞去,向云层飞去……那一场雍容富丽的牡丹,伴着声声唢呐,盛唐一般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在每一个春天都会想起。
看罢牡丹,再开的花儿就是芍药,就是苦楝,就是蔷薇,春天就进入尾声了。春天要走了。春来人人欢呼,春归,满世界都是怨怅。你看那飞红万点,花落水流红,柔情万种,可不就招惹得人生出惆怅来?“春归当向何处去,春亦不言花乱飞”“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沈周叹过,李煜叹过,黄庭坚叹过,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春天,它还是离开了。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诗人们问过流水,问过蛛网,问过燕子,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后,终于在青杏枝头找到它,在杜鹃声里找到它。杜鹃啼声里,墙头梅子肥,枝上青杏小,满世界绿肥红消,瘦损了的那些落红,都在泥土里、在流水里摇摇身形,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染料,待到夏来,待到秋收,纷纷在果实上复原,红花爬上苹果的脸,黄花攀上酥梨的鬓,紫花悄悄把李子浓浓地抹了一身。当此时,诗人们不惆怅了,开始赞叹橙黄橘绿了,杜鹃也不再是泣血的古蜀国国君,它的歌声不再凄切,“播谷播谷,快快播谷”,满怀欢快地在催促农事了。火热的夏天就要来了。

(本期组稿、编辑:戴旭东。图片来自网络)



张秀云
中国作协会员,副刊编辑,出版有散文集《一袖新月一袖风》《安之若树》,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
《绿潮》栏目由绿色文学社主编,与《同步悦读》合作推出。绿色文学社由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郭因先生发起并创建,现任社长为马丽春。《绿潮》将以郭因先生的发刊词(见《绿潮》第一期)“凡是有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身和谐的现象与问题,凡是有关人类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美化的现象与问题,都将为我们的笔墨所触及”为办刊理念。
《绿潮》编辑:马丽春、胡迟、王金萍、戴旭东、乐华丽。顾问:春桃、苏北。
《绿潮》投稿信箱:
qcqc4574@163.com
篇幅3000字以内为宜,杜绝错别字,未在任何平台推过,来稿文责自负。投稿格式:作品+个人简介+个人照片+文章配图。
©原创作品gongzhong号转载需授权,有关配图来源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gongzhong号联系
倡导全民阅读 打造书香中国
不厚名家 不薄新人
投稿邮箱
tbyd2016@163.com
作品80%赞赏付给作者




 点击左下角“”投稿指南
点击左下角“”投稿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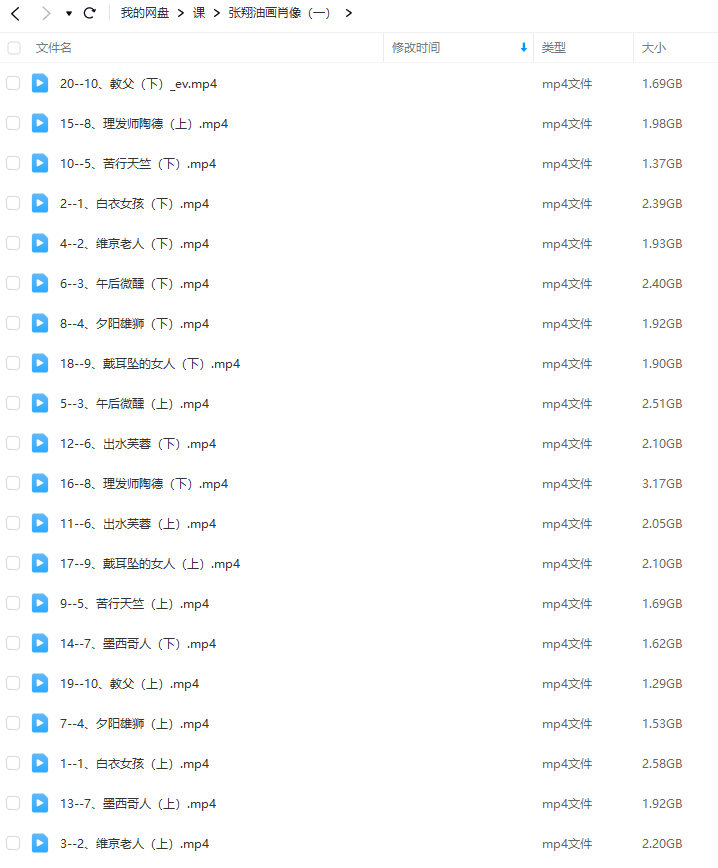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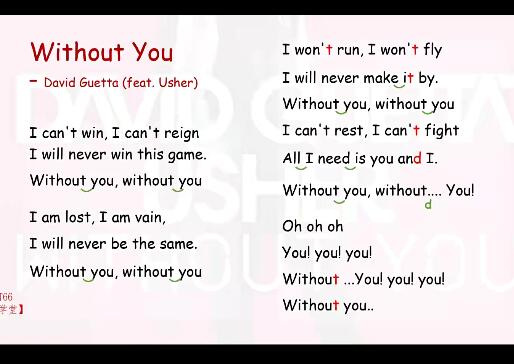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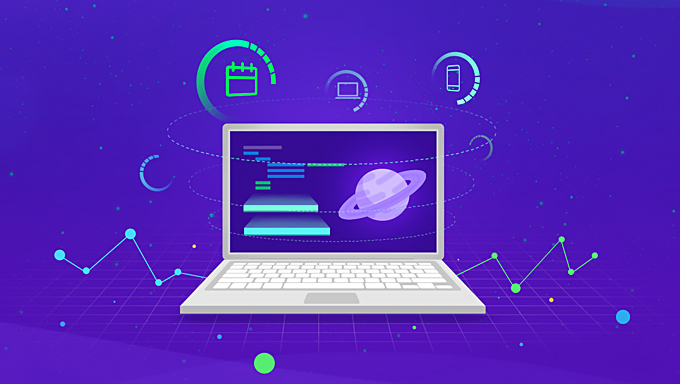


![【朱秀宇】2022年朱秀宇历史一轮复习[百度网盘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505ml2/92-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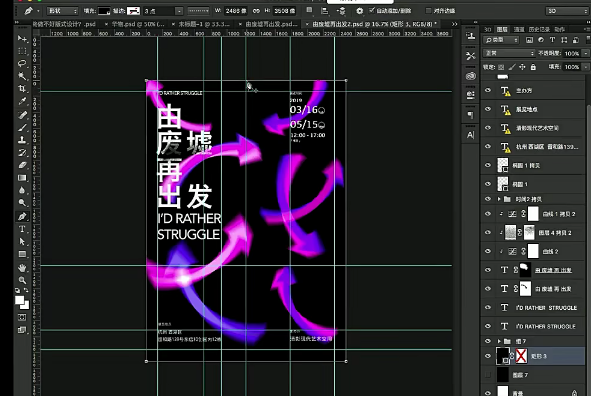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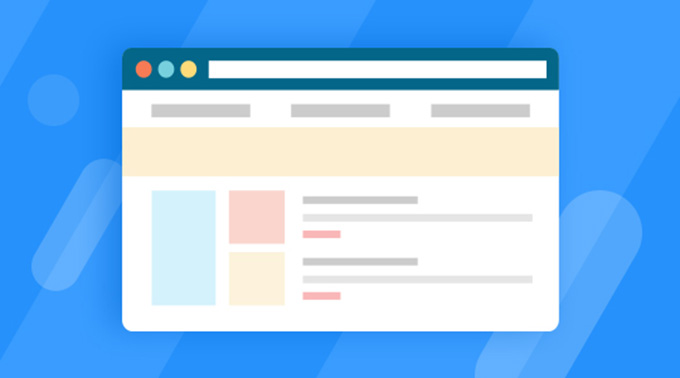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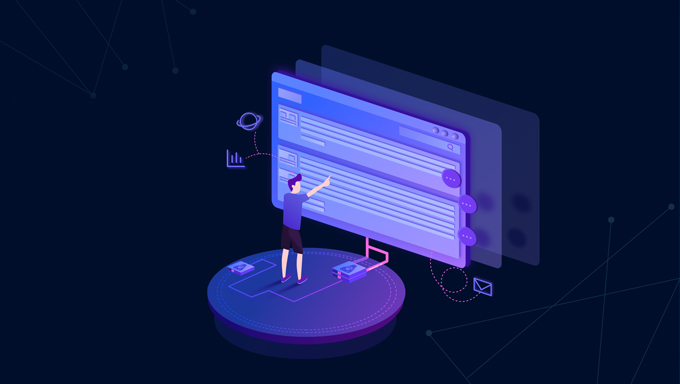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