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铭 | 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
发布于 2021-03-29 00:05 ,所属分类:知识学习综合资讯
西南边疆地区现在分布着壮、布依、傣、佤、德昂、布朗、彝、白、哈尼、拉祜、基诺、傈僳、怒、独龙、景颇、阿昌、藏、苗、瑶、回、汉等20多个民族。其中,百越系的傣族、壮族和百濮系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先民是西南边疆较早的居民。氐羌系民族、汉族、回族和苗瑶语族诸民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从中国西北和内地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人口迁移,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虽然历时漫长,民族迁移活动纷繁复杂,但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
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85年7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期间,全国实现一年以上迁移的人口共有3413万,其中农村迁入市镇的人口数为1672万,占市镇迁入人口的59.24%[1],东部地区是迁移人口的接收地,而西部地区则是迁移人口的出发地。与此相反,历史上西南人口迁移的流向主要是内地人口密集区向边疆人烟稀少地区流动。以清代汉族在西南的流动为例,无论是新从内地到达西南地区的汉族,还是此前就生活在西南地区的汉族人,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道光《威远厅志》卷三载道光十六年云贵总督稽查流民疏奏说:“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辟之区,多有湖南、湖北、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当时,仅开化府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二千余户。”然而,在雍正《云南通志·赋役志》的记载中,清代初期,广南、开化二府一带的居民还“俱系夷户,并未编丁”。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向人口稀少地区流动的趋势更为明显:如中老边境的勐腊,元代以前主要居民是傣族、佤族及克木人,元代后,哈尼族、彝族迁入,明清时期汉族、瑶族、布朗族、苗族、壮族、回族、拉祜族、基诺族等相继迁入;江城最早的居民是傣族,唐代哈尼族迁入,清代以后汉族、彝族、拉祜族、瑶族陆续迁来。尽管有历史上的一连串的民族迁移活动,但直到近现代,勐腊、江城仍然是地广人稀。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勐腊县的人口密度仍然只有6.94人/平方公里,江城县的人口密度只有9人/平方公里,而当时云南省的平均人口密度是44人/平方公里[2]。西南地区历史上形成人口向低密度地区流动的特点,其主要原因:
(1)容易获得耕地和新林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和森林是狩猎、畜牧、农耕民族的生存基础,并且,氐羌、苗瑶民族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传统方式对土地和森林的需求还有数量大、使用效率低的特点,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迁移,土地和森林相对容易获得,便于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
(2)生活自由。边疆许多地区,历史上封建统治薄弱,其生活无人约束。连续移民,尤其是大规模移民,往往是在封建统治者或土司头人的军事、政治压迫之下发生的,其迁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因此,他们在选择迁移的流向时,总是以人口稀少、统治薄弱的地方为首选。如清代傈僳族向怒江峡谷的大迁移,虽然那里生存的条件并不好,但人烟稀少,无人管束。拉祜族向滇西南大迁移,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躲避封建统治者的压迫。
(3)利于民族关系的调适。人口稀少的地区,不同民族可以择地而居,少有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民族间的分布保持一定的地理距离,是保持良好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
西南地区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尤其是少数民族迁移群体,总体上看,人口的流向特点是向南迁移。如清代景颇族大规模从今缅甸江心坡等地南迁到了今德宏地区;清代傈僳族迁入怒江峡谷后,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又不断南迁入今保山、德宏以及临沧、耿马、孟连;另一支傈僳族则从德宏东南下到今缅甸景栋一带。唐宋以前还分布在洱海——滇池一线地区的哈尼族、傈僳族、彝族、拉祜族、基诺族等民族,近现代时已散居于滇西南及东南亚等地区。苗族、瑶族自东向西迁入云南后,绝大部分转而向南流迁,到达东南亚北部山地一带。南迁流向形成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气候因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劣及变迁,往往是引起民族迁移、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南沿边及东南亚北部山地,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是山地民族理想的生活地区。从怒江峡谷南迁到德宏盈江县苏典乡的傈僳族说:他们的祖先是因为追猎麂子,发现这里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就从怒江南下而来;德宏的景颇族传说其祖先勒排堵先因撵白马鹿南下到德宏,找到了气候好的地方;拉祜族中的一支也是因为追赶马鹿到达了气候条件好的牡缅密缅(今临沧),其史诗《根古》说:“沿着马鹿的足迹,去寻肥沃的地方。翻过牡的嘎的山,穿过九林麻栗树。走到八节八那山,眼前一片芭蕉林。觅了九个月,翻越了九十九座山。穿过了九十九片林,来到牧缅密缅。”
(2)地理因素。西南地区的山脉大多是东北——西南走向,西部的横断山脉则表现为典型的南北走向,江河山脉相间并列,由北而南地势缓降,河谷逐渐宽广。历史上,源于北方的氐羌系民族,正是利用了这些天然的地理通道,顺着江河,沿着山脉走向向南迁移。因此,氐羌民族中,南和北的方向概念很强,在他们的语言中,“江头”往往就等于“北方”,“江尾”则等同于“南方”。如南迁到今德宏州、保山地区的傈僳族,他们称怒江上游怒江峡谷内的傈僳族为“洛五扒”,意为“江头人”,即居住在北方的傈僳人;而怒江峡谷的傈僳族则称德宏州、保山地区的傈僳族为“夏夏扒”,意为“江尾人”或“欢乐的人”。彝语中,“北方”意为水之源或江头,“南方”意为水尾;纳西语中,“南方”意为“江尾”或“下头”,“北方”意为“水头”或“上头”。
氐羌系各民族、苗瑶民族及部分汉族移民,他们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另一特点是从一座山迁到另一座山,很少下到低地和河谷中。究其原因,文化和生态的作用十分显著:
(1)防止疟疾的需要。一般认为:氐羌、苗瑶各族,由于迁入边疆的时间较晚,河谷坝区已有傣族、壮族等民族居住,因此只能选择山区居住。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河谷平坝地区历史上就有百越民族居住。如云南屏边县,彝族是最早迁到该地区的民族,其次是苗族和瑶族、壮族和汉族,但民族分布的格局却是彝族住半山(种梯田),瑶族住山箐,苗族住高山,壮族住水滨,汉族住集镇和附近乡村。又如地域辽阔的江城县,傣族、哈尼族在唐代时几乎同时到达这一地区,并且傣族后来又迁往勐乌、乌得(今属老挝),在以后的数百年间,江城则主要是哈尼族居住,直到清代以后才又陆续迁入了彝族、汉族、瑶族、拉祜族和另外一些支系的傣族。尽管哈尼族也有水田在山脚下,但他们并没有居住在河谷坝区,而是选择凉爽的高山或山腰地区居住。哈尼族也是绿春最早的居民之一,早在元代时,他们已定居于此,但他们到该地后,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海拔1000-2000米的半山腰或更高的山地,只有极少数在河谷地区。而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年)才从石屏五郎沟河范白寨迁徙来的傣族,却定居在了骑马坝河谷平川肥沃的地区,傍水而居,耕种水田。双江外来民族的山地分布更有代表性。尽管坝区地域广阔,土壤肥沃,田地较多,但外来的移民都集中在坝区周围的山地,纵然山地土质较差,耕地较少,人满为患,但也没有哪个民族愿意下坝定居。
造成这种从山地到山地迁移的重要原因是,历史上西南边疆河谷平坝地区多是“瘴疬之地”,疟疾肆虐,随时给人带来死亡的威胁。20世纪上半叶,曾在双江任职的彭桂萼在其著作《双江一瞥》中描述当时人们对疟疾的恐怖时写到:“在勐勐、勐库坝内,自夏至起即发生瘴毒,至收获时的谷搓瘴为最烈,霜降后才渐减去。在瘴疬高涨的时期,日间虽有坝外人敢下去,但入夜即不敢住宿。凭何天生的硬汉,只要在坝内歇着几夜,没有不送命的。因此,除摆夷族(傣族)外,四山已有人满之患,还没有任何民族敢下坝居住……”对瘴疬的恐惧心理还反映在许多民族的传说、歌谣中。哈尼族在追忆其祖先为什么山居的原因时说:从前哈尼爱找平坝,/平坝给哈尼带来悲伤,/哈尼再也不找坝子,/要找厚厚的老林高高的山场,/山高林密的凹塘/是哈尼亲亲的爹娘[3]。因此,哈尼族的俗语说:鱼上树不会动,老鼠下河会淹死,哈尼下坝不会生活。在滇南金平的河谷地区,民国时金水河行政委员会地志资料记载:“夏末秋初之际瘴毒为灾,斯时不惟外方客不敢至此,即本地人亦迁深山茂林躲其酷暑热……然既经染患此病,好者十无二三。”故民间有“要到茨通坝,先把老婆嫁;十人到勐拉,九个不回家”的民谣。
滇西傣族地区也是疟疾的高发区,13世纪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说:“夏季期间,这里一片山岚瘴气,郁闷不卫生,商人和其他外地人被迫离开这里,避免无谓的死亡。”明初,钱古训、李思聪出使缅甸,留滞麓川,他们在《百夷传》中写到:“病疟者多死”。当地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要到芒市坝,先把老婆嫁”。景颇族南迁到德宏地区后首先选择的是山地,从事旱地农业。传说景颇族的浪速支以前有人种过水田,回山后打摆子,以后人们就不敢下坝种水田了。
关于边地“瘴疬”的危害,史书、民谣不胜枚举,傣族、壮族人民经过千年的生存适应,对一般疟疾已有了较强的免疫力,同时也探索出一些治疗该疾病的方法,所以他们能够长期生活在河谷平川之区。而外来移民中,氐羌系民族来自西北冷凉的山区,苗瑶民族则来自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地区,因此他们入迁边地之后,多选择凉爽低疟的山区。如在滇西潞西县,海拔1100米以下为高疟区,死亡率最高,海拔1100—1600米的半山区和高坝区是中度疟疾区,海拔1600米以上的山区和高寒山区则是低疟区[4]。为了避免疟疾的危害,历史上外来的汉族、景颇族、傈僳族一般都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在滇南的金平县,难以适应河谷坝区湿热气候的苗族、瑶族、拉祜族即主要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低疟疾山区。[5]
汉族在边疆的山区和坝区都有分布,民国以前迁入边地的汉族多是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民国之后入迁边地的汉族主要以从事商业贸易者为多。如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汉族就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布于山区的旧汉人,他们是民国以前入迁该地区的;另一种是分布于集镇上的汉族,他们多是民国以后迁入,主要从事商贸活动。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坝区的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及医疗卫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2)传统文化的惯性。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许多外来民族,在迁入前就一直是以游牧采集和山地刀耕火种为主要生计方式。《史记·西南夷传》在记载汉代滇西氐羌的生产活动时就说道:“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以后,氐羌中的一部分人口如纳西族、白族、彝族的一部分,他们进入云贵高原后就在坝区发展起了定居的锄耕、犁耕农业,而留居山区的氐羌系其他民族则仍以传统的畜牧采集为生,往往迁徙不定。由于人口的增殖,仅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能维持山区民族的生存,需要发展一种山地栽培农业来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于是刀耕火种农业在山区的氐羌民族中兴盛起来。自发向西南边地迁移的氐羌诸族,其迁移的主要原因就是刀耕火种农业需要经常更换新的山林和土地,因而,他们在进入西南边地时,自然首选山地为其目的地。如:傈僳族迁入怒江后,赶走了原居住在峡谷低地的“白衣”(傣族),但他们并没有在傣族原来定居的地方居住,而是在山坡地带发展起旱地农业。苗族和瑶族的情况也与氐羌民族大致相同。清代以前,苗族的居住中心在今湘西和贵州,这时很大一部分苗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是:“刀耕火种,日食杂粮,山中即有水田,亦不种稻”,“苗耕男妇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垦”。[6]瑶族也是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广东通志》卷二七八载:“(瑶族)伐木耕山,土薄则去,故又名过山瑶。”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需要经常性更换山地,所以每当一处林地砍烧耕种、地力耗尽之后,从事这种生产方式的苗族和瑶族就要重新更换土地,开始新一轮的迁徙,去垦种另一块森林茂密的山地。迁入西南边疆地区之后,当地良好的自然条件使他们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长盛不衰。民国《新编麻栗坡特别地区地志资料》载:“靛瑶人,僻居山野,专以伐木种靛为业……此种民族之住居无有一定,全视山林之繁茂与否为定度。若彼所住之地山林被其砍完,则迁其他山箐茂盛之地矣。颇似古代逐水草而居之游牧民族。”
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其迁移过程多是十分漫长的,并非一次迁移就完成,在此过程中,刀耕火种已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化为一种文化模式,渗透在生产、生活、观念等各方面,成为一种传统的习惯。
西南边疆民族的现实分布特点是在历史上多次人口机械变动中逐渐形成的,从当代边疆民族分布的特点来看,迁徙民族虽然散布面很广,但同一民族的聚居性、分布的选择性十分明显。
从宏观分布来看:一些民族迁入西南边疆后,相对集中在边疆的一些州县。如苗族进入西南边疆后,主要聚居在今滇东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金平、屏边等地;景颇族清代时从江心坡地区大规模南迁,在中国境内其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滇西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红河自治州是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地,并集中分布于该州的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金平县,而其他地县市则较少。即便是在一县或一乡之内,西南边疆地区同族相聚的特点也很突出。如:江城县有哈尼、彝、傣、瑶、拉祜、汉6个民族共同居住,但哈尼族主要集中在曲水、嘉禾区,彝族比较集中在国庆区,傣族主要集中在康平区,瑶族主要集中在瑶家山乡,拉祜族主要集中在板河乡,汉族相对集中在勐烈镇。
从微观分布来看:西南边疆民族村落一般是一个民族一个村落,多民族共居一村寨的情况较少,同时还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村寨交错分布的特点。无论是水平分布还是空间分布大多如此,如:在滇东南的马关县,各民族垂直方向的分布是:“汉族住街头,壮族、傣族住水头,瑶族住箐头,苗族住山头”;在滇南的屏边县:“汉族住集镇,壮族住水滨,瑶族住山箐,彝族住半山,苗族住高山”。在金平县的者米乡,海拔400—600米之间的河谷地区是傣族、壮族的分布地区,630—790米的半山区是苗族分布区,480—1580米之间有瑶族分布,哈尼族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山腰地带,苦聪人大多分布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又如在滇西德宏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一般为傈僳族的分布区,海拔2000米至1500米间多为景颇族居住,而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多为傣族和汉族居住。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角度分析,同族相聚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迁移方式决定了同族相聚的特点。一般而言,迁移者在迁移时多遵循先行者的迁移路线和方向,分享先行者的经验和信息,以减少迁移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这样,不同时期迁移的同一民族往往最终聚在了一起。
(2)亲缘关系。如瑶族民间广泛流传着的“歌信”,其主要内容即是介绍本宗支的祖先源流、迁徙路线、指导同族亲友前来相聚等。又如景颇族的迁移是在同族一部分人先行到达德宏地区,然后“呼朋引辈”而至的。现代农民进城务工也与此相类似,但更突出地缘性特点,他们大多经老乡、亲戚、朋友等熟人引荐,取得一定的就业信息后才开始迁入并聚居在一起,他们迁移的目的性和选择性都很强。
(3)土、客矛盾因素的影响。迁来民族与原住民族,由于迁入时间先后的不同,他们之间往往会因为土地、森林、河流的使用和归属以及宗教信仰等发生矛盾与纠纷,而土、客之间经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又往往使弱势一方(多为迁入较晚者或人数少者)更倾向于迁移到同族、同乡人数较多的地方居住。但是,由于边疆地区山脉、河流纵横,并有其他民族先期分布,迁移者虽然可以相对集中分布在一片大的区域(如:滇南哈尼族的分布),但往往只能实现小块聚集,和其他民族交错分布,而不是连片的大范围单一民族分布。
(4)同族相聚有利于相互通婚。在传统的社会中,同一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常常是婚姻缔结的首要条件。
一个民族群体迁走之后,其原居住地迁入另一民族群体或同一民族群体的其他支系,这种情况在西南边疆地区十分常见。那种一片地方被一个民族放弃之后无人垦种的情况并不多见。如:元江、普洱县,历史上是傣族土司的辖地,也是傣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但现在境内的傣族人数极少,而哈尼族、彝族成为主体民族;再如滇西南的澜沧县,清代中叶以前,县境内的傣族极为强盛,人口遍布各地,此后,随着拉祜族迁入人口的剧增,傣族逐渐南迁,有的迁往勐遮、勐海,有的迁入缅甸,澜沧境内的傣族人数大大减少。
地名是一个语言词汇,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分布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生息繁衍于此的民族以其语言命名。地名产生之后,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迁走之后,其地名往往被后来者沿用。“磨黑”一名是傣语地名,意为“盐井”,历史上这里也曾是傣族的聚居区之一。但现主要居民是汉、哈尼、彝、回等民族。古代人对此也早已注意到,隋朝人裴矩在其《西域图纪·序》中曾说道:“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可见地名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一个地方民族迁移递进、兴衰胜亡的历史。递进式迁移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1)以刀耕火种、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其游动迁徙性很大,一个民族迁走之后,其迁出地会有其他民族或本民族的其他支系、家族迁入。因为土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耕之后,地力又恢复到一定程度,又可以重新耕种。
(2)氐羌、苗瑶历史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防疾病的能力十分有限,灾害发生后人们只能通过迁离故土来躲避。如今西双版纳哈尼族爱尼支追溯祖先来到“曼尾(今勐海县境北部)”的迁徙原因是遇到了水灾。《雅尼雅嘎赞嘎》中说:暴雨下了七天七夜,/小金湖不见了。/山花已经凋谢,/雨水淹没了村寨,/雨水冲跑了牛、羊,冲走了寨门。/则众人不能在这里了,/众人在德其的率领下又开始迁徙。[7]金平的一部分瑶族是因为遇到了旱灾而迁来的,其《漂洋过海歌》说:“谓因寅卯天大旱/深塘无水平有鱼/樵林出烟木出火/官仓无米度春秋/人民也慌官也乱/到处慌忙处乱州/三朝两日谢了圣/拆散香烟各自游/一份进落韶州府/二份广西省上游/三份散上云南地。”灾害过后,土地仍旧可以耕种,但原住民已迁走,后来者则占据这块土地。
(3)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排斥性。所谓“强势”和“弱势”,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以人口的多寡来决定的,并不以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来决定。“弱势”者往往就会迁离原居住地,远走他乡异地。
(4)文化冲突的推动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发生的矛盾称之为文化冲突。西南民族人口迁移的过程之中,文化的相互抵触,尤其是风俗习惯的抵触,是引发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景颇族南迁到陇川之后,原住民德昂族逐渐迁走,主要原因就是德昂族信仰小乘佛教,不杀生,但景颇族有杀牛祭鬼的传统习俗。两个民族因生活习俗的不相容,导致了德昂族主动迁离了生活已久的居住地,以回避文化上的差异而带来的冲突。[8]虽然文化的冲突可能引发民族的迁徙,但这种事例并不普遍。回首历史和面对现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时候,新迁入者总是以一种低调友好的姿态与原住民族相处,逐步达到文化的相互适应,这也是西南边疆多民族共存的成因。
西南边疆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是有一定特点可寻的,这些特点有的是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有的则是各地人口迁移的共同特征。各民族总体向南迁移的趋向是一种地域特征,而向人口稀少地方迁移的特点则与现代农村向城市、西部向东部的流向相反;从山地到山地的迁移是自然地理气候、民族文化以及外来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族相聚的迁移原则是古今移民共同心理状态使然;边疆移民的递进式迁移是向边远和人口稀少地区的迁移,与当代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小城镇人口到大城市的递进式不同。文化和生态环境是西南边疆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特点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
苍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编 辑:丁存金





![[Android基础] 史上最详细的Android Studio入门及使用详解全套视频教程](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fd5a6305469616cdc05c47fa0e881d00.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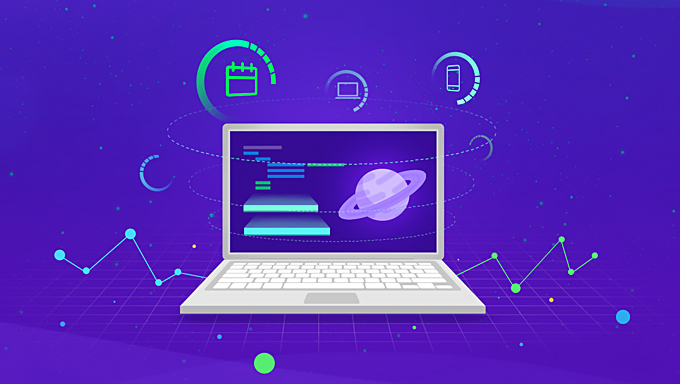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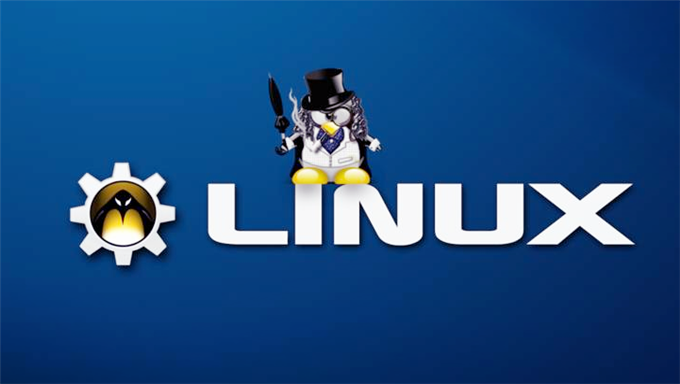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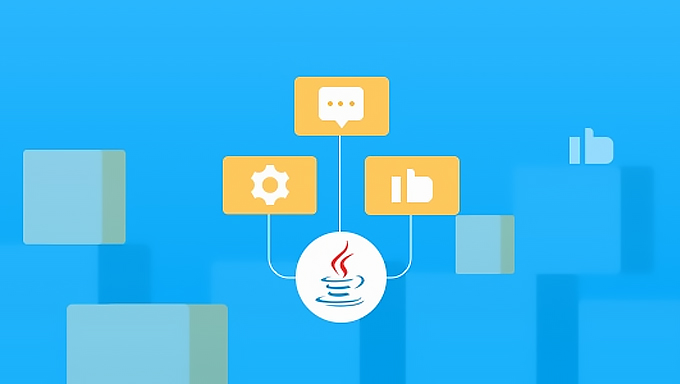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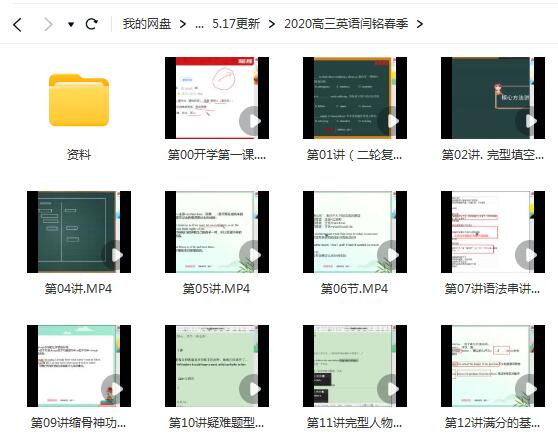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