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艺术留学周记43完结篇: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思考摄影的三个问题
发布于 2021-05-20 12:54 ,所属分类:出国留学学习资料
Artcan help
我是摄影师陈荣辉,正在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摄影研究生。
我会每周在公号分享自己的艺术留学经历,和大家探讨影像艺术。
大家好,这是我的第43篇留学周记,也是最后一篇。在两年前开始动笔的时候,我只是想督促自己做些事情,帮助自己回忆下上课的内容。后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让这两年过得如此充实,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老师和朋友。后续我会继续分享一些我的思考,只是不再以周记的形式出现了。大家如果对过去的周记感兴趣,可以点击文章最上方的话题标签进入。欢迎大家继续点赞、分享、打赏。
这段时间除了要准备毕业展,我还要准备最后一次critique,确实有点忙不过来。这周稍微稍微可以喘口气,让我有一点时间可以简单梳理下自己这两年的MFA经历。To learn is to create,学习即创作,这句话是当年徐迟对赵无极说的,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很多真正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艺术留学生,特别是在疫情当下,继续选择出国留学其实是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两年也有很多老师和朋友问我,究竟我这两年在做什么,我一般很少谈论创作本身,因为在网上谈有时候是空对空,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到现场看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交流。抛开具体的创作本身,我可以分享下自己这两年的一些思考。
思考摄影这个媒介的历史
前两天我在工作室看着我新打印的那些照片时,我终于理解一些事情。虽然我不知道将要去哪里,但我终于认识到我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里有很多重解释,我先说下和来自于摄影这个媒介本身的事情。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先锋或者新锐艺术家,我总喜欢回过头看一些东西,不管是我拍摄的题材本身,还是我使用的很多技法以及理念。特别是摄影这个媒介的历史,是我总是琢磨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并不在乎媒介的历史,因为习惯于“拿来即用“。当然,拿来即用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在某个角度上成立的。我来自于摄影这个媒介本身的历史,在我开始学习摄影史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去钻研里面的那些优秀的艺术家的突破。

无题,陈荣辉作品
在周一系主任和Jeff Wall对谈中,系主任最后让Jeff Wall给大家一些建议,Jeff Wall说,relentlessly study the best artists and do nothing else。在当下听到这么“复古”的建议其实真的不多了,但是或许Jeff Wall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从学习过去那些最好的艺术家开始的。在国内,不管是谈论艺术还是科技,我们都在强调“创新”,一定要有新的东西或者突破性的东西。但是回头看,我们虽然偶有创新,却少了真正的突破。因为真正的突破不是凭空出现的,凭空出现的经常都是那些作怪的事情。
在摄影发展的180多年时间里,我们对于摄影媒介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呢?我们在想尽办法把中国的叙事放到摄影媒介的历史中,比如把小孔成像的历史放到摄影史前的发明,把邹伯奇对于早期摄影的思考和探索说成是他发明了中国最早的湿版摄影等等。属于我们自己的叙事是否是有必要的呢?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自己学习的摄影史基本就是西方摄影史,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就是在过去,摄影这个媒介是欧美等国家发明推广开来的。既然我们要掌握一门语言,我们就要深刻学习这门语言的来历。这也是像赵无极他们那批艺术家去法国学习,走出了国门后,赵无极重新认识了自己喜欢的油画这个媒介,与此同时,他又批判性地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结合到了抽象绘画里。所以赵无极在回中国美院讲学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有这么多最好的传统,每一个人只要拿出一部分自己最喜欢的,对自己性格最接近的,把它消化,然后把学到的西方的东西——要拿好的东西,也不要收他们旧的东西——把两方面最好的东西合起来,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个性,慢慢地、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那你的作风就有了。其实这个观点很像另一位学者许倬云的观点,他对于当下我们的困境的解决之道依然是认为要把全人类最好的东西都拿来所用,而不是固守我们原有的那些传统。
在摄影史180多年里,有着太多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值得我们去反复琢磨。每个学期的VA课程,我总是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有趣的艺术家创作。而这些是我在国内几乎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尽管因为疫情,我失去了和很多艺术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是我们又多了POP UP 讲座,让我可以聆听来自Jeff Wall、Robert Adams、 Nan Goldin等这些在摄影史上留下来名字的老师的教诲。这也让我对这摄影这个媒介真正怀有敬畏之心。当然,敬畏之心不是意味着要诚服于这个媒介,而是抱着尊重的心态,并且是有所突破的心态。那批最早出国的中国艺术家的气魄就是,我们既不要做西方的艺术家,也不是要做东方的艺术家,而是要做世界的艺术家。

无题,陈荣辉作品
当然,我在这里谈的更多是关于摄影创作层面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思考摄影史,所以切入的方法一定是看照片,看作品,而不是过度去解读理论。艺术家当然也在“书写”艺术史,只不过是靠作品。我们要知道艺术家创作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才是最有趣的部分,至于怎么创作,我们看到照片的时候基本就明白了。当然,艺术家是会骗人的,不管是在访谈还是在自述,艺术家都会“藏”一些东西,这就靠我们个人的领悟了。
摄影这个媒介的过去不是绘画,未来也不是视频。摄影的过去就是摄影,摄影的未来还是摄影。很多人会沉溺于媒介的迭代,陷入了纯科技发展史的维度来思考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表达方式推陈出新,这些进步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感受摄影。不管是360全景照片还是谷歌图片,都在各个维度上加深我们对于摄影本身的思考。摄影的可能性在于摄影自身,而不是其他媒介。至于摄影和视频的关系,我之前在周记也分享过很多。让我们借用下大卫·霍克尼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把时间予以摄影,但是视频却将它的时间强加给你。人们记忆静态图像的能力更强,而静态图画能进入思想更深处。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看过的那些经典电影,一开始或许还有一些对白,但是到后期我真的只记住了那些固定的画面。从这点看,杉本博司那组关于电影院的摄影作品,真的是绝妙。
诗人和评论家大卫·施特劳斯在他新出版的Photography and Belief 中说,摄影一直以来都比现实更加虚构。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探索是摄影这个媒介非常擅长的事情,也是这个媒介一开始自带的“档案”属性决定的。其实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边界上探索。而耶鲁摄影系前系主任Tod曾经说,在摄影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所谓的“叙述(Narrative)”,去强化这种感觉很重要。“叙述”不是一个好词;它不是最好的词,但也不知道最好的词应该是什么。不管怎样,就阅读照片来说,这个词非常重要。摄影不是简单的“图解(Illustration)”,摄影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张照片能够迫使聪明的读者去思考照片和“现实”或“真相”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把一张照片作为一个故事来阅读,那么这个故事和我们所处的周遭世界究竟有什么关系?照片就是这么一个变体(transformed thing)。Tod说他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有像Gregory这样的学生;因为他从来不会说摄影是“真相”的传递者。摄影对于他来说完全是虚构的,不管它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图解。
与此同时,Tod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虽然摄影非常擅长虚构的,但是很多时候,年轻的艺术家(学院派的学生)想象力却远不如现实精彩。所以在探讨摄影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的是图像本身,然后是艺术家的观念,但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个好想法,最后的结果却是有些勉强。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摄影这个媒介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艺术家会把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来进行创作,但是那些摄影作品的完成度或许不高。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当然可以说不好。因为这里面是有提升空间。好的摄影作品理应是有好的图像表达和好的观念。至于大家经常讨论的摄影的艺术还是艺术的摄影,或者是纪实摄影、艺术摄影等,我觉得作为创作者大可以放弃这些争论。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拓展各种边界,形成独特的表达。当然,我们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管形式如何,我们终究是为自己创作的。这也引入了我在下一个内容中想要分享的。
思考摄影这个媒介和自身的关联
“我们只看过这世界一眼——在童年之时,
剩下的都是回忆。”
诗人路易丝·格吕的这句诗总是在我脑中徘徊,让我回想起自己在童年时是如何观察这个世界。在耶鲁的各种Studi Visits和Crits中,很多艺术家都想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摄影,并且如此深信这个媒介。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以前看到的图像基本都是一些海报,主要是政治领导人海报和港台明星海报,然后就是菩萨的画像。我一直觉得这三类人都是具有同样的作用,具体就不阐释了,相信大家都明白想要说的。后来学习摄影后,我看到奥古斯特·桑德的肖像,看到梅普尔索普的肖像,看到迪克西亚的肖像,我觉得摄影在肖像方面的刻画一直非常神秘。
这让我后来在国内做创作的时候一直很肖像的创作,虽然在美国我拍摄肖像其实非常少。主要还是一些客观原因,我想一旦我更熟悉这块地方,我应该会拍摄更多的肖像。这背后其实是反映了我内心非常朴素的人文主义和关怀,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被误读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样极度自由的国家,他们会非常注重个体对社区的贡献。但是反过来,我们这样极度强调统一思想的地方,我们要更注重的是个体的独立。

迈耶柠檬,陈荣辉作品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不是绘画也不是音乐,主要是因为条件有限,但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个人订阅的杂志报刊比县城很多公家单位都要多,这是我在邮局工作的姨夫告诉我的。我第一次遇到西方的一些经典名画就是订阅了一本杂志叫做《散文诗》,那是一本开本非常特殊的瘦长型杂志,每一期杂志的都会赠送一张西方绘画或者雕塑的照片。然后经常都是一些裸体的画面,所以每次都要被我妈妈“没收”,经过讨价还价我才有机会要回那张图像。这也让我倍加珍惜这些图像。
在小县城里,美术基本上就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升学途径。专注于中高考的普通人家基本上没有机会接受相对正规的美术教育。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我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我再次有机会接触图像。而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丽水摄影节和丽水摄影博物馆的出现,我好几个亲戚都是有摄影的经验,这让我家人接受摄影相对比较容易,觉得起码可以去文化馆谋职或者去报社电台。
在后面的故事其实我已经分享过了。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当年在申请耶鲁的时候写的个人陈述,我讲述了我的成长经历,如何从一个浙江小县城到了杭州、上海工作,也讲述了我如何和摄影相识。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如何从新闻摄影转到艺术摄影,以及为什么我做出这个选择。一些具体的内容我在第一篇周记里面分享过,大家可以再看看:三十而立,我选择辞职去耶鲁学艺术。
本质上,摄影给我提供了一种观察自我的方法。在我看来,摄影不会骗人这句话在某一个层面是对的,也就是摄影会非常真实反映拍摄者的情况,而不是被摄者的情况。我们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反映了拍摄者的审美、操作、理解能力等。这也是做艺术难的地方,我们需要不断给自己创作困难,然后不断去突破。突破后,又给自己新设了一个难题。艺术家放弃的次数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一直创作的艺术家真的非常艰难。这种艰难基本上就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来了耶鲁以后,我一共要经历12次critique,一直到即将来的最后一次,我才对自己的认识有了一点点顿悟。在过去的11次创作中,我尽力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有依托于文献的二次创作,有在街头的全景视频创作,有做的行为表演等等。经过不同的尝试,我才慢慢发现那个“我”。那个来自于浙江丽水小山村的小孩,经过了多年成长后,来到了这个地方学习艺术。我的过去所学,都深刻影响了“何为我”。摄影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在我拿到相机的那一刻,我已经试着往外看,放下相机的时候,试着往内看。相机不会简单地带领我找到真理,但是每一次seeing,observing,thinking都让我接近一点真理。

迈耶柠檬,陈荣辉作品
回望过去的三十年,我越来越有信心去拥抱自己的过去,尽管过去的经历充满着很多的曲折和痛苦。离开家越远,心里距离家里的距离或许是最近的。当我准备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我希望在他的名字里带一个序字,也就是我从小生活的村子招序村。不管以后在哪里,那里都是我最美好的童年回忆。里尔克说,即使在监狱里,我们也拥有自己的童年,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宝库。当然了,在这里说自我,并不是自私,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创作之所以是独特的,就是因我们有着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与此同时,我们的创作和当下的社会是紧密连接的,这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
思考摄影这个媒介和这个时代的共鸣
2004年的时候巫鸿和Christopher Phillips在ICP策划了首个中国摄影和录像艺术的展览。在展览画册里,巫鸿提到了这批最早从事影像艺术的艺术家在面对中国的剧烈变化时,都开始拿着相机或者录像机去纪录、创作某些影像。但是他们更多思考的还是社会层面的事情,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怎么样子的,并没有花心思在摄影本身媒介的突破上。其实这个现象一直影响到了现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摄影。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美术馆和画廊是不会考虑中国摄影师的摄影美学突破和创新,更多的是借助这样影像作品来观察发生巨变的中国。所以那批展览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行为为主,然后借用影像来发声。之后很多艺术家也很少、甚至不怎么使用摄影这个媒介了。当然,这批艺术家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在海外最知名的艺术家。

观看王维的19种方法,陈荣辉作品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我们做艺术创作当然不一定要为了社会出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当下特别是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我们的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政治是紧密连接的。因此,我们或许要思考自己的作品和当下更大范围的某些时代特征进行共鸣。安塞尔·亚当斯其实在早年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声望,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即使在大萧条和二战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拍摄那些宏大的社会题材。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等摄影师就嘲讽安塞尔·亚当斯和爱德华·韦斯顿,说一个只知道拍山,一个只知道拍人体。但其实安塞尔·亚当斯是有自己的思考,他对于美国西部景观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实观察到了一个更持久性的议题那就是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远比大萧条和二战等显性的社会题材更重要,或者说更深刻。所以在晚年的时候,安塞尔·亚当斯的声誉伴随着美国人对于美国西部的重新认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不断上升。当然,回到当下,这段时间除了疫情以外,大家也都意识到了我们要非常注重环境问题,包括碳排放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是非常政治的,但实际上却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细节,世界地球日的时候,我在朋友圈看了下中国的艺术家朋友,几乎没有人发相关的信息或者创作。而在ins,我看到了大量国外艺术家对这个话题的以及思考。或许,这就是一些区别。

观看王维的19种方法,陈荣辉作品
国内的一些情况是,我们以为关心的事情是重要的,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在不经意间卷入了太多的“纷争”和社会教育。之前有个耶鲁的朋友想回国做艺术相关的事情,有位国内前辈说让她多多体验下社会。从实际情况来说,确实体验下某种规则,做起事情来或许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可以不需要去体验这些规则,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呢?我这里并不是否认美国没有潜规则,而是面对这些规则,我们是否真的要去面对。特别是当下,艺术圈子的内卷也是非常可怕,艺术家之间的比拼是全方位的。之前听闻国内某顶级绘画艺术家的女儿要申请耶鲁的绘画系MFA,帮忙写推荐信的都是古根海姆的策展人,不过最后还是被拒了。找个潜规则相对少一点的地方做点事情其实也是可行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体验,本就是一些没有必要的经验,最后却成为了前辈们的经验之谈,可惜这经验之谈对艺术或者学术的价值其实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如何保持一种批判性地思考,在当下都是特别珍贵的事情。因为“变坏”真的特别容易,做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却很难。在文章最后,我想用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84年的一篇对大学生的毕业演讲来作为结束:
无论你们选择做多么勇敢或谨慎的人,在你们一生的过程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而是,说得客气些,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品性良好或精于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邂逅的可能性就越大,冲击力也就越强烈。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有能力做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原因之一是它往往会以善的面目出现。你永远不会看到它跨进你的门槛宣布:“喂,我是恶!”当然,这显示出它的第二种属性,但是我们可能从这观察所获得的安慰往往被它出现的频率所减弱。
因此,较审慎的做法是,尽可能密切地检视你有关善的概念,容许我打个比方,去细心翻查一下你的衣柜,看是不是有一件适合陌生人穿的衣服。当然,这有可能会变成一份全职工作,而它确实应该如此。你会吃惊地发现,很多你认为是属于你自己的并认为是好的东西,都能轻易地适合你的敌人,而不必怎样去调整。你甚至会开始奇怪到底他是不是你的镜像,因为有关恶的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它完全是人性的。温和一点说,世上最容易里面朝外反过来穿的,莫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这里,一个最明确的危险信号是那些与你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数目,而这与其说是因为意见一致具有沦为一言堂的倾向,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个可能性——隐含于大数目中——即高贵的情感会被伪装出来。
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看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喜欢稳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确定无疑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稳定的资产。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利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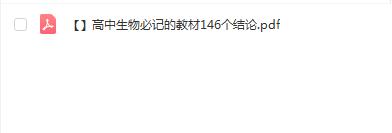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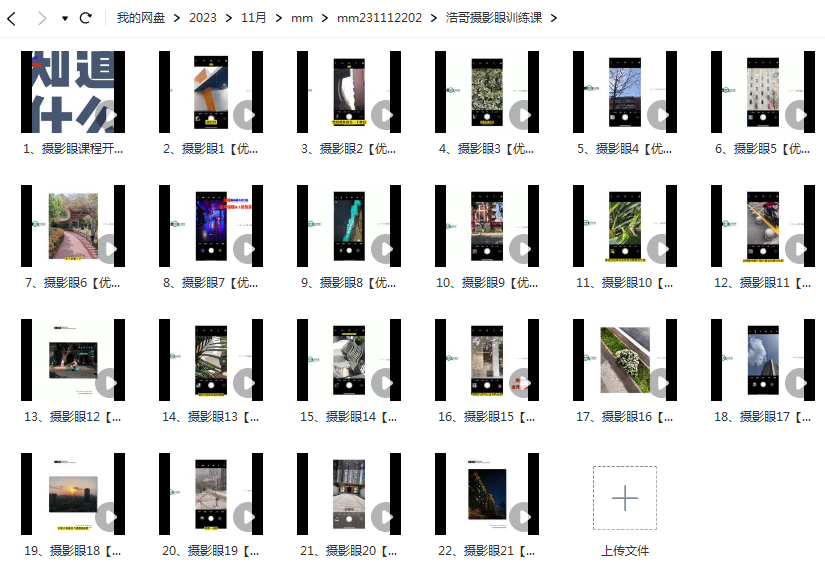




![[人工智能] 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 生动形象的了解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发展现状和趋势](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21c8d9e6ea7677019ecb6283d30c4f42.pn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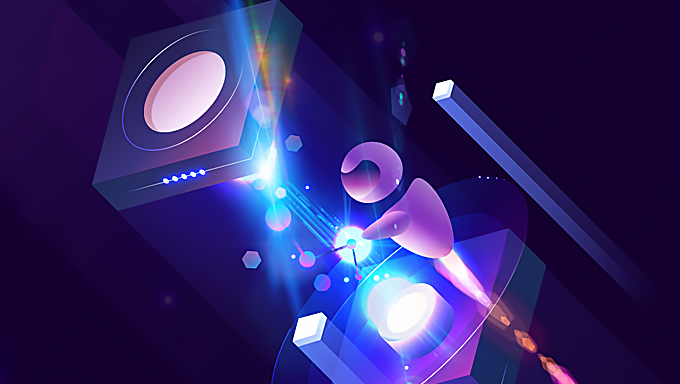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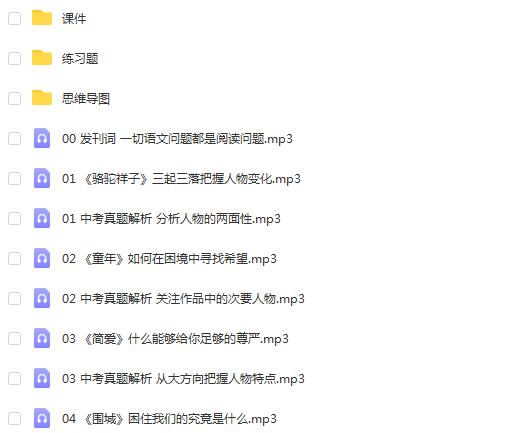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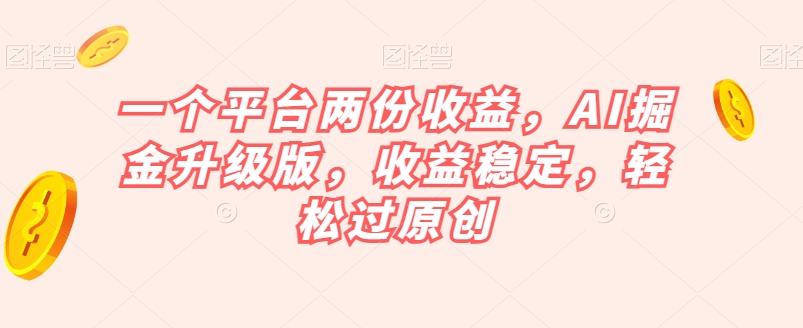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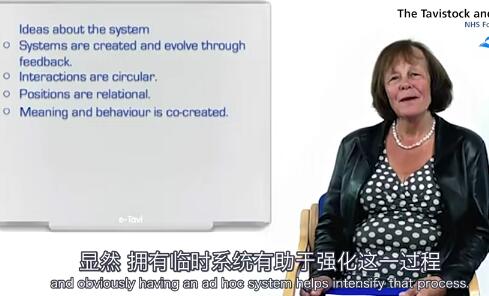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