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后台有朋友会莫名其妙发个书名过来,是觉得我这有资源吗?朋友们,我看纸质书比较多。
在我心里,之前是孔乙己、太宰治和卡夫卡混合起来的样子。后面读了《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印象才逐渐转变。激情有,绝望也有;理想主义有,现实主义也有;呆板天真有,放诞不羁也有……本质上我觉得他非常有热情,只是那样一个时代,世界之激变,国家之孱弱……确实太容易让人体会到个体的无力和渺小,生出绝望的感觉。可他也没有完全放弃,你如何能想得到一个放弃希望的人,会写出这样的句子?郁达夫1933年从上海搬到杭州,秋天去了趟浙东,第二年春天又去了趟浙西。虽然黄山绝顶没有登上,雁宕天台也不曾去过,可也出了这么本游记。典故、佚闻、民生状况、传承风俗、风景的特点几乎都有涉及,自己的联想和感慨也不少。但现实旅行中的色、香、味……那可就一个也遇不到了,得找些其他乐子。全赖作者的文字能给出多大想象空间,和可供咀嚼玩笑的余味。双十临近,郁达夫和两个朋友、一位英国军官定下去富春江旅游的计划。郁达夫看着他微俯向前,蹒跚于斜阳、衰草的山道上,忽然想起了哈代的一个短篇:《德意志军团的忧郁的轻骑兵》(关于身处异国他乡的军人,以及某些美丽的错误)。又想到刚刚在鹳山上聊严子陵垂钓的石碑(钓台题壁就是这里),聊谢皋羽的西台恸哭(可参看《登西台恸哭记》,悼念文天祥的文章)。作为国庆日(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双十是国庆)的哀词。是一次从上海到无锡的旅游。住旅馆就不开心,听到旁边房间的响动(此处大约少儿不宜)、舞乐以及伴奏的弦索,也觉得是“勉强的乾兴”,是四万万受难人民在野声里的啜泣。杨维桢吃完饭在桌上写:“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当时罗贯中也在旁边,附和写了一首“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惠山路上看到一群人在惠山泉水大嚼豪游,好多武装同志沿路放肆高笑。一爬就到了头茅峰,可算是个没人的地界,周围只有蓝苍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岚。比如,这本书最开始不是这个名,它曾经可以有更明显的名字。比如《达夫游记》,达夫同学觉得太骄傲;或者《山水游踪》,觉得太文雅了……这种自嘲的能力,如果面向其他人,也就成了强力的嘲讽。说以前看古人的游记,开场白总有那么一句:“余性好游”。嘲讽游记算是开胃菜,后面游狮子口,逛天目山,更是狠狠嘲讽了文学。讲的天目山昭明太子的传说(此处略过,自己去搜,爱看古文可以去看《太平寰宇记》)。说文人啊,活的时候文章不值钱,能把自己饿死。可只要一死,等骨变成碳,肉化成灰,都跑过来攀龙附凤,难道这就是文学永久的效力?你看,文人活着就是吃饭穿衣生儿子。可死了几百年之后,就不需要给他提供这些了。能给当地活人吸引不少游客。和尚道士还可以骗点钱,给自己起个庄严灿烂的寺出来。当时出去玩也兴组团,郁达夫就跟林语堂、潘光旦之类笼统四五个人出去玩。
觉得夏天时候就应该跟老婆孩子到这桃花源住个几天,外面的事就不管了。饿了吃点山里的野菜,村里的牛羊,渴了喝些清溪的淡水。中午衣服脱光了去溪水里面游泳,晚上困了就睡月亮底下,都不用关门!电灯也不用,有一支雪茄,一张行军床,一条薄被,和几册爱读的书就好了。“像这一种生活过惯了以后,不知会不会更想到都市中去吸灰尘,看电影的?”
虽然只是林语堂的自言自语,不过旁边的郁达夫表示已经看穿了一切。
路上一遇到不开心的事就说:“这是Wahrheit!”(从歌德那里来,现实和理想不能相符的意思)。现在全团都学会了,一遇到可爱的就“这是Dichtung!”,遇到可恨的就“这是Wahrheit!”那天下雨,林语堂一整天都躺床上看书打瞌睡,其他人倒是都出门了。碰着小商人陪着去游艺场,又去了这位商人熟识的乐户家里。听完戏,街上还遇到几位时尚的美人。商人就讲开了:三位以前是上海来游艺场献技的坤角,后来有主顾就没唱了,再后来主顾们有了新欢,就成了街头的神女。可惜我们中间那位江州司马没有同来,否则倒又有一篇《琵琶行》好作了。
附一小彩蛋,在郁达夫的经历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蛮喜欢。当时去栖真寺玩耍,看到别人都在殿外的墙壁上写东西。他“附名胜以传不朽的卑劣心也起来了”(贬低),就也写了一首,是昨天在兰溪放的“臭屁”(贬低*2)。那里有三片千丈大石,直立山巅,相传是江郎兄弟三人入山成仙后所化。花船统名江山船,而世上又只传有望夫石,绝未闻有望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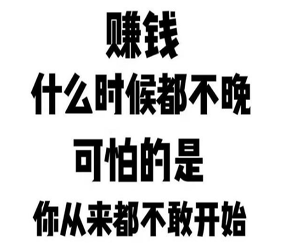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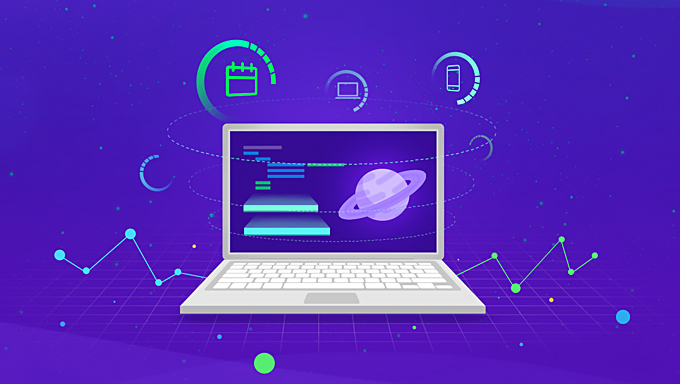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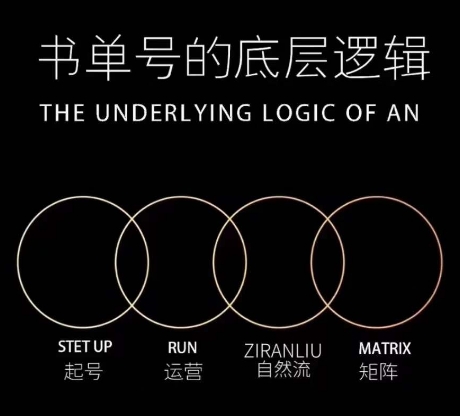


![[C语言] 达内C++教程全套视频 超过3个月的学习课程(笔记+代码)](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bbd86cdbb3fa3bb4fb568a4350cd10c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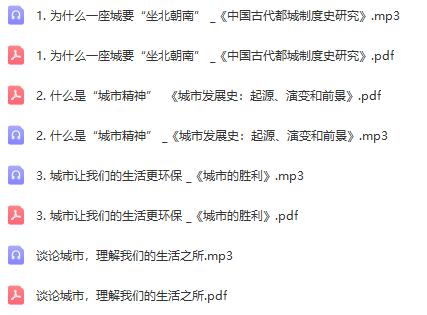



![[Python] 2017年11月最新版 尚x堂_Python视频教程 全套视频 32G](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5ecc7b88e610fb14a592598c781e3659.pn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