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大师张俊功_评书学习资料
发布于 2021-06-17 11:51 ,所属分类:评书学习资料大全
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我们删除

在我看来,张俊功是陕北说书史上不世出的奇才。陕北说书正是在他手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陕北说书人从他开始,才完成了由“书匠”到“现代艺人”的伟大转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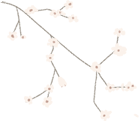
张俊功(1932—2008),祖籍陕西横山县柴兴梁村。自小父母双亡,两岁时出天花,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同村的老婆儿以缝衣针挑开眼帘,刺破左眼,导致失明。三岁时随叔父逃难,落脚于甘泉县桥镇安家坪村。八岁开始揽工,放牛、拦羊、种庄稼,样样农活干遍。由于视力模糊,锄地分不清草和庄稼,常挨东家打骂。25岁拜本县下寺湾艺人张金福为师,学习说书。四个月后,学会本书两本半:一本《汗衫记》,一本《吴蛮子贩人》,半本《劈山救母》。师傅希望他留在身边继续学习,出门行艺也好有个引路之人。但张俊功决定自立门户,勇闯江湖。

张俊功
事情发缘于一碗杂面:
有一天,师徒二人到王家洼说书,主家姓王名三,许下口愿要说书。旧时的艺人说书前不敢吃饱,等说书结束后,还吃一顿饭。“饱吹饿唱”,是这个行当由来已久的规矩。他们认为吃饱了唱会伤气。且说那天说完书,王三的婆姨擀了两碗杂面,端到炕上。师傅端起一碗吃开了,他也端起一碗,正准备吃,王三的婆姨走到他跟前说:娃娃,你甭吃!让你师傅先吃,吃得剩下了,你再吃。他只好把碗放下,但浑身难受得怎么也坐不住了,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让他钻进去。师傅看他难受,就把第二碗端起,吃了两口,说:我肚子疼了,你替我吃了。他只好再把碗端起,眼泪和面吃完了。那一晚,他整夜没有睡着,第二天就告别了师傅,开始了他一生漫长而艰辛的卖艺生涯。
1978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北斗》,要为演员王润身配制一段陕北说书。当时韩起祥身体不好,推荐张俊功赴东北录音。导演以为这三段唱词,对一个目不识丁的盲人来说,至少要背几个月,但张俊功下了飞机就会唱了。他在长春共呆了两个月,每天住在带浴室的甲级房里,随时有人配送瓜子、花生、水果、香茶,觉得当皇帝也不过如此,但实际配音只有十分钟。张俊功在电影中创造性地运用陕北说书的喜调、苦调、武调三种调式,成功地刻画了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他的喜调变化灵活,忽刚忽柔,忽粗忽细,既塑造了喜剧的气氛,又对美猴王起到了造型的作用。从此张俊功一举成名,成为陕北说书界一时无两的人物。
1979年5月,张俊功重组甘泉曲艺队,自任队长。恰逢改革开放初始,陕北民间信仰复苏,各地重修庙宇,大办庙会,张俊功带领一班徒弟走州过县,四方行艺,足迹遍布延安、榆林各县,以及邻近的宁夏、甘肃、内蒙等地。1982年,陕西音像出版社又为他录制了《快嘴》《武二郎打会》《卖婆姨》等说书磁带,这些盒带一上市便立即告罄,并以几何级数被复制、盗版。那时你到陕北旅游,街上到处播放着张俊功的说书,随时可见一个小卖铺的柜台上,放着一台录音机,店外有一群仰长脖子的民众在听书。张俊功的名声在陕北超过了任何一个当红明星,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致一个外地记者来延安后抱怨说,张俊功的说书阻碍了港台流行音乐的传播。
巨大的名声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当时陕北各县的电影院一张门票售价一角,而张俊功带领徒弟在县城“搭野场”演出,一张票售价一角五分。令电影院售票员眼红的是,人家一场下来能卖六七百元,算下来入场人数要达到四五千人次。徒弟们跟着张俊功每月能领到一两百元工资,而当时在政府上班的干部每月工资也不过六七十元。张俊功用演出的收入给每个徒弟都买了一身白衬衣、黑裤子,脖子上都打着一条红领带,胯下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当他们的车队穿过大街小巷时,着实把路两边的年轻人羡慕坏了。因此,在当时农村光棍成群的年代,他的徒弟们都娶到了漂亮婆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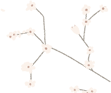

二
毋庸置疑,在陕北说书的历史上,张俊功和韩起祥都属于“改革派”人物,但二人所走的路径却截然不同。如果说韩起祥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以编新书、说新话,来迎合随时变化的政治形势,张俊功则完全相反,即使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没有向体制靠拢,而是自觉回归民间,靠一把三弦、一副铜口钢牙将陕北说书由庙堂拉回炕头。他的口头禅是,“我不爱跟公家人打交道”。他常对徒弟们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既然你不愿“伺候君王”,“君王”还会跑到安家坪问你:老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回归民间,对张俊功来说就是把陕北说书在“文革”中以及更早年月里被掩埋、被破坏的东西打捞出来,重新上釉抛光,并让它再度回到乡间庙宇、农家小院等固有的舞台上。这个舞台被尘封得太久,以致于它一旦被清扫出来,便焕发出了无限生机。
陕北说书就主题而言,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古典戏曲、讲唱文学没有多大区别,不外乎“忠臣良将、才子佳人”的老般数。说书人也常常这样自曝家底:
闲官员编下书两本,
代代相传到如今。
一本叫奸臣害忠良,
一本叫相公找姑娘。
说书人离开这两本本,
再能行的行家也说不成。
“文革”复出后的张俊功并没有沿着韩起祥开辟的“编新书、说新话”的路子走下去,而是毅然扛起传统的大纛,回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路上。除了偶尔应景编个小段,如《一个存折》《老牛卸套》等,他从来没有把精力放到编新书上。平时在乡间演出基本都是传统书,音像出版社为他录制的如《沉冤记》《清官断》《五女兴唐传》《武二郎打会》等都是传统书,只有一两个半新不旧的小段如《算卦》《懒大嫂》等。因而就说唱的内容而言,张俊功并没有多少创新。人们觉得它新,是因为这些旧的东西离开听众的耳朵太久了。
张俊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说书的音乐和表演的形式方面。
在说书音乐方面,张俊功博采众长,充分利用单音弦的技术特点,在原虎皮调的基础上糅合了眉户(劳子调)、梅花调、靠山老调、道情和秦腔音乐,去粗取精,成功地打造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迷花调”的音乐。这种音乐的最大特点是欢快、明亮,非常适宜现代人的耳朵。
陕北说书起源于乞讨,伴奏音乐历来以悲苦见长。原因简单:你上门要吃的,不把自己说得可怜兮兮,反而理直气壮或慷慨激昂,让施主听了觉得你比我还牛,还跟我要?我跟你走算了。后来又和神卜联结到一起,伴奏又显得阴沉、郁闷,尤其是韩起祥惯用的“靠山老调”和“巫神”很像。张俊功和韩起祥虽同是横山人,但他俩同里不同派、同艺不同师,韩为三弦双音派,张为三弦单音派。韩派说书正宗古板,表现人物以平调哭音见长;张俊功说书活泼欢快,表现人物以平调花音见长,故有“韩帅张怪”之说。
张俊功熟悉陕北说书各流派的唱腔曲调,又大胆吸收各种地方小调、眉户戏、碗碗腔、秦腔音乐,甚至口技中的精华,并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说书中。加上张俊功本人闯荡江湖多年,善于模仿社会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语,这使得他的说书现场感强,气氛热烈。如悲伤时用虎皮调中的哭腔,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但有时又会加进眉户戏中的“哭板”,使得唱腔细腻、婉转,一唱三叹。武将交战用的是双音调中的武调,这种调式经韩起祥改编后紧张激烈、威武气派,战斗一起,就仿佛听见了千军万马的撕杀之声。但他的说书音乐最迷人的地方还在于“迷花调”的反复响起。经他改编后的“迷花调”柔美、动听,一扫传统说书的质木无文和阴沉悲苦之气,使得听书成为一种享受,而不再是为“哄神神”而受罪的差事。
在表演形式方面,张俊功最大的贡献是,大但借鉴了戏剧表演的形式,将陕北说书由“坐唱”改为“站唱”。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陕北说书自诞生以来,就是坐着唱的,“坐唱”的历史和陕北说书的历史一样长;但现在这个半盲人将它改为“站唱”,好比爬行的猿人突然开始直立行走,令好多艺人目瞪口呆。

这不是改良,而是革命。这场革命据当时的参加者、张俊功的儿子张和平回忆,发生在1973年的2月:
那年我已经虚岁16了,会弹三弦了。常和我爸(张俊功)串乡演出。有一天前晌,记得刚过罢正月十五,我们俩到我们村对面的潘圪坨说书。我爸一直就会打四片瓦,常在演出开始之前说快板,不算“正场书”,只能说是“打耍耍”。那天说完快板,要开始说正书了,他突发奇想,说:“我看人家唱戏的,是站下唱了。咱们也试试,你坐下弹,我给咱站起来说,看怎么样?”说完,他就打起四块瓦说开了。村里的几个老汉儿稀奇得不得了,说:“活了一辈子了,从来没见过个站起说书的。这个好!又能听,又能看。”从那天开始,我们说书就再没有坐下过。以后带的徒弟多了,又加了二胡、板胡、笛子、马锣等乐器,但人再多,主说的人也一直是站着的。
从坐到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转换,而是由弹唱分离带来的表达自由。这种表达自由是前所未有的,说书人的身体从此由怀抱三弦的坐姿中解放出来,可以随意表演动作,并在舞台允许的范围内来回走动,这使得说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听觉艺术的局限,有了初步的视觉艺术的效果。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自由,有的人天生就恐惧自由,就像华阴老腔,原来只是附属于皮影的幕后戏,后来才撤掉幕布,与皮影分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刚开始撤掉幕布后,好多人无法适应。原来有一块幕布挡着,好坏美丑都看不见,现在一切都曝光在众人眼皮底下,许多唱家都张不开口了。他们说,来的都是乡党,臊得很!说书人也一样,他们坐着说唱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现在突然让他站起来,他不知道干什么。尤其是对那些双眼失明的艺人来说,这场革命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身体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站起来表演。张俊功之所以能创新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右眼能看见。加上他从小会唱戏,爱丢丑,这些因素加起来才使他的革命能够成功,而对于大多数盲艺人来说,走路都要人扶,遑论站起做动作?加上本身缺乏表演天分,生计就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就像当年韩起祥禁止说书人卜命算卦一样,很多盲艺人有意见,说:你进了公家的门了,有饭吃;我们是受苦人,没吃处。你说算命不顶事,顶事不顶事那是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碗饭嘛!现在张俊功将“坐唱”改为“站唱”,说书人群起而仿效,盲艺人本来就光景不好,现在站不起来,更没人要了。因而,很多盲人对张俊功恨得牙痒痒,认为就是这个“坏怂”砸了他们的饭碗。直到2008年,当张俊功去世的消息传到延川后,盲艺人白旭章竟然幸灾乐祸地说:“咋把一个害除了!”
但对那些有表演天分的明眼人来说,张俊功的革新无异于锦上添花。陕北话说“正想上天了,等上个龙抓”,有些人在张俊功将陕北说书革新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子长县有个说书人叫贺四,从小就跟着父亲唱道情,他演的丑角戏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在当地很有名。16岁拜当地一个老艺人为师,学习说书,但一直进展不大。25岁时改投张俊功门下,技艺大长。虽然由于年轻时过度用嗓,不懂得保护,把嗓子说坏了,但他把演丑角戏的“童子功”用到了说书上,使他的说书生动活泼,喜感十足,很受观众追捧。在这些有表演能力的人成功转型后,那些表演稍次的艺人,在市场刺激下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寻求突破。短短十来年功夫,艺人们从口才、形象,到动作、台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经过近五十年的舞台实践,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站唱说书”拓展了陕北说书的表演空间,释放了演员对剧情的想象力,从整体上提升了陕北说书的舞台魅力。

三
如前所述,陕北说书属于北方鼓词话本系统,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坊间刻印了许多供说书人讲唱或文人案头阅读的底本,好多说书人家里都珍藏有这样的“猴本本”。过去的老艺人虽然大都不识字,但他们会请一些识字的先生或秀才给他们“指拨”。他们背会以后才能开始表演,尤其一些“书套子”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但张俊功从来没有在书词上下功夫,他的智慧告诉他,即使你把底本倒背如流,也无助于你的表演引人注目。因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与传统艺人比试“词功”。他把所有的书面文本都变成了临场的即兴发挥。一切形象都在他随意而诙谐的表演中创造出来。借助过人的口头表演才能,他把所有传统的故事都变成适合此时此地的当下演出。他演唱的经典《卖婆姨》,在韩起祥的唱本中叫《五红镇》,除了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外,甚至连“关口将名”也换了。他演唱的短篇故事《快嘴》,在韩起祥的说唱曲目中叫《巧嘴媳妇》,除了大致框架相似外,血肉、枝叶都被他换得面目全非。他说的《破迷信》,在韩起祥的演唱曲目中叫《请巫神》,随意加减、破坏的痕迹很浓。
传统说书不管哪家哪派,都十分看重书本。即使那些不识字的艺人,通过师傅严格的口耳相传,也和“猴本本”上写的八九不离十。但从张俊功开始,说书脱离了固定的文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表面上看,这比过去的说书容易多了,实际上它对艺人的口头表演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他不要求徒弟死记硬背。在某种程度上他颠覆了讲唱文学传统的授徒方式。传统的授徒讲究“口传心授”,徒弟拜师以后就住在师傅家里,除了跟师傅学书,还要帮师傅担水种地、喂马劈柴。农闲时,师傅才将古书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并要求徒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但从张俊功开始,徒弟一跟十几个,男的女的都有,他哪有那么多的空窑让徒弟们常住?他授徒的方式很特别,就是跟上他跑场子。在实践中观察、模拟,有点像现在大学里说的“现场教学”。他从不要求徒弟一字不差地背书词,而是边学边练,边练边演,只要书理通顺、合辙押韵就行。至于以后能不能出彩,就看各人的造化了。师傅不仅不要徒弟担水种地、喂马劈柴,还给徒弟发工资,吃工作餐。有些品行好的还给挛婆姨,比如定边的贺改民,家境贫寒,但为人忠实厚道,师傅就给他挛了一个婆姨,她就是后来有名的“女书匠”牧彩云。

超常的口头表演能力,与人世间所有的技艺一样,少不了刻苦地训练,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天赋。说到底,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禀赋是无法相互传授的。张俊功自小盲残,目不识丁,但他善于观察社会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善于捕捉大地上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声音。举凡婆媳吵架、男女斗阵、老妪学舌、老翁叹气,村姑浪谑、婴儿啼哭、鸡叫狗咬、驴马嘶鸣,无不穷形尽相,信口即来。《清官断》中,他一人一口,模拟两个姑娘穿过一片幽深的森林,遇到的布谷鸟、水咕咕、鸱怪子、猫头鹰等多种鸟叫;说《卖婆姨》到高兴处,拿起快板,随便打了几段,就把一个两面三刀、贪得无厌的媒婆形象活生生托出,而这个媒婆在原作中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快嘴》中他表演的秀兰想男人,语气至柔至美,令人骨酥;《武二郎打会》中他和张和平父子两人表演的庄稼人、小学生、赌博汉、老婆子,从口吻到语气都惟妙惟肖,武松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陕北民俗风情画卷……这些章节都已经成为陕北说书史上“教科书式”的经典。他的传奇是不可复制的。他的名字以及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那些风流韵事,将会被人们长久记诵。
甘泉县文联主席、作家刘虎林在散文《张俊功说书》中,记录了一次张俊功在张家畔的说书实况。这场书是应乡民曹四所请,说还愿书。几句开场诗说罢,他没有按照传统程式说一个“小弯弯”,而是现编曹四的故事,先从两口子赶路说起:
曹老四,三十三,家住横山响水湾。
娶了个老婆是张家女,名字就叫张凤兰。
两口那天吃罢饭,一卦就想起张家畔。
老婆忙把包袱绽,一层一层往上换。
条绒裤,月蓝衫,塑料底板鞋脚上穿。
老汉一看笑哈哈,就把老婆身上拧了一把。
老婆说:
哟,死老汉,挣你的命!捏捏揣揣像个甚?
要是在黑夜里就没个啥,大白天操心人笑话咱。
老汉说:
你不要怕,不要管,谁不晓得咱们是婆姨汉。
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同睡一条毡。
老婆骑驴老汉赶,
嘟—呆—
驴屁股上就踢了一脚。
老婆说:
死老汉,挣你的命!凭什么赶驴不出声?
要不是我两腿夹得紧,一卦就跌我个倒栽葱。
老汉说:
嗨,不是我吹,不是我夸,侍候你我是老行家。
晓得你两腿夹得紧,老汉我才敢耍威风。
......
站在台下人群里的曹四婆姨高喉咙大嗓子对男人说:“你那张烂嘴,逮住什么都往出说!”曹四嘿嘿笑了一声,说:“那是张先生现编的,我有毬的办法!”众人听到他们两口子的对话,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羞得曹四婆姨满脸通红,再没敢啃声。
也许这是张俊功说书生涯中极普通的一幕,但被有心的作家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可以从中窥探一代说书大师是怎样利用口头文学的自由性,随意编织故事,即兴创造笑料的。据他晚年回忆,年青时他曾在古书上下过功夫,不止一个师傅给他逐字逐句地“指拨”过,但他并没有墨守书本、寻章摘句,而是把所有的故事和词章都糅合到他的即兴创造中。批评他的人说,张俊功的“词功”很差,全靠一张嘴骗吃骗喝。抛开这里面羡慕嫉妒恨的成分,他们讲出了口头文学的实质,那就是随物赋形的口传能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一个口头文学的从业者不靠“嘴”骗吃喝,而靠傍官媚权、拉弄富人,才是真正可耻的。相反,张俊功,一个逃奴揽工,翻转于草莱之间、寄生于沟渠之中的残障人,上帝没有将他轻看,反而把他从尘土中举起,又赐给他超常的智慧与口讲的能力,使他成年后,靠一把三弦、一张绣口,红遍整个陕北,生养他的故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
在我看来,张俊功是陕北说书史上不世出的奇才。陕北说书正是在他手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陕北说书人从他开始,才完成了由“书匠”到“现代艺人”的伟大转变。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5期
作者:狄马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马 娜
海报:贾 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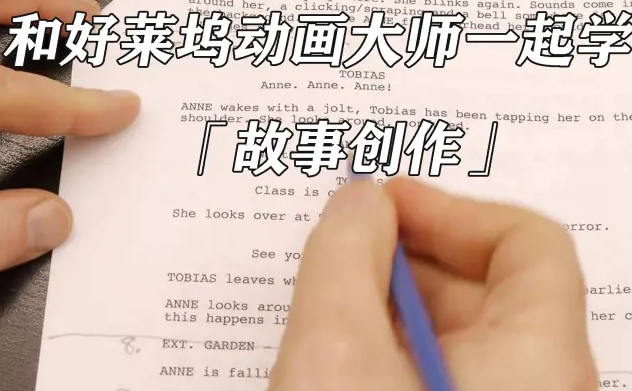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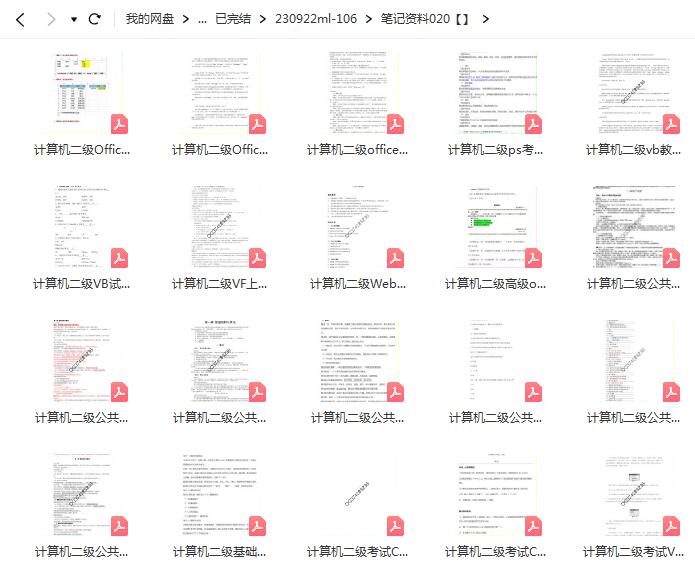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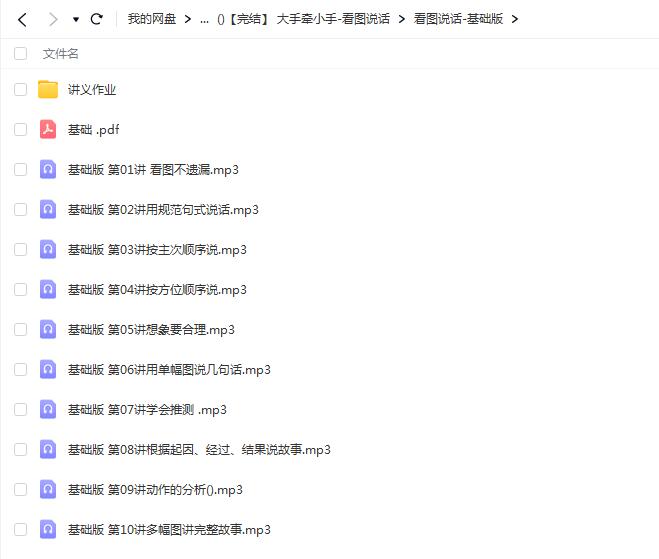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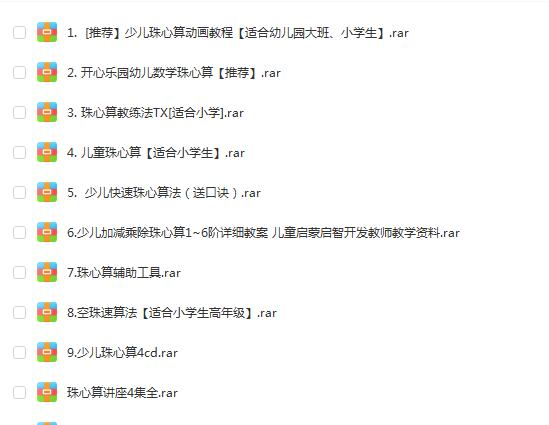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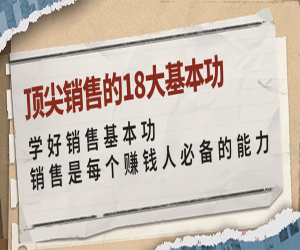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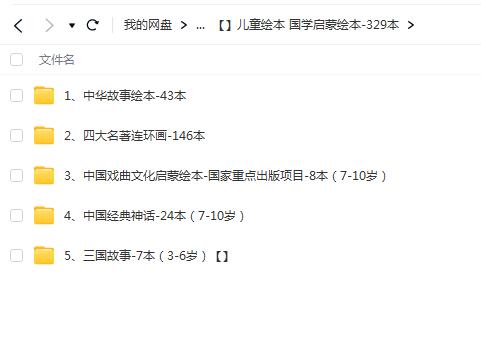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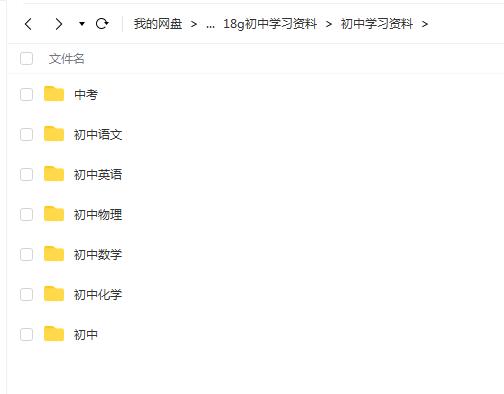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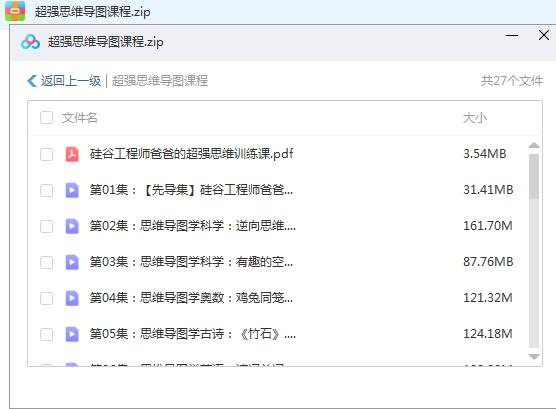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