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田耳:你看云时很近(汤成难小辑)
发布于 2021-11-22 19:02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 作者简介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小说七十余篇,计两百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选和排行榜。结集出版作品十余种。曾获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供职于广西大学艺术学院。

一
看汤成难女士的小说是一个意外,2018年冬天应邀给江苏省青年作家作讲座,一项任务是看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并点评。这便读到《月光宝盒》,当时心存感激,若没这篇,我不知道点评如何撑满课时。这篇小说我点评起来容易发挥,却又是因为另一重意外:我曾经构思过一个小说,没能完成,待我看这一篇,就意识到:如果那一篇构思完成,会与《月光宝盒》在情节主线甚至诸多细节上有惊人的相似。倒不是觊觎“这篇要是我写的就好”,心里更明确的意思是“可惜下手太晚”。又不禁自问,“相同的题材你能写得更好吗”,便也舒一口气。面对好的小说,不管作为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幸事。
时下作家常以社会新闻或热搜条目作素材,酝酿并发挥,有时还未构思得当,就见手快的作家已将同一素材写成小说并发表,写作遭遇“撞衫”。这样的事情,我总归碰上一两桩,一截稿子便废在电脑。
《月光宝盒》是写耍猴人与猴的关系,我许多年前看到过一组名为《最后的耍猴人》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耍猴人的妻子给猴喂奶。我一瞥即知,这一张照片,就能生发出一个独特的故事,于是这便成为我一个素材。看了《月光宝盒》,我甚至坚信汤成难也是看了同样的一张照片,写出这个小说。后来有机会找她求证,她说这小说来自一则新闻:一位耍猴的老汉因贩运珍稀动物而被捕入狱。所谓的珍稀动物,不过是老汉从小驯养长大,用于耍猴戏养家糊口的的几只猴(猕猴)。虽然这则新闻激发了她去了解耍猴人生活,但这小说能够浑然一体地“搬运”出来,显然也是她得知耍猴人的老婆会给猴喂奶。在我的理解,这恰是一个素材的“关键信息”,如此看来,我和她对素材的把握,妥妥地又撞上一回。
正好我在戏影专业教“编剧基础”,其实就是教学生怎么编故事。写作这么多年,我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应该去编故事;故事无所不在,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如果具备足够的写作经验,素材自带有前呼后应的伏脉,故事往往有内在的逻辑法则,从一个素材出发,不同的作者捋出它内含的各种可能性,往往是用“优选法”的方式推进并编撰:在每个情节点上,找出尽量多的可能,是为往下推进的选项;在诸多的选项上进行优选,故事得以一折一折推进。这是故事编撰的基本方法,我知道,许多作家无非这样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故事,面对相同的素材,往往会作出大同小异的选择——故而,我们才会面对别人率先发表的作品生发出“这篇是我写的就好”的感叹。这就是撞上了,彼此心里明白的,那个故事就在那里,只是被别的搬运工率先寻得并搬运到纸面。
因小说《月光宝盒》与我从单帧照片得来的构思脉络基本一致,这两年上课,我都以《月光宝盒》作为故事编撰的一个案例,事实上,学生课堂的反馈也一再证明我对故事编撰内里逻辑的判定:故事原本就在那里!关于这个案例,我是先展示那帧照片:耍猴人的妻子喂一只猴,而耍猴人在一旁抽烟睃来几眼,脸上有一份古怪的得意,似乎是想:我这老婆真是不错,肯帮我喂猴。我将这照片展示给学生,要他们先行发挥,当堂写数百字梗概即可。他们对图片信息的读解,往往难以完备,找不出更多的、溢出画面的信息和选项,大半的人一编就成了这样:一位耍猴人的妻子痛失爱子,但坚持以母乳将一只失去母猴的猴崽子喂养大,女人和猴之间便建立起一份不可思议的母子之情,再往下发展还可以从猴崽收获各种不可思议的回报,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在我看来,学生大都未曾进入社会,编撰故事缺乏生活逻辑支撑,扔一块西瓜皮,往往老实地往上面踩。我有些于心不忍,甚至怀疑在大学当老师异于耍猴人者几希。之后,我要学生再次将照片看仔细,梳理其中的人物关系。照片上虽然只有耍猴人、妻和猴三位,但还掩藏了一位小孩,因这小孩,妇女得以处于哺乳期,从而有照片中场景的出现。在此我不惮于指出,学生们的想象容易温情泛滥,那是做不到严谨地依从生活逻辑和生存法则。我提醒他们能多带一些“残酷”和“冷峻”,才可能透皮透里地想象并还原他们并不熟悉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底层生活。在我看来,耍猴人的妻子给猴子喂奶,不必注入过多情感因素,最大可能,只是耍猴人以妻子的乳汁代替奶粉,以管控“生产成本”。如果他家的小孩意外死亡,我不认为耍猴人的妻子仍有心情将哺乳行为进行下去,在这伤心的时刻,一只猴子胆敢将女人视作自己母亲,女人极有可能拎着它能扔多远扔多远……
如此一来,这帧照片其实包含有三组一对一的关系:猴子和耍猴人、猴子和耍猴人的妻子、猴子和小孩。人物关系全都展示出来,下面的学生几乎一致认为,故事应该围绕猴子和小孩来写。当我问及小孩的性别,又是两个选项在他们面前敞开。他们不得其要,我说,如果这个小说取个名为《月光宝盒》呢?当然,小孩只能是女孩,他们“95后”仍能背诵至尊宝对紫霞仙子的那段经典对白。
二
找对人物关系,往下的讨论变得顺畅。我个人的引导也起作用,事实上,两次课堂上的讨论,在每一处故事节点,大家先找出往下发展的诸多的可能,再从中选定最优的选项,如若争议,动用投票机制……讨论或者投票的结果,整个故事的走向神奇地与小说《月光宝盒》吻合。
比如说,既然要以小女孩的视角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她看待这只猴,会与父亲有什么不同?答案几乎是明摆的:小女孩父亲把猴当成赚钱工具,但小女孩不一样。小女孩,甚至我们所有人幼年时,会对动物高看一眼,那时候我们还未生发出万物灵长的傲慢。尤其对于猴,小孩心目必有着特殊地位。我们都是看《西游记》长大,班上有姓孙的同学,若胖不起来,绰号指定是“猴子”。
既然这样……我和学生有了商榷:这只猴的名字都可以确定了。……悟空?不对,太直接了点。……至尊宝?土行孙?也不好赤裸裸地把《大话西游》或者《封神演义》再抄一遍吧。于是,叫它“阿圣”如何?底下也没异议。到这时我还不急着说出来,汤成难女士的小说里就诌这么个名。
好,接着往下爬梳……既然小女孩认为猴子兄弟有异能,甚至宁愿相信猴子就是孙悟空,且这相信日益地坚定(小孩更擅长宁可信其有),那她会对它做些什么?眼下猴子还不是孙悟空,她忍不住要助一臂之力,那么她会从哪入手?教它走路?这显然不对,如果女孩与猴一般大小,猴会比女孩更早学会走路。女孩会走路时,这个猴兄弟已在树杈间荡来荡去,女孩看来简直就是“腾云驾雾”嘛。(说到这里,我总感觉《月光宝盒》里女孩和阿圣年龄设置成一样大小,不太符合情理。如若女孩大几岁,而阿圣是和女孩的弟弟一同钻进母亲的怀里抢夺乳头,情节应会更妥帖。而小女孩,作为猴子阿圣的姐姐,大这几岁,观看的眼光会更从容,也将进一步优化这故事讲述的质地。)小女孩要确认阿圣就是孙悟空,她必然要考虑一个问题:猴子不会说话,但孙悟空是会说话的。如果阿圣连话都不会说,那么,往后怎么去跟人学七十二变呢?小女孩免不了想教阿圣说话,就像她父亲会教阿圣耍猴戏。在她看来这也不是大问题,她坚信它不是一般的猴。
于是,在小说《月光宝盒》里便有如下描写:“我从没放弃过训练阿圣开口说话,这与父亲对阿圣的训练不一样,父亲是为猴戏,而我则是为了阿圣。当然,这也是一个秘密。我用两截树枝儿撑开阿圣的嘴,拽出舌头,再用大木夹子夹住——这是从一本残破的书上学来的,书上说,不会说话正是因为舌头不灵活。我对此深信不疑。”从技术层面说,越是偏于虚构的情节,越是要充塞以准确的细节,让虚构进一步夯实,让想象力得以脚踏实地。作者想在此处将虚构夯实,并作了一番努力,用上了“一本残破的书”和大木夹子,仍是语焉不详。事实上,一个人如何教猴子说话,作者在此处犯难,往下只能笔头一转,描写小女孩的母亲“傻英子”跑来凑趣,小女孩便用木夹子夹母亲的舌头。这无奈的转笔,也正表明想象力必有限度,诸多虚构的场景,作者确实难以“设身处地”,也就寸步难行。许多时候作者只能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动用手段和技巧,绕开障碍或是暗自拗救。这会减损成色和质地,创作本身也是在顺畅与无奈间往复跳宕,形成一股合力。
再往下,小女孩让猴子变孙悟空的努力只能一次次落空,而父亲作为耍猴人,却有传承有序的训练方法。阿圣不能说话,但学会越来越多的猴戏。接下来必有的冲突,就是小女孩将目睹阿圣的表演,她心目中的孙悟空没能上天遁地,而是在观众嘲弄的眼光里搞起表演。她接受不了阿圣被人当猴耍的事实,虽然阿圣本就是猴。别人看它是猴,她坚信它不是,它自有真身,阿圣总会在某一时刻发现自己是孙悟空。《月光宝盒》中,父亲本想带一只母猴四处游走挣钱,母猴意外的死亡,阿圣不得不火线上马,立即干活。因为女孩母亲傻英子的死亡,父亲带上阿圣还有女儿,开始了小女孩最初的远行,流浪般地送傻英子的亡灵回归故乡。而远行的方式,也是耍猴人通用的:爬火车。故事延展到此,作者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换来一段特别扎实的叙述:“……你看到列车头上写着“郑局平段”吗,这是从襄阳开往平顶山的;等到了平顶山,再扒车时,就是“郑局商段”的,我们就能到商丘了;到商丘再坐“上局徐段”的列车,可以到江苏徐州;再坐上标有“上局南段”的机车,我们就到达南京啦。”这是要用多少次扒火车的经历,才能换来的冷知识,恰到时机地被父亲道出,虚构的小说便如亲历一般纤毫毕现,纹路精微。这种化虚构为真实,把假的写得像真的一样,本就蕴蓄着创作独有的快感。至少,我想,汤成难女士写到这一段,狠狠松了口气。
叙述至此,故事会自己长脚朝前走:小女孩既有这样的不能忍受,她带着阿圣逃离父亲挟制也是个必然。小女孩看见人群中有着僧袍者,就当其是唐三藏,想将阿圣拱手送出,对方却不接纳,甚至逃离小女孩的纠缠。小女孩带阿圣的逃离,面临绝境,她必然对阿圣是否是孙悟空有了犹疑,或者此时她更急于阿圣身上潜藏着的异能。她会动用手段逼着阿圣“现真身”。小说中是写小女孩与一个带宠物狗的男子相遇,发生矛盾,一阵口角以后,对方说:“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让它从湖这边游到湖那边,就是齐天大圣。”小女孩为让阿圣现身,就将它一次次扔进人工湖,想要阿圣现身。于是,我便与学生商榷,这一处理似乎随性且随意,能游泳就是齐天大圣,那小女孩和阿圣这一路的苦难又为了什么?其实有更多的处理方式:小女孩既然与陌生男子发生矛盾,既然阿圣又在场,如果她真的相信、笃信阿圣身上潜藏的异能,那么何不让这矛盾更激烈点,是否可以玩一出苦肉计?女孩让自己处于不利,受到伤害,逼迫阿圣出手相救?当然,阿圣只能爬到树梢上,看见小女孩被人欺压,也会呲牙咧嘴,但它同时也能审时度势,知道自己根本帮不上忙。小女孩把它当人,它也只是假装在人间,它更懂得趋利避害,冷眼旁观。小说不同于玄幻故事,不会有从天而降,如果此处将矛盾激化,会有特别冷峻的一笔。冷峻本就是汤成难写作的一大特质,但在此处她的笔头故意宕开。猴子一次一次落水,并狼狈地上岸,场景更多的是滑稽,不至于坠入悲惨。
这次出走换来小女孩彻底的失望,她这才确信阿圣就是只猴。她拿走附着在它身上的所有希望,远离它。而父亲接纳了阿圣,他只是耍猴人,阿圣也只是他要耍的猴,因这层既定的关系,两人方得不离不弃。往下写到小女孩对猴的绝望,并有相关的行径,就是捉弄猴,比无聊的看客捉弄得更狠,因为她知道阿圣不是孙悟空以后,她就比看客更知道它是一只猴。此处便有了极为细微的戏剧化冲突,源于父亲发现收到一张假钱,忘了数钱以后照例得摸一摸猴头以示嘉许,导致阿圣往父亲要吃的面里掺一把沙。小女孩认为要教训阿圣,父亲还解释,自己数完钱都要摸一摸阿圣的头,刚才一摸假钱把这一茬忘了——事不归罪于阿圣。但小女孩的惩戒依然展开。“我突然改变主意,将端着面碗的左手缩回来,右手拿起木棍从火塘里夹住一个烧红的砖块递给它。阿圣看着砖块迟疑了片刻,但还是去接了。它对我无比信任。”这突然发力的一个细节,异常凶猛,小女孩的惩戒,实是对自己当初希望落空的报复,而报复又借助了一只猴对于主人顽固的信任。这一笔几乎是反向发力,写出禽兽之所以异于人者几希。父亲的态度不作太多描写,但这时候他既心疼猴子,又反驳不了女儿的振振有辞。两代人对于同一只猴的态度,并导致的行径,于此有了鲜明的分野。猴只是猴,一切超出它本身范围的期望,几乎都是灾难性的。
小女孩长大,外出求学,远离了父亲和阿圣。父亲和阿圣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走南闯北。家族的耍猴史行将在父亲手上结束,父亲也知道这赚不了多少钱,但接下来的四处游荡仿佛是向家族传承的事业,向自己唯一的手艺作漫长的告别。小女孩这时已是大学生,她趁父亲醉酒时将阿圣送去了动物园。“而酒醒以后,父亲没有责备我,只是他的双眼像秋天的早晨,变得充满水汽。他穿上鞋,背上背篓,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父亲去动物园找阿圣,却因偷盗动物面临刑事责任。虽然通过各种努力,父亲免于判刑,但他在押期间,阿圣莫名失踪。毕竟是一只猴,不熟悉它的人管不住的。父亲被释以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阿圣找回,就像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但事情毫无进展,阿圣音讯全无。父亲终于放弃,生平第一次买票坐车返回家乡:“父亲的脸倒映在窗玻璃上,隐隐约约,像猴的脸。真的,父亲越来越像猴了。”
接下来便是父亲必然地死去——是的,顺着故事脉络前行,便有许许多多的必然,而作者编撰过程中,有些时候是天马行空地发挥,有些时候确实就是按照规定性做填空题。填的这些空,便是故事逻辑延展的必然,而故事创作者所谓的成熟,就是知悉故事逻辑中富含的种种必然。
阿圣的失踪,导致或是加速了父亲的死,他一辈子利用猴子赚钱,耍猴、盘剥猴,仿佛远离仁义和关爱等大词指涉的范畴,事实上只有耍猴人才可能与猴结成生死相依的关系。往后,这故事还有规定性——阿圣势必还要现身,而故事本身还需要一个结尾,最好是逆转性的,那显然关乎长大以后的小女孩在何种情境里,如何与阿圣再次相逢。
长大后的小女孩埋葬了父亲,回到童年的住所,不远处的山丘有一个洞,那是很久以前她给阿圣挖的“水帘洞”。
当父亲满世界寻找时,阿圣早已循路回到了故乡。通常说法是“狗记千里路”,当然信鸽更具备这样的本能,现在把这能耐搁置到一只猴身上,显然毫无不妥。接下来,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呢?阿圣的出现还不能叫做逆转,它总得做些什么,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以此终结全篇。故事的结尾永远是点睛之笔,最能考量作者能耐,前面的所有情节,总要归置并收拢为一个点,必须压稳了全篇。《月光宝盒》是这样处理:
最初看到这个结尾,阿圣戴上面具……倒有意外,但也意外地轻盈。阿圣精准地戴上齐天大圣的面具,仿佛也回应了同名电影里的剧情,但这意外是否能算一次小小的奇迹,是否足以收拢耍猴人父女与猴十数年时光里的灵肉沧桑?故事里的“我”对此反应便是一通狂笑,笑得前俯后仰,笑得眼泪横飞,不敢再睁开眼面对阿圣。但这笑,我同样觉得有些突兀,并揣测,是否是作者对这样的结尾也无足够把握?许多人在对事情没有把握时,应对之策不就是一笑了之?但这小说已有不凡质地,作者不可能轻易处理结尾,必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时隔半年,因为要在课堂上跟学生交流,将小说仔细地重看一遍,这才发现这结尾确乎是一个奇迹,且是让这只猴回应了父女两人对它不同的态度。阿圣是孙悟空,是齐天大圣,这本是小女孩最初的认识和愿望,也动用手段迫其“现身”,但这样的愿望,落空之后换来小女孩对阿圣的鄙视和侮辱。父亲最后的岁月与阿圣日夜相伴,不离不弃,这才换来阿圣对自我的确认。阿圣便在小女孩悼念亡父、追忆往事的一刻突然做出一个举动。举动虽小,却在恰切的时间和地点,有如奇迹一般发生,自带光环,耀人眼目。所以,“我”的一通笑,是因在看到期盼已久的奇迹时,忽地了然奇迹背后涵涉的所有辛酸。
故事就这么结束,我引导学生一步一步推进,得来和《月光宝盒》大致相同的结果。也许我的主观意图包含其中,学生看似自主的选择,依然落入我事先的设计,但效果也是明显,他们跟随一对父女和一只猴,最后见证了小小的奇迹。他们不免会认同我一直强调的那个观点:故事原本就在那里,编撰者只须遵循经验,遵循故事内里的法则,就能捋出相差无几,甚至完全相同的故事。我对课程的设计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我让他们确信,同时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但事情真是这样吗?故事原本就在那里吗?
三
后有机会读到汤成难即将出版的小说集电子稿,虽以《月光宝盒》作为书名,但通读其中十七个中短篇,类似于《月光宝盒》这样倚赖于想象,侧重于虚构的篇什并不多,甚至很少。以我的分类,《寻找张三》和《奔跑的稻田》能与《月光宝盒》归于一类;而其他十四篇有着惊人的一致:每篇着力刻划一个人物,写实,伴之以一成不变的苦难和沉滞。
《月光宝盒》源于一则社会新闻,《寻找张三》似乎也源于无意中看到的一张陈年发黄的请假条(当然,对于小说的发生论,我乐于猜测而懒于求证),故事便从一张请假条展开。“我”在冶金厂废弃的旧厂房里找到一张1982年的请假条,请假人名为“张三”,而张三几乎是最常用的代称,张三李四,可能是任何人。事实与虚构就在这个名字上产生一刹那的重叠和恍惚,假条是具象的,但请假人却如此模糊;此外,车间主任“杨国强”的名字却立体般地清晰,同样清晰的还有“他在空白处用犹如受过机器碾压,捶打,敲击,撕裂的字体写下了三个字:不批准。”这虚实掩映,多年的一张请假条,几乎已具备一篇小说发生发展的所有势能。往下便是恍惚的寻找,这种恍惚性我乐意看为小说区别于故事最明显的表征:“我”一路寻找,张三固然是遍寻不见,杨国强随着叙述,必然有些曲折也必然露面,他必然地也把张三忘了,存在的事实只有这张请假条。而这故事的结尾,我甚至疑其是个唯一,没有更多选项:事隔多年,张三是谁并不重要,但“我”坚持要杨国强批复这张请假条,只为自己某种捉摸不定的情绪,和某种最为纯粹的坚持。
或许这才是当下一类小说坚定地远离传统故事后,能够到达的一个边界;一点模糊的意向外加一重轻盈的转折就能统摄全篇。青年作家似乎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力,他们抗衡于老几辈作家遍身的经历和满目的沧桑,唯有朝向幽微的局部发力,在事实与虚构间寻找存身的裂隙。《寻找张三》的结构、饱满度和完成度,足以成为这一类小说的范本。
“父亲在他五十岁那年决定出一趟远门,这个‘远’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时间上的,一年,两年,或许很多年……他也说不清楚。”《奔跑的稻田》开头第一句就让我有一种熟悉,感觉这是一个有原本,“致敬”的小说。当父亲背着稻种,说走就走,这感觉进一步强烈。及至父亲第二封信里谈到“那是一块没有地址的地”时,心头咯噔一响,知道父亲是回不来的。再往下看,父亲果然再没有回去,那么,我也完全明确:又一篇向若昂·吉玛朗埃斯·罗萨《河的第三条岸》致敬的小说。这并不奇怪,罗萨这篇几千字的小说几乎是写作者在文青时期必有的一道心结,写出向它致敬的小说,或者没能写出来。这一路数,最终要看的是作品的完成度,所以往下继续读,就有了明确的参照。
这个父亲再也没能回来,他也没法在任何一块稻田里长久地逗留,只能越行越远,不停地劳作并收获,用衣和裤管兜着各色土地生长的谷物送回家中。在他的信里,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也必然遭遇远方的各种奇闻异事,比如将蛇蜕当成衣服穿身上,野鸡在他臂弯里下蛋——这个远离人群却日渐亲近动物并融入自然的父亲,字里行间流布的是远离尘嚣之意。果然,这个父亲再也不出现,而通信终有一天也断绝,他就这么消失。对标《河的第三条岸》,“我”与父亲必然还要有最后的勾连。在原作里面是“我”想传承父亲,意外得到允诺之时“我”却落荒而逃……汤成难的这一篇里倒是没有落荒而逃,传承止于“我”鬼使神差般选择“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就读。卒篇之时,也仅仅是“我”保留的父亲当年用于装兜谷物的衣服,于午夜梦回之际如父亲一般张开了怀抱,而衣物的褶皱里谷物已发绿芽……
在技术层面,这篇“致敬”小说无疑是别有匠心,也与原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分寸。但还是让人感觉到它的规矩,分寸感保持这么好,在创作中未必是好事,我多么想这个文本里能有不管不顾的发挥,逃离原本的挟持,哪怕有一处失控搅乱了这种分寸感。事实上它没有,它像恋人一样在原本的阴影里依偎着原本。小说里不乏局部的缤纷,诗性的语言,绵延的想象,不免都是嫁接于其它母本的枝条,再怎么写,也不会因肢端的膨大而让主干难以承受,不会发出一丁点吱嘎的声音。
撇开以上三篇,小说集《月光宝盒》余下的十四篇小说,却呈现出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里面不再能找见偏于虚构的恣肆和轻盈,阅读过程滑入无边沉滞和浊重。小说写法忽然也变得单一,循其模式,不长的篇幅里大多写了某人跨度数十年的苦难,甚至是命途多舛的整篇人生。所有的沉滞与苦难,在一篇小说里往往又以一个轻盈的转笔统摄,那是这些底层的失败者偶尔能够感知到的温暖与奔放,却又让大全景更紧致地包裹以彻骨的冰凉。小说对于这些人不曾轻饶,死亡是最为常见的结局,以致某些篇章我看到最后,那个悲惨的人儿竟然没死,就暗自松一口气。
《搬家》中的农民工李城因与方作家笔下的人物同名,而得以意外相识,方作家得以窥知李城正朝着命途既定的悲惨结局一路滑落。到最后,李城临死之际唯一的希望,只是请方作家在小说里给同名的“李城”以美好的命运设置。两个主要人物的联结,仅在于人名的重叠,方作家笔下虚构的“李城”与现实中的李城对应。同样的手法,在《寻找张三》里面也有一点,但“张三”是一路虚写,而“李城”由虚到实,并一路被苦难夯实,反复辗轧。同样的手法,往后故事的编排,因为作者给予的虚实向度不同,而得来迥异的小说质地。
《我们这里还有鱼》写小姨父马沪生,《飞天》写舅舅刘长安。小姨父或舅舅,在两篇小说中命运惊人相似,几可对读。两人在小林(小说中的“我”)印象中,都是一番得体的记忆,在那个年代都算得讲究人,有能耐,都在别处不停闹腾,给人一种蒸蒸日上的虚幻。及至小林成年,对小姨父或是舅舅生活态势作仔细探寻,或于生活的交叠中有深入了解,头脑中的虚幻记忆立时解体,两人都无止境地陷入困境,于一地鸡毛中苦苦挣扎。小林分明记得舅舅刘长安以前跟自己描绘过西藏的美景,这些记忆激发了小林成年后自驾西藏。小林带着不虚此行甚至惊喜连连的感悟,重访刘长安,想与他交流也不乏感激,却于答非所问的交流中弄清了真相:刘长安长期困守西安,哪也不曾去过。相对于刘长安的困守,《我们这里还有鱼》里的马沪生一样困顿,最终难免于因病死亡。给儿子买房带来的焦虑,使马沪生慢慢地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像电影一样把自己缩小,这样就可以住进自己制作的模型豪宅或是盆景园林。
《共和路的春天》与《呼吸》虽然展示了王彩虹和苏小红不一样的苦难,却又因最后一笔大同小异的小温暖而有了关联性。《共和路的春天》里,王彩虹嫁给见义勇为却遭截肢的李大勇,嫁给英雄并不意味着要承受苦难,九年的婚姻生活里王彩虹看清这一事实,她唯一要做的事情,或曰与自己悲苦命运最坚定的抗争,只能是离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是错拿了一条羽绒裤回家,面对李大勇的怀疑,她本可以澄清,但她告诉他“这不是你的”。打算摊牌的一刻,丈夫并不在家。王彩虹在空空荡荡的家中,意外被被窝里一个热水袋温暖至热泪盈眶。苏小红面对着姐姐自杀和父亲病故,以及婚姻无望,接到父亲死讯后,孤零零的苏小红在挤进一辆公交车:“后面的人还在推挤,使得她和这个人靠得很近,她的脸几乎贴在对方的胸脯上,苏小红突然感觉到一种柔软而温暖的东西,是毛衣,和鼻腔里均匀的呼吸,它带着轻微热气,平缓地、有节奏地拂在她的脸上。苏小红抿着嘴,眼泪从眼角溢出来,她把脸紧靠在毛衣上,感受着一个人平静而均匀的呼吸,然后,轻轻闭上眼睛。”
所以,这一组篇什不免是雷同。《追风筝的人》里的杨红霞,《鸿雁》里的孟天城和何小玉,《小王庄往事》里的王彩虹,《8206》里的陈素珍,几乎都在生活的重压下难以呼吸。汤成难笔下有着真正的底层现场,有着难以负荷的沉重,每个人困厄于今天也看不见明天的亮光,所有的幽微的希望,都会遭致苦难和困顿进一步的碾轧。对比汤成难笔下耽沉于虚构,灵性而轻盈的几个小说,这连绵不绝过于沉重的苦难,阅读的某些瞬间,让我怀疑不是同一作者写就。
这一组小说里稍显异质的,应是《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毫不意外,这一篇是写一位年华老去,独自回望往昔的女人。这也是女作家常规的一种写法,她们作品序列里通常绕不开地有这么一篇,中年或到老年,回顾感情的历程,一无例外枯萎凋零,诗意和远方终成为隐约的疼。女人的老公和孩子都已进入无名状态,一个是“他”,一个是“高中生”,而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女人”。《锦瑟》的别致在于,在已无名状态的日常生活中,女人还有定期的逃逸,持续六年,去到相邻市区一家酒店,以守候之姿,其实是和自己日常拉开距离,和生活了十六年的那个家拉开距离,以便更完好地回顾,让一切历历清晰。六年前同一天,她在这个酒店相同的房间或是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也有过每年见一面的约定,但约定早已不重要,也如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约定并未履行……重要的是,女人把这经历里的对方掏空,仍有记忆中余韵徐歇的时空传承。女人需要这个余味,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每年留出一天时间游弋出自己日常的按部就班的一切。如此一说,似乎又与霍桑的《威克菲尔德》对标上了,但那绝非《锦瑟》的原本。
但在这一篇里面,我隐约读出作者对读者的担心,事无巨细,还有那么点苦口婆心。这又是何由而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沉滞?所以我仍宁愿相信,汤成难手中那支笔,须得有想象力、虚构力的烘托和抬升,否则便会一路下挫,沉重得难以握紧。
四
要谈汤成难的小说,前面对具体篇什略加评点于我不难,当手头这篇文章终至卒章,却一直煞不了尾。我不知道如何对汤成难风格差异巨大的两类小说拿捏出一个有统摄性的总结,所以又应了那陈词滥调:“这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多年以前我也是被一些评论家这么评定,或也暗自偷着乐,但仍有疑问:是我的难以归类还是你对我总结时的怠惰?当然,更俗滥于街的腔调是:这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被低估”几乎是所有写作者(肯定也存在于别的所有的行当)暗自的心结,是一种天性,谁又愿意裸露在被高估的层面,终日惴惴不安地面对一己志业?偌大一个中国,有这样自我煎熬着的写作者吗?为什么我总是看见同侪春风满面地述说着自己写作的困境?
直到一次试卷调查,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被低估吗?经过不少不痛不痒的问卷以后,这样突兀、直接的发问令我有生理性的爽快,我必须直面应对,于是我回答:我曾经也这么认为,直到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就决定不这么认为。不管真诚或狡黠,这一回答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自我审视的全过程,事实上写作者总是从头角峥嵘迅速地步入中年油腻,写作二十余年,于人于己,我确是见了不少。我也感谢这个发问压榨出我对此的回答,使得我偶尔看到一篇惊艳的小说出自陌生人之手,不至于轻易地再把“被低估”随手赠人,又成了不掏钱的伴手礼。
如果没有那次回应,那么看到陌生的汤成难拿出一篇《月光宝盒》,怕是难以禁住“被低估”的判断。事实上,我也把这篇小说推送给多位文友,甚至咨询是否有影视转换的价值。这一篇的画面感十足,情节独到,细节精准,但我也深知,时下国内的电影早已跟文学疏远,成了一种至少写作者无法判断、谏言的大IP游戏,你的质疑都会被观众义和拳般的集体失控强势回应,都会被票房统计数巨大的悬殊狠狠打脸。那么回到小说本身,它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才能倘或只是一种灵光乍现,怎么着也得看该作者更多的小说文本。毕竟,文学再也不复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浪漫时代,写作者都悄然地把天赋灵性置换为匠作精神,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而战略的心态,如同某位美国女作家所言:每天写一点,既不抱有希望,也用不着绝望。
汤成难耽沉于虚构而得来的一系列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她本人写作的特质,在虚构的领域往往有更充足的发挥和展现。两者的界限不一定清晰,比如《月光宝盒》何尝不是写了苦难,甚至其中的苦难一点也不比作者紧扣现实一类的小说稍有减损,但到最后,阿圣奇迹般戴起了齐天大圣的面具,前面一路滑翔终换来凌空高蹈的一笔。两种路数,同样的苦难叙述得来完全不同的质地,差别应在于作者对《月光宝盒》里耍猴人的生活完全陌生,只能倚赖相关的资料,这适当的陌生,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又最大程度地激活了想象力。而另一路写实的作品里,苦难全是日常的样貌和图景,似乎与作者确凿体认过的生活有关,切近的距离,直视无碍的眼光反倒限制了想象力在其中闪转腾挪。写作的想象力须基于一种忠直的品质,想象力的开启很大程度关乎素材的基质,也需要机缘巧合。汤成难对想象力的调度极为审慎,能收尽量敛紧,只在一切外因都恰到好处时,偶尔得以淋漓展现。她紧扣现实一系列作品构筑了一幅黯淡图景,而有限的偏于虚构的几个篇什,仿佛在这图景的裂隙里迸出的几缕星光。
通读汤成难的小说集《月光宝盒》里十七个小说,我竟得来一种后怕:如果当初我读汤成难女士不是从《月光宝盒》,而是从任意一篇写实的小说开始,那会得来怎样结果?事实上,我对杂志或选刊上陌生的名字葆有足够的兴趣,同时作为读者,我们都已在这阅读式微的时代普遍染罹了轻慢,或者带着试错的心情去读新人小说。如果这篇尚可,都不一定再寻同一个名字,除非有了惊艳,往后的阅读才会稍加留意。有人说当下写小说的比看小说的更多,虽不免夸张,实情似也相去不远。选刊目录里写作者的名字太多,相比之下能留下印象的小说篇什又如此稀缺。如唐诺先生所言:“我们已活在一个满街是作者,作者挡作品前头以至于快不需要作品的奇异年代,文学以及所有的创作性艺术逐渐归属于表演行业,读者买书是确认一种关系而不是为着阅读内容。”我个人是被唐诺的这一论断精确地命中,买书成了一种习惯,是被强迫症的驱使,买来百十本真正读过能有几本?尚未剥开塑料封皮便被新买的书堆叠枕压,像埋入上一个地质层。满街是作者那么作者的面目也极易于混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前面对于《月光宝盒》不惜笔墨的爬梳,正是想要展示作者“最大程度地激活”的整个过程。陌生的生活,犹如远方的一切,在作者笔下反倒具有历历清晰的既视感。作者沿着故事内里的逻辑,凭藉虚实之间的转换和调整,得以在自己笔端远走高飞,到达或者无限切近想去的地方。整体脱胎于虚构中的苦难,相对于作者笔下紧扣现实的苦难,明显多有一笔诗意的灵动,所以这样的作品,罕见地得以在一例阴沉的苦难中显现出斑斓、灵动与飘逸。
我未曾读过汤成难所有的小说,所以不知两副笔墨在她作品当中准确的比例。就这一个小说集而言,倾向虚构的部分数目甚少,仿佛是作者于现实描摹的沉滞中,偶尔挺起腰身长长地吐一口气,得来片刻闲逸。两副笔墨之间的关联,亦可于此寻踪:倾向虚构的几个小说,或是作者吸足了自己在写作紧扣现实一类小说积蓄的能量和情绪,反向发力以后偶尔得来的超拔。事实如何只有作者本人知悉,我对这个小说集的阅读,得来这样的印象也如此鲜明,甚而想起顾城那一首《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前不久与汤成难就安妮·普鲁的作品作一番对谈,她聊到一直热衷于自驾远行,仅西藏已独自去了数次,去过喜玛拉雅山。这似乎又成为我对她作品的印证和脚注,我不难理解远行对于她的想象力,对于她灵魂轻盈的一面的释放和抬升,但回到现实以后那难以排遣的沉重感,仿佛又是远行结束时的副作用。她的两副笔墨,在虚构与写实之间往复跳宕,风格反差极大。读了十几个篇什,我不惮于揣测,对于汤成难总体的写作,未必是“难以归类”,她两副笔墨的抒写未能产生某种合力,甚至,这些作品进入他者“高估”或“低估”判断之前,已然在自相扞格中彼此覆盖,自行掩蔽。
当然,写作多年,我绝不至于对另一个写作者,甚至是同龄的写作者作建议,“应该怎么写又不要怎么写”。这么建议于他人没有任何作用,只暴露自己无知且衰老。写作者各异,自带了配比稳定的洞见与愚氓,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扬长避短并更清晰地呈现独有的面容。幸好写小说未必是汤成难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她擅长绘画,热衷远行,一次一次去往离云很近甚至触手可及的地方。时至今日我已不会对几位作家整体的写作抱有阅读希望,在我看来,除非研究者,读到某作家一篇或几篇好作品,就去买该作家全集是最愚不可及的事。汤成难女士作品系列里有限的几篇,毕竟给我坚韧的期待,我会一路追踪这个有如被哑光漆打磨的名字,我相信这个名字蕴蓄的势能,总会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凌空高蹈,随手捧出一个乍现的奇迹。

上海文化
Shanghai Culture New Criticism
2021年 拾壹月号
方法与文本
程德培 对视、对话以及热衷于拆解的对峙——读李宏伟小说笔录
习 蓝 在追索中重新诞生——为《抚顺故事集》而作
王朝军 “泥塑”之道兼及聂尔散文断想
陈仲义 唐捐:身体里的“魔怪”
当代人
童 欣 从“弱者认同”到“修补父亲”——读汤成难中短篇小说
视野
柳宗悦 张逸雯 译 朝鲜的美术
跨界叙事
康 赫《小兵》,一位导演的身份证明
阅读札记
申霞艳 从“读什么”到“怎么读”——纳博科夫的脊椎骨阅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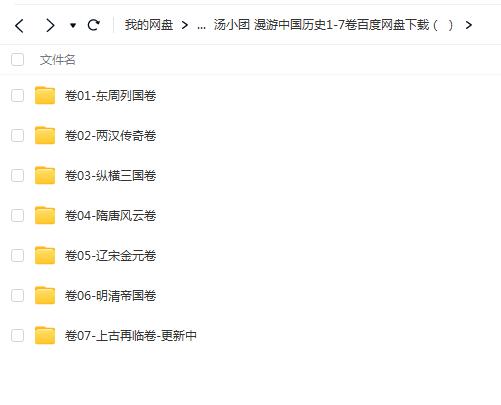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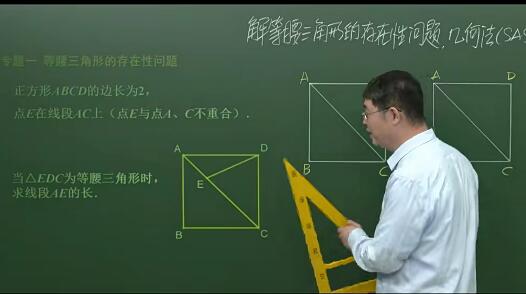







![[小程序] 9小时搞定微信小程序开发 微信小程序从入门到实战视频课程 高磊主讲](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570b1b552a766843b416fb28f2752248.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田佩淮】高中地理必修一、二(视频+讲义+习题)[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505ml3/60-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小程序] 9小时搞定微信小程序开发 微信小程序从入门到实战视频课程 高磊主讲 共91课](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5cb6f36e2f97b5067b9c315e510137a7.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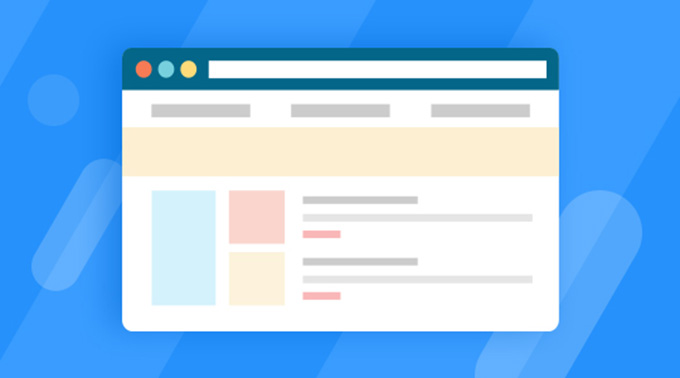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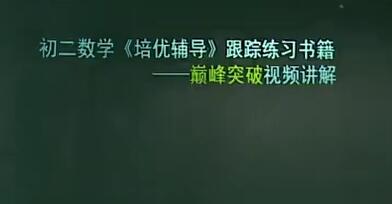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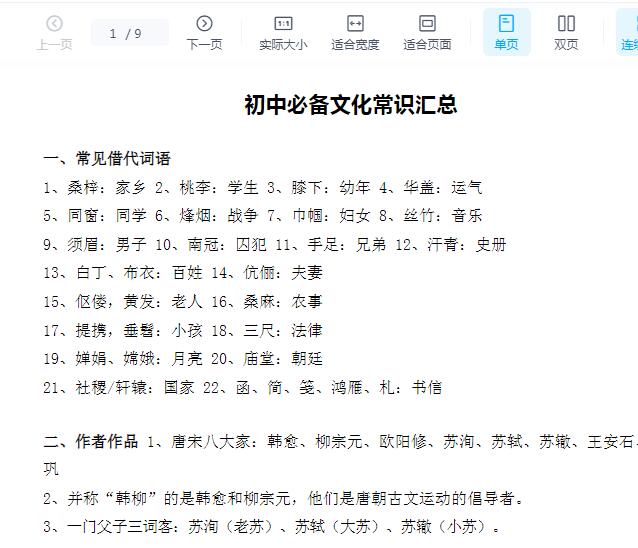
![[HTML5] Mugeda零代码HTML5动画教程全辑第一二三期合计视频 半天开发24小时收获1300万PV的项目](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ba2c0d8f9f28f0e81213ce063dc3801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付炫屿】10小时突破高考单词[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25ml/178-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