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标题下『中原作家群』,快速
号:zyzjqwx
河南省青少年作家协会
基于民族想象的疾病隐喻
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论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影响了大半个世界且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独特观点,他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称谓并非“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在安德森看来,“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1)。既然“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肇始于文字,而其发展及嬗变的历程,也必然离不开文字的功能。文学文本作为文字中最典型而且最易于传播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映现着民族的衍生、发展、衰颓乃至消亡,另一方面也对其兴衰荣辱起着不可忽视的传播功能及促进意义。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易卜生之于挪威、安徒生之于丹麦、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乔伊斯之于爱尔兰,均发挥着构筑其民族形象的重要作用。而国门之外的文学受众,也大多是通过鲁迅、林语堂、老舍、巴金、高行健、莫言等诸位文学名家的典型文本,来通过“想象”建构他们心目中的华夏民族形象。
著名作家墨白以一以贯之的先锋姿态,致力于对民族根性、人性弱点的挖掘与呈现,其小说既能对民族特质中善的一面如勤劳、善良、坚韧、隐忍等加以提炼与描述,更能对其恶的一面如贪婪、狡诈、嫉妒、善变等加以呈现与笞挞。对于人性之恶乃至社会之疾,墨白常常通过疾病的隐喻加以传达及批判,以此来映现并参与想象构造自身民族的特质,这一点,与中外诸多文学巨匠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加缪、乔伊斯、福克纳、鲁迅等薪火相传、一脉相承。“能指”与“所指”是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学术的精髓所在。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概念和声音形象的有机结合。然而,在日常生活使用中,语言符号这个术语一般只指声音形象,从而让部分要素包含了符号整体。索绪尔以“能指”与“所指”将二者区分开来,“能指”代表着语言符号最终指向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是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在墨白的诸多小说中,疾病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元素,甚至很多小说标题直接跟疾病相关,如《精神病患者》《梦游症患者》《霍乱》《狂犬》《夜游症患者》《哑巴》等。还有一些则与疾病的从业者或者疾病的“衍生物”死亡相关,如《局部麻醉》《流行死亡》《内科大夫》《洗产包的老人》《谋杀案》《葬礼》《埋葬》《受害者》《蒙难记》《某种自杀的方法》《白色病房》等。在如此众多与疾病相关的长篇、中篇或者短篇小说中,罹患疾病的人物更是随处可寻,数不胜数。仅以其中篇小说《光荣院》而言,其中的患病者或者另一形式的疾病——肢体残缺者,以及疾病所导致的最终结局死亡者就多达十余位,几乎涵盖了这篇小说所有的出场人物。光荣院的“英雄人物”各有病残:老金腿上受伤、老钱残臂,老天兴则死于打牌时因兴奋而致的脑出血;炊事员月红患有“气蛋”即子宫脱垂症;虾米的养父九生患了伤寒而亡;而小说的主线人物虾米则兼具先天疾病与后天伤残乃至精神疾病于一身,他出生之时“皮肤虾红头发雪白”,从医学角度推断,当与白化病等症有关,后来他还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遭遇过左手骨折,患有眼疾和精神性疾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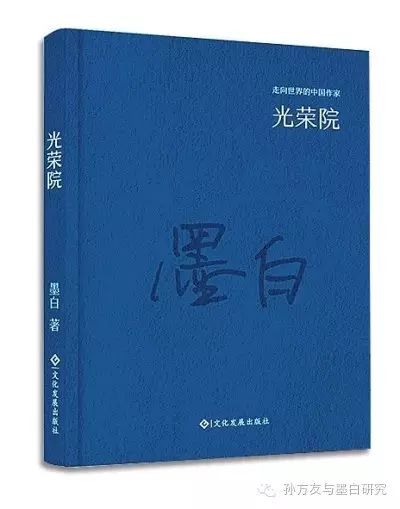
一般来说,疾病的“能指”含义丰富,延伸甚广。从生理意义而言,它是指生命个体生理机能的失调或者生理器官的缺失,需要依靠身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以及药物、外力如手术、针灸等的干预力量方有可能痊愈。与之同时,在社会学意义上,疾病还常常被当做不正常状态、不合理现象的代名词,如道德丧失、风气败坏、贪污腐化等,均能以病代称。而在文学内涵上,疾病在涵盖上述两者之外,还常常成为人性弱点、人格缺失、精神孱弱、民族劣根、历史混沌及遗忘等诸多复合元素的最佳载体。鲁迅的小说《药》以华家的痨病与夏家的革命被杀,暗示着“华夏”的现状及命运。墨白的诸多小说则延续了这一血脉,他将躯体层面上的不适与缺失、社会意义上的不良现象以及人性、民族、历史、政治上的伪劣属性统而概之,归结于疾病隐喻,中篇小说《光荣院》即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层建筑方面一直在提倡“男女平等”。从表面来看,男女关系也是平等的,男女共同参加革命,共同追求进步,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共同担负国家民族独立自主之重任。在墨白绝大多数的作品里,参加“革命工作”的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共同承担拯救国民推进发展的神圣使命。小说《光荣院》中,绝大部分的故事即是发生于这一阶段,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如炊事员月红以及那个死于盐业公司突发事故的女孩叶,均是从家庭走向“革命工作”的典型。事实上,这表面的男女平等之下掩饰的恰恰正是女性意识的缺失,这一特征恰恰是通过文学作品等文字载体媒介,参与民族形象发展历程的想象架构。学者王宇如是评说:“在50-70年代的意识形态运作中,妇女的走出家门、‘取消家庭’实际上更多的并不是在性别解放的意义上,而是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大面积渗透的用意上被提倡。在‘解放’名目下的妇女的政治化实际上是实施这种渗透的有效途径。”(2)从这种意义而言,男女平等关系仅仅是表层现象,在这表象之下,仍然深藏着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其中,女性意识的缺失是这种不平等关系最显著的表现。在《光荣院》中,女性的受歧视、受压榨尤其是女性意识的缺失,恰恰是通过对于疾病以及疾病的“衍生物”死亡的言说来具体演绎的。
在小说中,月红作为光荣院的炊事员,负责食物的制作及分配,除这一工作身份之外,她还兼具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妇科病患者、院长的亲属、一群男同事的揶揄对象等诸多社会角色。月红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符号,主要体现在她一嘟噜生下来七个孩子,以及诸多男性开玩笑时的性别投射上。作为一个受压迫受侮辱的底层女性,月红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榨与剥削,伤痛与酸楚,与之同时,她还身兼受害者与施害者于一身,对于更为弱势的人譬如虾米,作为院长二姨的她在给予女性的温情之时,也不乏取笑与欺凌,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作为一名“工作女性”,月红自身的性别意识丝毫无存,非常自觉地摒弃了自身的性别属性,并对这样的状态浑然不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说享受着这种混同男性而又轻贱于男性的待遇。按照正规医学的表述,月红所患的疾病为“子宫脱垂”,是非常典型的妇科疾病,性别属性极其分明,却被众人以另一个男性独有的疾病“气蛋”来命名。从表面来看,这是当时底层民众知识匮乏的表现,底层民众无力并不屑于了解“子宫脱垂”的具体病情、前因后果;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从国家机器上层到广大底层民众,乃至女性自身,对女性身份、女性权利、女性意识的无视、轻视,乃至蔑视。其中的一个细节可以作为明证,医生已经纠正过大家,月红的病变部位为子宫,而其“气蛋”的命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如此的社会境况中,女性意识的缺失绝非仅限于一个“月红”,而是整整一个民族时代的属性。如果说月红尚能以放弃性别身份的姿态谈笑自若的话,小说《光荣院》的另一女性叶,则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仅仅是一个从属于男性从属于时代的“失语者”。
叶的出场是因为一场灾难。她的未婚夫在建造库房之时从房顶上掉下来,摔破头颅而死,叶才因此得以从乡下进城,“幸运”地成为了一名盐业公司的工人。此后不久,她也在一场盐垛倒塌的事故中死于非命。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当叶的尸体不翼而飞之后,却被人们甚至叶的父母认为,是她的未婚夫的亡魂背走了她的尸体,“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可以说,从出场到终场,叶不过是那个男人的从属——或者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她即便不是这个男人的从属,也必是另一个男人的从属。然而,叶的悲剧并未因为身体的死亡就此结束,她的神秘失踪,则再次成为了男人的玩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孱弱男性压抑性欲、变态欲望的投射对象。叶的尸体被性压抑、性幻想症患者虾米偷走并埋葬在他所睡位置的地下,如此一来,虾米便可以像《红楼梦》中的贾瑞意淫王熙凤那般,每天在睡梦中与自己的梦中情人颠鸾倒凤……在这里,叶作为一个形象姣好的新社会青年女性,尽管生活在现代化的场所“公司”之中,却从未享受到现代生活所应给予她们的女性待遇,在其女性意识本应苏醒之际,一场不期而遇的灾祸轰然而至,她不得不因疾病的“衍生物”死亡而成为一个“失语者”。这一遭遇可以说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历程不谋而合,女性意识刚刚萌芽之际,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如“大跃进”、反右派、“文革”等便接踵而至,女性失语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或许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所说:“如果说,女人在男人间的移置方式始终是人类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叙述艺术的基本命题,那么,一个基于男权立场上的、关于女性命运的陈述,便成了叙述作品中社会象征与政治潜意识交互渗透的有力而微妙的方式。”(3)“政治无意识”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是有政治性的,文本的寓意并非停留在作品的表面,而是栖身于“政治无意识”之中,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文化文本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4)这种“政治无意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5)其政治意识的核心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指向则是国家政权。这一理论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形成了极好的辉映。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墨白的诸多小说中,政治形态作为一种背景,作为一种场域恰恰是“政治无意识”的一种存在与体现,映衬并构筑着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墨白的诸多小说文本中,其对于政治、民族的关心、以及自我表达,常常与疾病这一隐喻捆绑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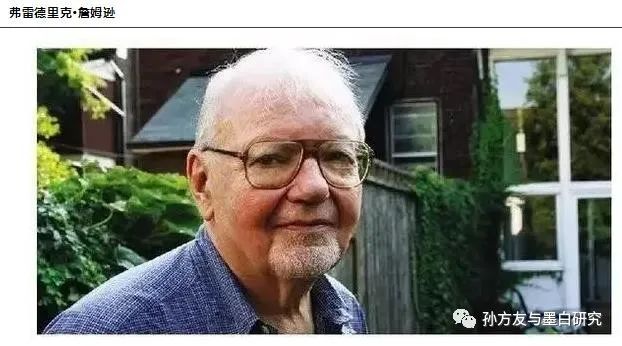
在小说《光荣院》中,其标题本身就是政治与疾病隐喻的极佳结合,所谓光荣院,即是为供奉那些因战争而导致伤残的军人的处所。与之同时,小说中最为主要的两个人物虾米和老金也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民族政治与疾病隐喻的双重意义。虾米和老金作为不同类型的病患载体,具有极其鲜明的对照意义,同时又共同指向了人性弱点与民族根性的政治实质所在。在性格上,虾米软弱,老金刚硬;在体质上,虾米先天不足,后天残缺,老金虽有战伤,但仍不失勇猛;两人在疾病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隐喻内涵上,也互为补充,大有差异。虾米出生时就有病态之貌,被人视为怪胎以及不祥之兆,从而被亲生父母抛弃,后天则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因盐业公司的事故而导致下肢残缺。细读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虾米是一个农耕文明即将消亡之际愚昧、孱弱、病态的底层小人物的一个代表,他承载了古老而又苦难深重的民族躯体上的疾患,同时更被赋予了精神残缺、欲望压抑、自轻自贱、自暴自弃等精神层面上的不足与残缺,最终,虾米还死在了自己愚昧固守的精神痼疾上。这与我们的民族根性中恶或者说劣的一面旗鼓相当,严丝合缝。工业文明的突然袭击,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孱弱的底层民众带来了便利与好处,同时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情感冲击与无情打击。盐业公司的坍塌事故,即是一个与伤残、死亡以及民族经历紧密相连的巧妙隐喻。
与虾米迥异的是,老金是底层民众中走出来的一个“革命者”,他依靠在战争中的勇猛表现、战争留下的“光荣伤疤”以及伤疤所带来的勋章,常常自以为是,自我炫耀,倚老卖老,欺凌弱小,甚至因为蝇头小利以及微不足道的权力,主动放弃原则,为丑恶行为开脱并成为其帮凶。小说中,老金与医生在杀人与勋章的问题上,有着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辩(这一段辩论可与卡尔维诺描写战争的小说《良心》相媲美),老金得出的结论则是:“不为连长打仗哪里来的勋章?……要是没有勋章,哪儿来的这光荣院?没有这光荣院,你会来这里享清福?”从此可见,老金自身对革命、对战争并没有清晰理性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成了一个听从号令的战争机器,而革命的崇高价值与意义也因此消解。如此来说,老金的疾病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与认知功能,以及自身对于权力的奴性上。与此相关,老钱、医生,以及小商贩对于勋章的质疑、嘲讽、轻贱的言行,亦是广大民众对于民族历史认识莫衷一是、似是而非的如实映现。以病为喻是墨白小说的拿手好戏,同时也是他剖解人性、解构政治、“想象”民族的绝佳利器,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疾病常常被用作比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疾病隐喻“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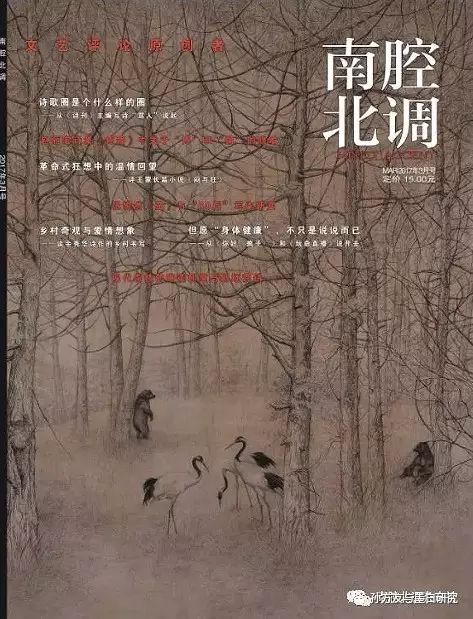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彭永强,1982年生于河南淮阳,文学硕士,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从事当代文学研究。陆续于《读者》《青年文摘》《格言》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近200万字,多次获奖,有作品入选中小学生教材、教辅读物。有散文集《马桶上的思想者》《冰淇淋的眼泪》等。
中原作家群
中原文坛自媒体第一品牌

亲,愿我们一起坚守文坛这方净土
青书坊文化
长按上图可以我哦
投稿邮箱:zyzuojia@sina.cn
中原作家,引领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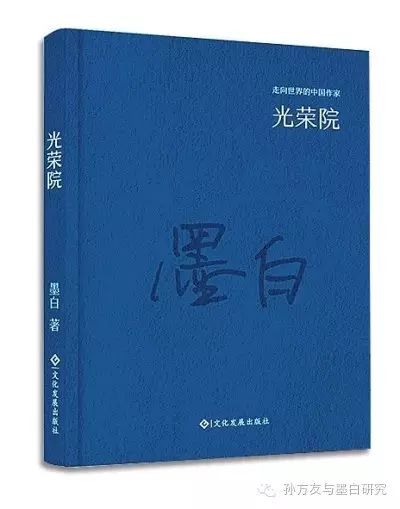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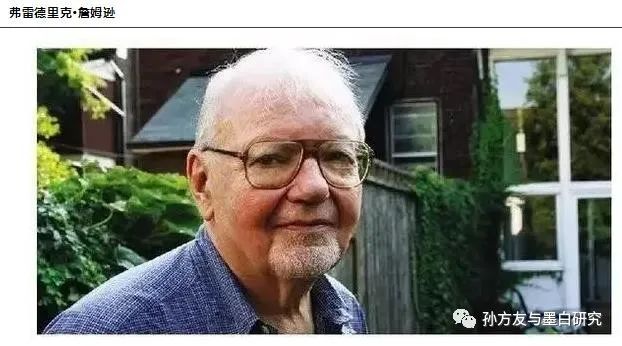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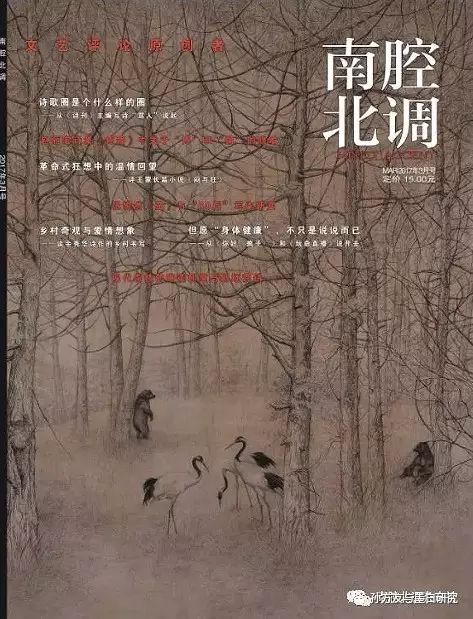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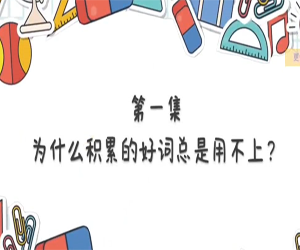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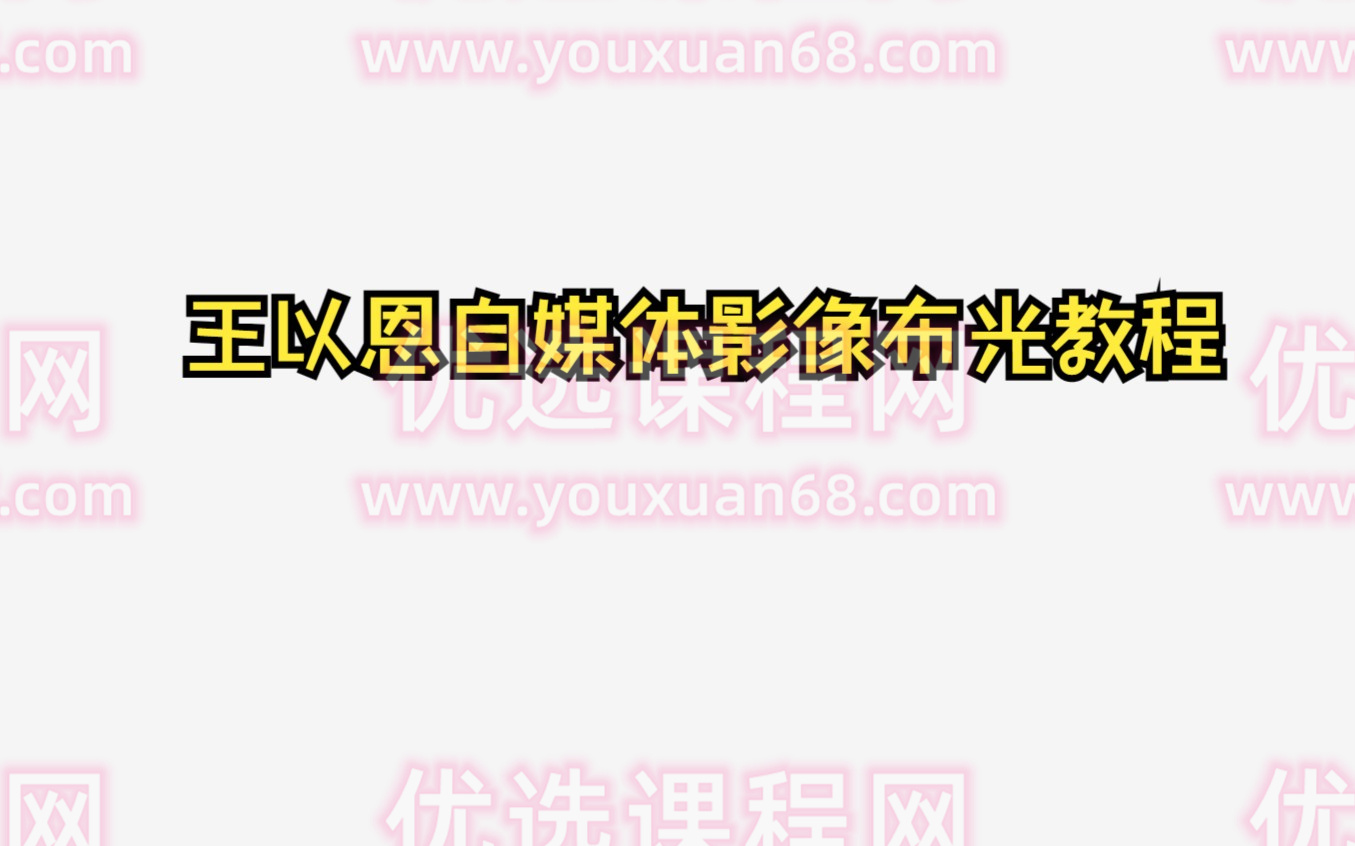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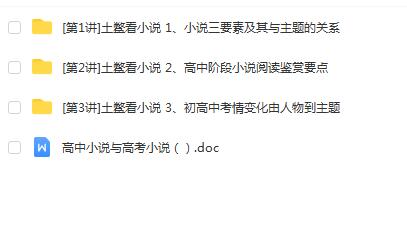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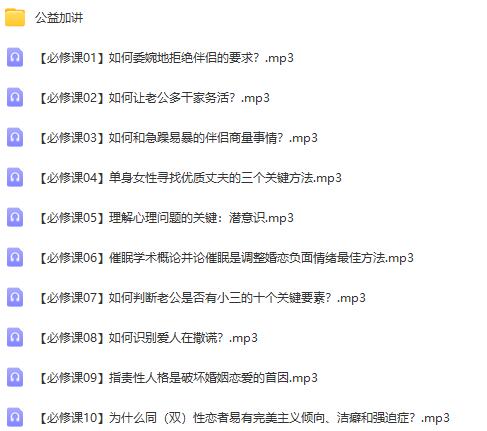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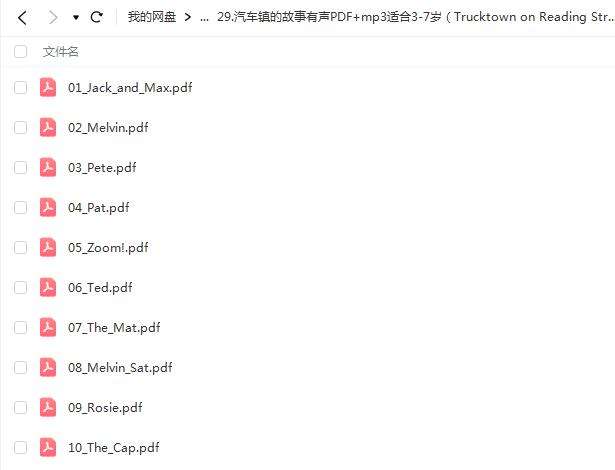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