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塔|每日一书】标准与尺度:读朱自清对时代问题的典型回应
发布于 2021-11-23 16:24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他出身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继承父辈的家学渊源,渐渐养成“整饬而温和、庄重而矜持”的文人气质。他是一身正义的民主战士,一生刚正,爱憎分明,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他是至情至性,孤高而又朴素的教书先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经典篇章,“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中来,腆厚从平淡中来。”
主要作品有诗歌散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文艺论著《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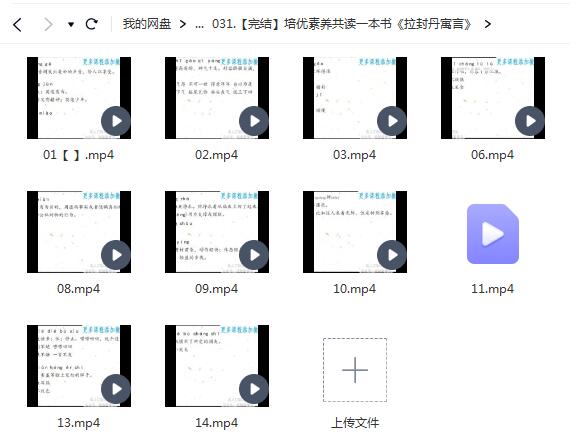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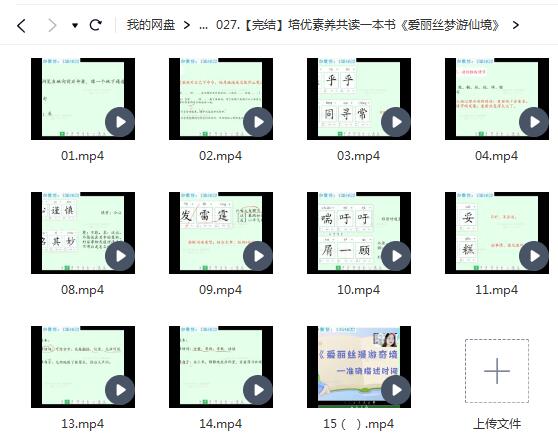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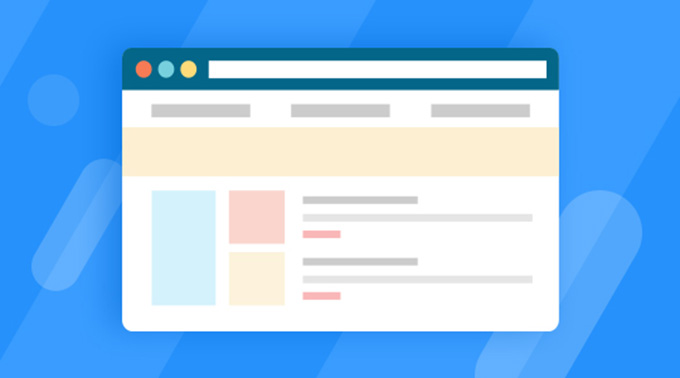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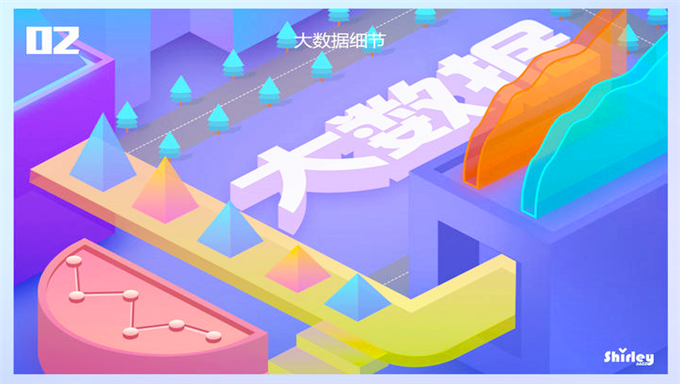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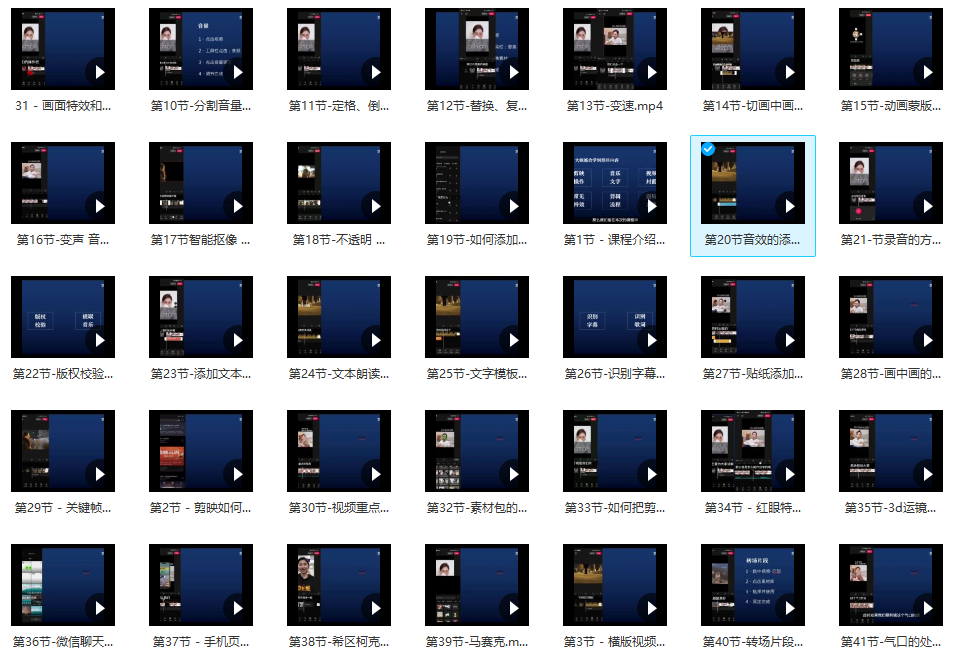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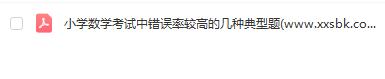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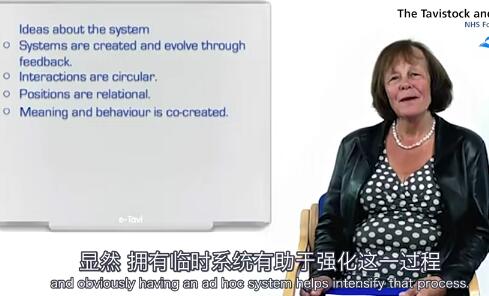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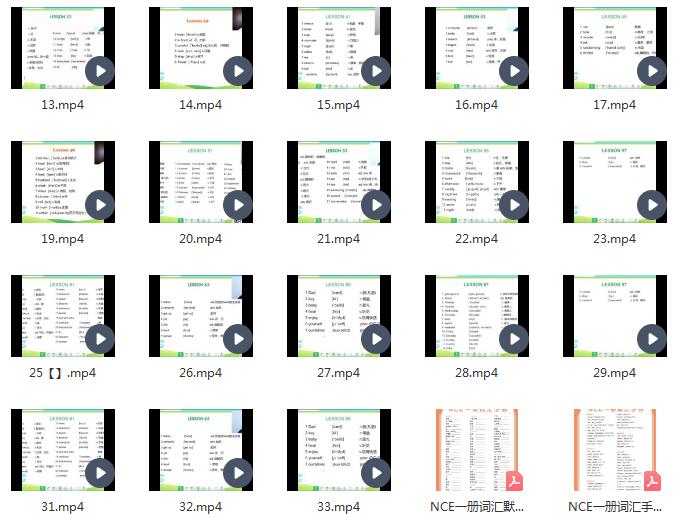

![[php基础] 解决PHP中的Bug,搞定PHP的错误体系的各种问题](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fd5a6305469616cdc05c47fa0e881d00.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