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2205年~前2255年间。传说古代有个叫瞽叟的人,欲谋害舜。于是舜在危机情况下,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粮仓上跳下逃生。这是我国史书最早关于应用降落减速原理的说法。人类关于飞行的梦想由来已久,摆脱地心引力,享受翱翔之美是全人类的永恒梦想。
杨亚贵,笔名:闻天籁。籍蓝田汤峪,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蓝田创作基地委员,蓝田县作协会员,西安市于右任书法学会会员。

《水经注》中记载:"水出杜县白鹿原,其水西北流,渭之荆溪。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东有苦谷,二水合而东北流,径风凉原西。《关中图》曰:丽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风凉原,在磈山之阴,雍州之福地。即是原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风凉原也是历史悠久。据说风凉原地处库峪,汤峪两谷出口处,冷风常沿谷而出,夏季亦凉风息息,故名风凉原。又因风凉原中心距长安区引镇,鸣犊,魏寨三地均八里,又名曰八里原。如今,蓝田县规划在八里原这里修建机场和通航小镇,一个关于飞行的梦在这里开始重新起航,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端感受一个《向往飞翔》故事。
人是陆生动物,凭借自己出类拔萃的智商,一统江湖,以至于走兽臣服,衍生出猪狗牛羊这些训养牲畜;以至于飞禽俯首,变异有鸡鸭鹅之类枉生翅膀,失却飞翔功能的家禽。人在孕育于母体时,就在母体的羊水内自在游弋,但毕竟不是水生物种,所以村南头的青田爷才会在人们苦于淅浙沥沥,似乎永无终止的秋霖时,摸着雪白的胡子总结说:人是旱虫。人,作为高级动物的旱虫,其实并不心甘情愿地仅仅当陆上生物,企羡水生动物的悠游,一些人,学会了游泳,但终究是蹩脚的游者。我与我的同伴,少年时,无数次地于水塘水库及库峪河畅游,宿命里,都是冒牌的游鱼。也曾经无数次地企羡空中的各种飞物,从苍穹里的鹰鹞,到檐下的麻雀,幻想着有朝一日,腋生双翅,翱翔长天。据说,儿童心智尚且稚嫩,魂魄尚且虚弱,就如牛痘研制出来之前,说不定哪一刻,死神一个不开心,便派遣无常上门,撒痘成秧,带上神魂还缺乏稳健,气虚力弱的人上路了。但心智未开,魂魄不健的儿童,也可能最适宜幻想,也适宜作梦。我儿童时期的飞行梦,就是从我们皇甫川柿园村,仰望八里原制高点飞过的飞机作起的。八里原的空宇,恰恰是西安与武汉民航班机的航线,当隆隆的滚雷之声由远及近,从村庄仰望原垴,飞机恰巧飞过古堡遗址上方,银白的机身衬映着苍穹,一线儿掠过去,不知天上比地上的温度如何,但听那声音,炎炎夏日的轰鸣声,似乎夹杂有热汗淋漓之下急促的喘息,数九寒天,又似是夹杂着难耐寒流,排气不畅的颤慄,这都是令人担忧的状况啊!一直目送飞机离开视线,方才可以放心。傍晚,银白的机翼披上晚霞,想那机内人员的脸膛,定当沐浴着霞光,满满荡漾着优裕的幸福,而飞机的飞行姿势,也似乎更其优雅。无月的夜空,飞机一路闪烁着首尾和机翼的红灯,更给祖母再三催促下,迟迟不肯进屋去睡的儿童无穷无尽的想象,并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行员。去高高的古堡练习飞行,爬坡爬坡,再爬坡,左腿紧忙间,一阵一阵麻木,一阵一阵沉重,总使不上劲儿,这是怎么啦?急得人气息沉重,额上显然滚落了汗珠,一颗浸入眼睛,又蛰又辣,必须强忍着,终于爬上了八里原畔横亘阻绝的古堡堡墙,俯视川道,房舍安晏,炊烟在桑榆间袅袅,先闭上眼沉静心神,想,下一刻,鹰鹞一样搧动变作翅膀的双臂,优雅地降落在阔大平坦的碾麦场时,轰动效应定当空前又绝后,自此以后,即使仍然时常算错两位数的加减法,也丝毫不会减弱同学们的钦敬。身生双翼,自在飞翔,除过我,还有谁?
徐徐地憋满一腔子气息,上身前倾,深度屈膝,一跃而起,腾空了,以极限速度挥舞双臂。气流呼喇喇撕扯着衣服,割剐着皮肤,身体浊浊跌落,呯地一声,脊背朝上,胸腹紧贴尘埃。但眼睛绝对不要睁开,心神决然要沉着冷静,一旦睁开眼晴,断胳膊断腿,跌落就成了铁定的事实,就这样趴着,捱过将近一两节课长短的时间,定能活蹦乱跳,上树逮鸟下河摸鱼。终究还是让祖母摇醒了:我的宝贝,作啥恶梦了?这一年冬天,例行冬季征兵,不同于往年的是,这次征的是航空兵,我们村一位姓刘的青年体检合格。这人了不起,命运好,身体棒,晚上睡觉肯定不出汗不作梦。学校放学,我和几位同伴,邀请与刘姓青年一个小队的同学引领,欣然上门,去一睹准飞行员的风采。刘家院子井沿,准飞行员屁股坐着大石头,手端粗瓷大老碗,呼噜呼噜喝老白包谷熬制的包谷粥,脚边的小菜碟,盛有萝卜缨子淹成的浆水菜。食物与他人无异,但人果然英俊,眼大眉浓鼻直口方肤色白,喝完包谷粥站起时,身材匀称而挺拔。心中有数啦,原来,长这个模样,才有可能成为飞行员啊。既然有了标准楷模,以后,眼耳鼻口的头,生有四肢的身子,必须尽最大可能向这个模样生长。尽管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曾听过相由心生的说法。万分可惜的是,姓刘的准飞行员,最后也没能穿上空军威武雄壮的军装,因为,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被划归四类分子之列,几乎天天接受批斗,四类分子的儿子,自是无缘入伍飞天的。
这个冬天,我有缘等到了一个好机运,某个黎明,母亲拍着祖母的木格窗棂,喊我赶快穿衣起来,说是要带我去看飞机。星斗满天,周身寒彻,一行人爬上村后的土坡,沿着八里原畔的小路行进,右侧,川道及八里原对面的一个个村落,都有灯火闪烁,一处灯火绵密的地方,听说就是繁华的引镇所在,终南山背坡的一个壑口,灯火通明,大人们指点说,那里是日夜不歇,正在紧锣密鼓修建的大峪水库工地。我从未俯视过皇甫川的夜景,上有星汉灿烂,下有万家灯火。这时候,一鸡唱晓,百鸡争鸣。我的川,我的原,竟然是如此的神奇和美好。看飞机的地点,是八里原以东汤峪川一个叫石佛街的村庄。若大的场地,是两个或者三个打麦场合成,周边竖起的木杆,围绑了一圈儿龙须草搓拧的草绳,数之不清仍还源源而来的瞧新鲜的人们,都被隔离于绳子以外,两驾军绿色的直升飞机拉开间距停在正中,几位身着军装的人,不疾不徐的在机身内外工作,好久好久,终于一驾飞机转动起了螺旋浆,终是没有起飞,直到日色过午,吃完兜里的干馍,仍旧饥肠辘辘的我们踏上归程。我至今也不知道,多年前的两驾直升机在石佛街停驻和检修的原因。第二年,一个周未的中午,同两位伙伴相约,去村后上原的坡旁的柏树碥玩儿。二月半之后的太阳,剥离掉人们身上的棉衣,风儿悠悠抚慰冻馁的地表和树木,一口口呵着温暖的气息,于是一川的麦子褪却稚气,一晚一挺身地窜高。杨柳质弱,但杨柳以异于别的树种敏锐的感知,枝叶款摆,飞燕也好,土雀也罢,但愿穿飞其间,都能得到温情无限的爱抚,柳丝儿正在一梳梳理顺它们的羽毛哩。榆钱满树,槐花的孕育行将完成,它时刻准备着与榆钱接力,救赎人们蔫瘪的肚腹。村庄静谧,瓦舍安闲,生产小队的耕牛,一头头松弛着皮缰,安闲地卧在八里原二崖子平坦的牛场,一牛一桩,似乎即将形成恒久的画面,千年不变。几位老饲养员从后边用作饲养室的窑洞里,一车车推出牛粪,牛粪堆积如山,又一车车铲满晒干拍面的黄土,推进窑洞。牛场窑洞,就处于柏树碥旁边,辨得清一张一合反刍草料的牛嘴,甚至辨得清牛圆睁的眼睛,几头完成反刍的牛,则闭上总是善意满盈的眼睛,一心一意享用春日。
这一坡柏树,植株尽都一丛丛团缩,以血脉绵密浓稠,抗衡生命里持续无涯的干渴。冠盖高不及丈,阔仅数尺,也许,树龄已是三百,也许八百千年,谁知道呢,估计白胡子的青田爷也说不清楚。柏树碥极其陡峭,我们爬上名叫高岭的顶端,又一声呼喊:冲啊!飞身由柏丛的间隙奔向碥底,比赛谁冲得最快,最快的,就能多抓几名鬼子兵。如此上上下下几个往复,胃囊里,早餐吃的包谷粥,便消化怠尽了。距离午饭时间尚早,玩耍的兴致尚还浓厚。一个说,咱玩开飞机吧。站在上位,扑上一株团状柏树顶端,双手平伸,作了机翼,双腿并拢抻直,是飞机的机尾。一人示范,余者扈从,身体极力摇动,机翼时而左高右低,时而右高左低,三副儿童的喉舌,模拟着飞机的轰鸣声,三团柏丛,荣幸地充作了肉体飞机的托举物。飞机不仅是左右盘旋,不仅是水平航行,还要仰升和俯冲,上升时高扬头颅,将重心后抻,机尾下沉,俯冲时,重心前移,姿态相反。综合考量,俯冲的难度系数最大。正因如此,差点儿断送掉我这条小命。起始俯冲,倒也平衡得宜,不成想一阵摇晃,头重脚轻,急忙收回双臂,两手攥紧柏枝紧急呼救。另外两架飞机及其兼任的驾驶员无动于衷,扭头轻描淡写地说:装,装吧!真的,我要倒穿下去,坚持不住了,救我!快!快!快!任凭百般呼叫,并不出手营救。力竭的虚脱,死亡的恐怖,都变作重量,把一颗头压得更低。灵魂行将出窍,鲜血将溅当场……我绝望地闭上双眼,最终流星一坠,完成了飞机的俯冲,至于姿态是否优雅,是否完美,全然顾不得了。能夠确定的是,先着地的不是头颅,一声钝响,我从柏树的间隙翻滚下去,速速越来越快,来不及心里边与亲人们一声道别,生命就要终结,穷凶极恶的死神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一块鲜美的嫩肉。断崖边那株柏树,注定是我前世修来的菩提,不偏不倚,堪堪挡住滚落的生命。同伴飞奔而来,一脸的惊魂未定。我只觉得一只重棰,急速而猛烈地一棰一棰擂击着我的心脏,许久许久,手握木棰的死神方才撇掉木棰,失望地打转身子离去。我坐起来,从头到脚,倒还浑全,只落得灰头土脸。扭头看那牛场的三十来头黄牛,一头头浑然不觉地卧着身子,仍旧倒刍和闲目养神———天下太平。
我的飞翔练习,在这一次精彩纷呈的演示之后,彻底终结。命运弄人,前些时,我见到了昔日的刘姓准飞行员,他已是驼背曲腰,白发稀疏的老头了。我没有问过他,平日会不会回想与飞行员身份失之交臂的过往,不知道他上小学的孙子有没有飞行的梦想。有的人和事,不经意间的偶遇,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前几天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一篇旧消息,叙述一个发生于十七年前更为惊险的飞行传奇。十三岁的昆明少年李攀龙,离家出走,与一位名叫束清的少年相遇,气味相投,意气相期,哥儿俩从昆明国际机场的围栏溜进去,再顺着飞机轮子爬进起落仓玩耍,竞然没被发现,恰巧飞机起飞,升高过程中,束清坠亡。穿云破雾,万米长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李攀龙奇迹般地降落重庆机场,捡回一条小命。相信李攀龙仅仅是玩新奇,并没有成心作一次飞翔梦,好在身手敏捷体质强壮,胆子也足夠大,运气足夠好,否则只会是釀成悲剧而非创造传奇了。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飞机是条龙,这个少年御风攀龙,一飞冲天。读罢,一边为束清痛惜,一边说李攀龙:这小子,比我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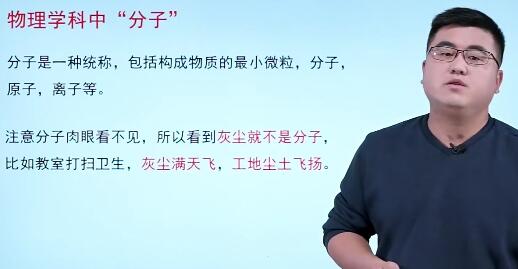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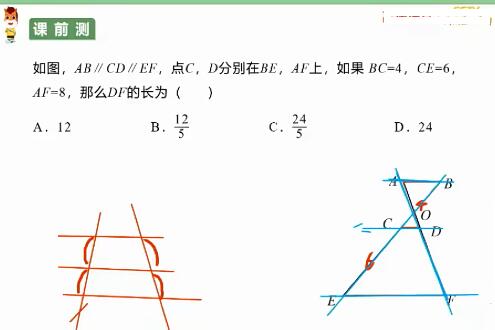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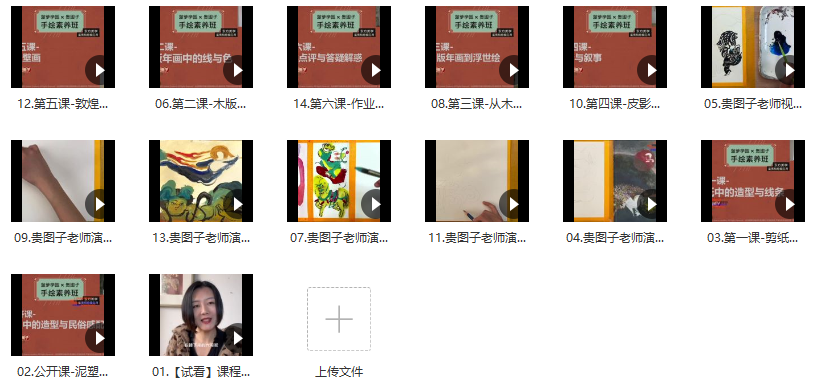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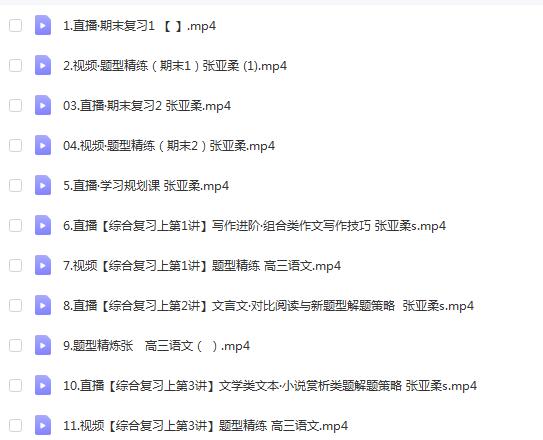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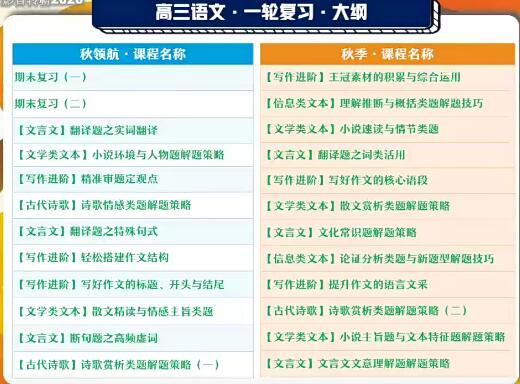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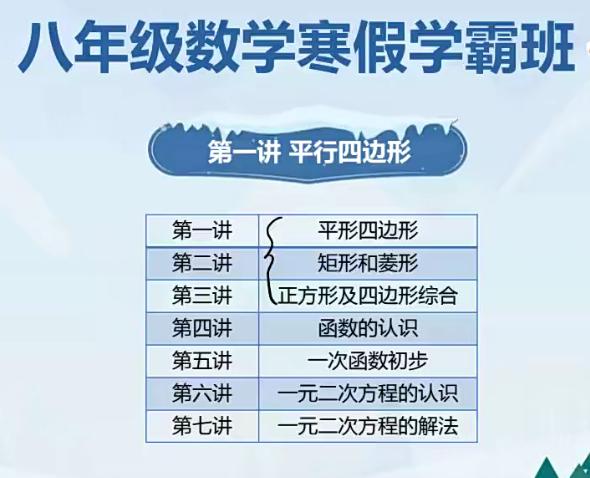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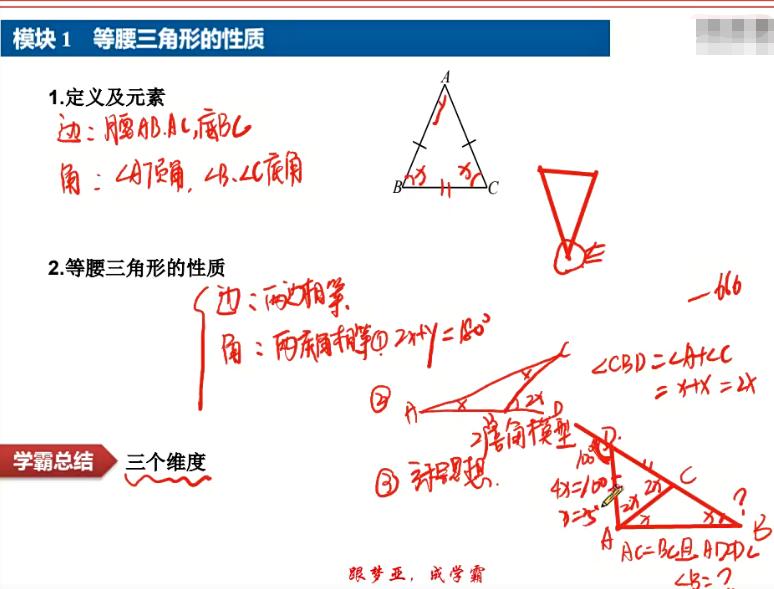



![【崔亚飞】2022届高考地理A班 暑假班 秋季班[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505ml3/38-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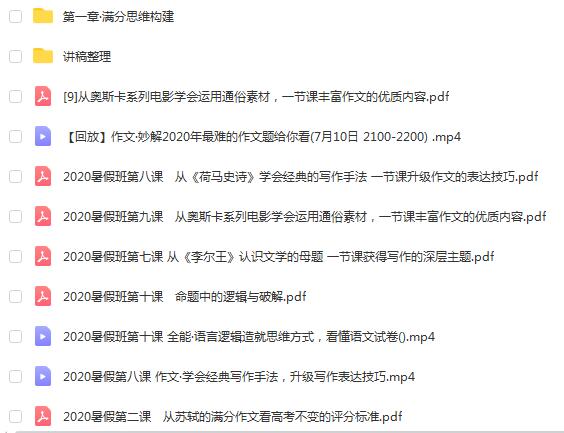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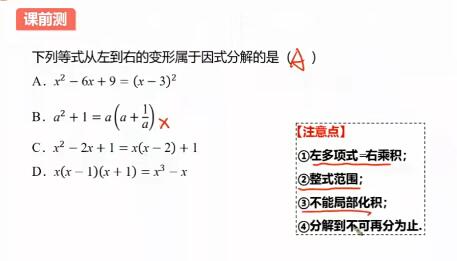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