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意清凉 | 丰灵散文四篇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05 18:26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丰 灵
本名侯晓萍,湖北省公安县人。在《长江文艺》《山东文学》《中外文艺》《短篇小说》《国家湿地》《作家林》《工人日报》《特别文摘》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数十篇;作品在全国散文大赛中多次获奖。
独 荷
独木不成林,我却异想天开拥有一角藕园。其实哪能称之为园呢?小到仅只一缸,内植种藕一截,间有小荷出水三五片。之所以戏称为园,不过终岁寂寥,藉此存些奢望。待他日风过帘动,兴许享用得一缕荷香。
这一枝独荷,远自乡下老屋后的池塘移来。四月,恰逢春旱连连,池塘干涸,滴水不见。塘底泥土皲裂,枯荷残梗遍及。其间有新叶钻出,大如手掌小若苔钱,也有卷叶相对者,怯怯的,小家碧玉得让人心疼。于是,拾路边柴棒,掀土取藕,连带那两三片绿叶,附裹了一身黑泥,双手擎举着回了家。路上还小心谨慎,怕无意中折断了枝叶。
阳台狭小,当西晒。娇气些的植株,在这里总难存活。兼之懒动,终于只余几盆无需费心的植物。也就棕竹一蓬,人称孤挺的朱顶红若干。得喜楼上人家空调水日日滴漏,还润泽了一株葡萄,以及架下那丛馥郁清香的金银花。
取了缸来,热烈地将种藕植入,蓄满水,再填足底泥。每日营营役役地过,得空就去看荷。不时往缸内续些水。两日后,有卷叶现,弱弱地不经风。真个是:田田“三两”叶,散点绿池初。大喜,狂奔入室相告。家人哂然:从今往后,就等着荷香满园吧。
然而接连不断的晴天,温度跟物价一样,居高不下。再看时,心就凉了大半,原来的旧叶,边沿已开始焦黄,更有渐向中央漫延之势。心中着急,电话里问朋友,称不如种些小巧的睡莲,好看又有趣。难道睡莲就不怕热吗?心下郁郁无言。又隔三四日,荷一点动静也没有,新生的叶片也随之萎顿了去。荷焦,我心焦,那么老屋种荷种稻的农人呢?到此时,已心绪尽失。知道世间物事皆不可强求,与其这样客死异乡,不如任其夭亡在生养它的荷塘。便后悔当初从乡下浑汗白流挖了它来。从此窗前来去,不想看一眼。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旱情,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遭五十年一遇的旱灾,矛头纷纷指向三峡水库。又忧心那荷,念及它亲亲的荷塘乃至广远的洞庭和鄱阳湖,也不免一番唏嘘。

突如其来的一场雨,下了若干日子。再看时,荷竟然生出好阔的一叶,那叶片足足有碗口般大小。出水的荷,用它细而带刺的柄撑着一朵高高的伞,伞面碧绿得照花太阳的眼,旁边还斜逸出几片初生的卷曲细叶,仿佛对折了一些不想让人探知的心事。这便是唐人李群玉笔下的新莲么?
春去夏来,蒲草一样的是心思。
一直不明白是先有藕,还是先有荷?又忆起老屋后的池塘来。几年前冬涸时,时常弯过去看人挖藕。挖藕是件力气活,光靠力气也不行,便又是件技术活。冬天里气温低,农人穿了及膝的雨靴,头顶着阵阵雁叫,在荷塘里挥汗如雨。把泥土一锹锹掀上岸,再顺着荷梗往下赶,一锹锹地追踪。一会功夫,就取出了大片的土。坑深,有水涌出。水积得多了,看不清泥里藕脚的走势,还得一锹锹舀出水去。待大部分的枝节显露,就可不太费力地抽取出整枝的藕来,等洗去敷在上面那层黑泥,藕就白亮白亮地呈现在人前了。很奇怪,年年挖藕,荷叶年年生,荷藕怎么就挖不尽呢?
久旱又成涝,不知乡下那片暴饮暴食的池塘怎么样了。窗外依旧雨势潦草,估计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云开。总是没来由地想起沟边向日葵的脸,想起老屋后那蓬栀子,想起一野麦黄的夏天。想起麦田里背着火铳行走的猎人和他的狗,那狗撒着欢地跑,莫非嗅到了野兔的踪迹?阳台上晚风中的呼吸,不知怎么就有了田野的味道。
以藤为裳
城南旧居,闲静幽雅拙朴如玉。墙角一支枫藤,别名小虫儿卧草。原本那藤是两年前,从邻居家后院移栽过来。只因特欢喜那名儿的别致,平白无故多了好些疼爱。
当春姑娘还在一路上跋山涉水的时候,枫藤柔顺而安静着。雨水节早过了,田野里、沟渠间,积雪还在一点点的溶化。枫藤的幼叶,就一小簇一小簇隐蔽于枝芽里头,伺机往外冒。但那粗壮苍劲的老枝,却是不避风霜的沿墙迤逦而上,一路攀爬至屋顶的飞檐下。

乍一眼看去,那不是藤,是树。一棵干枯的树,没有叶子,只有无数泾渭分明的枝条冷冷地撑开在二月的春寒里。也许更像一副画卷,是谁在不经意间寥寥数笔勾勒出的水墨韵味?
似树,而非树。其实不难想象,那枫藤原是借着风势,才吹成那树的模样。再细看时,发现灰褐的皮下有孔。枝上有卷须,卷须短而密,有许多的分枝。卷须的末端牢牢地吸附在光滑的墙壁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直让人叹为观止。
人类筑穴为室,这一室以藤为裳,旧居也因之生色不少。一年有四季,每一季的美又各有不同。人居此境,片刻烦忧也会随落叶飘去,任心思蔓延滋生喜趣的新芽。
春天,自然是满墙的绿萝满墙春。到夏天,那绿意会演变得愈加浓烈与醇厚起来。千千万万黄绿色的小花朵,随风摇曳。如同出海的小帆船,点缀在万顷碧波里,又如同千万只小虫儿匍匐在绿色里头。于是,那“小虫儿卧草”的别名更加意味深长了。秋天,换上红装的枫藤更是将它的美演绎到了极致。铺天盖地的红叶,简直浸染了整个秋天。而到了夜晚,一钩凉月、一墙枫藤、外加一桌一椅,名人佳士对壶邀月,带去无边风雅、向往与满足。
到了九、十月,枫藤结出小球形的桨果,熟透的时候呈蓝黑色,常常引来成群结队的鸟儿来啄食。我听说那果子还能酿酒,只可惜没人尝试过。不过,枫藤还有个俗气的名:爬山虎。
绿窗小记
四月维夏,五月鸣稠……窗外。
早起,上城西赶市,那天就五元捧了三棵苗归,丝瓜、苦瓜、黄瓜皆全。老农说他这苗壮实,种一棵活一棵,只管回去埋地里,淋些水了事。
母亲果然十分欢喜。从前在老屋居住时,也曾在门前辟出小块菜地,种些青椒葱蒜什么的,享过田畦之趣。见我买了秧苗回来,嘱咐搁荫湿处,等傍晚时分太阳下山了好去栽种。但我如何能耐烦等到那时呢,看看天又将雨,墨云在头顶的天空翻腾。若赶在雨水前种下去,应是好主意。于是拎了小铲出去,在阳台长方形的小花圃里刨坑、碎土,小心翼翼地将钵植入,怕伤了根须,掩上土又特意往上拉伸了些,再压实了面上的泥。左看右看,心下满意得不行,又灌了些定根的水,才放心罢手。午后果真就下了好一场透雨,直下到傍晚时分尚未歇息。记挂着秧苗,中途又撑伞出去察看了两回,三株瓜苗似也乐意这新的栖居之地,雨中更见活泼。那夜睡得格外沉,檐下滴答的雨声,叮咚催人入梦。梦里却已收获,请了诸多同事朋友一起帮忙,满藤满架的瓜果,摘的摘,搬的搬,抬的抬,好不热闹。
醒来却是空自欢喜,只因又逢着一场意外的低温。先是起风,好大的风,刮得行道树剧烈摇摆。接着是雨,一连好些日子,迁延地下着。我缩在屋里哪也不想去,就抱着杯热茶喝。母亲又摸索着穿上棉衣。嘟囔道这都农历三月半的天,还冷得这般异怪。持续的低温之后,天倒是晴了。然而苗圃里却只余得唯一的一株苦瓜苗,缩着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抖瑟;本来只有一株的丝瓜秧已然死去;黄瓜苗也是搭拉着叶子,病恹恹了无生气。这样守了几日,依然不见好转。再次特意的早起,去集市上转悠,却不见一个秧农来,郁郁地买些馒头回转。餐桌上,母亲问起秧苗的事,笑我心急得晕了方向。卖瓜秧的都在城东呢,那里市场大,卖菜的多,买苗的才多。
犹记得母亲那年在门前空地上,布置的遮天蔽日绿幽幽丝瓜。七月里虎渡河水猛涨,眼见得就爬上坡,漫过许多人家的屋门台阶,最后也波及了我家的房子。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搬到河堤上驻扎,那两株丝瓜自然无一幸免地淹了水。偏那瓜蔓值盛产期,早乖巧地攀到那高高的电线杆上头去了。我们就趟水去收获,可一根根苗条的翠绿丝瓜吊胃口吊得老高,风一吹便荡呀荡。就弄支竹竿来,上头绑个勾,瞄准了一使劲,丝瓜就啪嗒一声掉下,溅你一身的水。掉进水里的丝瓜漂啊漂,引诱你挽着裤管去捞。印象里那一年的丝瓜格外泼皮,泡在水里还拼命的结,常常一两天下来,能摘个十来条。吃不了,母亲就四下里送,三朋四友、邻里乡亲,有时走好远的路给亲戚家送去。我们免不了埋怨几句,母亲却只说,糟蹋了可惜。想不到的是,我的丝瓜幼苗却那么娇气难于成活。
月中去乡下一趟,特别留意了婆婆的菜园。但菜园寥落,只一角的黄瓜似乎还像样,瓜蔓壮实,都已开始顺着枝条牵架了。辣椒秧也有,只是已半大青春,恐难以移植成活。池塘边,几片小小的芋头叶芽才从地里探出头来。刚下过雨的泥地,湿漉漉一片。婆婆知我想要些菜苗,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帮着挑了好几棵黄瓜苗;又挖韭菜数篼,根上还染着草木灰的白。本来也想挖几棵芋头的,被先生阻止。算了,就那屁大块地,已经够挤了。我估摸着,是恐我弄去又生生糟蹋掉?最后就撮了些婆婆灶膛的柴灰,拿袋子封好拎回去作肥使。然而这乡下移来的几株黄瓜苗,次日就遇着毒日头。先是边上的三棵趴地上死掉,接下来又两棵一蹶不振,最后也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株。于是一早一晚,又是浇水又是施肥的,到得日中,还得费力搬块石棉瓦片上去给遮阳。这株黄瓜苗总算度过了最艰难的成活期,这也是一周后的事。
后来又有朋友送来几根苦瓜秧。也是听得我在寻思着种菜玩,就将她园子里的苗挖了几株送来。我自然欢喜得很,那瓜苗是拿一张白菜叶子包着的,都两棵两棵的粘在了一起,便小心地动手掰开,又怕弄伤它们。最终四株苗子,分三窝栽了。又是一些日子的焦急等待,最后也只留得一株活下来。至此,便有一株黄瓜两株苦瓜共三根秧苗正式落户我那小小的苗圃了。圃太小,横竖不过一米,土又贫瘠得很。圃上为窗,有系绳自然垂落,想瓜蔓有一日终会自己爬上去。那样母亲开窗,就能轻易摸到绿色的瓜条了,一定很开心。只是这幼苗,想它平安长大,却是多么的不易。光照强了弱了不行,雨水少了多了不行,气温高了低了也不行。得所有机缘都刚刚好,才有成活的可能。不独瓜果菜蔬,人畜禽鸟,无一不是偶然到极幸运才得以到世上走一遭吧。
到阳历五月,叶子一天天长大,瓜蔓开始往上蹿。此时,种下的韭菜也正儿八经的上了回餐桌。那时正值新鲜蚕豆上市,清炒蚕豆当然少不得一味伴侣的,那便是韭菜。虽然种在花盆里,收获才不过大拇指粗的一束,点点碧绿的韭叶在蚕豆碗里却是分外的惹人喜爱。这也是唯一饱过口腹之欲的自种的菜肴了。虽寒酸,却也欢喜莫名。
一直也没种过菜蔬,对伺弄土地这样的事情又一窍不通,闹出些笑话便是自然。好在这样的一时兴起觉得颇有趣味,且又无伤大雅,便到处搜罗种子去播撒。有母亲去年种在花圃里的三角豆,最后结了两串,被我收作种子的。于是翻箱倒柜去找,最后在壁柜的最顶层找到。剥开豆荚,取出歪歪扭扭的豆子来,一共十粒,都急火火地埋进土里了;隔天先生又带了玫瑰花种子回来,也心急火燎地种下;又翻出早些时候朋友给的一包决明子,想着也许可以种,也一并撒地里了。五月的雨,下了一场又一场,种下的那些却总不见冒芽。后来上网查过才得知,原来那些种子下地前,得事先浸泡催芽过的。
好在种下的,最后总算还是出了一棵苗。一开始是两片,渐渐的三四片、五六片,乃至越来越多的叶子,茎秆也一节节的拔高。沤了淘米的水浇它,渐渐地开花了,结荚了,荚壳一天天膨大。数数,有二十好几个豆荚呢。于是,就盼望着收获的日子,盼望着吃到那粉粉的、模样像极了花生的三角豆。
有日,一向对种植漠不关心的先生去圃里看过说,还三角豆呢,明明就是毛豆嘛。我无论如何也是不信的,明明种下的三角豆怎地成毛豆了,难道豆子也会戏法?后来,捏着豆荚去找母亲论理。母亲捏在手里反复捻着,没有错的,这确是毛豆。过一会又恍然道,莫非那日太阳下晒毛豆,不小心滚落下几颗搞混杂了?争论未几,豆子病了。先是叶片发黄,然后有密密的小洞眼出现。传了图在网上,有朋友诊断说是遭了虫灾,得起早去捉。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凌晨五点就起了,戴上手套去捉虫,结果也没见到虫子的影。也许虫子狡猾,听得动静都躲到泥土里去了。只好眼睁睁看它一日日萎黄,又不敢用杀虫子的药水。先生反而安慰了,说豆子都成熟了,收割吧。可是,可是……豆荚虽是黄了,里面的籽实并不见得够饱满呀。又去咨询那诊断的朋友,笑说,干脆摘了煮汤吧。于是都剥了,左看看右数数,怎么也不够煮一锅汤的。灵机一动,掺入冰箱里存货的黄豆,让母亲在某一天早晨打成豆浆,那真是香淳鲜美,别有一番风味。
继而农历五月,又逢端午,随大流忙着准备过节。起早去集市,见迷你黄瓜那般的小巧可爱,很想买两条来拿透明的胶布绑在藤蔓上,等儿子假期归来,好支使他去摘。像去年在水缸里种荷叶,偷偷从别处弄一支莲花嫩苞来插上,最后也哄骗得母亲相信了。那样的玩笑,实在是有趣。但迷你黄瓜的事后来一忙,又给忘了。
好在到了端午,瓜蔓上已结出一厘米来长的小黄瓜。顶端的花还黄艳艳的开着,拉了儿子去看,儿子啧啧地称奇:这瓜是世上最小最小的瓜,园子也是世上最小最小的园子,妈妈你呢,便是世上最小最小的农场主了。心里便乐上了好一阵子。到中旬,又是大旱天,久不见雨落,气温更是节节攀升。早晚要忙着浇水,中午更忙着搭凉棚遮阳。不知怎么的,那最早结出的小黄瓜,竟然全都死了,反倒是迟结的苦瓜越晒越见精神。后来才明白黄瓜喜湿,经不得太阳烘烤,而苦瓜却耐旱得多。而我却不懂得,只将两种性情不同的客人,一样招待了。日本畅销书作家藤田智教授的《在阳台上种菜》里写道:虽说是亲手种菜,但种菜的不是我们,是大自然神奇的力量。我们人类只是打了个下手而已。几日后,苦瓜开花,又结了小小的皱皱巴巴的瓜条,吊在藤条上打秋千。然后却有几条一声不响地夭折,让我心疼得傻了眼,可朋友说那叫“弃死宝子”,是自然淘汰。终于到了某日,有那么两三条生长成形的小苦瓜,竟悄然攀上母亲的窗棂。密集的绿叶,笼罩得母亲有了满窗的清凉。

母亲却更见安静了,她日渐老去,仿佛习惯身体一日日的孱弱下去,眼耳也越来越昏聩。那些悬吊在窗上的小小的瓜娃娃,她一个也看不见。却用颤抖的手,摸索着把那攀上窗棂的藤蔓一一绑好,怕哪一阵风不小心吹折了它。有时母亲在阳台上长久地站立,神情专注,像是在细细地谛听些什么。听窗台上那些藤蔓的絮语吗,还是它们绿色的呼吸?也许,她只是在倾听自己这一生的风雨往昔。我父亲早逝,几个兄姊夭折,柔弱而又顽强的母亲,多少温情与疼痛,最终只能由她自己消解承受。哪怕瓜蔓,哪怕我,至多也只能给她漫长而又匆匆的人生打下手罢了。
今晨看到些小小的红蚂蚁,在花叶间忙碌,它们是来帮忙授粉的吧,便轻轻道一句:辛苦了,小蚂蚁。
傍晚,一场阵雨过后,火烧云渐渐淡去,黄昏的天格外明净。栀子白了,又黄了,像一件被弃的旧衣。而我,守着这三株瓜蔓,并不觉寂寞。不时去浇水,施肥,像对待自己所出,关心它们的冷暖饥渴。若种得些环保又安全的菜蔬供一家人享用,便是至福了。但照这般长势,一时又恐难如愿。就让它们从容生长吧,圃不在广,有藤则荫。
六月徂暑,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授衣……
流光总也无情。盼着也能有那么一天,像母亲一样心静气和地老去。就仿佛心里驻着一个永恒的春天。独坐小窗时,总有绿色漫上衣衫。
马约兰,晚风渐凉
初夏把所有的繁盛都交付与你,马约兰。你听——云雀的哨音在林间起劲地吹,草莺和斑鸠,以及许多的布谷鸟,它们长一句短一句的对白。虽然我总是难以分辨出它们之中谁是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它们还不同我一样,对你,对这葱郁的季节欢喜莫名。
一些来自地中海的风声,马约兰。它们呼啸而至。当你柔软的藤蔓,悄然爬上我洒满月光的窗台的时候。
当你疯长的藤蔓翡翠般,就着一地月光的潮汐漫上来的时候,我便闻到夜色中弥漫的松树与柑橘的香了。那样甘冽的香味,让人想起牛至,想起薄荷,想起普罗旺斯香草的香,但又是优于这一切一切的香。是沙拉酱汁诱人的味道,是盛夏果子发出的邀请,是让茶碗与呼吸一起迷醉的甜。

如此敏感温婉如你,马约兰。我爱你丛生的小叶。这一瓣一瓣对开的手掌,仿佛从叶子里生出的叶子,从花里开出的花,从翅膀里又飞出的一双翅膀。我看见那个头戴花冠的新娘——执掌爱情的玛雅女神,怀抱荣誉、爱与繁殖,那样深情款款的走来了。女神,你的怀里抱着一个不安分的春天么?好多虫鸟的鸣唱,孩子和牲畜在风中奔跑,我甚至听到篱架上黄瓜、藤豆和茄子花开的声响。
你说,我若是那个安住乡间的隐者,会是何等的幸福呢。野花遍地,酽酽春困,寂静村落,狗都懒得叫。分明是烂漫繁华堆砌里,又拙朴到至简的一份散漫。鸟从一棵水杉跳到另一棵,苔衣水一样漫上树身。御风而行的杨树花,雪一般的落下,布谷的叫声多么的热切,它们联手将这五月的繁茂,从村庄深处铺天盖地的展开。而我,就在水杉的绿烟里,用一杆吊床摆渡,桃木手杖为桨,仿佛戴胜与鸥鸟相伴。这初夏的婷婷五月天,多好。
我爱这草木的枝繁叶茂,爱群鸟的百啭千声,马约兰。它们无一不是蓬勃向上的,追寻着一份恣肆放纵的挣脱,是生命的美的求索;我也爱你紫白的、素朴的小花朵。我爱你的典雅,你的静谧,和这静谧里流淌着的淡淡从容。
可是马约兰,晚风渐凉。
你听——远方,那被一场浩大的月光安抚过的原野,和意杨林的喘息已近平伏。水田里原本稠密的蛙声,也渐次寥落。所有的喧嚣都在隐去,包括满树栀子泛黄的白,包括醉蝶花一不小心的踉跄。
是的,沃野千顷——这漫长的一生,我必将臣服于这土地,以及这土地所缔造的种种神奇。只因生命中每一次的亲近草木,于我都是一场重生。但你又如何懂得我内心的悲伤呢,我不过是个孤独的局外人,痴坐在小城五月的静夜,独自仰望远方那无尽的葱茏。
不如归去,不能归去,这是最后的村庄。马约兰,晚风渐凉,晚风已凉……
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往期回顾
周记盐号 | 苏以吉
长堤巍巍|王书文
听鸟说甚 问花笑谁 | 魏金修
月泊长河 | 丰 灵
故园遗梦|崔迎春
太平狗 |陈应松小说连载
联系我们:
1、直接回复本账号消息。
2、致电:15927716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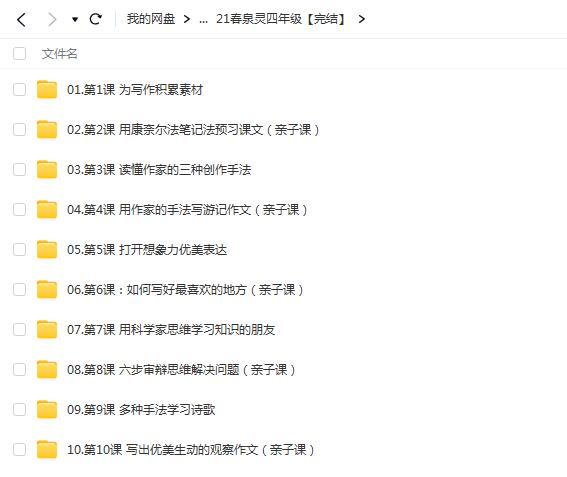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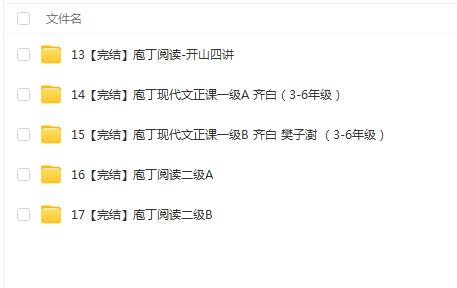




![【泉灵语文】2020春 泉灵三年级语文下讲课视频[百度网盘分享]](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30ml/65-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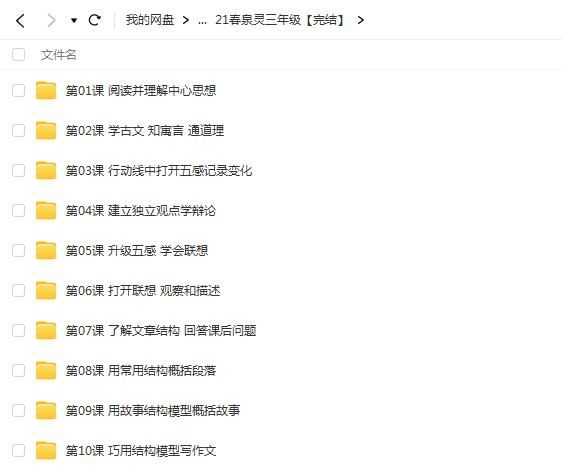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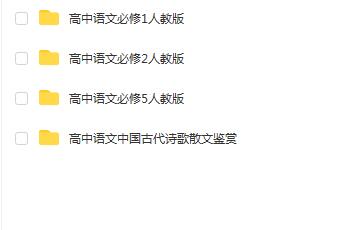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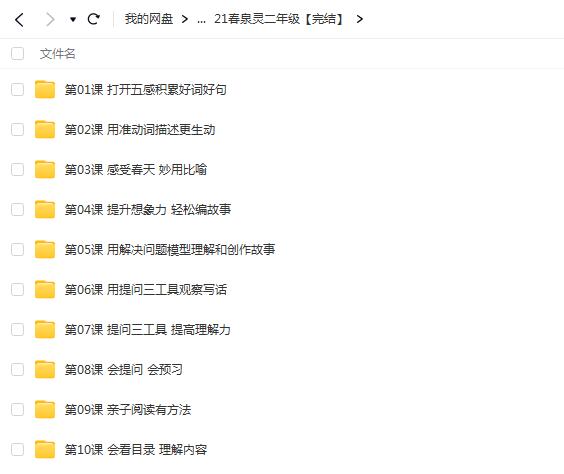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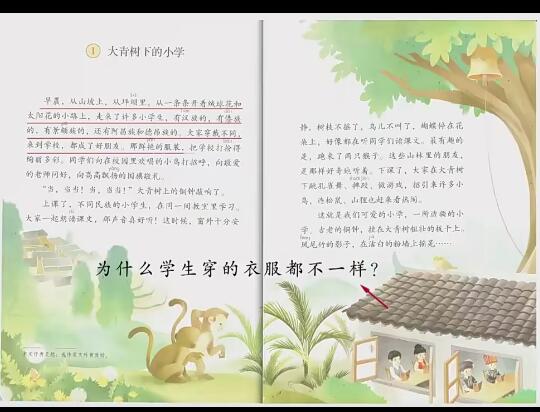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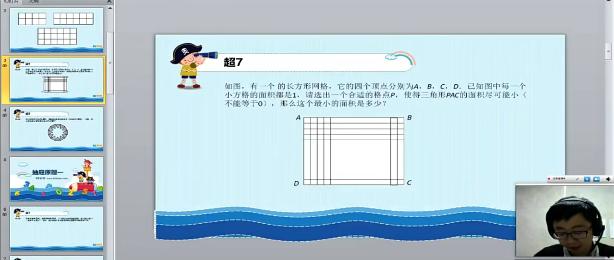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