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旧文拾掇 庙与学校(三) 2021年第100期(总697期)
发布于 2021-11-23 19:37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十)
这篇长文的标题是《庙与学校》,庙不但与学校有关与教育有关,而且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曾表述过这样的意见:世界上本没有上帝,上帝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于是我知道,人类创造了上帝和菩萨,也创造了庙与学校。
宗教的起源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自有专家论述,此不赘及。要说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上帝,他们供奉的是道教的“真人”和佛教的“菩萨”。而苏吕堡是典型的屯堡村寨,祖先崇拜是屯堡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祠堂(家庙)是一个供奉先祖的神圣的场所。在破旧立新的大趋势中,家庙不仅成为学校,而且成了知青的宿舍,“神圣”不再而乱世出焉。
在这个家庙的学校里有两个教师,都是男性,一个民办代课教师,姓苏,是村里的老学究,六十来岁;另一个是公派的正式教师,姓颜,安顺城里人,四十岁模样。苏老师家在本村,饮食起居有人照料。颜老师家在安顺城,必须自己烟熏火燎地做饭,生活苦而清贫。后来,我与苏老师的儿子一起在这个家庙里任教,成为老苏老师和颜老师的继任者,算是家庙里的文化承传罢。

知青在田间地头学习毛主席语录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家庙并没有给我们的知青“家庭”带来好运与和谐。本来,由上面强制组合的“家庭”就没有和谐的基础,产生矛盾是必然的事。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成为“新社员”不久,“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地委向旧州区派来了工作队,进驻苏吕堡的工作组来自息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不,是山洪即将爆发,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新社员”成为四清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有的知青还被工作组抽去搞文书抄写工作。詹家屯公社的书记和社长受批斗,苏吕堡大队的周西昌大队长受批斗后闹得跳河,河水太浅没有死成。
我们六个知青组住在祠堂木楼上,另三个组由所在小队另外安排。木楼呈“走马转阁”的形式,楼下吃饭,楼上睡觉,三十六个人搅在一起,十分热闹。晚上想家,睡不着觉,有人起头,各宿室的知青便躺在床上齐唱革命歌曲。有时还欢迎某位歌喉漂亮的女生独唱,大家躺在床上欣赏。这种床上联欢会经常举行,直到四清工作组进入祠堂办公才停止。
知青的饭量都很大,一把面条不够吃;我本人到旧州赶场,两斤粮票的米饭都填不饱肚子,只好外加两个菜包子,吃得肚儿鼓鼓的,转眼又瘪瘪的了。有的知青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有位知青将汗衣扔在地上,引来大公鸡“得得得”地啄食汗衣上的虱子。一个调皮知青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个场景,说大公鸡吃得打饱嗝了。很多年后我的儿子问我虱子是什么样,我顿有隔世之感。
提起我的儿子,顿时想起了那个时候我们“新社员”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姓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小二毛”。小二毛不是知青但却成了“知青”,这不知是他的光荣还是他的不幸。小二毛下乡时只有十三岁,基本上是个文盲。小二毛无父无母,依傍他的“姑爷爷”过日子。他的“姑爷爷”是一个早年出家的老尼姑。照此情况,小二毛不应当成为“知青”而应当被收进孤儿院。他之所以成为一名光荣的“知青”,那是由于某办事处为了完成任务拉来顶数的缘故。小二毛平坝口音,他很瘦,细长个,显然营养不良,他下嘴唇很厚,视力不好,看东西要紧凑上前,老远看去,就像一只觅食的螳螂。现在我已为人之父,以父亲的身份回忆小二毛,才觉得那是一个十分可怜的孩子。从学校来的知青一般不欺负小二毛,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变成“知识青年”的“新社员”却常常拿小二毛当成出气包。小二毛每天的工分只有四分,不到标准工分的一半。小二毛很少旷工,他没有朋友,他无处可去,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他默默地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动。他成天打着赤脚,他的脚很小,他的腿很细。闲下来的时候他就默默地坐在村口的树脚,望着淡淡的远山发呆。我没有看见他笑过,更没有听见他唱过歌。他说话像蚊子叫,细声细气的。有一次,在楼道上发现了一堆大便,有人说是小二毛晚上怕鬼不敢上茅房拉下的,那位拿小二毛当出气包的“新社员”要小二毛吃掉。小二毛急得涨红了脸,半天才吐出了声,那声音高而尖利,带着奶气,令我感到心痛。

下乡知青在安顺县委大门口集中准备出发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知青返城后大都安排了工作,但小二毛没有文化,只好在火车站做苦力,拉板车、蹬人力三轮。没有人关心他,知青聚会也不邀他。他就那么孤寂地成长起来,据说他长得很高大,穿四十三码的胶鞋,但仍然不会笑。
现在,曾经一起插队的苏吕堡知青都互称“同学”,不知他们是否也把小二毛列入“同学”的范围。其实,苏吕堡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初中毕业生,有高中毕业生,有应届生,有往届生,还有社会青年,情况多样。之所以互称“同学”,可能是把广阔天地当成了共同的学校吧,也许,还把苏吕堡的家庙当成了教室?
其实,我们插队不久“四清”就开始了,随着开展“四清”,苏吕堡“同学”的分化就已形成。“四清”草草收场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迅疾横扫全国,苏吕堡“同学”的大分化大改组也大大加快。除了小二毛外,似乎人人都想革命。人人都想通过革命寻找出路,告密和揭发开始了。一些苏吕堡“同学”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要从其余的“同学”中揪出“牛鬼蛇神”。他们在“同学”中揪出了九个“牛鬼蛇神”来批斗,罪名是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些革命的“同学”把一些侮辱人格的对联贴到“牛鬼蛇神”的蚊帐上面,并且不许撕毁。其中一个“牛鬼蛇神”的蚊帐上的横批是“毒蛇洞”。“牛鬼蛇神”统统受到孤立,他们在经受一天的繁重劳动后,只能默默地掀起蚊帐钻进“毒蛇洞”内自我抚慰受伤的心灵。
“文革小组”的知青在油灯下开会部署革命,很有革命风度,其中一位女生真还有点姿色,扮演江青一定很合适。
我也非常荣幸地成为革命“同学”的批斗对象,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原因可能是我曾发表过“豆腐块”文章罢?革命“同学”还勒令我交出女友的来信,我理所当然地严词拒绝。很多年后,我就此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邂逅放鸭人》,不是因为记恨那些革命的“同学”,而是为了祭奠我的青春。
大串联一起,知青大返城,革命的“同学”转移阵地,到更为广阔的天地革命去了。
“文革”爆发,红色大潮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知青大返城,接着是武斗,令人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除两个家在农村和一个无处可去的知青而外,其余的苏吕堡知青跑了个精光,连小二毛也不知去向。我糊里糊涂地卷入了大串联的队伍,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睡觉不要钱,跟着喊造反口号也不要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曾联合发出通令,不准农民进城造反,知青是农民,当然也在不准进城造反之列。但时局混乱,谁还管得了这么多?苏吕堡知青会同白坟知青和宁谷知青,到原安顺县老县委造起反来了。造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回自己的城市户口。知青们整天围着赵殿君(时任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记不清了)和何刚(时任县委秘书)闹,要户口!还有一位叫张广德的县委领导也被知青麻闹过。闹来闹去何刚成了知青的老熟人,大家有时还嬉皮笑脸地开玩笑。白坟知青还从跳蹬场公社抢来了全公社的户口簿,形成一场闹剧,多年以后谈起此事大家都哑然失笑,那时县领导对知青还是同情的,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措施。实际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身难保,哪有精力来处置造反的知青?在县里闹不成,有的知青还骑了破旧的自行车结队赴省城,麻闹了一回陈璞如(时任贵州省省长)。

大串连时在天安门留影的红卫兵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户口闹不回,众知青作鸟兽散,纷纷加入大串联的队伍,云游全国去了。借着那股乱劲,我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游览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中山陵,参观了大上海,还在天安门前留了影,穿着一双解放鞋和一条补过疤的破裤子,游览了大半个中国。有人在峨嵋山上题了一首打油诗:“人说峨嵋天下秀,我说峨嵋秀个㞗,不是天下闹“文革”,哪个龟儿到此游!”这首打油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境,“文革”时期千万青少年荒废学业,国民教育全部停顿这样的悲剧连世界大战时都未曾出现过,国家与民族的损失,无法计算,也无可挽回!
玩够了,游够了,回家了!回家来怎么办?家庭经济窘迫,不能呆在城里吃闲饭呀!于是我与一位姓王的知青(我在苏吕堡插队时的“家庭”成员之一)相约,到普定化处胡家弯当了两年民办教师。那个民办小学设在双凤山上的一座有名的寺庙里。在这里教书的两年,是艰苦而又十分浪漫的两年,是我刻苦读书的两年,这两年在我的一生中以及在《庙与学校》这篇文章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这两年在前而回到苏吕堡教书在后,我仍要把这两年的生活放到最后去写以形成《庙与学校》的最后章节。

荒废多年的双凤山永兴寺大殿 孙守红 摄
大概是1968年或1969年罢,当时安顺县的领导要求返城闹革命的知青们返回乡下干革命,不愿回原来生产队的可以另外选点另行安置。于是,部分苏吕堡知青另择双堡山京插队,部分则回到苏吕堡。不过,重新下乡插队的知青再没有被强行配对组建“家庭”了,大都单独起灶成为单身户,有的买了缝纫机,有的喂起了猪,俨然一户真正的农家。而且,每家都单独挖了茅厕以便积肥种菜。据说一个苏吕堡知青到山京的知青户做客,山京的知青主人要客人到他的茅厕拉屎,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当时,许多国家特别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正在往大工业时代迈步,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都在刻苦学习大工业时代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利参加全球竞争,我们知青中的许多“同学”,却变成了小农经济的固守者和小农意识的活标本,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

双堡山京农场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后来国家组织修筑湘黔铁路,各地都要组建民兵师到铁路工地大会战,这体现了搞基本建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回到苏吕堡的大部分知青都参加了湘黔铁路大会战,真正为国家建设出了力流了汗。
我是一个例外,我被大队支书张绍明极力挽留,留在苏吕堡当了村办小学的教师。我继承老苏老师和老颜老师的事业,在苏吕堡的家庙里像模像样地操起了教鞭,肩负起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伟大使命。但是,我错过了湘黔铁路大会战的伟大场景,至今引为憾事。

参与湘黔铁路建设的女“民兵”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为什么要把我留下教书?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全国停课闹革命后一时难以复课,苏吕堡小学的桌椅板凳及黑板诸物全都不翼而飞,教师一时间难以复归;二是村支书张绍明的儿子小筛子正是读书识字的年龄,支书怕误了儿子学文化;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绍明认为我既然曾被知青“同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想来一定是个大学问家;第四,苏吕堡的众老少认为我会唱“党歌”(革命歌曲),又会代他们写信,还会说《封神榜》。总之,大家认为我的学问很大,苏吕堡子弟交我教育,将来会有大出息。
当年,苏吕堡“同学”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可怜我连什么叫“学术”都不知道,几十年后的今天虽仍不能理解“学术”二字的真谛,但在其他方面还是晓事不少。今天,“晓事不少”的我回忆起苏吕堡大队支书张绍明时,对他存有几分敬意。这个人身材瘦小像只猴子,蹲在地上一只斗篷就可以把他盖得无影无踪;他基本上是个文盲,但是,在“读书无用论”畅销全国时他却懂得文化的重要,力主恢复村办小学并且择我任教。我敢说,这个大队支书比当时的许多伟人都要清醒都要伟大!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2021年11月
值班编辑:宋兴平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长按上方ErWeiMa《文化安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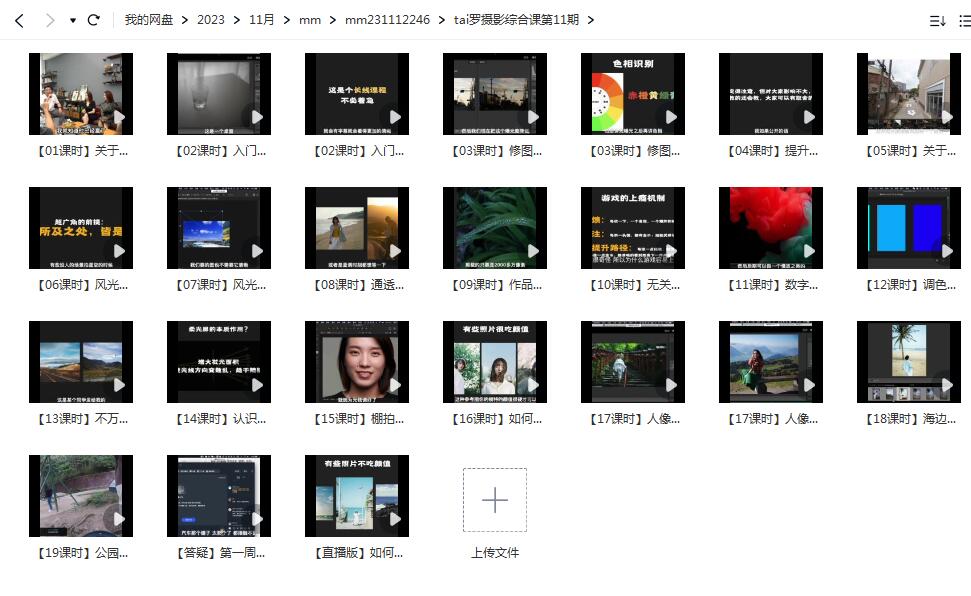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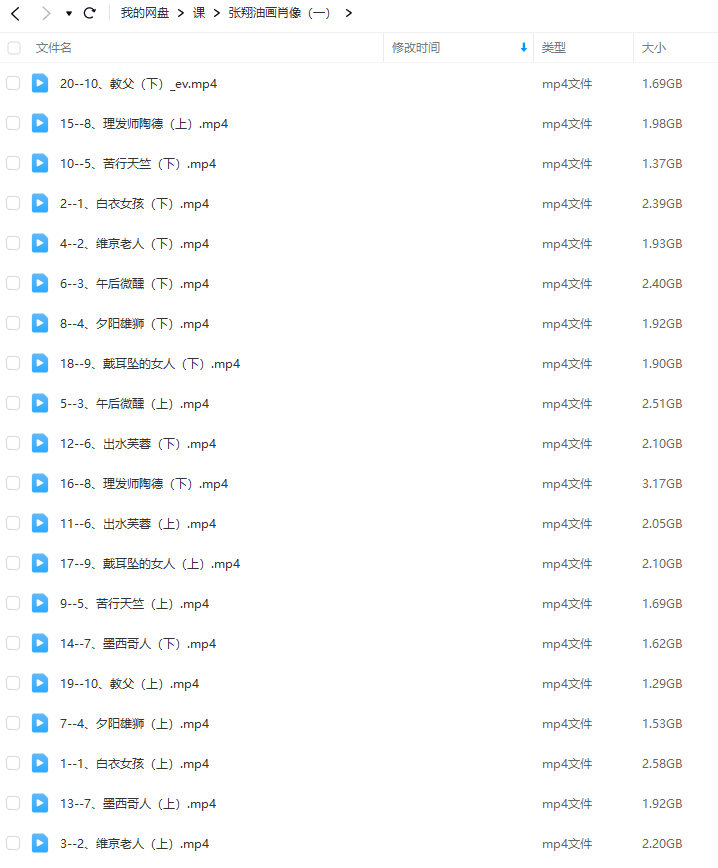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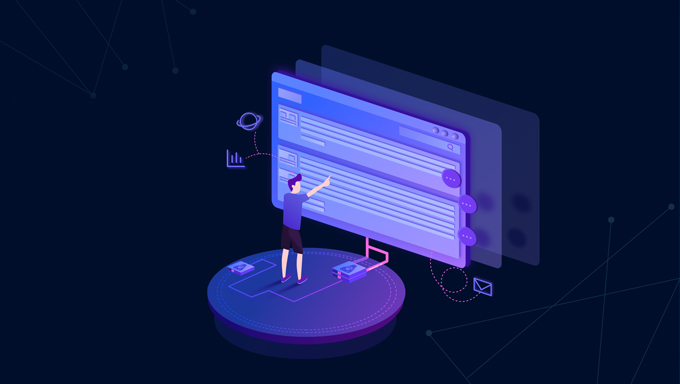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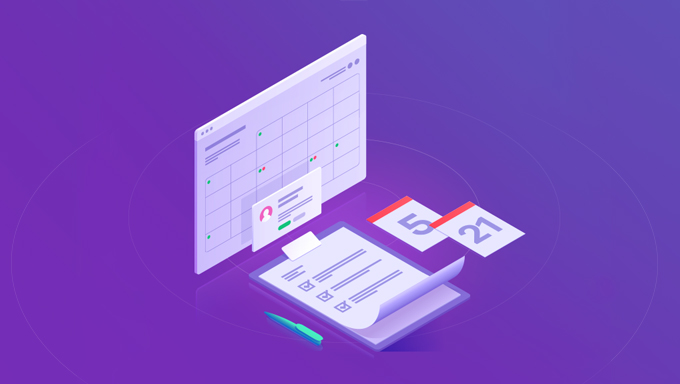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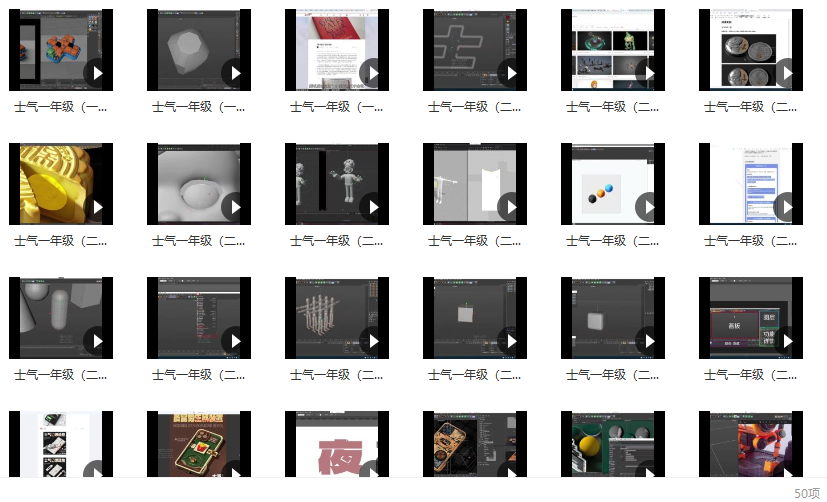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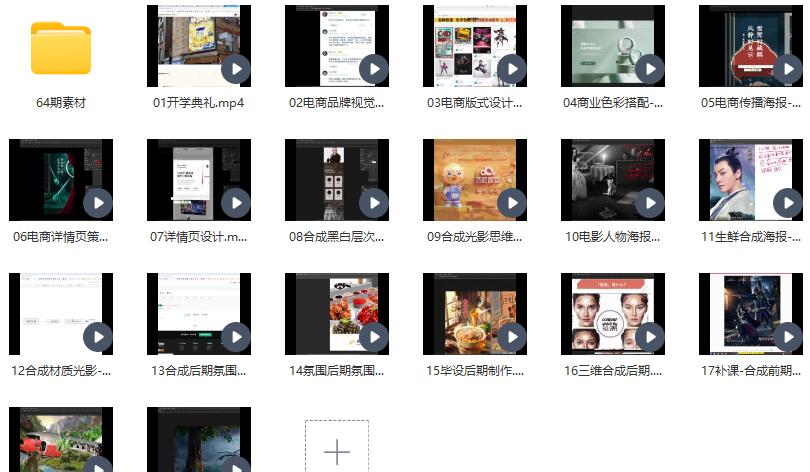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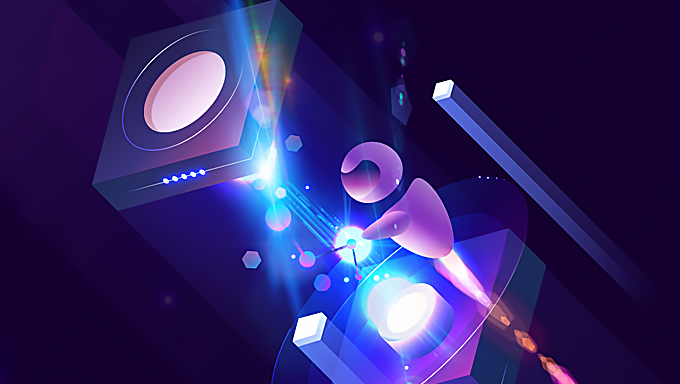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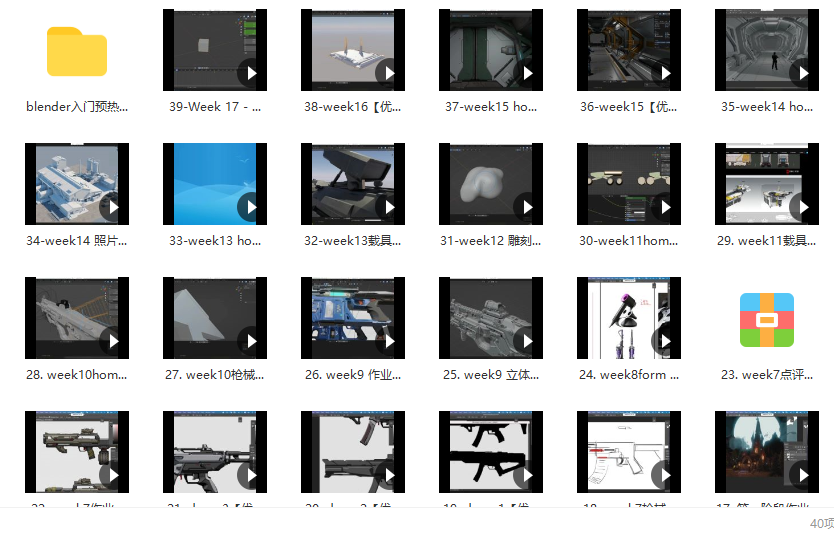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