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罗马小男孩 (散文)
发布于 2021-11-26 19:59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左岸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只身搬到中山区昆明街(五卅街)一处曲里拐弯的胡同里的老日本三层楼姥姥家居住,户口随之迁去,为占房(据说,一九四五年大连光复,我姥爷任某刷厂工会主席,必须带头搬进日本房栖身,因为害怕日本人一旦回来算账,职工们都忌惮的要命)。
这栋日本房通走廊在外,站在自家门口,都能清晰地看见浅黄色的火车站,巨人般屹立在那。有时就为听大钟的钟声,悠扬沉郁,有种穿透灵魂的暗物质进入身体。据记载车站由满铁留美建筑师太田宗太郎主持设计。大钟高直径3米多,时针足有一人多高,前些日子乘坐快轨,偶然发现它的背面也有相称的时钟。有的说火车站的大钟,1时响一下,2时响二下...12时响十二下。每响一下钟声要持续5秒,这绵长的5秒,世界仿佛停止了聒噪,所有的生灵领受一种圣教的洗礼和安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无不感慨地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按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大连火车站即是这个城市的黄鈡大吕。

时间是悠远的暮歌。记得当时我有个画画不错的朋友任宝海领我到他的画友家去玩,住处离我家不远,就在昆明街某处日本旧居。居家在一楼,门老半天才开了,我随好友进去,房间较大,但光线很暗,在有限的光亮里,我瞅见屋子的主人顶多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浓密的分头黑发,双眼皮下是波澜不惊的一泓深潭,藏蓝色夹克衫布满油彩,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他不苟言笑,随手递给我一支烟,就走回画架旁,留给我一屋昏暗的气氛。
作为第一次踏进别人的家,人们肯定都要无意识里瞅瞅这望望那,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具有意大利风格的铜床,坦白地说今生第一次遇见,床尾立柱顶端是铜球,床头比较讲究,由类似蝴蝶翅膀造型的大小不一的铜管焊接而成,立柱两头则是三个铜球大小叠罗汉似的组成,鸭蛋青的床罩直垂到地板。乳白色的窗幔垂帘似瀑布般落下,在透明与不透明中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我感觉到
贵族的气息,猜到这家的身世绝非一般战士。

视线在新奇中转向睡床的对面墙壁,那儿悬挂着几幅油画。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在中学美术课老师讲过,不过亲眼看到如此以假乱真的临摹,还是让我惊讶不已。仿佛我嗅到了伏尔加河那充满腥味的泥沙味,十一个不同年龄的纤夫拉着纤绳匍匐前行着,破衣烂衫在风中哭泣,每时每刻撕扯着他们苦难的命运。血液在身体里流动快了,我不由脱口而出:画得太好了!宝海转过身对我说,你看看这幅:我随着他手指的靠近窗悬挂的一幅画走去。他介绍说这幅画是侨居意大利的俄国画家阿•哈尔阿莫夫的传世之作《意大利小女孩》。我定睛看去,不禁惊叫起来,太美了!画面是一位十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她是面向右侧坐在椅子上,偶然侧身回眸,直视着着你!不,是整个世界!蓬松带卷的长发一直垂落到肩上,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直视着你,黝黑中透出淡蓝的雏光,似乎是两滴刚刚生成的露珠,纯洁里流露几份柔弱,小小的鼻翼微微翘起,本色的嘴唇一抹似光线,尖尖的下颏,玉膏似的脖颈清晰看见少女线,带褶皱的鹅黄上衣配有红底黑花纹的吊裙坐在一椅子上。背后涂抹的黑暗大色,前面棕黑色交织些土黄暖色,使女孩的脸越发凸出。增加了空间感。这应该是一位普通的女孩,劳动之余在小憩。画家正是抓住女孩动态的一瞬间,捕捉到灵感。后来据说这幅画原版无从查找,只有陈丹青在年轻时从扑克牌背面临摹过,流传至今。

墙上另外两幅,一幅是保罗•米勒的《拾穗者》,画面展示了穷苦人捡拾收割后剩下的麦穗。另一幅是荷兰油画家亚伯拉罕•胡克•二世的《海岸礁石》动感非常强烈,乌云正在把蓝天撕成碎块,海涛奔涌撞击礁石,颠簸的船只艰难行进,仿佛是一曲勇敢者进行曲。

墙旮旯一角矗立着缩小版的罗丹的《思想者》石膏像。非常有动感。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劳动男子。血脉喷张,弯着腰,屈着膝,右手托着下颌,默视下面发生的悲剧;深沉的目光以及拳头触及嘴唇的姿态,表现出一种极度痛苦的心情。

油画间隔则挂着两件面挂石膏像。都是初学者练习素描的最佳教材:一尊《阿格里巴》他是古罗马军事统帅,面部具有罕见的立体感,充满刚阳之气,蕴藏着典型、鲜明的人体头部比例和结构;另一尊《拉奥孔》:这件雕塑营造了高度的紧张气氛,将人物极度痛苦的情绪充分地表达出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雕塑之一。

转而,我的好奇心转向写字台上摆放一尊小石膏像,同来的宝海告诉我是《罗马小男孩》,作者无从查考。看那副乖样子也就十岁左右,卷曲的头发,头微偏,眼睛单纯地凝视着什么,他的天真无邪深深触动我的心,我知道是莫名地喜欢上这幅石膏像。
足足有十来分钟的观赏,我像突然掉进西方艺术的陷阱,难道这是另一种人类文明的终极体现?战栗、饥渴、麻木、兴奋、幸福等交织在一起,尤其文革运动尚在如火如荼进行,更显得极其珍贵。
这时,主人放下油画笔,拧亮落地台灯,说来了灵感,要立即抓住,慢待了。
我说谢谢你给我充分时间观赏大师之作。命中注定我们一见如故,在烟圈缭绕里,攀谈得很多。直至万家灯火复明。庆幸我认识了一位很有个性、极具天分的青年油画家,他叫复敬国。

至此,我与小复经常来往,请他喝了二次酒,那个年代,一次也就块八角钱。都说画家的眼睛非常毒。一次见面他对我说,知道你非常喜欢小男孩,我与朋友借了模块,你可自己翻一个吧。说毕他拿来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有大小七八块。告诉我如何制作:在桌之上把模块对好,用尼龙绳将它们固定好,之后,模块对接处用黄泥溜好缝隙,然后在底座倒入石膏浆,多少大约里面空间的三分之二,封实。最后双手抱住,三百六十五度不停地摇晃,为让浆糊在力的作用下朝四周跑去,形成空心。
他加重语气说,十五分钟才行。待石膏达到凝固,放到桌子上,松开绳子,小心翼翼按顺序一块一块揭下,凉半个钟点,用铅笔刀,把接缝处的毛边轻轻刮去,最后用细砂纸再精心打磨,慢慢晾干,就大功告成了。小复告诉我,坐车到老虎滩大道有个石膏厂去买料。我花了一元钱买了五斤。回来就按小复的步骤立即实施。
经过一番紧张的操作,步骤一个也没落下,尽管抱着摇晃累得我满头大汗,想到一条小“生命”就要在我手里诞生,心里像灌满了蜜。
阴凉了几天之后,再看,那男孩,新鲜出世,棱角分明,栩栩如生,越看越兴奋,哈,竟然成功啦!趴在写字台反复欣赏,石膏像那份白是天然质地,我想到白纸那种简单,但却蕴含无数,我痴迷地瞅着它,小男孩刹那活了,嘴角泛着一丝笑,兴许第一次看见奇妙的世界,单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种要拥抱大自然的怀想。来吧,亲爱的小孩,既然我给了你生命,就要无时无刻呵护你,绝不允许任何东西伤人害你,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的,无论生活苦难多于幸福,烦扰多于平静,每当侧目看到你,就会心安理得。就会嗅到从前。
其实生活就是在颠簸中度过,就是一条不断运动的曲线,就是在无数次布朗运动里找到自我的定力。我从五卅街搬到民主广场的七一街,又搬到甘井子区山东路大钢所分配的428号7楼,又搬到金家街宾馆附近一年左右,换房到香炉礁香秀街6-1号,十年前又住进美域盛景小区,前后搬了五次家。罗马小孩在我精心的保护下至今安然无恙,分毫未损,依旧如故,它已化作我的信念,支撑我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走到今天。弹指间,它已经五十岁。
回忆自己半辈子属于见异思迁、朝秦暮楚的人,早早扔下画笔,最后混进文字里去不能自拔至今。当然,我会给自己找下台阶,艺术的体裁之间是共性的。
因为不管是文学还是绘画,音乐,雕塑等,它们都属于感性活动。情感主宰着艺术活动的整个过程,贯串在艺术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之中。因此,不管这份感情是用什么体裁表达的,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倾诉的领域不一样,实则,殊路同归。人们熟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道理。一言以蔽之,无论多么有出息的家,说道底,都是杂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最好的注解。
而今已到杖乡之年,仍踽踽而行。我渐悟到作家半山所说的:“属于一个人的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包括生命。领悟这点,可以帮助一个人接受很多接受不了的事情。”由此我想到“随性”二字。
我喜欢小提琴,拉不好就会走调,它不是键盘,有固定音;当然耳音准,是关键。大千世界与生活也常常会走调,缘由千奇百怪。我就是在生活里经常走调,上面谈到的两个朋友也几十年渺无音讯,祝他俩平安无事,追求无涯,但不要为名所累,活得更好更长久才为上。
人有时很奇怪,越见不到的东西越想念,于是写下小文,聊以慰藉心灵。
2021/11/25于美域盛景小区寓所
照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左岸,本名杨庭安。大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荣获“中国当代诗歌奖•创作奖”(2011-2012)。短小说多次入选国家级各种年选选本。其《修鞋摊》被选为2017年东北三省四市教研联合体高考模拟试题、并被选为《小小说选刊》改革开放40年成果作品。出版诗集《一只晴朗的苹果》、《灵魂21克》,主编《中国当代短诗鉴赏》,小说集《小鸟是冬天树上的果实》、《冰乳房》等。现居大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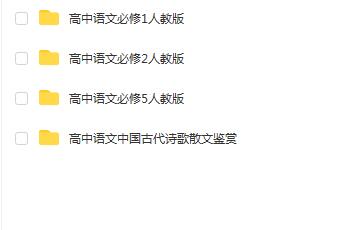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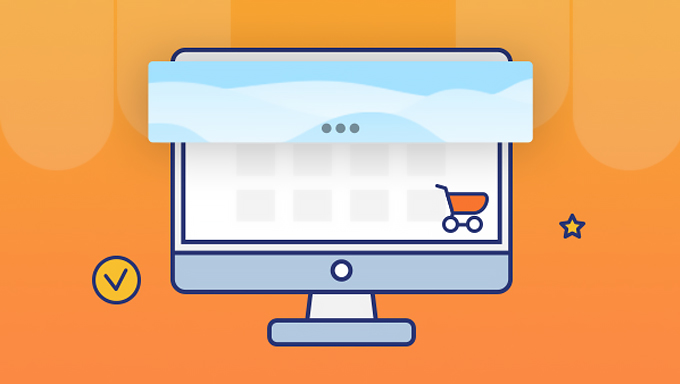
![[MySQL] 老男孩Mysql高级DBA 实战新浪首席DBA 老男孩Mysql视频 老男孩教育杨海朝老师全程主讲](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4027e7101793337f876a14b1ee38c950.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Python] 老男孩Python全栈开发第二期培训视频教程 老男孩教育Python开发课程 前端](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653dcd1a86323be436637425dbcbdd76.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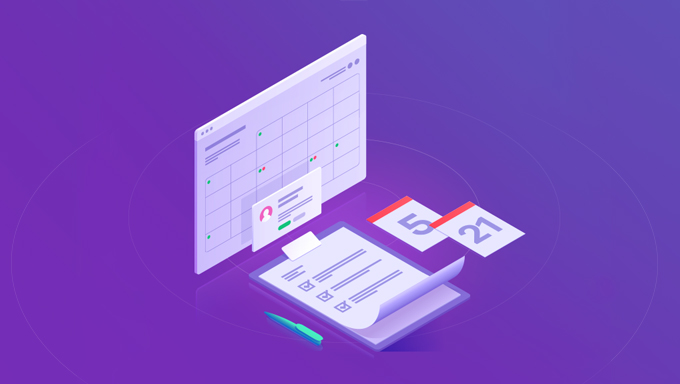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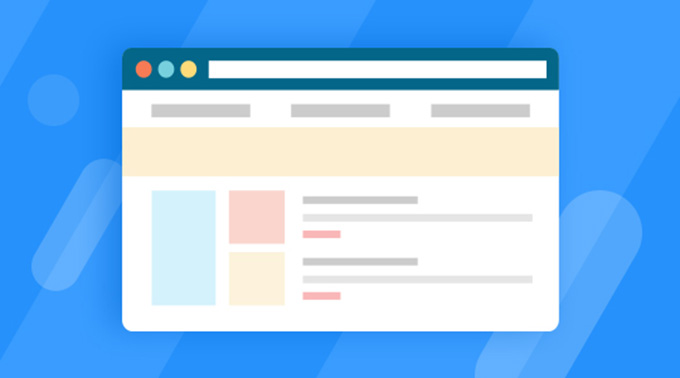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Python] 老男孩Python 高级全栈开发工程师培训教程 老男孩Python企业高级开发视频](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066218374b5f97fd899de7d05f4e502a.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