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413期● 阿拉尔本土文学作品‖肖道纲●天涯长路(剧本连载007)
发布于 2021-11-26 20:57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笔端下的文字●诗文画艺欣赏
微刊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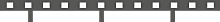



20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天涯长路》,根据肖道纲同名长篇小说改编,仅以此片献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

托儿所栅栏里,秋囡带着十几个孩子在玩耍。
阿宝走过来神秘地看看前后,然而招呼秋囡:“秋囡,来,我给你通个消息。”
秋囡:“什么消息,该不会又要专政谁了吧。”
阿宝:“秋囡,别老是孩子气,长不大,阶级斗争是残酷的。”
秋囡:“什么残酷不残酷,谁要弄到我头上,我会和他拚个你是我活的。”
阿宝:“看你吹牛;看见包谷馍都要昏倒的小姑娘,会动刀子拚命,我不信。”
秋囡:“不信,你就试试;”
阿宝:“我真的有事告诉你!”
秋囡不耐烦地瞟他一眼:“快说!”
阿宝把嘴往前凑凑,压低声音说:“秋囡,听说场里专政大队的要来剪你的头发,说你是‘里通外国’的分子,我好不容易找头头帮你说话,才压下去了。”
秋囡:“是你叫他们来的吧!阿宝,我说你还是少做缺德事,否则,哼!”
阿宝:“那我可不管你啦!”
秋囡:“我今晚就把头发剪掉,你去告诉他们,我谁都不怕!”
阿宝:“哟,想不到秋囡不满有志气的!”
秋囡:“只要他们敢来抓我,我马上叫你现眼报!”
阿宝:“真是狗咬吕洞宾!”
这时,一群人正朝阿宝走来,为首的牧兰举着砍土曼,她气咻咻的喊着:“叛徒张阿宝,我给你拚了,你这个贼娃子,还人模狗样地在十八连晃来晃去,你偷人家小黑子的鸡,你扒人家放水的渠口子,你以为你是谁,我打死你这个上海人的败类!”
阿宝一见牧兰气势汹汹的样子,后面又跟着那么多上海青年,吓得一转头跑了。秋囡哈哈大笑。牧兰还要追,大家拖住。牧兰见阿宝被自己吓跑,这才大声地哭了。秋囡过来劝她。技术员也赶来了,他气愤地说:“看来,是要收拾收拾这帮人,这连队才安宁!”
大道两旁,一边是参天的杨树,一边是渠坎下的沙枣林。
彩娣背着两大花袋棉花,慢慢地往回走。
太阳已落入远处的林带背后,西天一片红云。
忽然,从路那头走过来三麻子。
彩娣一看是专政大队的人,吓得丢掉花袋就往地里跑。
三麻子:“我又不是鬼,你跑什么?”
彩娣仍在跑。
三麻子:“他妈的,我堂堂专政大队的人,还把她吓成这个样子!我倒要问问她怕我什么?”
三麻子也向地里跑去。很快他就追上了彩娣。他抓住彩娣,凶狠地问:“你怕什么?我会吃你吗?”娣缩着头,吓得直打哆嗦。
三麻子:“你吓成这样子?我不相信。听说当初你勾引老林头,吃了喝了,还敢告到场里。我看你胆子不小!”
彩娣:“不是我勾引他的!不是我勾引他的。”
三麻子:“上海洋学生,呸!有什么了不起,不就还是那些玩意儿吧,来,让我看看变了什么没有。”
三麻子撕扯着彩娣的黄军装、黄军裤。
彩娣大叫:“来人呀!来人呀!”
三麻性起,抽着彩娣的嘴巴子:“你再喊!再喊!”
他将彩娣搡到在地:“妈妈的,老林头挨也没挨着,就被告到场部,今天老子要尝尝鲜,看你告到哪里去?告北京去?告诉你,到北京也找不着理儿!”
三麻子解开自己拴在黄棉袄上的皮带,又褪下自己的裤子,他抽着彩娣的嘴巴子,抽一下,叫一声:“脱衣服!”再抽一下,再叫一声“脱裤子!”
彩娣闭上眼,默默地抓着自己的衣裤。三麻子一见小姑娘反抗更朴上去,哼着亲着。忽然,他大叫一声:“哎哟!”
彩娣也吓得瘫了,满嘴是血。她咬掉了三麻子半个舌头。
人们都三五成群立在胡扬树下,立在俱乐部门前,立在林带里,宿舍前,都在传说彩娣的事儿。
“听说三麻要要强奸彩娣!”
“被彩娣咬掉了舌头!”
“上海人好欺侮的吗?叫你不了兜着走!”
“这就是报应!”
“这女子性恶呀,谁沾她谁倒霉!”
“当时咋没咬老林头的舌头呢?”
沙海躺在床上。
(字幕:1969年秋天,农场来了一批戴红牌的部队领导,革委会撤销,群众组织解散,牛棚里的牛鬼蛇神都各回各的单位,原先的领导大都各复其职。沙海也回连当了排长,但胃却还是经常出血。”
太阳从窗户里洒了进来,照在他的床上。
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阿静轻轻地走了进来。
沙海睁开眼,一看是阿静惊喜地叫道:“阿静!”
阿静脸色苍白。但她的眼睛湿润有神,乌黑长眉舒展飞扬。她走到床边把一包东西放在箱子上,然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沙海又叫了一声:“阿静!”
阿静点点头,短发轻轻的闪了闪。
沙海:“阿静,你受苦了!”
阿静笑了:“还好,有毛智们照顾我,吃的也可以,消息也灵通。”
沙海也笑了,彼此庆幸度过难关。
阿静:“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打你,结果还是成了这个样子。”
沙海:“我以为我会死,结果还是活了!”
阿静:“你害怕了?”
沙海:“我当时倒不怕死,怕以后见不到上海的亲人,还怕见不到你!”
阿静乌黑的睫毛遮住了黑眼球,她握住沙海的手又紧了紧。
沙海:“我真想见你!”
她的睫毛微微颤动,灿然的头发轻轻闪动。
他情不自禁地将阿静的手放到自己的腮边,轻轻的摩娑。
阿静轻轻地将前额擦着沙海的眉毛。良久,阿静抬起了头,说:“我要走了,毛智还在大渠边等我。”
沙海:“我送你!”
阿静:“不要起来,免得打草惊蛇。”
沙海点点头,又紧紧握住她的手。她坚决地抽出自己的手:“我走了,保重!”
他看着阿静轻轻地出了门,自言自语:“僵面孔说得好,她是地下党的头头,闪电般来,又闪电般走。”
他自语后,忍不住笑了,然后,久久地兴奋着。
好一会,他才打开箱子上阿静带来的一只牛皮纸包的方型饼干箱,里边是上海奶糖、饼干、肉松、香肠和云南白药。沙海抱着饼干箱子,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
连长、指导员坐在讲桌边。桌上放着两盏马灯。
指导员:“刚才已经念了文件,现在文教张建成提升为我们连的副连长,秀才宋百封任文教,希望大家收收心,把精力都放到生产上来。这几年,土地荒了几千亩,没荒的产量也下降了一半,从现在起,六个排长都要管好自己的人,技术员负责生产技术,文教要抓好田管各阶段的劳动竞赛,一切工作都要上正轨。过去两派间有隔核的,都要消除前嫌,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下面连长讲讲生产问题。”
连长:“当前最要紧的是收割水稻,沙海、勇发的男生排,牧兰的女生排,还有三排八排,全部上阵,每人每天割一亩地水稻,超额完成任务的发一、二、三等能手证。五排老职工妇女排去收包谷。小黑子当副连长,要和秀才组织好劳动竞赛。牛号老胡老婆先放着羊,托儿所颜宏昆老婆跟她那无产阶级革命派老头子调走了,现在只有秋囡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这样吧,等忙完这阵子再给你加一个人,好吧,秋囡,你一个人要多操心。”
技术员和牧兰站在胡扬树下说悄悄话。
牧兰:“技术员,我想把三农我管的100亩水稻地单独收打!”
技术员:“你是想看看亩产多少,我知道你的心思。”
牧兰:“这样我心里才有数,明年我想在场里夺高产。”
技术员:“又想当标兵了。”
牧兰在黑暗中点点头:“闹派性耽误两年了。”
技术员:“好的,我给连长讲,单打单收。”
牧兰:“谢谢你,技术员!”
技术员:“谢什么,咱们俩是有共同理想的嘛!”
牧兰不吭气了。
技术员:“是不是?”
牧兰仍不答话。
技术员沉呤片刻不追问她了,抓住牧兰的手,轻轻地问:“牧兰,咱俩难道没有共同理想!”
牧兰嗔怪地:“你真坏,非要叫人家说什么嘛?”
技术员一下子挽住牧兰的脖胫:“好,不说,不说!”
两人拥在一起,长久地不说一句话。
伙房后面的井台上,秋囡在提水洗小孩的几个尿布。洗完后,她提着一桶水,往托儿所走去。
秋囡把水桶放在火墙边,凉好尿布。她大声喊着:“小朋友,起床了!”
她给不会穿鞋的孩子穿鞋系带,一个个牵到小长条凳上坐好。
忽然,她喊了一声:“红红”,没孩子答应,她又喊了一声:“红红”,还是没人答应。秋囡急了,跑到托儿所棚子栅栏门口放开喉咙喊:“红红!红红!”
这时,秀才从办公室里过来:“秋囡,怎么啦!”
秋囡焦急地说:“指导员家的小四不见了!”
秀才:“指导员家的!”
秋囡:“是呀,来,你来给我把娃娃看住,我到处去找找!”
秋囡在厕所后面的地里边走边喊:“红红!红红!”又站在厕所门口伸头唤了几声,仍是不见孩子。
秋囡围着胡扬树前前后后绕了几圈,喉咙也喊涩了,仍没回音。
秋囡边哭边给连长汇报红红丢扔的情况。
连长说:“不会有啥事吧?走,到托儿所看看。
连长看了看红红睡的床,小被子掀开一半。
连长:“看来是睡觉时,爬起来逃走的。”
秋囡:“指导员今天在场部开会,不在家。红红妈妈在地里突击收包谷。他三个姐姐都在上学。”
连长:“这几天突击劳动,家里也没人,小家伙出去,也没人看见。”
有人在托儿所栅栏外面说:“妈的,刚平静几天,又有人兴风作浪了!”
连长:“不要瞎说,还不知道娃娃在哪呢?”
秀才:“也难说,这种时代,沉渣泛起,人的恶性就发作了,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连长:“涝坝边喊过没有?”
秋囡:“喊过了!”
连长对着托儿所外面几个人说:“快,你们到大渠上去看看!”
秋囡这时,忍不住大声哭了。
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孩子失踪的事。
指导员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女人的哭声。
秋囡瑟瑟缩缩靠在被子上。大家七嘴八舌问她。
沙海:“你离开过托儿所没有?”
秋囡:“娃娃吃了中饭,我把他们弄睡了,就到厕所去了一趟。然后,我就到井上洗了几张尿布,提了一桶水,最多十几分钟。”
牧兰:“十几分钟,人要走几百米远呢!”
秋囡吓得直点头:“我没想到他会逃呀!”
金良:“我看不是他逃走了,而是有人把他弄走了!”
大头:“秀才说,已经向场部保卫组报案了。”
秋囡一听报案,吓得又“呜呜”地哭出声来。
有人说:“是不是原来专政大队那帮子人又来报复了?”
沙海:“不要瞎说,保卫组的人会来调查的。”
巧蕙:“指导员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谁把他的孩子丢掉了……。”
沙海给巧蕙摇摇头,示意她别当着秋囡乱说:“好了,大家都休息去吧!”
其他宿舍的人都走了,沙海对秋囡说:“秋囡,你平时发现过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秋囡:“没有呀!就是去年拿锄头打阿宝的那天,阿宝说,专政大队的要剪我的头发,说我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说他说服了专政大队的人,是他保护了我。我当时火了,顶了他,说是他出的歪主意。其他人,我没得罪过谁呀?
巧蕙:“也不一定是冲秋囡的,会不会是冲指导员的。”
牧兰:“冲指导员,也不能害人家的娃娃呀!”
秋囡:“要是红红被人害了,我也脱不了干系呀!”
沙海:“别怕!等查案的人来了以后,你把情况给他们讲清楚。”
秋囡:“我也讲不清爽呀!”
半夜,月黑风高,老胡扬树“刷刷”地摇来摆去。
一个人影从女生宿舍出来。是秋囡,她提着一个黄书包,踮着脚尖,往厕所背后走去。
她急急行在包谷地中,偶尔抬头看,是沉沉的夜空。
两只脚,快快地在芦苇地走着。风吹着芦苇,吹着秋囡的头发。
秋囡已躲在一辆空的车斗里,蓬布盖着她的身体。
连长和秀枝正在吃饭。
牧兰和沙海进门来。
牧兰:“连长!不好,秋囡不知道哪里去了?”
连长:“什么?人不见了?”
沙海:“昨天晚上,她就吓得要死。”
连长:“她不要再出什么事啊!”
秀枝:“还不快派人去找一找!”
沙海:“我们排出去五个人分头去找了!”
牧兰忽然哽咽了:“连长,向场里报案吧!”
连长:“妈屁,啥球世道!简直叫人安不下心来工作!”
秀枝:“刚来塔里木时就不习惯新疆,想回上海。现在习惯了,这些不得好死的人,又逼得人家逃了!”
秀枝去打开鸡窝门,放下一个食盆,喂鸡。
她站在那里看鸡吃食。忽然,她一抬头,看见自家的鸡窝上有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打倒×××!”的字样。她惊骇得嘴打哆嗦,一转身跑回自己家。
秀枝跌跌撞撞进了门:“不好了!不好了!”
连长:“怎么啦,秋囡出事啦?”
秀技:“是,是,是我发现咱家鸡窝上有一张反动标语。”
连长大惊:“妈妈的,整到老子头上了!”
连长大步跨出门去。
指导员、小黑子、秀才、连长几个人围着鸡窝。
指导员:“我说,先把这反动标语收起来,免得扩大影响。赶快向场里报案。妈的,我的小四还没有下落,又搞这坐班房的反革命栽脏事件,这个阶级敌人完全是向我们的新的领导班子报复。连长、张副连长,我马上到场部保卫组去汇报一下情况。”
连长:“24小时内出了三件事,我心里乱得很!我还是下地去。小黑子,你派个人到托儿所去看娃娃。秀才,再带几个人找找秋囡。”
秀才:“好的。”
连长、指导员、小黑子、秀才三人在办公室。
连长:“场部保卫组是吃干饭的吗?报案了一个星期,都不来人!啥玩意儿!”
指导员:“人死吗,不得有个尸体吗,俺门家小四就这样无影无踪了!我老婆都一个星期没起床了,饭都没正儿八经吃过一口。你说这真是倒八辈子霉子,这几年,我们家就没安宁过。”
小黑子:“当牛鬼蛇神,我们几个都没少挨打,咳,你们说,这些事儿,是不是那帮人干的?”
连长:“烦得很,一说起牛鬼蛇神,我背脊上就发寒。噢,还有事呢?小黑子,勇发不是手指扎了刺化脓了吗?明天叫他别劳动了,夜晚叫他去花场换班守守花场,今天棉花刚上场,我们得小心点,派个有责任心的人去守夜。”
干冷的秋夜。花场上一大堆白白的棉花。
勇发左手食指包着沙布,整个左手放在套在脖子上的白沙布条里,他慢慢在花场上转圈。转一圈后坐在棚子前一只木墩上。然后,他又站起,又绕着花场走一圈。
夜,静静的,只有一阵风吹来,场边的白杨林带才发出沙沙的声音。
月亮西沉如钩,远处,夜鸟偶啼。
勇发又坐到木墩上,身子靠着棚子。两只大眼,在夜色中闪着2点光亮。
忽然,一声雄鸡啼鸣穿透夜空,从远处的连队传来。勇发打了一个哈欠,把靠着棚子的背动了动,想瞌睡。可是,他又站起来,又围着花场转了一圈。夜,平静得死一般寂静。
勇发又坐在木墩上,仍将背靠在棚子上。这时,勇发又听见一声鸡鸣,他自语:“快天亮了!”
他刚刚闭上眼睛,忽然,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嘴里喊道:“着死哩!”
花堆那边闪着亮光,火焰一下子冲过花堆。
勇发抓起地上一把捞花的耙子,一下子翻上花堆发疯似把那些着了的花扒下花堆。可是扒了这边,那边又着了,他一个人招架不住。
金良从宿舍出来,正在林带里解手,一歪头,看见远处花场上的火光。他慌得大叫:“失火啦!失火啦!”
秀才跳出门来,立即向老胡杨跑去,礑礑礑地敲起了钟。
一刹时,满院子里拿盆的、提桶的、拿砍土曼的都向花场跑去。几乎人人都在喊:“救火啦!失火了!”
人们赶到花场,见勇发裤脚着了火,眉毛头发都焦了。大家齐心把着火的棉花全部扒下花堆,又将扒下的着火的棉花全部扑灭。
指导员问勇发:“怎么回事,你睡着了吗?”
勇发:“没有呀,我刚转了一圈,坐下,正想瞌睡,一下子就窜起火来。我跳上花堆,就往下扒。可是收拾不住呀!”
连长:“幸好发现快,否则全花堆都着完球了!”
人们七嘴八舌,纷纷声讨放火的人。
“阶级敌人人不死,心不灭呀!”
“妈的个屁,谁放的火,抓住他狗日的送劳改队!”
“我看咱连得清理一下阶级队伍,把坏人抓出来!”
“奶奶的,搞地下活动,少不了那几个狗日的!”
“操他妈,这些人开始干杀人放火的事了!”
“强烈要求场里派人来侦破呀!”
指导员:“勇发,快去叫卫生员看看,烧伤的地方要涂点药。”
勇发这下咧着嘴叫“哎哟!”
俱乐部正在开大会。保卫组三人坐在台上。
保卫组组长正在讲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心中也是有数的,如果干了坏事,赶快来给我讲,坦白从宽;如果群众有线索,找我们谈,我们一定保密。”
保卫组长两眼放光,视线扫射着会场下面职工。下面的人,个个紧张、严肃。没有一个人乱说乱动,女的也没一个人纳鞋底、打毛衣。男的没有一个敢抽烟。
三个保卫组的同志正在讨论案子。
组长:“两天了,也没几个人来揭发什么人。”
一个说:“只有一个分析,是原来夺权组织的人,说他们没当上官,心不死,相报复。”
这时,张阿宝进来了,他提了两只热水瓶。他客气地说:“组长,天气冷,你们都用热水烫烫脚!”
组长:“谢谢!张排长,你说说对这几桩案子的看法。”
阿宝:“真的不好说,我看是有人故意搅昏水,让连长指导员他们怀疑过去对立派的人。”
组长:“那也不致于把娃娃给人家搞失踪了。人命关天啊!”
阿宝:“反正,这几年都无法无天惯了,没把杀人放火当回事了。”
组长:“那你最怀疑的是什么人?”
阿宝:“不好说,反标是要进劳改队的,谁敢胡来呢?”
组长:“那你对秋囡的看法呢?”
阿宝:“还不是怕追查责任,逃回上海了呗!”
组长:“你对勇发的看法呢?”
阿宝:“他干活认真呀!可是,怎么会他看花场时,又偏偏失火呢?”
组长:“好,谢谢你的热水,你回去休息!”
阿宝:“不要紧的,我每天给你们提点水来。”
炉子烧得旺旺的,三张床上各躺着三个女生,旁边都坐着一个男生,都说悄悄话在谈恋爱。“
不谈恋爱的围着炉子。巧蕙坐在炉门前,不停地加柴禾。彩娣在打毛衣。大头蹲在火墙边。达铭站着在吹口琴。秀才和巴子在悄声说话。
巧蕙忽然说:”这日子,没办法过了。雪菲回上海了,秋囡也逃走了。曼莉淹死了。三个案子都还没破,还不知,以后会出什么事呢?”
巴子说:“阿拉来新疆,是争取好的前途,谁知这几年把阿拉整惨了。过去还有点油吃,这两年慌了地,炒菜连油也少得可怜,这儿还有什么盼头!”
一个谈恋爱的男生说:“吃不好吗,只有谈朋友充实精神罗!”
秀才:“有道理!有道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摇头,有人做怪相。
大头:“秀才,你说说,有什么道理”
秀才:“物欲不满足,当然就追求性欲罗!”
女孩子们:“要死咧!要死咧!”
巴子:“我们二十多岁了,怎么办?难道就在此成家?”
大头:“我,坚决不在新疆过一辈子。”
巧蕙:“倒马桶,拾垃圾,你也回上海?”
达铭:“我是不回去,回去也是特务嫌疑分子,我还不如在兵团,当个军垦战士。”
大头:“秀才,你有远见,你给大家说说,到底谁有道理。”
秀才:“我进牛棚时,专政大队的人说我的国际象棋谱是‘赌经’,把我的英语课文烧了,还砸了我的收音机。但是,我还是不改我的初衷,我仍然要学习、看书,我相信,学习总是有用的。我的观点是,无论回上海还是在兵团,无论当官还是放羊,绝不能浪费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多学习,争取将来派用场。”
僵面孔不知什么时候进了门,他说:“我不喜欢学习,那怎么办?”
巴子:“那我们就听从毛主席安排吧。”
忽然门外响起了《克拉玛依之歌》的男中音,接着,沙海、勇发陪着嘉毅进门来了。大家高兴得欢呼起来。
巧蕙:“嘉毅,你在文工团也是个名角了吧?你们那次来场部演出,你唱的《克拉玛依之歌》,简直迷煞塌人啦,我们都叫你嘉毅,可其他连队的人都叫你“克拉玛依”知道啵!”
沙海说:“文工团解散了,嘉毅回连了。”
众人又吃惊,都在说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世难测呵!”
“艺术家又成农工了?”
“回来也好,大家一道,蛮好的!”
达铭惆怅地摇了摇头:“我吗是有才没人敢用,你是有才又有人敢用,可惜世道不行,完了,没前途了呀,像我一样,永远农工!”
嘉毅:“好,我永远是十八连的农工!”
达铭:“塔里木呵,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是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太可怕了,将来,我们都会慢慢死在塔里木,埋葬在塔里木,永远守望苍原!”
巧蕙:“和曼莉一样,永远葬身塔里木河?”
大头:“嘉毅出去又回来了,我们却还没出过塔里木呢!”
勇发:“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树挪死,人挪活,我迟早要回去的,不过,我要找个正常的途径,绝不会逃回去!”
(画外音)“昏暗的油灯下,人们叹息、沮丧,诅咒、我不着一个方向。”
沙海:“依我看,还是好好干活。像勇发经常说的那样,不要浪费生命,像秀才说的那样,不要浪费时间,就是修地球也要修个名堂出来!”
巧蕙:“我只想修个带阁楼的房子,花瓶里边插着鲜花,摆在红木家俱上。”
勇发:“像蓝丝带一样美好的梦!”
大家都笑了。
沙海:“休息吧!休息吧!”
大家都散了。
彩娣站起来,放下毛衣叹了一口气,对那三个谈恋爱的男生下队逐客令:“回吧,回吧,12点钟了!”
牧兰和周其旺站在胡杨树下,靠着树身谈情说爱。
其旺:“牧兰现在有探亲假了,我们一起回口内探一次亲吧!”
牧兰:“我们一道走,别人不笑话!”
其旺:“怕什么,我俩正经谈朋友的嘛!”
牧兰:“那我家里还不知道呢。”
其旺:“明天就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说你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牧兰:“不好意思的啦!”
其旺一把拥住她,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牧兰,我俩是一对最适合的对象。”
牧兰马上说:“有共同理想!”
其旺猛地亲她一口:“机灵鬼!”
牧兰:“其实,我老早就喜你了!”
其旺:“我喜欢你的鼻头!”他又吻吻她的鼻子。
其旺:“我更喜欢你的人,知道上进,”他吻住她的嘴巴。
寒月在幽蓝的夜空移动了一大截子,一只树叶儿落下来,掉到牧兰的头上,她忽然说:“不要有鬼啊!”两人终于匆匆离开了胡杨树。
勇发、沙海、大头坐在长条凳上,连长站着给他们交待:“这一批只批准你们三人回去探亲,我也有我的打算,第一,曼莉掉塔里木河以后,没见尸体,说她没淹死了吧,家里都没个消息,这次回去,沙海和大头都到曼莉家看看。第二,雪菲肯定是回上海了,因为阿静是她表姐,当然自有安排,但不管怎么说,雪菲这孩子跟老伍养猪,是有成绩的。勇发回上海去看看她,代连里问声好,说老伍想念她,给他派人去跟他养猪,他说啥也不要,说要等雪菲回来。第三,为了指导员小四失踪的事,秋囡吓得逃走了,至今也没个音信,你们去她家看看,安慰安慰她。
三个人的住址我都叫秀才到劳资股去抄来了,你们都抄一份带到身上,回去一定要打听清楚她们的下落。”
沙海:“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大头:“我真不敢到曼莉家去,是我叫她们上的船,是我惹的祸,我害怕了。”
勇发:“行啦,前两年大家都疯了,谁怪谁呢?”
沙海、勇发、大头出了上海火车站。
火车站人头挤挤,灯光通明。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都说:“这就是阿拉上海”
三人分手,各去自已家。
大头进了弄堂口,弄堂静悄悄的。
头上是晾满衣裳的竹竿。
进了楼梯口,他往上走。他摸着开关,“咔嚓”一声,灯亮了。楼梯又窄又陡。他笑了,摇摇头,自言自语说:“万古荒草都变绿洲了,这里还是老样子!”
他上了二楼,站在门口,靠着门听了听,才轻轻敲了敲那紫色的木门,没回声。咚咚咚,他用劲又敲了几下。
门里问:“啥人呀?”
大头:“是我,姆妈!”他的喉咙梗住了。
门里还问:“啥人呀?”“喀嚓”一声,门里在开灯。
门开了,一个50来岁的妇女伸出了头:“啥人呀,介晚了!”
大头:“姆妈!是我呀!”宋飞一下子抱住了母亲,哭了。
母亲哭着:“飞飞!是飞飞!是我儿子回来啦!老甲鱼,快起来,阿拉儿子回来啦!”
里屋,老爷子:“啥人呀!”
母亲:“死人呀,快起来,阿拉飞飞,阿拉新疆的独生子回上海来啦!”
父亲:“飞飞?儿子?阿拉飞飞回来啦?”
母亲:“快点,快起来!”
大头:“爸,是我回来啦!”
父亲鞋也也没来得及穿,就走出来了。
儿抱住父亲。
父亲:“今朝是啥好日子,老天爷把我儿子送回来啦!”
母亲又把儿子拉过来,上下打量着,摸摸头,摸摸肩,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老甲鱼,你把我儿子放天边去了,快把我眼睛哭瞎了呀!”
老爷子看看儿子,也滴下了眼泪,他拍拍儿子的背说:“好!长大了,黑了,像个男子汉了,飞飞呀,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上海家长都到街道办事处来造反,把主任打得死去活来。说孩子们在那寸草不长的沙漠去,像犯人一样干活,肚皮也吃不饱,还说,那里有人把上海青年围到房子里乱打,死了好多人。”
大头:“爸,姆妈!听我慢慢说!”不过,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母亲:“有的吃的!有的吃的!泡饭、带鱼、小白菜。”
大头:“好的,几年了,就没吃过带鱼。”
母亲:“作孽啊,作孽啊!”
宋飞边吃边说:“还是上海饭好吃,还是上海菜香。”
母亲:“飞飞,从小顽皮,出去又没爹娘管你,你惹过事吗?那些坏蛋打过你吗?吃过大亏吗?”
大头:“小亏吗总要吃的,大亏没吃过。”
母亲:“是你学好,还是领导管得好!”
母亲:“领导比爹娘管得严,训起人来好厉害呀!上班迟到一分钟也不行,下班也不能早收工。”
父亲:“这是好领导,把儿子也管好了。”
大头不言语了。好一会才说:“你们喜欢这样的领导?”
父亲:“经过严格的训练,娃娃就容易成材!”
大头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不过也是。”
母亲:“听说新疆吃不饱?”
大头:“有时,我真想到伙房去抢两个馍吃。”
母亲:‘没偷过吧?”
大头:“没!不过偷过瓜”
母亲:“作孽啊,小孩子都成贼了呀!”
大头:“听那些老职工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农民都在人民公社吃青!”
父亲:“阿拉是上海人,上海人不作兴偷盗的。”
大头:“不过,我们每顿都有一个馍吃,只是我不够吃!”
母亲:“妈知道了,下次每月给你寄几斤挂面、咸肉给你。”
大头:“姆妈,谢谢你。我真想吃咸肉,那些资本家出身的有钱人,一个月收到两个包裹的都有,有的谈女朋友的,小姑娘吃得少,省下来都给男孩子吃。”
父亲:“你有女朋友吗?”
大头:“没有。”
母亲:“那你就可怜了!”
大头:“姆妈,我不可怜,我在连队都是主要劳动力了!”
父亲:“不错不错,阿拉儿子也长成人了!”
勇发边走边看门牌号码,一个店铺一个店铺,一个弄堂一个弄堂数过去。正在东张西望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勇发!”
他转过头,看见了雪菲。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勇发:“雪菲,我正要到你家去找你。”
雪菲激动脸通红:“你怎么回来了?”
勇发:“现在兵团职工可以探亲了。”
雪菲:“太好了!勇发,我走了,没有找麻烦吧?”
勇发:“谁也不知道是老伍和我把你送去的,连沙海都不知道。”
雪菲:“说明老伍和维族老乡都是可靠的。”
勇发打量着雪菲:“雪菲,回上海来,你可洋气多了,我都不敢认你了。”
雪菲:“走,到我家去。”
33、雪菲家日内
雪菲家的客厅里,摆着沙发、长条茶儿,墙上挂着一幅油画。
勇发和雪菲一进门,就睁大了眼睛:“哟,西洋式的客厅呀?”
雪菲:“这房子是阿拉香港的伯伯买的,他在抗战时期捐过一大笔钱,街道的老人都知道。我父亲是地理学家,经常出外,满辛苦的。不知怎么搞的就躲过了红卫兵的抄家,真是上帝保佑。”
勇发:“我有点怕也,你父母呢?”
雪菲给勇发冲了一杯咖啡,放在茶几上:“父亲到广西去了。母亲在大学里,没事干,但每天还得去,扫扫地什么的。别怕,我哥哥到香港四年了,我现在是家里的当权派。”
雪菲帮勇发脱掉军棉大衣,挂在衣架上。示意他坐在真皮沙发上。勇发不敢坐。
雪菲拉住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不等勇发明白过来,他就搂住了他的脖颈,对着他耳朵说:“勇发,我天天在想你,担心你!”
勇发:“后来,我、排长好多人被抓进牛棚当了牛鬼蛇神。”
雪菲:“哦,我知道他们会抓你的。上海也是这样,凡好人,真本事的人,都揪斗了。勇发,他们打你了吗?”
勇发:“踢一脚推一把是少不了的,我拚命干活呀!”
雪菲心疼地:“我知道你吃苦最多。”
勇发:“冬天,罚我们赤脚立在冰上,这是我最受不了的。后来,有人还放火害我。”
雪菲:“勇发,你受的罪太多了,十八连就数你干活最多!”
她抱住他,不停地抚弄他的头发、他的脸,把自己的脸挨着他的脸;”勇发,我们是一对可怜的人;明明不喜欢的事却非要我们干,可我们还要干得最好!”
勇发也笨拙地亲吻着雪菲花瓣似的嘴唇。
雪菲喃喃地说:“勇发,我喜欢你。”
勇发:“我也是。”
雪菲:“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勇发:“远远!”
勇发忽然坐了起来,他走到油画前:“奇怪这幅画里的那棵树,真像阿拉十八连的那棵老胡杨树。”
雪菲也走到画前:“这是18世纪欧洲的一幅油画;”
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那幅画,画中草原上有一条路一直通往远方。途中,有一棵大树,那树型,浓荫,酷似十八连那棵老胡杨。
雪菲端起茶几上的咖啡,送到勇发唇连,他喝了一点,又喝了一点。
放下茶杯,她拥着勇发向她的卧室走去,她详:“亚,到我卧室亚,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雪菲房子挂着黄色厚毛的落地窗幔。梳妆台上摆着名贵的香水和雪花膏瓶子。立柜和书桌黑明锃亮。订罩上印着紫红色的圣诞老人和戴小红帽的孩子们,漂亮极了。
雪菲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只丝绒盒子,拿出一块石头,给勇发看。
勇发:“这不是伍班长红宝书上的那块石头吗?”
雪菲笑了,抿着嘴点点头。
勇发:“这不是和田玉石吗?这宝石是他1950年解放和田时捡的。”
雪菲:“我偷着拿走的?“
勇发:”你也偷东西?“
雪菲点点头。
勇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老伍把你当最单纯、最美的女孩子,你却偷他的宝物。”
雪菲:“我想新疆时,就拿出来看看。看见它,我就像看见了老伍和你们,看见你们在摘棉花,在说说笑笑……。”
勇发抱住雪菲:“那你还回新疆去吗?”
雪菲:“勇发,我天天在想你,担心你!”
勇发:“后来,我、排长,好多人被抓进牛棚当了牛鬼蛇神。”
雪菲:“哦,我知道他们会抓你的。上海也是这样,凡好人,有本事的人都揪斗了。勇发,他们打你了吗?”
勇发:“踢一脚推一把是少不了的,我拚命干活呀!”
雪菲心疼地:“我知道你吃苦最多。”
勇发:“冬天,罚我们赤脚立在冰上,这是我受不了的。后来,有人还放火害我。”
雪菲:“勇发,侬受的罪太多了,十八连就数你干重活最多!”
她所住他,不停地抚弄他的头发,他的脸,把自己的脸挨着他的脸:“勇发,我们是一对可怜的人;明明不喜欢的事却非要我们干,可我们还要干得最好!”
勇发也笨拙地亲吻着雪菲花瓣似的嘴唇。
雪菲喃喃地说:“勇发,我喜欢你。”
勇发:“我也是。”
雪菲:“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勇发:“永远!”
勇发忽然坐了起来,他走到油画前:“奇怪这幅画里的那棵树,真像阿拉十八连的那棵老胡杨树。”
雪菲也走到画前:“这是18世纪欧洲的一幅油画。”
他们久久地注视着那幅画,画中草原上有一条路一直通往远方。途中,有一棵大树,那树型、浓荫,酷似十八连那棵老胡杨。
雪菲端起茶几上的咖啡,送到勇发唇边,他喝了一点,又喝了一点。
放下茶杯,她拥着勇发向她的卧室走去,她说:“来,到我卧室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雪菲房子挂着黄色厚重的落地窗幔。梳妆台上摆着名贵的香水和雪花膏瓶子。立柜和书桌黑明锃亮。床罩上印着紫红色的圣诞老人和戴小红帽的孩子们,漂亮极了。
雪菲从书桌抽屉拿出一只丝绒盒子,拿出一块石头,给勇发看。
勇发:“这不是伍班长红宝书上的那块石头吗?”
雪菲笑了,抿着嘴点点头。
勇发:“这不是和田玉石吗?这玉石是他1950年解放和田时拣的。“
雪菲:“我偷着拿走的。”
勇发:“你也偷东西?”


笔端下的文字●诗文画艺欣赏
总413期●2021年第62期

微刊主编●图文编辑:海阔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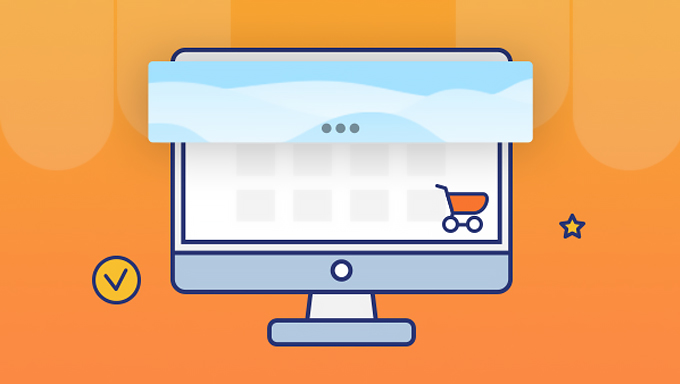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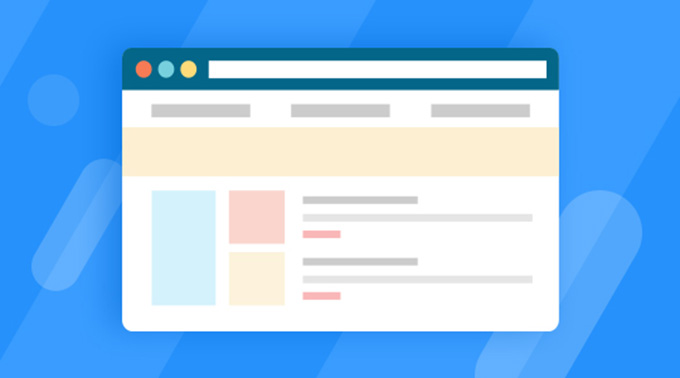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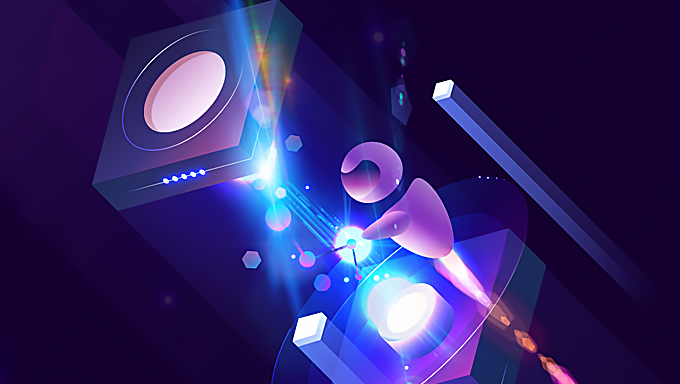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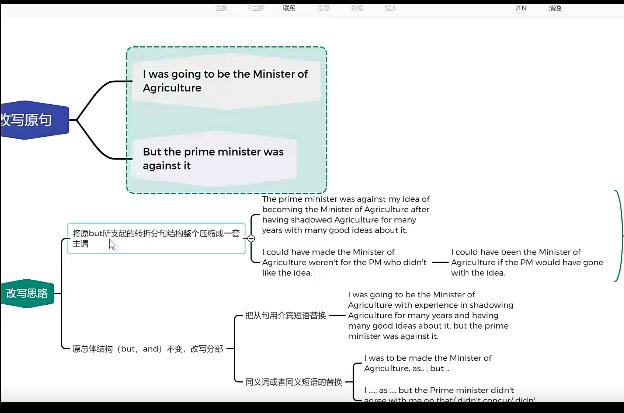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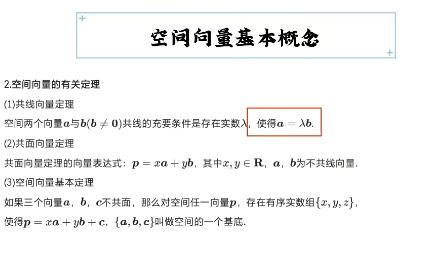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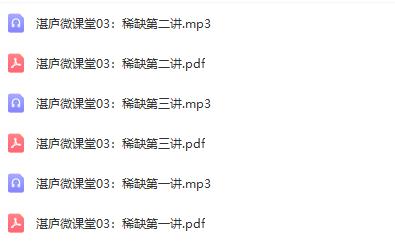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