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张法 教授 ‖ 中、西、印美学比较中的喜
发布于 2021-11-30 13:50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中、西、印美学比较中的“喜”
张 法

[作者简介]张法,1982年在四川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宾州州立大学、1996—1997年在哈佛大学、2002—2003年在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20);主要从事美学、审美文化、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美学的中国话语》《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等。
摘 要
在美学中,“喜”是低于人而又于人无害的笑的对象。它有三种类型:一是生活中的眼前之景的笑,以具体的场景为主。这时的笑,以美学方式强调和维护正常为其文化功能。二是与生活之笑同质的小型艺术之笑,如中国的宋杂剧和印度的笑剧,以及当代的的脱口秀、相声、喜剧小品等。这是把生活之笑进行艺术集中和典型化,突显了文化对笑的焦点。三是艺术型的整体叙事之笑,体现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戏剧中的喜剧、文艺复兴以来的喜剧性小说,20世纪以来的喜剧性电影。这是把笑作为专门的审美类型进行呈现和探讨,使审美之“喜”得到突显。中国和印度的审美之喜,以前两类为主,都把审美之笑视为审美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有紧密的关联,不能将之独立出来。这与中印两国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宇宙整体的设定相关。西方的审美之喜,以后一类为主。这是因西方文化对宇宙作已知部分和未知部分两分而产生。由于审美的喜之知被限定在已知世界之中,从而被作了单独的呈现和专门的思考。审美之喜的中、西、印差异,在分散的世界史中各自发展,但现代性进程把世界带进统一的世界史之后,三大文化的三种不同的审美之喜开始了互动和互补。前两种类型在西方有了新的演进,后一种类型在中国和印度也已出现并有了新的进展。三类审美之喜的互动,构成了审美之喜的新型景观。而审美之喜的核心,也得到了更鲜明的突出,主要有五点:第一,喜的对象是引人笑的对象。第二,这一对象具有在形体上、心智上、言语上、行动上低于正常尺度的特征,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组合。第三,这种低于正常最初是以正常的面貌出现的,使人们用正常的眼光去期待其正常运行;但这一正常却在言语和行动的运行中,突然显示出非正常的失常。第四,主体面对这一突显的失常,往往是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第五,主体的笑,一方面感到对象的低下,并意识到了何为低下,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处在正常,并意识到了何为正常,因而笑是从这两个方面的合力产生出来的。文化的正常在这笑中得到了维护,文化的失常在这笑中得到了。
关键词
审美之喜 美学比较 三种类型 多元演进
审美之“喜”是美学中的一大类型,形态多样而理论不少,但审美之“喜”究竟是怎样的?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自轴心时代以来已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理论言说,在现代性以来的文化互动中又有新的演进与思考。本文力图通过中、西、印关于审美之喜的呈现和分析,希望进入到这一现象的理论本质中去。
如果对审美类型作区分的话,它可以分为美、悲、喜三大类。在这三大类型中,“美”是与人同一并与人的理想相连的对象,“悲”是比人强大而与人敌对的对象,“喜”是比人低下且于人无害的对象。美的对象在社会、自然、艺术中大量存在,易感易言;悲、喜相对来讲较为困难,二者要成为审美对象需要一定的条件。悲既比人强大并与人敌对,其成为审美对象的条件在于人处于安全地带。人在安全房屋的窗前,观赏暴风雨,后者成为审美对象。在艺术中,悲的对象虽然比人强大并与人敌对,但伤害不了人,从而成为审美对象。喜成为审美对象同样需要一些条件,而且更为复杂。对此,世界各文化美学都有言说。下面,仅从中、西、印三大主要文化对喜为审美对象的理论进行归纳,呈现其基本特征。
第一,“喜”从西文的“the comic”(喜剧性)更好理解。西方的喜剧性第一次在希腊的“comedy”(喜剧)得到典型的体现,而喜剧的核心就是“喜剧性”。喜剧落实到细节上就是“funny”(滑稽)或者“thecomic”(滑稽)。可以说,“滑稽”是美学之喜的核心。如果从各文化美学的比较上讲,“喜”(thecomic)的对象不是“喜”而是“笑”,正如希腊佚名的《喜剧论纲》讲的:“喜剧来自笑。”这笑不是一般的“笑”(smile),而是特殊的“laugher”(笑),即这笑是有限定的,由低于人而又对人无害的对象(即喜的对象)所引起。笑,从内容上讲,是人对自己的正常得到肯定而生的满足和开心,虽然开心之笑缘于对象的低于正常,但开心运行的结果是对正常的珍惜,突出了对社会和文化的正常的维护。其深处,是维护宇宙整体的正常运行。正是在宇宙应正常运转这一目标上,笑之喜与美之娱、悲之乐,具有了“美感之感”(amusement)的共性。可以说,并非喜剧性客体的“喜”,而是主体的美感之“喜”,是笑的审美本质。喜的对象“the
comic”使人产生笑,笑的结果是达到包含喜的特殊性和美感共同性为一体之“喜”(comic
amusement)。笑最后走向美感之感的共同性。笑是喜的审美表现(使笑作为美感之感的特殊性突显出来)。因此,用汉语“喜”字来对译西方的“the
comic”(喜剧性),更好地呈现了审美之喜由始至终的运行全图。
第二,“低于人”。这里的低于人,指的是低于人的正常尺度。这一正常在古希腊,就是德尔斐神谕讲的“认识你自己”中的“自己”。在演进中,被希腊哲学规定为人的本质,实际上体现为具体社会的整体本质。进一步讲,是人应按此本质对自己进行理性的和自觉的自我管理。人在与低于自己的对象的对比中,既感到了对象低于业已拥有人的本质的自己而产生笑,这笑内蕴着主体对自己作为正常而感到的满足和自尊,霍布斯(T. Hobbes,1588—1679)名之曰“superiority”(优越感);同时,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何为正常,增强着维护正常之心。“低于”之低有三个方面:一是外在形象偏离正常之低,如矮人、侏儒、畸形、残疾等。二是内在智力偏离正常之低。三是行为和语言偏离正常之低。前两种是由历史演进形成的,是产生美学之喜的天然基础。这一基础被艺术之喜进行了充分的运用,而成为喜的典型形象(前者成为喜的艺术中丑角的外形,如方成的漫画《武大郎开店》;后者成历代笑话中的角色,如康德讲喜的例子,一个黑奴说,我并不奇怪这么多啤酒泡是怎么冒出来的,只奇怪它们是怎么被装进去的)。第三种既可产生于低下的形体和低下的智力中,但更多地产生于正常的形体和正常的智力中,正常的形体和正常的智力出现了偏离或低于正常的行为和言语,使其偏离正常的言语与行为与正常的形体与智力形成强烈对比,哈奇生(F.Hutcheson,1694—1746)将其命名为“incongruity”(不伦不类的组合)。优越感是从主体方面立论,不伦不类的组合则是从客体方面立论。严格地讲,是这一类把喜之笑提升到审美的本质,既居审美之喜的核心,又拥有最大的广度。后来美学家对喜的特点描述,如门德尔松(M. Mendelssohn,1729—1786)的“不完美”、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的“僵硬论”等,都是低于正常,且与不伦不类的组合有这样那样的关联。从历史上看,喜的形态也主要由不伦不类的组合扩展开来,特别体现在幽默、诙谐、讽刺三大类型中。这种正常的外形与低于正常的言行之间不伦不类的组合,产生出更为深刻意义的美学之笑,对于维护社会、文化、宇宙的正常运转具有更大的美学力量。以上三种美学之喜,既可分别出现,又可相互结合,呈现出美学之喜。喜的审美类型从原始时代萌生,到轴心时代定型,此后蓬勃展开。
第三,“于人无害”。这是喜的对象可以让人放心地开怀大笑的基础。倘有害于人,那就不是喜,而是悲的对象。悲是严肃的,喜是放心的,放心是建立在主体对自己、对对象,特别是对主体和对象在内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绝对自信和满溢的信心上。喜之笑只有在人达到自由的高度方可产生。可以说,在审美心理所划定的空间范围内,喜的对象让人体会到自己的自由所达到的高度。能笑与不能笑,是衡量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信和拥有自由的一个美学指标。成熟的喜剧首先诞生于古希腊。正是古希腊文化从早期文明到轴心时代的理性进程中,喜剧产生出来。公元前581年,古希腊本部的梅加腊(Megara)人建立民主政体,喜剧正式诞生;到前487年,雅典城正式开始演出喜剧,标志着美学之喜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美学类型。
第四,“引人发笑”之“引”。西方学人讲过,主体的优越感中有好些情况并不产生喜剧性之笑,客体拥有不伦不类组合在好些情况下也不产生喜剧性之笑。喜剧性之笑是怎么产生的呢?霍布斯等讲了突然性,即喜之笑来自一个突然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康德(I.Kant,1724—1804)从理性上总结出“期待落空”之论。即人按正常方式去期待对象的正常之行之言,结果对象出现的是不正常的行和言,主体的正常期待突然落空,由正常与不正常的突然变转中,对象低于主体的面相呈现出来,“笑”不由自主地因之而生。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从心理学上总结出心理释放论。即正常期待在心理上集聚能量以准备投入下一步的运行,期待落空使能量无需投入,能量节省使人产生快感,这快感同时是心理紧张的解除,心理压力的释放,从而人产生了获得自由之笑。
由以上四点可知,低于人的对象,达到了于人无害,而产生美学之笑。这笑,关联到人的自信和自尊,围绕着文化运行和演进中正常与非正常的复杂变化,成为美学类型的喜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笑的基础从现象上看是人的自信与自尊。审美之喜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是与文化对“正常”的尺度标准相关的。在关于正常的不同理解中,产生出不同的笑的类型。在这一意义上,“正常”本身的演进史和“偏离”本身的演进史,构成了审美之喜的丰富多彩。
从类型上看,审美之笑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以生活为主呈现出来由“眼前之景”(从一人一言一行一物一事一态)的笑,此类可称为生活场景之笑。二是把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之笑进行艺术加工,成为具有小结构的简单故事。这类故事主要不是为了故事本身,而是以故事为线,把笑组织起来,以笑为目的,可称为小型艺术之笑。三是把现实之笑与小型艺术之笑组成具有艺术性的整体故事,笑在故事中也被进行了类型化的组织。这种以艺术为主“虚构之象”(具有相对复杂的“叙事整体”)而来的笑,可称为叙事之笑。生活中个别的眼前之景与艺术中类型的叙事之象,构成了审美之喜的两极。生活之笑进一步与叙事之笑退一步,都成为小型艺术之笑。进而从中、西、印三大文化去观察,可以发现,在审美之喜上,中国、印度以小型艺术之笑为主,西方是以叙事之笑为主,这与三大文化对宇宙整体的设定相关。中国的“天人合一”宇宙,印度的“色空合一”宇宙,主要产生眼前之景的喜和小型艺术之喜,两种宇宙结构都阻止生活型眼前之景的喜向艺术型叙事之象的喜转化。西方文化把宇宙分为已知、未知两个对立部分,在区分之下对已知部分进行实体性思考,会促使其不断把生活型的眼前之景的喜与小型艺术之喜转化为艺术型的叙事之象的喜。理解了美学与宇宙设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体悟为何三大文化在审美之喜上有如此的不同,以及还有其他一些由宇宙设定带来的重要不同。这对从理性的统一性上理解审美之喜,是重要的。
印度美学之喜,具有独到之处。印度思想强调一维时间,形成“是—变—幻—空”的宇宙,历史显得不重要,思想本身是重要的,从而对其审美之喜从理论形态本身予以呈现,更易把握。印度的美学之喜,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笑的对象在形体上的限定性。在“笑”偏离正常的形、心、言、行四项中,印度在形上的偏离只在人世凡人中而不存在神界之神中。原因在于,印度的理性思想,从早期文明向轴心时代的转变。一方面,世界整体本质升级为理性之“空”(Śūnyatā);另一方面,世界现象总称为“色”(rūpa)仍以宗教为主要载体和外在形式。印度的宇宙结构图式是:核心是宇宙的整体之空,空之下是宗教的主神,神主宰着种姓社会。这是一个三极互动的运转结构(见图1):

在如斯的宇宙结构中,神的形象在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印度教各主神在种姓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佛教讲生命在六道(领域)中轮回升降,其中两道是天与阿修罗,皆为神。神可以呈为正形或美形或畸形,毗湿奴的十大化身之一是侏儒,佛陀的主要形象之一是骷形。这侏儒、骷形因为是神,而且处在神的各种形象的整体张力之中,因此与美学之笑无关。但在凡世间,畸形、枯形的人就可能成为笑的材料。《舞论》讲印度戏剧主角有男人上中下三类、女人上中下三类,辅助角色除了国舅、侍女、阉人外,还有丑角。丑角就包括形体上对正常的偏离,具有身材矮小,长有獠牙,弯腰曲背,两舌,貌丑,秃头,眼睛发黄等特征。因此,印度美学在形体对正常的偏离上呈性质不同的两分:神的畸形不是笑,人的畸形才可笑(参见表1)。
 二是笑的类型在审美类型体系中的独特性。印度审美类型中,一般的笑与低于心理正常相连,滑稽味则主要与性爱相关。二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先讲一般的喜之笑。佛教认为人生即“dukkha”,汉语译为“苦”;汉密尔顿(Sue
Hamilton)说,更接近梵文原义的翻译应为“insatisfactoriness”(不圆满);用通顺的汉语讲:人生即遗憾。这遗憾之苦,在佛教看来,主要由人的三个心理因素造成:贪、痴、慎。这里的贪、痴,与美学之喜的笑关联了起来。中国古人从中印互动中创造了《西游记》,其中的猪八戒,就与佛教的贪相关,并由贪而突显为好色好食,常常表现为对正常的好色好食的偏离,而突显出美学之喜的笑。最体现出印度特色的是痴。痴在生活中多体现为笑,如猪八戒的好色,除了贪之外,还内蕴着痴。这痴在艺术上,与印度美学八味中的“滑稽味”(hāsya)关联起来。“滑稽味”是笑,但这滑稽之笑是从男女主人公在恋爱的痴迷中产生出来的,从与平时正常不相同的穿着打扮、姿态、行为、语言中体现出来。恋爱中的滑稽,虽然显得可笑,但在本质上是可爱。正如主神的正形、美形、畸形具有内在的统一,使神的畸形从笑中超离出来,性爱中由痴迷而来的滑稽味,与艶情味组成对子,二者内蕴着统一性。滑稽是爱过度了而产生的偏离,因与爱之深相关,虽笑,却没有要使之转向对正常的负面偏离;虽然是滑稽之笑,却与西方的滑稽之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二是笑的类型在审美类型体系中的独特性。印度审美类型中,一般的笑与低于心理正常相连,滑稽味则主要与性爱相关。二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先讲一般的喜之笑。佛教认为人生即“dukkha”,汉语译为“苦”;汉密尔顿(Sue
Hamilton)说,更接近梵文原义的翻译应为“insatisfactoriness”(不圆满);用通顺的汉语讲:人生即遗憾。这遗憾之苦,在佛教看来,主要由人的三个心理因素造成:贪、痴、慎。这里的贪、痴,与美学之喜的笑关联了起来。中国古人从中印互动中创造了《西游记》,其中的猪八戒,就与佛教的贪相关,并由贪而突显为好色好食,常常表现为对正常的好色好食的偏离,而突显出美学之喜的笑。最体现出印度特色的是痴。痴在生活中多体现为笑,如猪八戒的好色,除了贪之外,还内蕴着痴。这痴在艺术上,与印度美学八味中的“滑稽味”(hāsya)关联起来。“滑稽味”是笑,但这滑稽之笑是从男女主人公在恋爱的痴迷中产生出来的,从与平时正常不相同的穿着打扮、姿态、行为、语言中体现出来。恋爱中的滑稽,虽然显得可笑,但在本质上是可爱。正如主神的正形、美形、畸形具有内在的统一,使神的畸形从笑中超离出来,性爱中由痴迷而来的滑稽味,与艶情味组成对子,二者内蕴着统一性。滑稽是爱过度了而产生的偏离,因与爱之深相关,虽笑,却没有要使之转向对正常的负面偏离;虽然是滑稽之笑,却与西方的滑稽之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三是笑的类型在整体之美中处于辅助地位,而非一个相对独立的类型。印度生活型的眼前之景,也向着艺术生成,但只提升为小型艺术之笑。按照婆罗多《舞论》,印度戏剧体系有十类:传说剧、创造剧、感伤剧、纷争剧、独白剧、神魔剧、街道剧、笑剧、争斗剧、掠女剧。其中,笑剧是专门的喜,但为短小的独幕剧,后期方发展为两幕,仍然简单短小,属小戏。例如,最有名的《尊者与妓女》(Bhagavad-Ajjukam),是二人灵魂进入对方身体而产生的笑,类似于中国宋杂剧中的笑,并未达到整体叙事之喜。还有独白剧、街道剧,也充斥着滑稽搞笑,与笑剧一样简单短小。因此,印度之喜,仅在眼前之景的笑的范围之内,尚未达到艺术之象中的整体叙事之笑。可以说,笑剧是印度之喜向艺术演进的界线,再有前进,就成为其他剧种有的辅助因素。正如丑角在各戏剧中扮演的是辅助角色,亦如在有关恋爱的故事中,滑稽味作为艶情味的辅助。由于笑剧在戏剧中的非主导地位,因此,生活型的眼前之景以及由之形成的小型艺术之喜,成为印度审美之喜的主色。
四是在基本用语上的独特性。美学之笑而来的喜,与西方美学之喜有较大的差异。喜在印度具有最高的地位,《泰帝利耶奥利书》第二章是欢喜章(Brahmānanda)。在第二、第三章中,都讲梵即“欢喜”(ānanda),“欢喜”是梵。《中阿含经》卷二十二把获得佛理的觉悟称为“成就欢喜”。《十地经论》卷二把诸佛菩萨所住之地称为“欢喜地”,把念佛向佛所生之心称为“欢喜心”。喜成为从世俗心中摆脱出来并等同于形上之心的审美之心。如果说,西方审美之“喜”强调的是审美现实(开端)中之“实”,那么,印度的审美之“喜”彰显的是审美结果(终端)中之“虚”。
中国美学之喜,极为丰富而具有特色。中国文化的时空合一,使审美之笑的文化整体性质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以俳优侏儒的宫廷之笑为主,语言呈现的“滑稽”是核心,以外笑内智为特色。第二时段,以唐参军戏—宋杂剧为主,以净角装傻、末角逗趣形成里外皆笑的特色,关键词是表演与语言兼顾的“科诨”。第三时段,戏曲达到成长质点,完成艺术转型。宋杂剧中的主角之笑转为专角丑,降为剧中次要角色;同时,笑的科诨遍及剧中的生、旦、净、末每一角色中,典型地体现了审美之喜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
这第一时段,是中国审美之喜的来源与雏形。中国的审美之喜,来源于原始社会和早期文明的仪式。在轴心时代到来的春秋战国,仪式的整体产生分化,主要分为祭祀天、地、祖、山川、房屋之神的严肃仪式(雅与古)和纯为宫廷娱乐的舞乐享乐(俗与新)。后一方面随着原始社会和早期文明中原有神性的内容消失,转为为君主服务的具有理性内容和纯粹享乐形式。从审美之喜来讲,以前具有特异功能的寺(阉)人转为身体非正常的宦官和身体正常的诗人,瞽(盲人)转变为以视力正常为主的乐师,侏儒(畸形)成为宫廷里的娱乐伎人。与之相应,在春秋战国的转型中,原始仪式的色、声、味普遍成为享乐,而原始仪式中以祝辞、咒语方式活动着的语言成为诸子散文和宫廷雅言,保持了文化高位。在这一氛围中,审美之喜的语言也在宫廷娱乐中占有高位。在正史中,专门为审美之喜立传的“滑稽”,主要用来指宫廷娱乐人员在语言运用上所具有的笑的特点。先秦两汉宫廷中,审美之喜的娱乐主要以三个词描述:一是侏儒,主要指喜的形体;二是优,主要指喜的表演(《正字通•人部》“优,戏也”,主要为笑的表演;《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国语·齐语》“优笑在前”,《管子·四称》“戏谑笑语”);三是俳,主要是笑的语言,如《韩非子·难三》“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宴之乐)也”。形体、表演、语言三者一体,用哪一词只是表明强调的重点不同。其中,语言之俳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三者一体中的语言效果或语言风格,称之为滑稽。司马贞作《史记·滑稽列传》索隐,说:“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释词或可讨论,姜亮夫《滑稽考》讲,滑稽应为连绵词,源于圆转机巧,与一系列词如诙谐等皆同;但释义是到位的,即对语言作不伦不类的组合以引人笑。)三位一体的滑稽,进一步在全社会展开,一方面成为百戏中的滑稽表演(如汉代的黄公戏、沐猴舞等),另一方面成为士人间的俳谐诗文(如汉末蔡邕《短人赋》、晋代李充《嘲友人诗》、南朝齐袁淑《俳谐文》,谐之词义如南朝梁刘勰《文心心雕龙·谐隐》所释:“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再一方面成为社会中的笑话录(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俳调》等)。后两个方面,自汉魏到明清一直兴盛着、扩展着,但审美之喜在前一个方面(即表演艺术中)于唐宋达到一种定型模式。第一时段的喜,突出的亮点是装傻讽谏。春秋以来,俳优侏儒很多,但可以进入史册的,则是那些通过表面上滑稽笑语达到政治上讽谏目的的人和事。中国宫廷,俳优侏儒呈现笑料是本职,通过滑稽之笑对主上的不当决策或政治过失进行劝阻,先是假装心之低下的傻,认同主上的错,接着将之夸张到极端,最后在傻言笑话中让主上认识到自己错了。因此,与西方滑稽的特点是呈傻之笑不同,中国的滑稽讽谏的方式是装傻之笑。
在第二时段,中国审美之喜得到专门性突出。这就是起于六朝形成于唐的参军戏,以参军与苍鹘两位角色进行以笑话为主的滑稽表演。到宋金杂剧,演进为以四人或五人一场,形成三段结构:“艶段”开场引戏,然后进入正剧(一般是两段),最后以“散段”结束。整个剧的主调是:“务在滑稽。”艶段要好看(可用舞的形式),散要搞笑(一般嘲弄外地人),正剧中副净和副末为主,“副净色(角色)发乔(装傻),副末色(角色)打诨(逗趣)”。这时的滑稽,不仅保持以语言之笑为主,而且增加了动作之笑,因此,“科诨”一词兴起。科即用动作逗笑(徐渭《南词叙录》“身之所行,皆谓之科”),诨即用语言逗笑(徐渭《南词叙录》“于唱白之际,出一可笑之语,以诱坐客,如水之浑浑也”)。可以说,在唐参军—宋金杂剧中,科诨形成了专门性的审美之喜。第二时段的喜,其亮点是以娱乐为目的的笑。
在第三时段,戏剧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戏曲形成和定型为丰富多彩的艺术性戏剧。“笑”这一宋杂剧的主角,到这时转为辅助。从角色体系看,元明清戏曲形成生、旦、净、末、丑的体系,生旦为主,净、末为次,专门的丑角更为次。就此而论,笑被次要化、边缘化了。从审美之笑的角度去看,在宋杂剧本为主要功能的科诨,也随着戏曲角色本身的扩展而扩展,并渗透到每一个角色里,生、旦、净、末等各类角都有科诨,只是上等角色呈雅科诨,下等角色做俗科诨;与此同时,除了丑角之外的每一次科诨的出现,都是辅助性的,成为插科打诨,是“插”进去的,“打”弄出来的。包括丑角本身,都是插加进去搞笑的。不过,这插弄进去的科诨,又是整个剧必需的调味品,用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的话来讲,是剧中的“人参汤”。可以说,科诨之笑在整个剧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俳谐诗文在整个诗文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如笑话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应着的,是作为笑的审美之喜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个时段的亮点,是笑寓在各类艺术之中,服务于各类艺术的整体目的。
中国古代的审美之喜在三个时段各有特点:装傻讽谏,笑为娱乐,笑寓艺术。前者体现了笑在以政治为主的整体性中的意义,中者突出了笑在生活娱乐为主的整体性中的意义,后者彰显了笑在以艺术为主的整体性中的意义。
西方的审美之喜,与中印之喜的区别,不仅是眼前之景的笑(及其在艺术中的片断体现)这一类型上的“同”,更在于整体叙事结构之笑的“异”。中国的宋杂剧和印度的笑剧,是对“眼前之景”从艺术上进行扩展,但并未达到对审美之喜进行完整呈现的叙事结构,从而在本质上还处于“眼前之景”的范围中。之所以如此,不在于中印艺术家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是这样做与宇宙整体的规定不符合,要在艺术性质上与宇宙合一。因此,中国和印度的艺术之喜,如果从宋杂剧和印笑剧再往前走,在中国就升级为明清戏曲,在印度就转成其他剧类。可以说,宋杂剧和印度笑剧之喜,是中印审美之喜所能达到的最高度,是由文化划定的范畴所决定的。西方的宇宙观,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不同,与印度的色空结构有异,是由已知和未知构成的二分宇宙;与之相应,审美类型出现了专门的“悲”与“喜”。悲与未知相连,喜与已知相连。由于西方之喜把自己限定在已知世界,从而不但普遍出现了眼前之景的喜之笑,而且还形成了专门的具有整体叙事结构的喜之笑。这首先从古希腊的戏剧形式显示出来——喜剧。喜剧与史诗、悲剧一样,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像宋杂剧、印度笑剧那样,主要是如节日礼花般的放出一个一个的笑话。
作为具有整体叙事的审美之喜,西方的喜剧有三个特点:一是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讲的,喜剧是模仿比正常低的人(主要是心智低于正常);但喜剧性之人,正如尼柯尔(A.
Nicoll,1894—1976)讲的,不是塑造人的丰富个性,而是抽象为笑的类型。如塞万提斯(M.d. C.
Saavedra,1547—1616)写《唐吉诃德》,一定是一言一行皆充满滑稽,没有相反的内容在他身上出现;如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写《吝啬鬼》,其人一定一举一动都透出吝啬,绝无相反的气质存在其中。二是尼尔(Steve Neale)讲的,喜剧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叙事。这里的日常生活,不仅是已知世界的生活(这里重在“已知”二字,与未知不相关),更是已知世界中的平凡者下等人的生活(这里重在“生活”,与严肃的政治等不相关,即或写了上等人,也是上等人的活泼泼的生活一面,而非拿着样的政治一面)。三是尼尔讲的,要有欢喜的好结尾。已知世界是人能把握的,皆大欢喜是必然的结局。但已知世界的好结局,是由已知世界的正常运行而产生,喜剧对偏离正常进行了幽默、诙谐乃至讽刺之笑,都是为了将已知世界的运行带进应有的美好结局。由(对偏离正常进行的)笑而(使偏离在笑声中走向正常之)喜,是审美之喜的叙事整体的基本结构。可以说,西方美学通过把各种眼前之景的喜,组织成艺术的整体叙事之喜,以符合世界的二分世界中的已知世界部分,是西方审美之喜的主要形态。或者说,形成了艺术型整体叙事之喜为主,眼前之景(以及小型艺术)的喜为辅,而且眼前之景和小型艺术之喜不断地被组织进艺术型整体叙事之喜中去,从而艺术之象的整体叙事之喜成为西方审美之喜的主色。这一西方审美之喜的主色,其历史演进体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古希腊开始,以喜剧这一戏剧种类为主,开始审美之喜的主潮演进。产生了克拉提诺斯(Cratinus,前519—前422)、欧波利斯(Eupolis,前446—前411)、阿里斯托芬(Ἀριστοφάνης,约前448—前380)三大喜剧家为代表的众多喜剧作品,特别是而今得以保存下来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鸟》《蛙》等,以及在旧喜剧向中期喜剧和新喜剧的演进中,米南德(Μένανδρος,前342—前291)的《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公断》,展示出希腊社会各种各样的笑如何被艺术集中起来,形成艺术型叙事整体。古希腊的喜剧,主要运用于城邦政治上,以讽刺(在喜剧家看来)政治上偏离正常的人和事为主。
第二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不但戏剧中的喜剧开始了现代提升,新起的小说以及稍后新起的绘画开启了新型的喜剧性艺术方式,这就是喜的小说和漫画。二者与戏剧之喜一道交织演进,使审美之喜在三原色中幻出一片灿烂之景。在喜剧这条线上,以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1564—1616)、康格里夫(W. Congreve,1670—1729)、莫里哀直至王尔德(O.
Wilde,1854—1900)的喜剧,仍守着喜剧与已知世界相关和喜剧性是类型化的笑的基本原则,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笑集中到艺术之象的叙事整体中。尼柯尔把喜剧分为:闹剧、浪漫喜剧(幽默喜剧)、情绪喜剧(讽刺喜剧)、风俗喜剧(风趣喜剧)、文雅喜剧、阴谋喜剧。经过总结的艺术之喜,反过来又渗透到生活的每一方面,但以笑的艺术为主要目的。西方喜剧的基本模式都在此形成。在小说这条线上,拉伯雷(F. Rabelais,约1493—1553)的《巨人传》、薄伽丘(G.
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斯威夫特(J.
Swift,1667—1745)的《格列夫游记》等开启了一种新的喜剧性故事模式。在漫画这条线上,英国贺加斯(W. Hotarth,
1697—1764)、吉尔雷(J. Gillray,1757—1827),法国的菲利浦(C. Philipon,1800—1826)、杜米埃(H. Daumier,1808—1879),美国的纳斯特(T.
Nast,1840—1902)、奥特考特(R. F.
Outcault,1863—1928),使西方的小型艺术在笑上有了一新模式。由这三个方面交织并进的审美之喜,蓬勃展开,直达西方文化的各个边缘,如北欧和俄国。总而言之,戏剧之喜为核心,小说之喜和漫画之喜为展开,生活的眼前之景的喜,被三种艺术之喜组织起来,形成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审美之喜的新结构。就这一时代的总体来讲,艺术之喜成为审美之喜的太阳,将条条光线,遍照在已知世界之喜的方方面面。
第三阶段,电影产生之后,电影所体现的审美之喜,加入到戏剧、小说、漫画之中,与之交织互动,成为审美之喜的主潮。在四线交织的喜剧这条线上,一个重大的新特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科学和哲学的升级之后,专门为笑的喜剧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被反思,正如斯特林堡(A. Strindberg,1849—1912)讲的:“这个人愚蠢,那个人残忍,这个嫉妒,那个吝啬,等等……应当受到质疑。……我尝试着不让分裂的片断进入情节之中。”喜剧之笑被要求融进社会整体关联之中,于是出现了悲喜剧和正剧。同时,戏剧之喜与小说之笑,融入整个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服务于艺术的整体目的。在四线交织的小说和漫画这两条线上,专门的喜剧故事日益渐少,喜剧性作为某些因素进入各类小说和各类漫画日益渐多。从审美之喜的角度可以发现:荒诞剧中的笑,黑色幽默中的笑,表现主义艺术中的笑,存在主义艺术中的笑等等,在四线交织的电影这条线上逐渐成为艺术中的主潮;审美之喜又从电影中产生出来,呈为持续不断的电影之喜的景观,如英国从卓别林(C. Chaplin,1889—1977)到艾金森(Rowan Atkinson)(即憨豆)、美国从基顿(B. Keaton,1895—1966)到伍迪·艾伦(“Woody” Allen)、法国的塔蒂(J. Tati,1907—1982)、德国的刘别谦(E. Lubitsch,1892—1947)、加拿大的凯瑞(Jim Carrey)等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喜剧电影游荡在世界各地,并产生了新的本土类型(在中国就有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和开心麻花的喜剧电影)。电影又产生出动画片,动画片不仅在方式上是儿童的,天生就有喜剧性,而且还专门创作了喜剧性叙事,如名扬全球的《米老鼠与唐老鸭》,成为喜剧的新形式。第三阶段西方之喜总的趋向在于:一是电影作为工业文化的商业性质,主要靠类型化电影进行运作,因此,喜剧性正是在精准定位的类型化商业运作中,得到极大发展。二是其他艺术形式中的审美之喜,包括戏剧、小说、漫画,都在从类型走向关联,约似于古典时代中国和印度的艺术。然而,无论是在类型化的电影中,还是在非类型化的戏剧、小说、漫画中,西方审美之喜的双向演进得到彰显。
从以上中、西、印审美之喜的演进中,对审美之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1)在古代世界中,审美之喜与宇宙设定的关联,决定了中、西、印之喜的关联范围:西方之喜,集中在已知世界中的实体的类型化;中国之喜,主要在虚实结构中的实的部分的类型化;印度之喜,在于下梵的世事之色与上梵的本质之空的关联中。而西方在科学和哲学的思想升级中,趋向于从古典的实体世界转为与中国的虚实相生和印度的色空一体类似的新结构。审美之喜的新变应,由这一新的宇宙设定来说明。(2)中、西、印之美呈现两大类型:中印以与眼前之景的喜同质的小型艺术之喜为主,西方以艺术之象的整体叙事之喜为主。中印主要体现为,对喜的片断本身进行类型化;西方主要体现为,对笑进行人物和故事的类型化。(3)中印之喜,主要作为文化整体中的因素,加入进各类结构中,组成虚实相生(中国)与色空对照(印度)的关系。西方之喜,体现为一种独立的类别,与其他独立性类别一道,构成一个实体间互动的世界。(4)自20世纪的全球一体和多元互动以来,喜的类型化主要体现在喜剧性的电影上,而其他艺术中的喜成为了一种因素,与整个世界互动;同时,西方的脱口秀和中国的相声以及与之同质的喜剧小品,以生活化的方式进入艺术,类似与宋杂剧、印度笑剧,实际上与生活世界紧密关联和基本同质。小型艺术之喜,在现象上是艺术的,在本质上是生活的。这样,审美之喜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生活型眼前之景的喜,出现在生活的各方面;二是艺术型的整体叙事之喜,主要以喜剧性电影突显出来;三是形为艺术而质为生活的脱口秀和相声以及喜剧小品。这三种喜的类型,加上其历史来源,可作图如右(见图2):

图2 三种喜的类型及其历史
总之,世界的审美之喜,由中、西、印三大文化不同的宇宙结构,产生了三大喜的类型:生活之喜,小型笑剧之喜,叙事喜剧之喜。审美之喜的核心是人的优越感、正常感、自信心、自由观。而这一核心,要在对西方“已知未知”的二分世界、中国“虚实—关联”的世界、印度“是—变—幻—空”的世界的认知中,方可得到更深的知性理解和形上体悟。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編者註:此文刊发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4期第540—54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文章的原文,请发邮件到“wptian@um.edu.mo”信箱索取PDF版;如果您想投稿,请发电子版到“ias.scq@um.edu.mo”信箱;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https://ias.um.edu.mo/2021-contents/),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
主办:澳门大学
·前沿聚焦·
特区基本法理论体系框架之构建(460-472)
◇ 骆伟建
澳门大学法学院 教授
原思:作为人文学的哲学文本
——兼论中国哲学的思维特性(473-492)
◇ 胡伟希
清华大学 哲学系 教授
天道与机心:可信自主系统的多元定位(493-506)
◇ 黄鸣奋
厦门大学 中文系 教授
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507-517)
◇ 陈军亚
·时代问题论争·
东亚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
——以中日“村落社会”为中心(518-528)
◇ 田毅鹏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教授
读者解放:从文本阅读到文本能力的转向(529-539)
◇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系 教授
·东西文明对话·
中、西、印美学比较中的“喜”(540-549)
◇ 张 法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
中西学术书写伦理中“抄袭”的演化(550-558)
◇ 江宝钗
中正大学 中文系 教授
·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三皇五帝的文化(559-567)
◇ 黄开国
四川师范大学 杰出教授
规约与突破:恩德文化中的中国文学主题(550-558)
◇ 杨春时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
从以“名”言“道”到体“道”
——《老子》对“名”“言”之域的拓展(581-594)
◇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智慧研究院/哲学系 教授
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的历史真相
——兼论正嘉之际中外关系转折与文化变迁(595-608)
◇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金融的操控(609-622)
◇ 朱荫贵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教授
·信息速递·
《南国学术》二〇二一年分栏总目录(623-624)
◇ 田卫平
《南国学术》 编辑部 二级编审
排版、设计:田卫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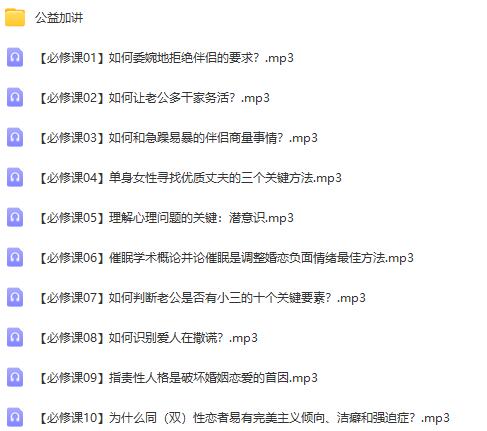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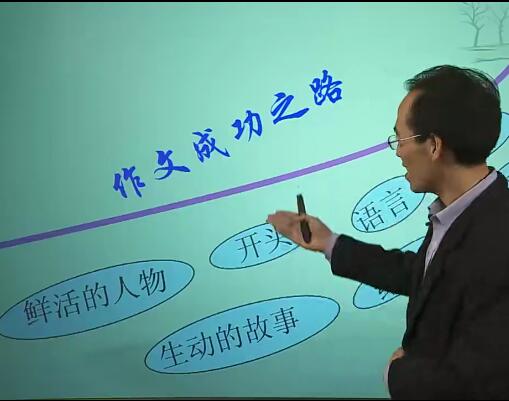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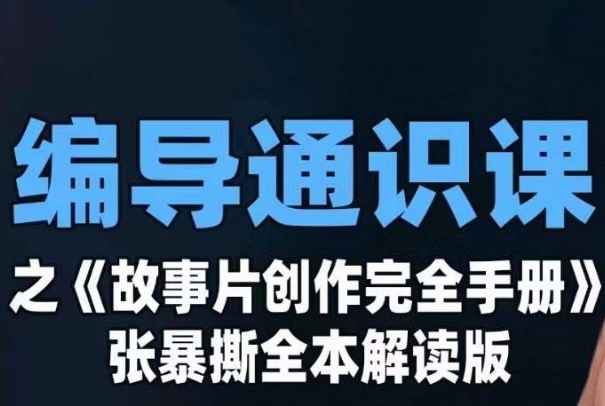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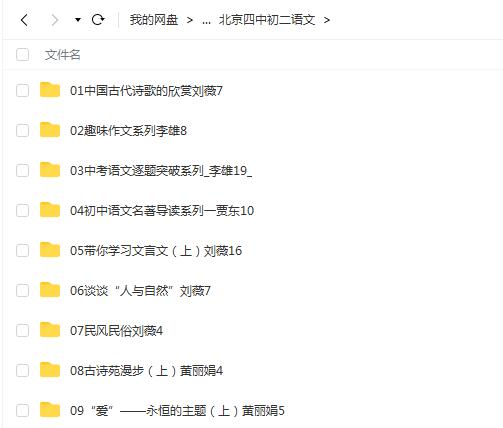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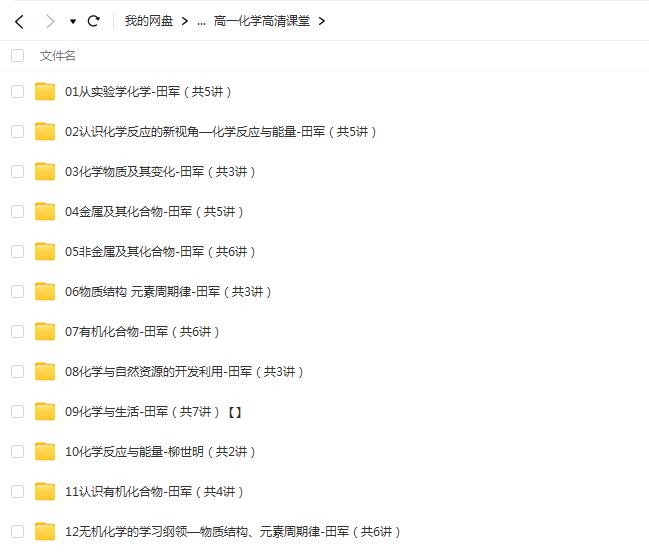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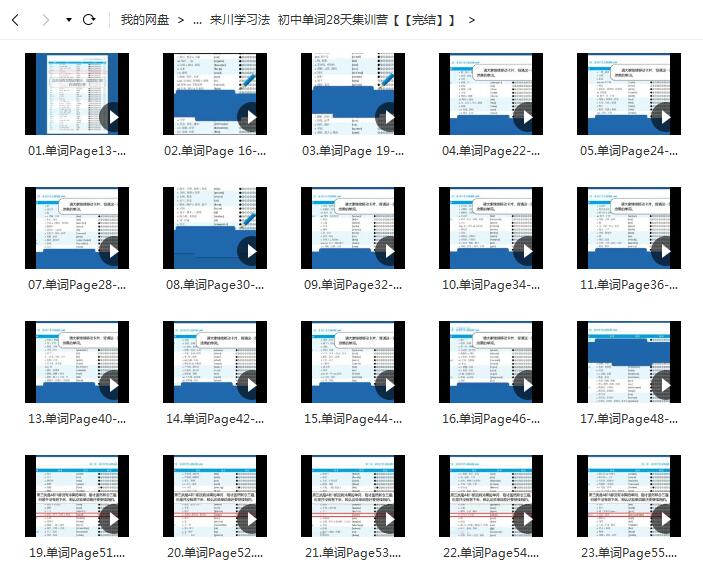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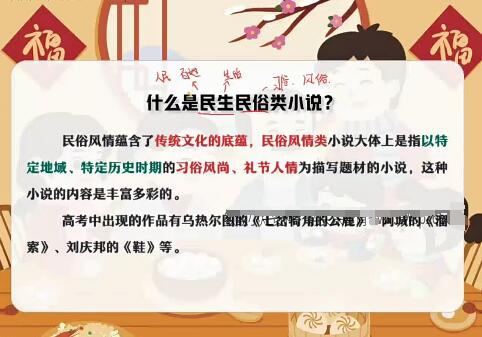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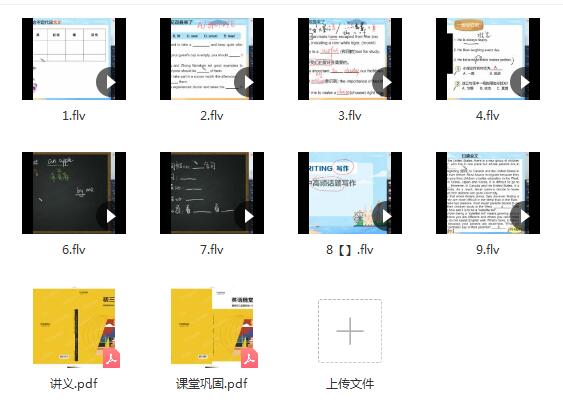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