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乡的风物(三题)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05 17:18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家乡的风物(三题)
程相崧
大蒜
我的家乡种植大蒜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久。记忆中的少年时代,每到古历五月末六月初,壮妇粗汉还要弓背为牛,拉着满车的麦子往土场上赶。如今,土场已成废墟,齐膝的茅草有羊啃的痕迹,青白色的石磙弃在一旁,半截迎着日晒,半截没入土中,让人徒增对岁月的些许感慨。
蒜是辛辣之物,性阳,每年五月,一根根冒出蒜棵的蒜薹如同一根根细小的狗鸡巴,也即狗的阳物。待过几日,蒜薹甩了尾,若拔得不及时,顶苞让日光晒得通红,梗梗着脖子,模样更似人中的“愣头青”。这副模样,一定意义上是代表了蒜的性格的。
蒜味儿很“冲”,所以在佛家看来,它是“荤菜”,认为吃得多了容易上火,容易性情暴躁,跟人大动肝火。这个有没有科学道理姑且不论,但是在收获大蒜的季节,因为吃蒜过多,夫妻打架吵嘴的却不在少数。
在官方的材料里,宣扬的多是蒜的正面作用。什么杀菌抗癌,延年益寿,美容养颜,给蒜穿上了“神”的外衣。其实,有研究结果证实,蒜的医疗作用很是有限。最好的疗效,是烧食治疗腹泻,因为它是大肠杆菌的克星。当然,中医里也有一个说法,蒜吃多了会“损肝伤眼”。这个足以让我们家乡人骂娘的说法,虽尚无科学实验数据的佐证,可家乡人中多老花眼,又多少白头,大约就是食用大蒜过量了的缘故。
但是,蒜不为大家尤其是城里人所喜,却并不是因为“损肝伤眼”,而是因为吃了蒜,会带来诸多的麻烦。例如,口是不能不漱的,牙是不能不刷的。不然,同处一室,共坐一车,就会有说不出来的尴尬。甚至,纵使你做好了这些,也难免不露馅。我认识一个农民,他有一次去市里看病,看完病去厕所小解,并排站着一位大夫。大夫解完打了个哆嗦,一手掩鼻,一手提着裤子,说你金乡的吧?农民以为遇到熟人,正惊愕间,听到那大夫说:你们金乡人尿出来的都是一股蒜味儿哩!
这位农民兄弟没有吭声,心里竟然是满满的自豪,回到村里见人便说:咱县里领导整天在电视里讲要将大蒜打造成咱金乡人的金字名片,俺总觉得吹牛!这一出门,人家就凭这认出了俺哩!看来还真给整成了一张名片了呢。
名片不名片,说到底蒜还只是一种佐料,一片绿叶儿。它的身份,甚至没法儿跟葱啦姜啦这些“大绿叶”比,它有点儿像芫荽、胡椒,得吃的人好这口儿。这些年出门在外,常常被人好奇地问:你们平常怎么吃蒜哩?他们总觉得就像湖区的人吃鱼,一条鱼能有十多种吃法,种蒜的人吃蒜,也必能吃出十几种花样来。其实,说老实话,蒜的吃法并不算多。当然,有些人偏不承认,甚至还挖空心思,推出了“全蒜宴”。这个“宴”听名字让人好期待,其实也只是忽悠外来人的一个噱头——一盘“蒜瓣烧鲤鱼”,你说你是吃的蒜还是鱼哩?
我觉得蒜最地道的吃法,还是啃着蒜瓣就馒头。蒜最好拿刚掘下来,还未晾干的鲜蒜,咬起来脆,汁水儿多,辛辣味不冲。馒头呢,最好也是刚出锅的馒头,抓在手里暄暄的,带着一股小麦粉的自然甜香。大蒜的辛辣浓郁,加上小麦粉的清香甘甜,跟津液混合起来,真是越嚼越想嚼,越嚼越有味道。当然,其中的滋味儿,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就跟嚼着花生米喝白酒一样,得重口味儿,得好这口儿。
退而求其次呢,便是大蒜和煮熟的鸡蛋一同捣碎,或同青辣椒一起捣碎,名曰“鸡蛋蒜”和“辣椒蒜”。这两宗小菜,开胃,也下饭。做鸡蛋蒜,鸡蛋跟蒜的比例,要掌握好。鸡蛋多了,看上去显得干而散,吃起来也感觉淡而无味;蒜放多了,鸡蛋的香味儿没有充分的舒展,抹在馒头上粘度也不够。相对来说,辣椒蒜的讲究就少一些,只是要选青椒,红色的或半红的弃之;辣味要适中,辣味小了寡淡,辣味呛了又会喧宾夺主;皮要薄,如误用了厚皮辣椒,做出鸡蛋蒜,则味同嚼蜡矣。
从前,家乡的土民,每年大蒜收获,都要做一罐子糖蒜。糖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真的加糖,一种是不加糖,取其自然的“糖化”。其他的配料,不过是盐、醋、味精、料酒之类,按照一定比例调和,浸入蒜头密闭十天半月即成。此吃食儿易制,但近年来,多不为年轻人所喜食。老人泡制,大半亦是怀旧,因此,夏末秋初,或秋意阑珊之际,多有食之未竟,弃于坑畔沟沿者。
有一种“泡蒜”,多见于超市货架,玻璃的罐头瓶儿,铁盖,看起来很精致,可惜我没有吃过。不知做法是否类似于糖蒜,或者说不定就是糖蒜的别称?即使不是别称,也应该是表兄弟或者堂兄弟的。虽然名称不同,却都离不开水来泡,让蒜浸染了种种调料的味道儿。这两种泡法儿,都比较讲究,做起来颇费些时间。我倒钟情于另一种简单的泡法。即将蒜剥白,切片,盛入盘中,然后用酱油、味精、味达美、芝麻油调和。随便放在桌上,搁它个一天半晌,食之,味道上佳。
这样说来说去,我觉得吃蒜最有意思的吃法,还不是拿它当主角儿,还不是让它挑大梁,而是从一桌子荤菜里,一块一块儿地挑着吃放入菜里的蒜瓣儿。蒜熟时本来是寡淡无味的,但因为浸透了肉味、鱼味、料酒味、葱花味、花椒大料的味儿,却有了说不上来的味道。
当然,这种吃法,需在酒足饭饱之后,或者干脆睡上一觉,待酒醒来,再找上顿的剩菜,从里面淘金。
这多有意思?吃不吃的,不就是一个玩儿吗?
红三刀
我们家乡人管红三刀不叫“红三刀”,也不简称为“三刀”,而是叫“果子”。这说法有些不确切,因为,“果子”是个统称,指的是所有的糕点。但是,从这个说法上,也足看出它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这就如同管小麦叫粮食,管馒头叫干粮。
在金乡,做红三刀的老字号,从前叫“东长兴”,说起来,那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事儿了。解放后,县里有了国营的糕点公司,金峰糕点,当时请的就是东长兴的师傅。现如今,这家金峰糕点还在,已经是一家授牌“中华老字号”的老店了。
红三刀,其貌不扬,长方形,比麻将子略大,比火柴盒略薄。表面缀以芝麻,饰以刀痕,看起来简单;做法呢,说起来也容易。先用面粉、小米粉加蜂蜜、麦芽糖、芝麻油调和,然后往表面撒上芝麻,在上面用快刀连砍数下(可见,这个“三刀”的“三”,不是确数),再用热油炸透,即可。
你回家之后,可以按我所说的步骤,如法炮制,炸出来,我敢保证,肯定不是“三刀”,而是一种叫不上名堂的什么东西。这就足见师傅的手艺——火候的掌握,油温的掌控,时机的拿捏,全在意会,不可言传。
红三刀的包装,从前是先用长方形的纸盒盛好,再用四方的草纸对角折叠包裹,上面覆上红色的果签儿,最后用纸荆子四面缠绕,挤一个结儿。因为走的亲戚多,从前过年,腊月二十六七赶年集时,每家都要买几十斤散装的,回来在灯下自己包。那样的夜晚,闻嗅着三刀的香气,听着折叠纸张轻轻的“啪啪”声,摸着通红光滑的果签儿,欣赏着果签上印刷的图案和字号,春节的感觉就近了。后来,先是金蜂改了包装,有了专门的纸盒,里面用塑料袋儿封口,其他作坊也纷纷效仿。精致是精致,省事也省事儿,年的味道反而显得淡了。
红三刀既然叫果子,是糕点,那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家乡人逢年过节,走亲串友的必备礼品。如果按照老礼,春节串门,可以不拿苹果香蕉,可以不提香烟白酒,但如果不提两包红三刀,就如同拜神少了猪头,考试忘拿了准考证,跟空手跑一趟是差不多的。
在年节里,任谁去别家走亲戚,都会提几斤红三刀;任谁家里来了客人,也都会收到几斤红三刀。这样一来,年节里攒下的红三刀,从前是不舍得吃,现在是不愿意吃,总是出了正月,还在那里放着。有的人家,过了二月二,看天渐渐热起来,犹豫再四,就将之心疼地丢掉了。
——这说起来,实在是吃红三刀的一个误区。
他们不知道,红三刀是要“睏”的,这就如同酒要窖藏,方显香醇;刚刚收获的地瓜需放上一个冬天,让它出出汗,来年春上吃时才会甘甜。这红三刀若是“睏”上个把月,按从前用纸盒包装的情景说,那就是待到包装纸已让油津得透明闪亮,才是吃的最佳时机。
这时的三刀,就如同四川人吃的腊肉,油还是油,但绝不会那么腻了。你轻轻地取开了包装纸,拿一个小碗或者小碟子,盛上那么一两个,或者三四个,注意,事不过五,五个就过犹不及。干什么呢?煲汤馏馒头的时候,放在笼屉里,透透地一馏。糯而不粘,香而不腻,那是人间美味!
这种吃法,最好是掀开锅盖,直接拿筷子往笼屉里去夹,夹了就赶紧往嘴巴里送。如同南方人吃醉虾,有钱人喝蛇血,吃猴脑,时间上最要紧。你如果不得门道,眼看着馏得透透的了,待到将碗碟端到桌上,再坐下来慢吞吞夹着往嘴里送时,已经失去了方才的滋味儿了。
这样吃,不必选三刀中的上品,倒是以二流作坊的货色最佳。他们生产的三刀,面粉多,白糖少,蜂蜜少到以至于无,炸得将透未透,甚至有些夹生,上锅一馏,却是恰到好处。如果是金蜂牌子的呢,油和糖都足,炸得又透,馏着吃倒有些影响口感,甚至不影响口感,也总让人感觉暴殄了天物。
在我的家乡,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食用此物,不是不好吃,是不得法儿。红三刀里的上品,自然还是吃新鲜的,开袋即食。可是因为油大,糖高,吃三刀跟吃肥猪肉片子相似,要求人胃好。这个福,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了的。你眼见别人连干三块肥肉,你动筷子试试?我们一般人吃红三刀,最好手头放一杯红茶。时间呢,也最好选在午饭前,十一二点钟的光景。早晨的饭食,消化得将尽未尽。然后,将三刀拿在手里,沿着原有的刀痕,一瓣一瓣儿地掰着吃。吃一瓣儿,用红茶送一下;再吃一瓣儿,再用红茶送一下。
你吃了那么三五块儿,果断地就此打住,纵使喉咙里有馋虫往外伸手,好了,不要再吃了!这种方法,下次吃的时候,才会有食欲。吃三刀,要拿捏着“度”,过犹不及。
这个原则,细想来,又何止三刀哩?
金谷
有一个谜语,“小时青,老来黄,金色屋里小姑藏”,说的就是谷子。谷子不同于稻谷,稻谷的种植离不开水,脱去麸皮后是洁白的大米,为南方人的主要口粮。谷子需在旱地种植,生在北方,打出来是金灿灿的小米。
谷子在我的家乡,不统称为“谷子,而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金谷”。取这个名称,除了方便跟其他谷子加以区别,还因为它色泽比市场上同类小米较重,呈金黄色。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例如,它生在金乡,所以带个“金”字儿;再例如,当地土民把它看得重器,故而以金子作比,等等。
我家乡人种谷的历史,比蒜要长得多。你去百度搜“中国四大名米”,这米便忝列其中。这一类的物产,大抵都有些传说的,金谷也难免其俗。有故事说是康熙爷微服私访下江南,路过此地,饥饿难耐,幸而一个老婆婆给了他一碗小米粥。回京之后,康熙仍对这碗小米粥念念不忘,钦点为宫廷御用。古人说:“饿时吃糠甜似蜜,不饿吃蜜也不甜。”此言不谬!
当年康熙拴马喝粥之处,后来便易名为“马坡”。这块著名的地方,原本应该立碑,勒上“康熙拴马处”的,但在我的儿时,却是一片生满庄稼的沃野。我生而有幸,孩提之时,便常在康熙爷拴马的地方玩耍,吃瓜啃枣,撒尿和泥。那时,还不知道有这段佳话,只知道马坡地里那只野兔子骨骼俊奇,体型肥大,常站立如人状,哭声如婴啼,好似修炼成精。再有就是,那块地里长出的铁连草,稠密如壮汉之须,根茎膨大如丸,缠绕如麻,农人想尽方法除之,仍绵延如烟,连年不绝。
——那时不知,现在想来,这就是所谓的“异象”了。
家乡人喝小米,喜用大火熬至糊状,拿筷子“咕噜咕噜”往嘴里扒拉,稀了则寡淡无味,失其神韵矣!吃这饭食得在冬天,最好是冬天的早上。有事儿不行,急了不行,小米粥的味道,三分在喝上,七分在熬上。
冬日的早晨,农事已了,五谷入仓,偎着锅灶,望着锅底红红的焰火,闻着氤氲的米香,听着“咕嘟咕嘟”的声音。那一刻,一切都是慢吞吞的,连时钟也似乎停止了运转。煮饭人时不时欠起身来,用勺子在锅里搅和搅和,因为时间久了,不动弹动弹容易坐锅(烧糊)。煮饭人全没了农忙时候的焦躁、匆忙、脚板不沾地,脸也没洗,头也没梳;心里懒懒的,身上散散的。那种感觉:万事不关心,唯有吃与睡!如果配上画外音:那真是农家乐,真是活神仙哩!
这些年,我在外面每喝小米粥,入口如虫屎,不是米不行,是全没了那份心境。小米的味道,是用煤气灶和电饭煲的上班族注定没法子体会的!如果你是上班族,在金乡的街头,却可以经常品尝到白粥。白粥的主要原料之一,便是小米。
此“粥”并非常说的“稀饭”,而是在头天下午,就把上等小米用水泡软,磨成米糊,过箩去渣。黄豆打成豆浆,大锅烧水,下锅烧开,撇去浮沫,将澄了一夜的米糊搅拌均匀,倒进沸腾的豆汁锅里,顺着一个方向不停搅拌。开锅后,用特制的大马勺把粥扬起,浮沫去净,粥就好了。
这粥除非买来喝,家常难做。当然,如果你有兴致,将小米和大米一起,放在豆浆机里,打制出来,跟“粥”虽不同,倒也有几分别样的风味。
现在市面上,金谷米的价钱,要比普通小米昂贵几倍,且不知真伪。当年,这昂贵的物件,却倒是我自小到大的口粮。因为日常饭食的简单粗粝,那时对这金谷小米,真是喝到心生厌恶。每顿饭,都要母亲忆苦思甜,父亲说服教育,才能挺挺脖子,勉强把碗中的小米粥咽下。
那时的我们这些孩子,多想喝一口白白的大米粥啊。可大米是湖区的产物,我们这里缺水,种不得,想吃需拿钱买,或用小麦换(每年大米成熟,湖区都有换大米的,赶着驴车,到我们这里来,以物易物,赚取差价)。有一年,县里的一个大干部下来包村,轮到我家派饭。母亲将珍藏的半斤大米拿出来,舀上小半瓢,熬成晶莹透亮的白米粥,给那干部端上。那干部看了一眼,脸上显出掩饰不住的不悦。说:早知道你们给我喝这个,不包你们这个村了!
这也难怪,康熙爷喜欢喝的东西,谁不想喝一口哩?不仅康熙爷,据说,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还亲自吩咐大厨,让山东省长送些金乡的小米过去,给尼克松总统熬粥。插上一句,据传,周总理一生独钟金乡小米,每逢国宴,必上此粥。尼克松喝了,临回国时,还专门吩咐工作人员,要往飞机上再装上那么三五十斤。尼克松平常喝惯了牛奶和咖啡,想来难得尝到这样百姓的饭食,难怪他要带回白宫,与老婆孩子分享了。因为这个,在外国历届元首里,我们家乡人独对尼克松印象极佳。
这段佳话不知何处记载,在百姓的想象中,两国会晤,倒像老婆子走亲戚。这事儿现在看来,虽然难辨信史还是演绎,可影响却无疑重大而深远。从前,农人不论饭食好赖,吃饭必端碗出胡同,蹲在门口享用。有一家人喝着小米糊糊,吃着馒头,啃着蒜瓣儿。当儿子的心里不满,嘟嘟囔囔地说:也没炒个菜嘛!当老子的便开口骂道:娘的个屌!还想啥?尼克松也就这哩!人家尼克松可是吃好东西的嘴儿哩!你比尼克松的嘴还金贵?!
此事年代久矣,当年,恰被年少的我遇见,至今思之,每每仍要捧腹,记下供诸君一笑!
2017.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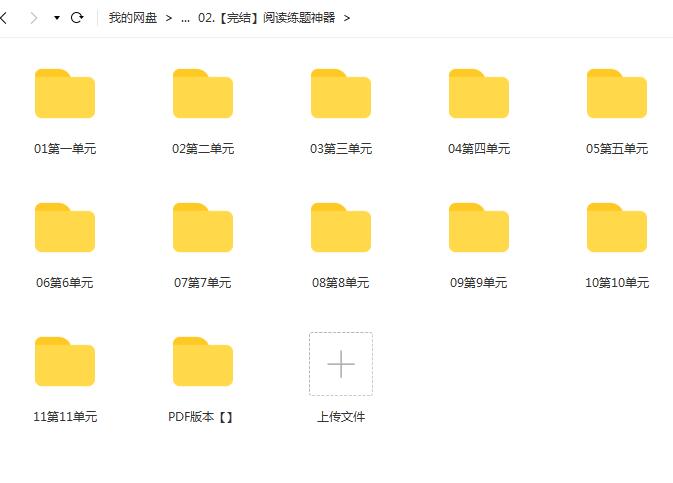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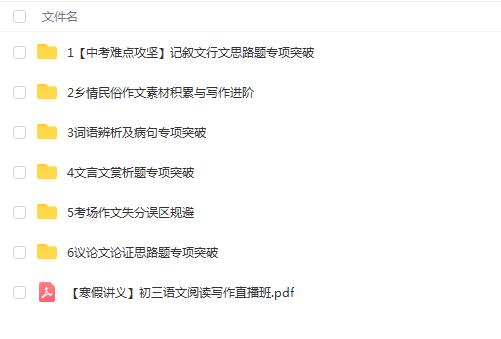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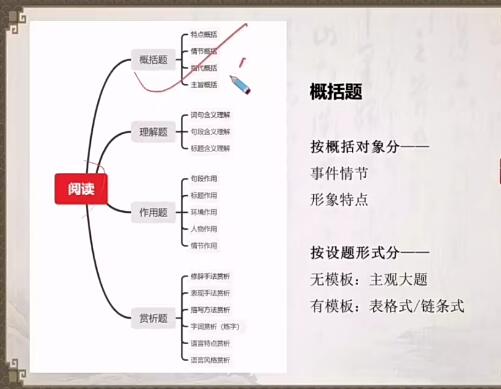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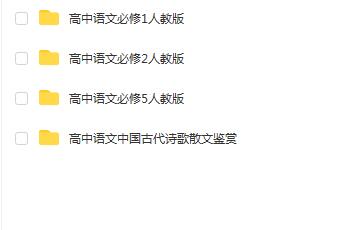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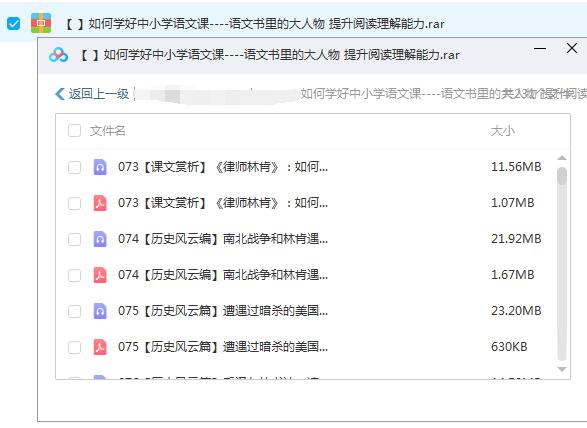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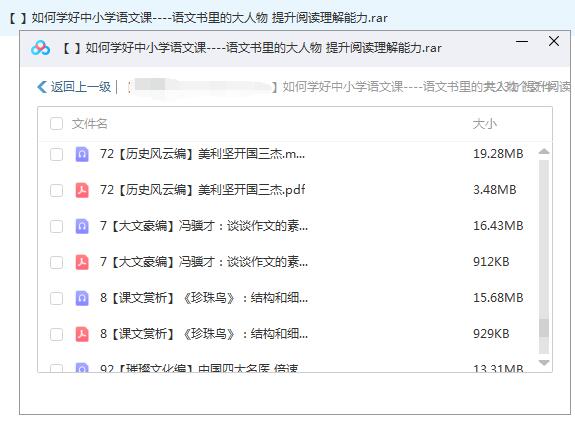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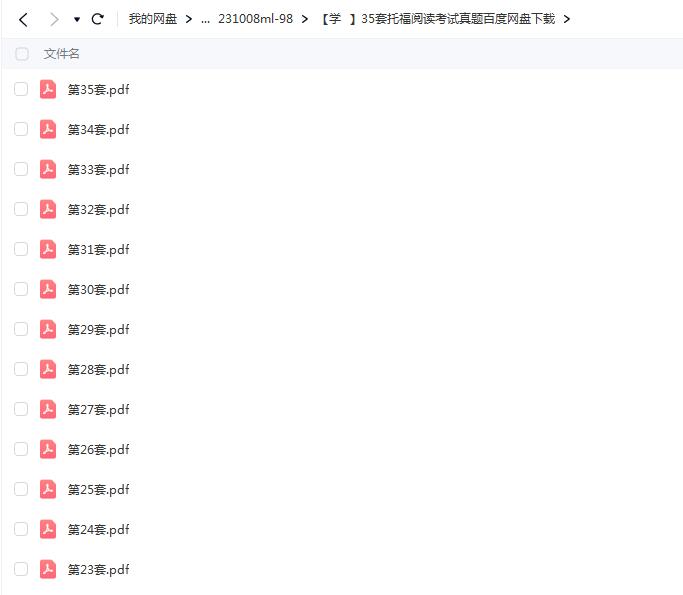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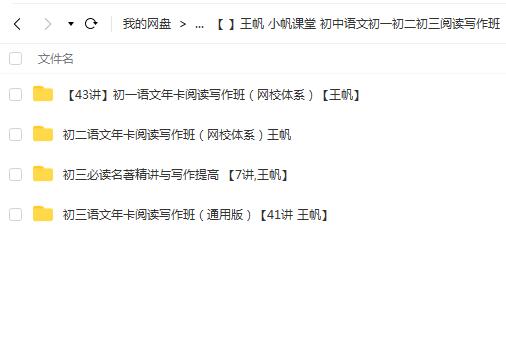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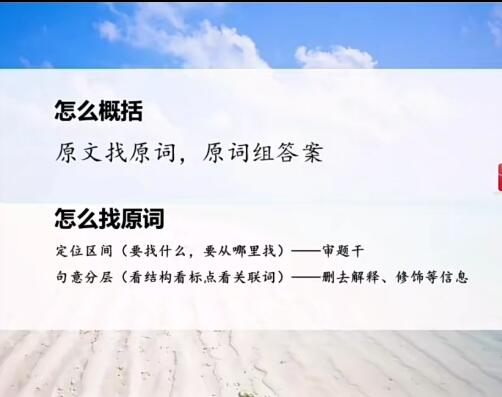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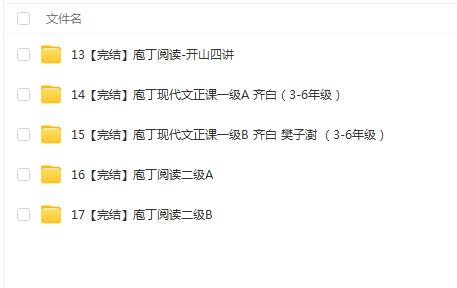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