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青春的诗意,诗意的青春 也谈朱自清的《春》
发布于 2021-11-23 09:47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用笔如舌,气韵生动”,我想朱自清的《春》当如是。写于1933年的《春》,穿越了历史的天空,成为一代代年轻学子的精神记忆。朱自清在《春》里织就的诗意空间,让无数年轻的心灵如获雨露的滋润。我们仿佛看到了“春色”哺育下的生命之光,正喷薄欲出!
但凡有些文学质感的人,就不难嗅出:作品流淌着浓郁的文学气息,更渗透着对生命的热情礼赞。饱满的情感,浓烈的诗意,优美的文词更使朱自清笔下的“春”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作者抓住春天最富生机的生命律动,让大自然在经历冬的蛰伏后再次焕发出生命的魅力!这既是对自然生命的刻意诗化,也是对青春民族的殷切呐喊!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绘景写实之作,而是表象世界里情思的深层迸发,是超越现实的艺术营造。
《春》的景物描写有其独特性。不得不说朱自清是使用修辞的行家里手。大量比喻、拟人等修辞的运用,令人应接不暇,但却自然、可爱。让人只读其文,便觉春色缭绕、醉意浓浓。我想这和作者对自然物象的敏锐捕捉和多思善感的情感体验是分不开的。朱自清对《春》中景物的细致描绘,正是他充分调动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对南北方春天的深切感受,当然还夹杂着对江南春色的儿时回忆。所以是虚实相间的想象之“春”,是诗意化和人格化的“春”。这里的“春”已超出“自然之春”,具有了象征意义。象征着民族之春,未来之春。
从美学价值看,朱自清笔下的《春》玲珑雅致,是自然的灵动美和温情的人性美的和谐统一。《春》的世界可以说是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在语言的使用上非常注重色彩的搭配,如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红、粉、白”,再加以比喻的修辞手法,给人以视角的冲击,有一种“淡抹浓妆总相宜”的舒适感;再如音韵的流畅和谐。文中有一段极富音乐感的句子: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华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闭上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这种生命的形式借助错落有致的乐感,既赏心,又悦目。同时还把生命的律动通过长短句的交错和盘托出。故钱理群先生评价其语言风格:“它是漂亮、缜密甚至华丽的。”笔者认为以“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评价之,亦不为过。读罢此文,让人感到丹田内似充盈着一股青春的少年之气!
《春》,其内在的气韵犹如一杯香茗沁人心脾。朱自清用他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和体认,更是为作品营造了一个虚实相间、似真似幻的艺术境界。既有对自然物象的深情描绘,又有超越自然世界的情感寄托。我以为,解读《春》我们要明确朱自清的两重身份,即文学家的朱自清和民主斗士的朱自清。我们可以认为《春》是作为文学家、诗人的朱自清与自然生命的“热恋”,是一种纯审美的“文学游戏”。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良知的民主斗士的朱自清。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主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后来逐渐成为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方法。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对解读朱自清的《春》同样有参考价值。在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每一篇作品都是作者生命形式的艺术呈现,更是对现实郁结的“精神突围”。当他用文字这种可爱的“小精灵”来表达自己浓烈的生命意识时,作者往往把对现实世界的深沉凝思隐藏在文字的“空隙里”,让读者去发现、填充。比如作品一开头就写到: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热切期盼。拟人化手法的运用,更是把自然的春天人格化,赋予了人的灵动。“盼望着,盼望着”,重复使用显得有力、急切。这何尝不是作者对青春国家、青春民族的另类表达!其实这种解读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如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李大钊在《青春》中放声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以国家民族为己任,振臂高呼,以新文化再创我青春民族、青春国家、青春国民!宋炳辉先生曾说:“这也是自梁启超以来的新文化人士,对于少年和青春倾情赞美传统的延续。他们颂扬青春,赞美少年,书写春天,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对象本身,而是在那些对象上,更多赋予象征意味,在这些作家的笔下,他们象征着对新时代的期盼,象征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朱自清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他的首要身份是文人、诗人。所以他便以诗人的方式把内心的感受糅合在对“春天”物色的赞美中,以诗意的语言“遥有所寄”。
《春》是朱自清专门为中学生而作,是献给中学生的诗意之春。文中的“春”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而初中生正是人生如花的年纪,青春年少,富有朝气,从里到外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张力。正所谓:“春色人情两相和”。朱自清应当是充分考虑到中学生的年龄和心理认知特点。这从他一开始接受受人之托的任务时就了解到了(笔者按:受邀为朱文叔主编《初中国文读本》撰文之事)。所以朱自清在写作《春》时,就刻意在思想情感上作了价值引导。比如作品里不管大人小孩,都个个精神抖擞,充满着希望(孙绍振先生语),给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朱自清接受的任务,到底有何要求?宋炳辉先生有如下表述:“这是朱自清为朱文叔主编的《初中国文读本》量身定做之作。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中,朱文叔介绍了该读本编选的主旨:不仅考虑选文的文学性,更重视'民族精神之陶冶’和‘现代文化之理解’,因而‘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并在课文标题左上角特别标注“*”,以示区别。”这段话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初中国文读本》的编选宗旨;二是文章的阅读对象。编选宗旨考虑到选文的文学性,即文辞翰藻。《春》所表现出的文采飞扬,色彩斑斓,正是作者对这一标准的接受和认可。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民族精神之陶冶”和“现代文化之理解”,即文的思想意蕴和精神旨趣。《春》里散发出的对生命的礼赞,正是对民族未来的无限憧憬。朱自清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曾提出要有“假想的读者”,即写作对象。显然《春》的“假想的读者”就是朱自清所处时代的中学生。如宋先生所言:“按照初中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为了贴近中学生的心里认知特点,作者以诗化的语言、诗化的意境把《春》的灵动、华丽和趣味表现出来,思想意蕴不直接与学生对话,而是隐藏在诗化的生命空间里。所以诗化的文辞可以与诗意的青春产生情感的共鸣。应当说《初中国文读本》的编选标准,是我们解读《春》的一个重要依据,不可忽视。
朱自清写作《春》有没有“微言大义”,笔者不敢胡乱猜测。可以肯定的是解读文学作品,“知人论世”当不可偏废,尤其是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清楚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写作对象,可以使欣赏者在文辞的空白处捕捉到更深沉的情思。但就《春》而言,这种深沉的情思在作品中是以明快的格调呈现出来的。《春》写于1933年。正值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之际。那是一个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时代。面对现实,朱自清心情是沉重的,“颇不宁静”。但是考虑到《春》这篇作品是为初中生而写,不能太沉重。所以作者隐去了严肃的“成人世界”的话语,而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营造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理想王国”。朱自清以自然生命的盎然生机,引导学生进入“自由王国”彼岸。或许这会给人一种避世的错觉,就像汉大赋的“劝百讽一”。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作者对年轻心灵的特殊“保护”,其目的是营造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与其说朱自清在自勾自画避世的“桃花源”,不如说是先生以一种轻快的笔触把一个纯净诗意的世界呈现给年青的孩子,给孩子留下一份希望,让孩子变得更加坚强。
对于朱自清的散文,不少学者认为过于“阴柔”。余光中先生就曾指出:“朱先生好用‘女性拟人格’的修辞。”这话固然中肯。但就《春》而言,似乎有不妥之处。文章的最后朱自清写道: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其中“健壮、铁一般”不正是阳刚的表现吗?看问题不能只看一面,鲁迅说陶渊明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不是一个道理吗?孙绍振先生认为这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们以更积极、更昂扬的精神诱导,却可能脱离了文章整体。笔者认为,这种精神引导很重要。孩子们毕竟要长大,要面对现实世界,民族的重担也必定要落在他们身上。诗意的“理想王国”不能代替现实的希冀。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很重要。因为学生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迎接现实,唯有此,才能创造美好未来。所以,在文学性之外,绝不能忽视“民族精神的陶冶”。
综上,笔者认为朱自清笔下的“春天”,不只是对大自然春天的新鲜、美好和生机盎然景象的描绘,也不只是为了用优美的文辞编织一篇美文,而是作者用强烈的情感营造了一个诗意的青春世界,让自然界的生命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寄寓了作者对蓬勃生命与青春的赞美和激励,也是对民族与国家未来希望的诗意表达。
坐忘斋主作于2021年11月20日
修改于2021年11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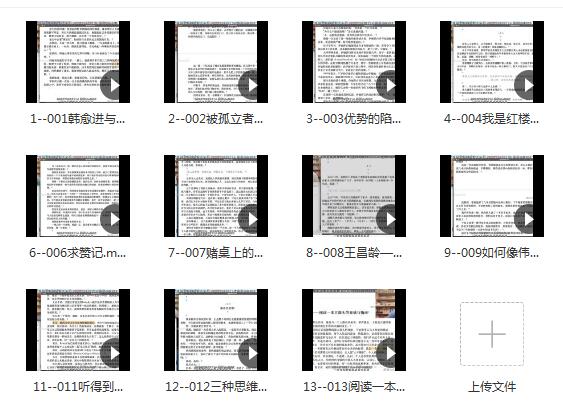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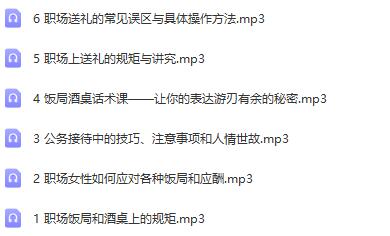

![[php基础] 解决PHP中的Bug,搞定PHP的错误体系的各种问题](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fd5a6305469616cdc05c47fa0e881d00.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Hadoop] 新版视频下载 hbase 是hadoop的重要组件 分布式的、面向列的开源数据库](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c5ca5ce9c087063421b806fd24132729.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C语言] 如鹏C语言也能干大事第三版 超经典的C语言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490160590fa102677140a8524e4e0415.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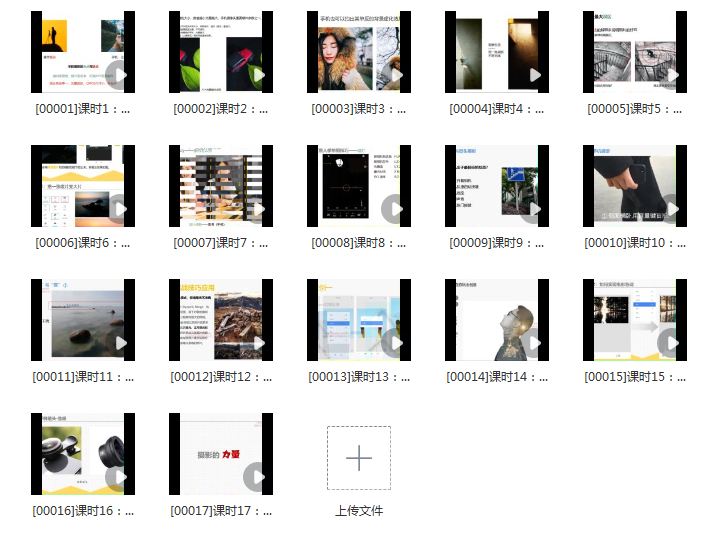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