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小说 | 张淑清:米鹿的夏天
发布于 2021-11-26 22:11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米鹿的夏天
张淑清
米鹿没有事的时候,就坐在院子的石阶上,看一群蚂蚁搬家。米鹿只有八岁,她能有什么事?米鹿用一根细细的铁丝,捅蚂蚁们,不是想伤害它们,就是想和蚂蚁近距离接触一下。蚂蚁的尾巴很酸,米鹿尝过,比树上的酸梨还酸。米鹿吃蚂蚁尾巴是有原因的,祖母说过,蚂蚁尾巴能治相思病。米鹿不懂相思病是什么病。她向祖母要妈妈时,祖母就把米鹿揽在胸前,喃喃自语说:“米鹿又害相思病。”祖母说这话时,一只黑色的蚂蚁,在祖母的腿肚子上游弋。祖母捏住蚂蚁,说:“米鹿,舔一舔蚂蚁尾巴,相思病就好了,就不想妈妈了。”祖母不会骗她的,米鹿信以为真,她照做了。蚂蚁尾巴酸得米鹿呲牙咧嘴,暂时忘了想妈妈。祖母叹口气,从那以后,米鹿一说想妈妈,祖母就逮住一只大蚂蚁,让米鹿吃。
风静静地拂来,有蛙鸣从荷塘传了进来。蚂蚁很团结,米鹿很难拆散彼此。祖父在劈柴禾,阳光这么好,木头的味道,清澈地传来。柴禾被一根一根劈好后,垛在墙角。祖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说过,等一会儿,去街上的阿来商店买冰棍给米鹿吃。一只冰棍五毛钱,相当于花掉祖父攒了一斤纸壳的钱。之前,父亲每个月给家里打一笔钱。祖父带米鹿坐客车到镇子的邮局取出来,给米鹿买两颗棒棒糖、一个蝴蝶结。爷孙俩在羊汤馆喝两碗羊汤,就着烧饼;在百货商店给米鹿选一件花裙子,皮凉鞋,买一个皮球,布偶猫。几乎每个月如此,最多耽搁两个月。父亲打钱回家,那是米鹿幸福的日子,不仅能喝上热气腾腾的羊汤,吃一个正宗的北山烧饼,最主要的是棒棒糖与蝴蝶结,让米鹿在玩伴们那被羡慕、被妒忌,看到他们的眼神可怜巴巴的,米鹿就开心,就欢喜雀跃。“你们不是说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吗?看到了吧?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谁敢比?”
去年夏天,祖父就不怎么去镇子了。祖父拾掇完几亩地,就骑着一辆脚蹬三轮车,四下捡废品卖。祖父对着半弯月儿抽大烟斗,一锅接一锅。有时,米鹿都睡了一觉,下地解手,看到祖父仍坐在暗影底,唉声叹气。祖母也陪着叹息。米鹿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米鹿和母亲的视频也少了,父亲的视频和电话更是少的离谱。米鹿问祖母:“是不是爸爸妈妈出了问题?”祖母说:“别瞎猜,没事的。有奶奶在,米鹿就有靠山,有人疼。”米鹿就没再刨根问底,因为刨也刨不出。
今天是周末,米鹿睡了一个懒觉,被一对落在窗前的花喜鹊叫醒。堂屋通向厨房的门是虚掩着的,空气里弥漫着祖父的旱烟味儿,没有苞米粥,没有煎小河鱼的饭香,也没有拍黄瓜的清新气息。米鹿这才想起,最爱自己的祖母走了。一个月前,祖母患脑溢血走的,祖母走得匆忙,没给米鹿留下只言片语,脸上很安详,睡着了似的。米鹿总觉得祖母是睡沉了,不会走远的。祖母活着时,米鹿每天夜里,睡在祖母床上。米鹿在里边,祖母在外边。米鹿本来想在外侧,祖母不答应,米鹿为此生祖母的气。米鹿坚持睡床外边,无非是想多看看窗外的世界。院子很大,石阶两旁是两株郁郁葱葱的杏树,此刻,青黄的大杏子挂在枝头,风一摇晃,瓜熟蒂落,就有杏子落地,啪嗒啪嗒响。蚂蚁瞄准目标,组团下手。甬道上的月季花开得肆意,花花草草,杏子,桃子,黄瓜,小葱,绿色的植物,全是祖母的杰作。米鹿愿意趴在窗台,看院内的草木繁花,望着日头,一寸一寸朝天空中央挪移,然后,再一寸一寸下到山坳。望着那条父亲出资修的柏油路,曲曲弯弯伸到村外。一天不见父母,两天不见,一年不见。父母究竟怎么了?米鹿也不问了,没有答案的。米鹿闲下来就在院子一角,琢磨一只蚂蚁的命运。蚂蚁有几只眼睛、几条腿、几个鼻子?蚂蚁是不是也有爸爸妈妈?米鹿不厌其烦地讨教祖母。“蚂蚁几条腿?”祖母在一个簸箕里搓苞米,米粒金黄耀眼,发出粮食独有的光芒与香气。祖母想了想,说:“我也没数过蚂蚁几条腿,这好办。”祖母放下簸箕,在门楣上发现一队蚂蚁,正训练有素地朝一颗大米粒爬去。
米鹿就想到,这颗米粒是她不小心甩在门楣上的。米粒本来要进入她的牙齿,舌头,最后在胃里停留。出了什么状况,米粒沾在了门楣上?米鹿想到吃饭时她听到一首歌,他们玉树临风的班主任唱过,《可可里海的牧羊人》,好听到爆。学校的学生都爱唱,米鹿也不例外。米鹿端着饭碗,有一搭没一搭塞米粒,《可可里海的牧羊人》的旋律就激情四射地飘过来。米鹿撂下碗筷,冲出屋子。米粒就是在她迈门槛时,通过她袖口掉在门楣上。那颗米粒是在嘴边的,米鹿用袖子擦了一下嘴,事情就这样尘埃落定了。蚂蚁和人类有许多共同点,比如对美食的欣赏与占有。蚂蚁单飞的可能性不大。祖母为破译蚂蚁到底几条腿,按住了门楣上的一只蚂蚁王,食指拇指一夹,把蚂蚁王夹晕,摊在掌心里,数蚂蚁几条腿。看起来很荒唐的一件事,米鹿与祖母却津津有味,这是夏天以来,米鹿比较开心的日子。祖母可以停下手里的活,陪米鹿研究一只蚂蚁,几条腿。米鹿认为祖母一大把年纪,怎么会不清楚蚂蚁几条腿呢?祖母在米鹿眼中,是神一样的存在。现在,祖母张着漏风的嘴,对米鹿说,蚂蚁有六条腿,比人多四条腿。祖母说出这个数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这是一块泰山石,压了她好久。但米鹿的问题又来了,米鹿歪着小脑袋说:“蚂蚁有六条腿,爸爸妈妈才两条腿,加一起四条,蚂蚁走不远,可爸妈走到米鹿看不着的地方,他们的两条腿为什么走那么快?!”祖母说:“蚂蚁没有火车、客车和飞机啊?”米鹿不满意祖母的回答。米鹿八岁了,她有自己的思维。米鹿说:“按常规,蚂蚁会走得更远。父母坐两个小时的车到海南,蚂蚁理应一小时就抵达。”祖母诧异地问:“米鹿,你咋计算的?”米鹿说:“老师说了,二二得四,蚂蚁六条腿,爸爸妈妈两个人四条腿。多出来的两条腿,就相当于人坐的飞机、汽车。”祖母就不说话了,祖母说什么呢?苞米粒沙沙沙落在簸箕内,光影下扬起小小的灰尘。
米鹿有空就咂磨蚂蚁为什么比人多两条腿,似乎这项研究比她的学习成绩重要。祖母不止一回告诉过米鹿,她的父母在南方做事,很忙很忙,没有时间回家。米鹿上学后,见小朋友都有爸妈接她,只有她形单影只。偶尔祖父去送送,基本是她一个人独来独往。米鹿就恨父亲母亲。米鹿在祖母面前埋怨,哭着喊着要爸爸妈妈。祖母安抚米鹿:“如果你爸妈不努力赚钱,你就读不起书,也住不上二百多平的大房子啊?!”米鹿说:“我宁肯睡窝棚,也不想他们出去。”有时候,米鹿的父母三年两年都不回来。他们给米鹿的祖父祖母,各买一智能手机,有空了发视频,和米鹿、老人唠十几分钟,就挂了,说要谈生意。米鹿对着视频里的母亲,一个劲地追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我想你和爸爸。”母亲说:“快了,快了,做完这笔生意就回北方。”米鹿不知道父母做什么生意,父母从南方开回越野车、甲壳虫样的车,一进村庄,引得很多人放下手里的农具,跑来围观。有识货的人啧啧称赞:“这车少了二百万,买不了。”米鹿的祖父腰板挺得刷直,一支一支递烟给大伙。那烟草真的香,米鹿捡过大人抽完的烟蒂,闻了又闻。米鹿在人们艳羡的神情里,知道父母是干大事的人,父母有本事,祖父祖母脸上也有光。平时,那些欺负米鹿的孩子,都上杆子讨好米鹿。米鹿昂着头,终于可以在他们面前扬眉吐气了。
那些天,家里很热闹,来串门的男女,问父母如何做生意,在南边咋样。人们把米鹿父母在的城市,称作南边。他们热切希望米鹿的父母带带他们。米鹿管不了别人,也不想管。米鹿想留住母亲,躺在母亲的怀里,枕着她的臂弯,听母亲讲南边的故事。守着母亲从南边捎回来的变形金刚、芭比娃娃、巧克力,米鹿像是在做一场梦。母亲在的那些天,米鹿比过年还兴奋。
米鹿感到时间太快太快,她想让祖母信奉的菩萨,莲花一抖,绊住父母的腿。她希望时光慢下来,再慢一点。菩萨终是没出现,月亮走着走着偏西了,星星亮着亮着就隐匿到云层。
父母走的那天,车上拉了三两个青壮劳力,搭米鹿父母的顺风车,去南边淘漉生计。米鹿攥着母亲的胳膊,不让走。母亲头一年走时还哭过,一步三回头上了车,想米鹿了就打电话来。后来,就不怎么哭了。家里却发生着变化。原来的五间破瓦房换成了二层小洋楼,轿车代替了自行车。这变化哪里来的?人挪活,树挪死。就连村支书老马,也冲米鹿的父母竖起大拇指。村里那条土路,是米鹿父母掏腰包修好的,他们不去打江山,就唯有住破房、走泥泞不堪的土路。这是成年人的想法,米鹿不这么想。米鹿就像一头小鹿,在长身体的阶段,她需要母亲的呵护,谁也取代不了母亲在米鹿心中的位置。祖母再怎么好,也不是米鹿的母亲。祖母也没文化,认识的字没有几个,对米鹿的学习辅导不了。祖父倒是读过几天私塾,但祖父有地种,有事做,整天不在家,关心不了米鹿。米鹿的母亲高中文化,字写得好,读书时,拿过省内征文大赛奖,辅导米鹿的学习绝对绰绰有余。母亲选择在南边做生意,米鹿阻挠不了。父亲和母亲出了什么幺蛾子,米鹿一无所知,甚至在祖母突然与世长辞后,只有父亲开车回来奔丧,不见母亲踪影。米鹿看到,父亲瘦了,黑了,眼圈发乌。父亲进了风门,对着躺在几块木门上的母亲,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崩溃的样子,叫醒了麻木的米鹿,原以为祖母是睡着了的米鹿,哭得寸断肝肠。米鹿这一哭,带动了所有人。他们是米鹿家的亲戚,平素没空交流和来往。这一次,米鹿祖母一去,大家反而聚在一起,简单聊几句,拉近了彼此的感情。米鹿也被一种浓烈的人情氛围簇拥着,家里突然的喧闹,让米鹿又悲又喜。悲的是,从此后人间无祖母这个人;喜的是,一个电话把父亲揪回了家。母亲为什么不和父亲一道回?米鹿揣着疑问,一遍一遍看向父亲,她想叫父亲主动对自己说母亲的去向。可父亲一直没提母亲,好像他的世界从来没母亲这个人。
米鹿很想对父亲说,带她走,去南边。到南边,米鹿可以和母亲在一起,吃什么都行,干什么都可以。洒水扫地,擦玻璃,烧火做饭,轰鸡撵鸭,只要有母亲在身边,怎么都行。米鹿在家又不是没干过活,给祖父担水,提着泔水桶喂猪,铲地,拔草,生炉子,拾柴禾,掰苞米,收谷子,插秧。米鹿是祖父祖母身后的一条鱼,走到哪,跟到哪。
从进门到祖母入土为安,父亲都没正眼看米鹿,米鹿怀疑自己不是他亲生的,不然,怎么如此冷漠?!那晌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告别米鹿的祖父,扔一点钱,开车走了,头也不回,仿佛是这个家的客人!米鹿咬着牙,不许自己哭出声。八岁的米鹿,意识到那些孩子以前的话应验了,她成了父母的累赘。父亲走的那晚,米鹿迷迷糊糊睡着了,不吃不喝,睡了三天。祖父请村里的医生来给米鹿看病,医生说,米鹿是受了风寒,高烧不退。服了退烧药,不一会子就醒了。米鹿醒了,四处找祖母,房间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找了,没有祖母。房前屋后以及果园也寻遍了,哪里有祖母的影子。祖父的头发一夜间都白了,祖父说,你奶奶在山里睡着了,不回来了。米鹿不听祖父的,她趁着祖父给菜地锄草的空隙,去了祖母睡觉的山坡。夏天,各种植物正茂密,古木参天,野花怒绽。祖母睡觉的地方,几天时间,长出一片蒲公英,开着艳黄的小花。山谷的松树、柞树被风一吹,发出低吼,像几匹马在嘶鸣。米鹿跪在祖母坟头,说一会,哭一会,哭一会,说一会。米鹿说:“我想去妈妈那,父亲不带我。奶奶保佑我,找到妈妈。奶奶走了,这世上,还有像奶奶一样爱我的人吗?奶奶说过,妈妈因为爱我,才去那么远的南边做生意。”米鹿说着说着,累了,也许是乏了,就依在祖母坟前的一棵山楂树上,睡了。
一抹紫色的霞辉抻进房内,两只花喜鹊吵醒了米鹿。米鹿以为祖母尚在人间,想着苞米粥,煎小河鱼及有祖母味道的早餐,而这一切只是一个梦。米鹿照旧过村头那座石桥去上学,曾经取笑米鹿的学生,又登场了。他们的牙齿比魔鬼还锋利,他们的话语比魔鬼的咒语还可怕。他们围着米鹿又蹦又跳,说:“米鹿就是没人要的野种,村里人谁不知道,米鹿的娘在家做姑娘时,就怀了米鹿,米鹿的父亲不知是哪个!”米鹿一张嘴抵不过十张嘴。米鹿就抓起一把沙子,扬了过去,那些野蛮孩子跑了。米鹿垂头丧气回到家,二层楼越发空旷。祖父埋着头,抡着一把小铁锤,砸一枚杏核。白色的肉,像一块玉,无暇纯粹。祖父把那块小小的“玉”,递给米鹿。米鹿一下子拍掉了那块“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爷爷,告诉我,我是不是爸爸亲生的?妈妈也不要我了吗?!全世界的人,都瞧不起我,小明、小花,我最好的伙伴也不理我了,我做错了什么?!爷爷,呜呜呜……
天边堆来一朵积雨云,一朵又一朵,雨点先是铜钱那么大,噼里啪啦,滴在水桶上,瓦楞间,水缸里,石槽内。不久,雨小了,乌云散尽,天阴着,有蚂蚁爬过灶台,进了米鹿睡觉的房子。它们排着队,一只紧接着一只,马不停蹄的,不知在追逐什么。米鹿感觉这群蚂蚁很眼熟,仔细看,其中有一只体型大一些的,五条腿,左边少了一条。米鹿记得,这是蚂蚁王后。祖母让她舔过蚂蚁王尾巴,蚂蚁王就死了。祖母说,蚂蚁王是不堪羞辱,咬舌自尽的。难道,蚂蚁王后进房间是为蚂蚁王报仇?米鹿想不通,脑壳想得生疼生疼。这一次,米鹿没有碰蚂蚁们。米鹿望着蚂蚁成群结队,在她床上绕了一圈,最后又沿路返回。米鹿茫然地看着它们,走开,消失。
祖母百日那天,父亲没回来,村支书老马来了。老马是带着两个陌生人来的,米鹿嗅到气氛不对劲,攥着小拳头,护在祖父前面。老马支书说:“米鹿,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马伯伯。别挡着我们,这二位叔叔要和你爷爷谈点事。”
祖父支开米鹿,米鹿没走远,就站在门外竖起耳朵倾听。老马支书声音不高,唯恐米鹿听到,但米鹿已经听个八九不离十。父亲做生意赔了,这处楼房抵押出去了,刚才那两人是银行的。
米鹿和祖父搬进了偏厦子住,他们的二层楼被人买下,做了一个旅游开发商的寄居地。米鹿的祖父被那个开发商雇用,给他们打更,看管上百亩桃林。杏林。祖父对米鹿说,这片宅基地是他们张家的,他是不会离开的,他在这里等着米鹿的父亲东山再起,将宅院赎回来。
夏天很快过去,秋天到了,米鹿读四年级了,米鹿的蜡笔画,被推荐上了本市一家杂志,并得了五十元的稿费呢。米鹿的画很有内涵。她在大地上花了一棵向日葵,一个小女孩站在向日葵下躲雨,雨滴稠密,斜斜地落在硕大的向日葵盘上,女孩闭着眼,双手合十,在祈祷着什么。她的内心干净纯净,小小的年纪,目的很单纯。她就是想要一个怀抱。世间薄凉,她想找一个港湾取暖。
这幅画走出大山,走进城市,最终在一家画廊驻足,获得市年度绘画比赛二等奖。
米鹿所在的村子,被开发成风景区。米鹿一边读书、绘画,一边帮祖父干活。米鹿的画里藏着她的梦想,她将树木叶子、花卉、昆虫、蚂蚁,还有蓝天白云都画进去。夜色如水,米鹿就对着这些画,想远方,对着树叫妈妈,对着月亮喊爸爸。她想,总有一天,父亲、母亲会回来的。如今祖父一天天老去,米鹿要陪伴着他,祖父也是不肯离开村子半步,他经常去米鹿祖母的坟前,说一阵悄悄话,说米鹿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夏天再来的时候,米鹿的母亲开车回来了,她一身珠光宝气,挎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油腻男子的胳膊,走进米鹿家原来的二层楼。她看到门口挂着的风景区牌子,吃了一惊。显然,她被这个变化吓了一跳。当她获悉所有经过后,执意带米鹿去南边。米鹿很平静地回复:“不去,我留在这里陪爷爷,哪也不去。
北山区的夏季风很蛮横,也有几分清凉。此时,山愈发绿了,水愈发清明了,米鹿的心越来越安静了。她抱起一捧柴禾,倔强地进了厦子内。
厦顶的烟囱,不多时,袅袅炊烟。
这个夏天才真正属于十岁的米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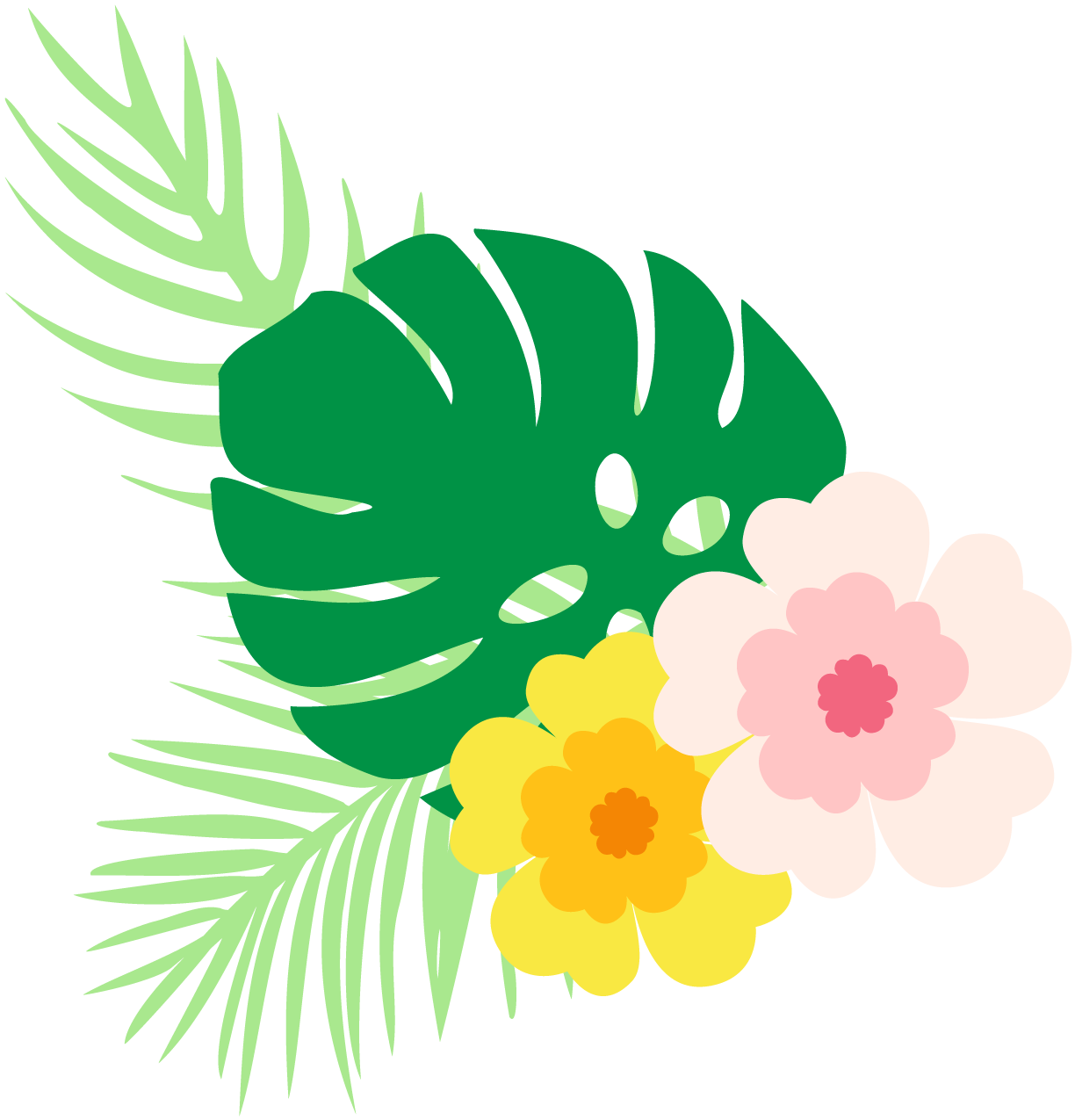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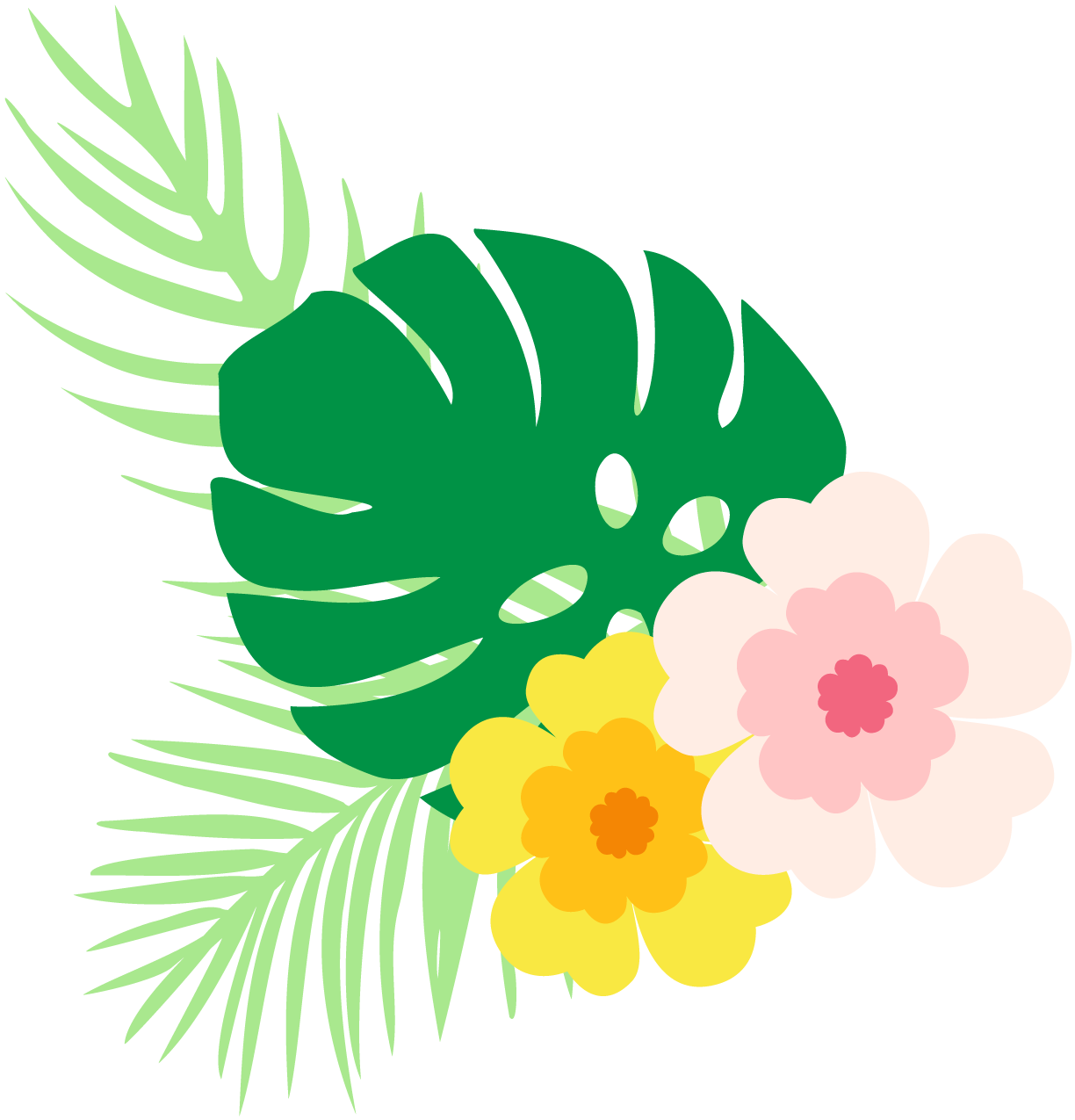
张淑清,辽宁省作协会员。作品在《北京文学》《鸭绿江》《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牡丹》《短篇小说》《大鹏文学》《岁月》《小小说月报》《海燕》《椰城》《散文百家》《辽河》等刊发。

热爱文学的志愿者
为奔流文学基金发起筹款
为一个善意而美好的世界
献上我们微薄的一份力量
快行动起来吧小伙伴们!
阅读|文学|情怀

繁荣文学 培养新人
扫描ErWeiMa

gongzhong号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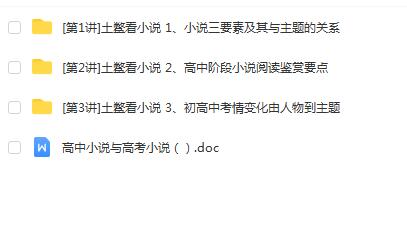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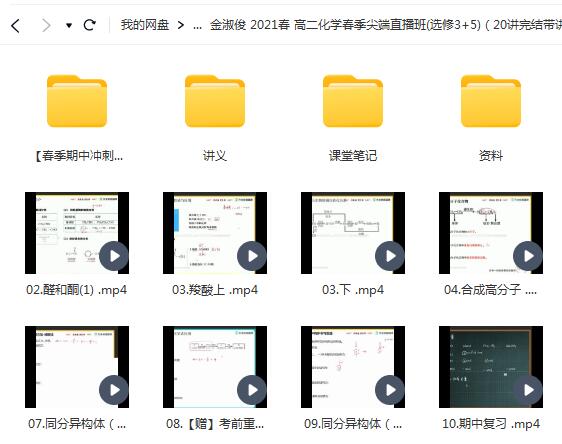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