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周凌云:村中遇雨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06 09:56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村中遇雨
周凌云
对太阳出没于村庄的上空,我对它的考勤记载不全,哪天是火焰,哪天晒得温暖,更没有记录。只要把雨天记清就够了,雨天的日子一剔出,几乎都是太阳。太阳照耀的村庄,模样一样,升升落落是它的本分,不会编纂大起大落的故事。
雨天呢?不同。村庄的悲欢,有一部分是雨写的。雨天值得记载。我对雨天有耐心,心态也复杂。有时,我歌颂雨,为它献诗,有时,我跺着脚骂天,让雨也听见。
——题记
太阳雨
立秋后,常下太阳雨。
太阳仍然火辣辣,吊在村庄的高空,放射出丝丝缕缕的金光,照在树上,落到禾苗上,钻进了土地。几团云追撵着太阳。
突然,太阳的金线上,闪闪亮亮,好像金线在熔化,簌簌坠落。喔,这是太阳的金丝在补缀满天的雨帘。有些雨顺着光飘飘洒洒,有些雨,落在光上蹦蹦跳跳。太阳晒着,雨下着,分不清哪是雨,哪是太阳。雨和太阳律动着,一起编织太阳雨的奇景。
我琢磨着,太阳在天上,雨也在天上,走着走着,突然纠缠到一起了。有时候太阳蓬蓬勃勃,雨擦身而过,只湿透几缕金光。太阳照样扫过天、扫过地,扫过我们的头顶,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如果雨占了势头,就织下天大的麻袋,把太阳罩下了,万箭齐射,天地混沌,滚过雷鸣般的声音。雨的缝隙,发射出三四缕强烈的光芒,照在奔跑的羊群上,为羊群划一条明晃晃的道路。
下太阳雨,最神奇的是田坎雨。突然从山外涌出一股,越过太阳山,落进山腰,盖住一片林子和房子。雨在公路上跑着。密密麻麻的向我身边靠来。雨像无数的鞭子抽打着太阳,太阳退到我头上来了。我吓得想跑。跑得过太阳,但跑得过雨吗?我的头上,一边是雨,一边是太阳了。我眼前的一头老牛也是这样,脊背的一边晒着太阳,另一边淋着雨,脊背成为分水岭。前面的那片田呢,田坎外雨雾蒙蒙,弯弯的茅草,高高的槐树,都在雨帘中模糊了,而田坎内,庄稼仍顶着密密麻麻的太阳光。我看见农民正在地里收拾苞谷,太阳雨来了,来不及躲跑,男人淋得如落汤鸡,女人却干干净净。雨和太阳一直在田坎上僵持着,斗牛的架势。太阳和雨,谁更有力量呢?
太阳雨,从西边窜到东边,轰轰隆隆,一溜烟就跑了,有时又是啪啪啪啪,铺天盖地,一股一股抛洒雨花。
下太阳雨,农民喜欢。太阳有了,雨水也有了。连庄稼也喜欢。
雨,慢慢退了,退到田坎的外边,退到树林之中,最后又退到山后边去了。无边的雨帘,像舞台拉上了幕布。
昌亮扛着长长的竹扫帚,带着十几个娘们儿扫公路时,遇到了太阳雨, 昌亮淋了一身,雨过了好一阵子了,衣服也还没干透。金娥、万福、学珊几个女人却干干爽爽,有的只是头上跑了些雨星子,有的在树下躲过了。太阳雨一过,都朝回赶了。雨下过的地方,公路冲洗得洁净,没雨的地方,也只是囫囵扫了几下,把杂物、塑料袋撩到了公路外,下雨了,早点收工。
我坐着村支书的摩托车,赶到扫公路的现场。昌亮扛着长长的竹扫帚,一手持着农药瓶,一瘸一拐地走着,女人们三三两两紧跟着。
我对昌亮说,公路两边的杂草,不能图省事,用草甘膦一喷了之,使用农药我们要节制。
村支书沿途看了看公路,对打扫的情况很不满意。公路靠山边的水沟,拉圾并没有清除,一下雨到处漫流,庄稼地会被冲刷,水土会流失。我们就近借来些工具,一起又干起来。村支书叫来一辆三轮车,把垃圾全拖走了,拖了好几车。
每个月扫公路时,都是昌亮带一班娘们儿干。大伙儿心里有意见,扫公路怎么都是贫困户和低保户的事呢?村支书也没有好法子,琢磨着让全村的党员来干,但80多个党员都是老弱病残,青年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只能安排贫困户和低保户轮班来扫。他软硬兼施,要么说些好话,要么来硬的,不听安排,就说:下掉你们的贫困户和低保户!
虹,出现了。妖娆袅娜舞着长袖。先是若隐若现,飘飘忽忽,接着才是一个大的跨步,坚定的跨步,从太阳山跨越到后山。虹,是太阳雨的幺女儿,太阳雨把七彩灿烂的衣服都给她披上了。
太阳重新普照大地。好干净的天空!几只鸟躲过了太阳雨,向村子的上空飞来,有点悠闲和舒漫。
连阴雨
雨,下了一个多月了,大雨一阵,小雨一阵,绵绵细雨一阵,总是没有停歇过。天,总是睁不开眼睛。要下到牛年马月吗?太阳到底跑到哪里去呢?
一直没听到鸟的鸣叫了,影子也看不见,空中飞行的痕迹,早就织进雨帘中去了,那些山雀子不知会躲到哪里去,我替它们操心,真是无处可去啊,树上的鸟窝,编得再坚固,风雨飘摇,一两个时辰就被摧毁了。
花花朵朵也遭遇不幸。一切树木瓜果刚开了花,瓣儿和蕊就被雨打掉了,没绽开的花蕾,好像一直停顿在那里,休眠着,不能绽放,还有,本来饱满的蕾怎么就萎了。柑橘花也纷纷落下,秋后的好收成,别抱太大的指望了。蜜蜂们飞不出去了,就是雨暂停个把时辰,嘤嘤嘤飞出去,会落在哪朵花上呢?是吮吸雨水还是花蜜?生存有了危机。向老幺养的蜂子,死了一多半了,四十多筒蜂箱,只有十几筒还有嗡嗡嘤嘤的声音。
向老幺从12岁起就会养蜂了,从小就喜欢,一辈子就干了这件大事。他自认为这是件大事。他是个快活的人,会拉二胡,天天拉,也仿佛拉了一辈子,雨天,我隔三差五去他家听他拉一拉,但感觉不出好在哪里,都是几支老曲子,还走很远的调,不像是拉了一辈子的,但是我听到了他的快乐情绪。他家的房屋,一面墙都是蜂箱,几十桶,是全体蜜蜂的家。蜜蜂是养蜂人的千军万马。养蜂人却不是指挥官,不能发号施令,在哪里采花,吸什么蜜,是蜜蜂们的事情,只有蜜蜂们知道,桃花、李花、杏花、樱桃花在哪些人家,菜花儿、橘花儿在哪座山坡,红色的、黄色的在哪儿,紫色的在哪儿,花儿们在全村的分布,都在蜜蜂们的心里。养蜂人只顾用艾叶熏棉虫,打打扫扫蜜筒,让蜜蜂们住得干净就行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割蜜。蜂儿们飞来飞去从不停歇,跑到几里外甚至几十里外采花蜜。
淅淅沥沥,一直是连阴雨,向老幺损失惨重,他的经济柱子是靠卖点蜂蜜,当下死了那么多蜂子,别指望像往年一样收获了,是拦腰折断了。不过客观地说,向老幺蜜蜂产量也没怎么增长,都与上年持平便不错了。农户种植的瓜果蔬菜、橘柚桃李,还是喜欢打农药,花儿开得蓬蓬勃勃时,蜂儿飞上枝头,有的药死了,有的无功而返,有的在空中飞着飞着就栽倒,像一架小飞机中途失事了。向老幺厌恶别人打农药,看见人在橘树上喷药,就喷口水偷偷骂几句。村里的生态好不好,向老幺的蜜蜂是试剂。房前屋后,蜂儿莺歌燕舞,在村庄里穿来梭去穿针织线一般,空气就像脆生生的苹果,香甜得可口。蜂儿飞得少了,空气就是旱烟呛人的味道。连阴雨也下得好啊,虽然饿死了些蜂子,但可以把些污垢淋一淋,冲一冲,太阳最终会出来的,天地焕然一新时,再开些花,蜂儿们又会忙碌起来的。向老幺多养蜂,还是为了女儿菊英。菊英精神病不好,他一直都有一块心病。好一阵,歹一阵,变变幻幻。要吃药,要住院,要开销,养蜂酿蜜都贴了她,虽然享受了扶贫医疗政策,但养蜂的事业丢不得。不论好歹, 一年有好几万元的收入。
二胡的声音并不清脆,不是把好二胡,我并没有享受到音乐的美感。但是这把二胡是菊英在县城读书时买回来的,他很珍惜。向老幺后来才知道,班上一个男生爱拉二胡,菊英爱听。回家了也要爸爸天天拉她听。
我来听,也是在连阴雨里度时光,天气压抑人,要自寻乐子。菊英听,是向老幺在疗养女儿的心情。长长的连阴雨,让我和这家人有了融洽的联系。饭熟了,留我吃,我也不假意推辞。农民都是直肠子,不是弯弯拐拐的,虚心假意,繁文缛节,只有饿肚子,和农民打交道,要直,要诚,要真心为他们办事儿,才能和他们交上朋友。我虽然不会拉二胡,但是我喜欢音乐。他没有简谱常识,全凭感觉。一支新歌子,他只要听别人唱两遍,就全会拉了,这也是天赋。如果他还年轻些,我可以在县城找个老师教教他,纠正一些毛病。上了岁数了,就让他这样接着自己的路子拉下去,他有自己的“简谱”,如果再去纠正一些习性,反而不会拉了。菊英爱听就行!
雷阵雨
看起来,天晴了,但还是有云,一团一团,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有的还一丝一丝,一时云,一时太阳,阴一阵晴一阵。太阳从云缝中挤出来,就像射出的一束束激光,照射在太阳山上。瓦栎树,银杏树,刺槐树,高高挑挑,也泛出金光,仿佛太阳山上真的长出了金条,一下子好像冒出了一丛丛的美丽传说,此时,山上的万物都在兴盛繁茂。
突然,太阳又被遮住了,太阳山又暗淡下来。整座山像泼满了淡淡的墨水。但是一切都是清晰的,山的轮廓、树和人家,并不是模糊一片。但是一块天大的幕帘,罩住了村庄。每一种事物都倒向荫处。太阳不再沉默,谁也抵抗不了太阳。当幕帘开始揭起的时候,云慢慢退去了。山峦重新灿烂起来。一团云,两团云,还在与太阳周旋的时候,就像一两团淤泥沉落在地上了。
这是上午的景象。
晌午后,云层慢慢堆积起来,密密实实的越积越厚,越积越黑,比村头那棵核桃树的大黑洞还要黑,黑鸟在空中飞行,已不能分辨,压在我们头上,像一口巨大的黑锅,我们的头发甩上去,可以绞缠到乌云中去了,呼吸也感到急促。
有一个小小的闷雷在天外响了,听起来,好像卢二不经意的一声叹息,隔了一阵子,这阵子正好是卢二从家里走向村委会的时间,他顶着黑云,仿佛戴着无边的帽子,来取救济的衣服和被子。闷雷多起来,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了,像我的鼾声连续不断,一高一低,一长一短的,有时听起来,不止一个雷,很多雷混在一起。感觉有一支神秘的部队降临,脚步是多么密集和紧迫。
一团光在黑云中闪过,刹那,黑云被撕裂了,散乱成无数块,丢在天边,这道光并不是直线,是一团神经系统,像我随意画画写写的折线,散乱无序,瞬间即逝,比我眨一下眼睛还闪得快。闪电,总是开路的先锋,是探路的旌旗,它指向哪里,雷声便冲向哪里,这是一场战斗。闪电和雷声组成了军团。有雨点密密麻麻洒下来。闪电扯得更远了,像导弹在天空穿行,雷声大起来,狂风随即也到了。
卢二领了物资硬要回家。
耀眼的强光在我的眼前乱射起来,我立即捂住耳朵,“轰!”,巨大的雷声还是炸响了,好像就在头上。雨,倾盆而下。天地一片混沌。一会儿,雨,奔跑到太阳山那边去了,一会儿,又从太阳山跑回来。反反复复。
一阵闪电;
一阵响雷;
一阵骤雨;
一阵狂风;
突然,一声开天辟地的雷响,炸在古老的核桃树上。
一切平息下来后,我们去看那棵核桃树,它被击倒了。哇—哇—哇,我们在路上行走时,听到空中有一只黑鸟悠闲地叫着,接着又听到一只在叫,感觉是藏在一棵高大的树上,哇,哇,哇,节奏急促一些,另一座山上,也有几只黑鸟仿佛在应答,哇哇,哇哇,哇哇。凡听到黑鸟的叫声,村里都没有好事情。
卢二被雷打死了。
几百年的核桃树,看起来粗壮,里面已空洞了。我曾看见村中的孩子,捉迷藏,在里面躲藏过。卢二肯定是藏在里面躲雨,被雷打了。卢二只在村外偷偷摸摸,并没做过好多坏事。
跑暴
有一只黑鸟从太阳山的最高端飞过来了,哇,哇,哇,声音由远及近,翅膀扇得越来越快。村庄那棵最高的树上,好像也有几只鸟回应了几声,我的头顶也有一只,哇,哇,哇,也叫了三声,好像在接应那只飞回的鸟。飞回的黑鸟绕树三匝,离开了高大的皂角树,它的身后也飞动着几只黑鸟。我才看见皂角树上有一个鸟窝。
哇,哇,哇。
哇,哇,哇。
村里的黑鸟,大部分起飞了,跟着那只大黑鸟飞翔的方向。平时也没注意,村里究竟有多少鸟,现在集结到空中了,黑压压挡住了太阳,才明白,鸟比人多多。鸟都飞走了,留给村庄的会是什么事情呢?》
天气闷热极了。我无缘无故地冒汗。狗喘着粗气,舌头伸得更长。树静止不动,蝉也不叫了。
太阳山的头顶突然冒出一团乌云,像核反应堆,朝天上膨胀,膨胀,膨胀。无限地膨胀,也向村子压来。有一阵风也掠过来。并不是那种凉爽的风。头顶几个“炸雷”把我惊吓住了,仿佛失了魂魄。
“跑暴了!跑暴了!”有人喊叫。
“跑暴了!跑暴了!”都在喊叫。
人们惊慌失措。有的赶紧收拾院坝上的苞谷。金黄耀眼的,如果被雨淋了,会烂掉,猪也不会吃呢!有的扛了工具,从庄稼地拼命朝家里跑。先是看见核桃大的雨点,零星地落在地上,旋即,密密集集坠下来了,仿佛听见了急促的马蹄声。我的心揪起来了。
雷声滚滚。狂风大作。暴雨翻过太阳山,越过几条岭,像城墙一样碾压过来。暴雨跑到哪儿,哪儿就地动山摇。整个村庄很快被暴雨包围了。
跑暴过后,高木秀林折断,山洪咆哮,有些地方改变了模样。村民的房子有倒塌的吗?贫困户的橘园和茶园有冲毁的吗?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从村委会出发,紧急分头行动,检查灾情。
还好,全村还没有房屋倒塌,也没有群众伤亡,田土冲毁却普遍。各户都报了损失。
我们工作队住的房子受到摧残,这是银之的家。
“长头发”的牛群冲散了,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我和八组的理事长组织了十来个人,让“长头发”带路,遍山寻找。“长头发”给牛搭的棚子全被风雨掀跑了。“长头发”没有在自己房屋周边给牛建几个牛圈,如果将牛集中起来关在一个圈里,也不是好事,那么多牛挤到一起,迟早会干出些蠢事来,怕不好收拾残局。把牛棚分散,在各个山坡儿搭建些棚子,让牛各有其所,悠闲地吃自己的草,风雨来了,到自己的棚子里躲躲雨,也都安心,各不理视,也互不往来,牛们觉得自在。如果之间有灵犀沟通的,彼此在各自的山坡上“哞哞”的叫几声,算是打个招呼,实在是想聚拢一下,干点事情,也是耳鬓厮磨一番,再在牛背上架一架后,又各自散了。如果有些事情没有干成,大概要待几个时辰,直到把事情做彻底。也有牛聚起来闹事儿的,“长头发”有两条牯牛,“长头发”叫它们大牯子和二牯子,它们好像前世冤家一样,一聚头,四只弯弯的大角就绞到一起了,不是你进就是我退,一直从一个山坡斗争到另一个山坡,有一次斗了半天,都斗红了眼,还是不分伯仲,“长头发”只好将一把长长的竹扫帚点燃,伸进弯弯纠缠的四角间,两个冤家才骤然分开。
“长头发”的牛群,陆陆续续有了下落。有几条躲在倒岩屋下,能挡风雨,还惊魂未定。大多都进了山洞。“长头发”在山洞一出现,牛们都“哞哞”的叫了一阵,都从洞里出来了。
大牯子和二牯子滚到山崖下,摔死了。“长头发”哭丧着脸。
“我就指望这两条牯子啊!以一当十啊!”
没错,这两条牯子作用大着呢,“长头发”十多条牝牛全靠它们繁殖。我们给“长头发”也报了损失。村委会当即将四千元产业发展经费先补贴给他,上报的损失批下来,再补给他。
秋雨颂
终于下了!下了!!下了!!!
该死的东西!怎么才下啊!
雨是一根一根密密麻麻的针,发出冷光,扎破云层,从空中飞跳,又扎在农家的屋上,也扎在庄稼和土地上,发出的都是钢针般的声音。雨,深深地扎进土壤里就好了。
秋雨,是来得太迟了些,但我还是叫它:甘露。
全村60多口堰都干了。村民们不知渴望了多长时间。天天望着天。习惯仰头走路了。几个月时间,雨都跑哪儿去了呢?也有村民骂天,有种你就一直别下。人们对雨又爱又恨。
柑橘和庄稼可以揪个秋尾巴。以为今年的收成大势已去,看来还有转机。
下雨前,柑橘卷索了,蔬菜瓜果也都趴地上了,都感到无望。但村民们一直抗旱,拖着长长的黑黑的管子,从堰塘里把水引出来,像无数的长蛇在喝水。也有的从河里往山上抽。人还是不能胜天的。大自然无法战胜。天灾不可预料。
我从村委会出来,往租住的房舍赶。
天黑了,黑锅一样盖下来。突然,扯了一个闪电,几声闷雷滚过。怎么还打秋雷?正准备向天问一个问题,一阵大雨扫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射在我身上。脚湿了,裤湿了,什么都湿了。
回到宿舍,蹦一蹦,抖一抖,落了一地秋雨。
我不骂雨。
篾匠也跑到我们宿舍来,躲一会儿雨。身上全湿了。他说他刚从土地庙那里来,是他把雨求来的。求了个把月的龙王爷,没求来雨,今儿到土地庙,求土地公公,求了十遍,这雨就来了,真灵啊!篾匠说的土地庙,我知道,几乎天天要从土地庙前走过。如果把它说成是一个“庙”,那就是把堰塘夸成了海洋,把芝麻说成了西瓜。矮矮的,窄窄的,建得粗糙,容得下三四只鸡。里面也并没供神像,只立了块小石碑,碑上刻有两行字,一边一行:保一方水土,佑四面平安。一块红布披挂在碑上。碑前放些吃的。大概土地公公也要吃吃喝喝吧!土地公公,也叫土地神,是最小的神。这个庙也有些年头了。是怎样建起来的呢?某年,几个人在这个沟边,开山炸石,改田,一个人被夹入石头之间,挤压死了。后来,这几个人就在这里垒了个土地庙。实际上,谁也没把这当个庙看。偶尔有人来燃香焚纸,求子求福求平安的。也有求了无数次,始终没有显灵的。有人说,篾匠哀求过土地公公,叩了好多头,也是一样不显灵,心里一时来了火,还在土地庙上洒过一泡尿呢!
篾匠说,雨是他求来的,我暗自好笑。我对篾匠说:这雨是怎么求的?我想听听。篾匠便小声地对我说,你听到就行了,不可让龙王爷和土地公公听到了,不然,这一求,就又成了淫雨天了。
公公,公公,
干得可怜啊!
干死了青苗,干死了草木,干死了百姓啊!
请求土地公公,及时打发龙王,打发雨王,把陈年老雨都送下来吧!
送雨20天。
大年三十,我接公公吃猪脑壳肉!
篾匠说,要求上十遍,哈哈哈,我求了第九遍就来雨了。
看着篾匠念念有词,我想起了村支书对篾匠说的话。
村支书曾对篾匠说:你把雨求下来了,村里把你养起来,当个金宝卵。
篾匠对我说:我要找村支书去,他说只要把雨求下来,村里把我养起来的。
我说:这话你也听进去了?激将你,随口说的,我这时和你赌一下,你把太阳求出来,村里把你养起来!
篾匠说:现在时刻不对,不是求太阳时间。
我听听,我对篾匠说。
皇天,皇天。
淋得可怜,淋死了青苗,淋死了百姓。
请求开恩,退下云罩雨雾,显现日月之光。
大年三十,我接你吃猪脑壳肉!
篾匠求完,说:天晴了,我会去找村支书。
秋雨总算下了,真是好雨啊!篾匠心里舒服了,这不是给挖苦他的人,还了一个嘴巴吗?甚至骄傲起来,说自己是半个仙了,天旱能求来雨,涝天能喊来太阳。
我送篾匠回家。篾匠72岁, 腰也弯成了72度。稀稀拉拉的头发,全白了,而眉毛却像黑漆一样,像两把刷子。我在篾匠家里又聊起天来。讲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他与儿子住在一起。想与他分开。儿子偷了他的腊肉,送别的女人了,老子心里气,只图自己快活。父子见面都是横眉竖眼的。
篾匠也想找个女人。让女人做饭。自己做篾活。篾匠打听郑家湾有个寡妇,又有房子,房有屋后还有大片的竹子,他愿意到女人家住。请介绍人跑去说了,篾匠住了两天,女人骗了他5000块钱,介绍人也骗了1500块钱。
有一天,外村来了个妇女,买了2个篾背篓,过了几天,又来买了几个。篾匠明白了妇女的意思。又动了心,要请人去挑明。村支书知道了,跑到篾匠家,要篾匠断了这个心思,来骗你钱的,这大年纪了,真的是来找你谈恋爱的吗?篾匠说,是对他真有意思。村支书说:去请人说媒也行,把你的存款折放到村委会里来,村委会帮你保管。存折上几万块钱总是有的吧,我不怕你贫困,就怕你被骗。
我对篾匠说,钱再被人骗走了,村里真的要养你了。
篾匠,篾活儿做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啊,靠这门手艺养活了自己,也拉扯大了两个儿子。女人被他打跑了。没有女人了,一直后悔。

作者简介
周凌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在全国数十家纯文学刊物发表散文作品,著有《鹰走峡江》《诗魂余韵》《诗意村庄》《屈原的村庄》《驻村记》等散文集。散文集曾获宜昌市“三峡文艺明星奖”和“屈原文艺创作奖”,散文作品曾获中国报纸副刊散文年赛二等奖,《为屈原守灵》获首届“汨罗江文学奖”白话散文离骚奖(一等奖)。
《三峡文学》2021年第9期目录
头条
于船长的最后一次出海/厉佳茜
访谈
努力钻到人的内心之中 ——刘德东访谈 /刘德东 孙红云 王 迟
小说
散步去桃花源广场/倪月友
平安无事/郭晓畅
散文
村中遇雨/周凌云
老房子/王倩茜
铁树花开/张 蕾
诗歌
诗歌人类学简史(组诗)/臧棣
土豆长在土里/赵俊鹏
小布丁的诗/小布丁
明月凹凸不平(组诗)/阮雨航
评论
电影《摔跤吧!爸爸》的会话含义探析/王 荣
“介入”与“活力”——重析“中生代”诗歌的价值走向/夏慧玲
译窗
论罗伯特·潘·沃伦的诗创作/哈罗德·布鲁姆
柳向阳 译
悦读
深爱那抹红/谢凤琴
书屋
学习雷锋好榜样/戴志梅
本刊声明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三峡文学》杂志。
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宜昌市云集路21号老市委大院,联系0717-6243541。
3.本刊唯一投稿邮箱为sxwx@vip.sina.com
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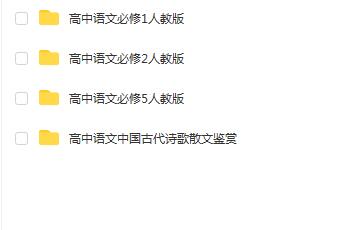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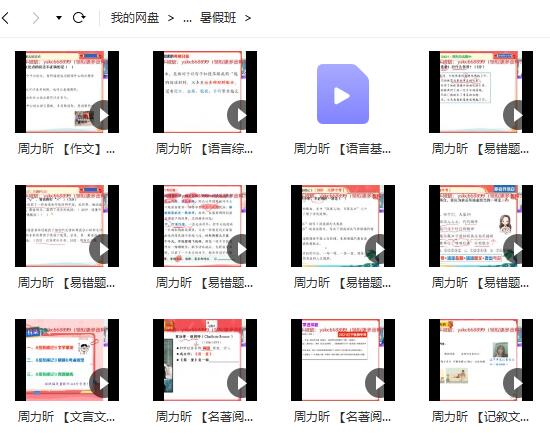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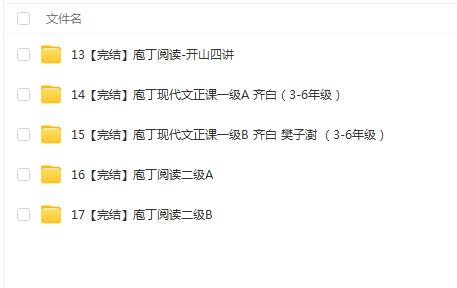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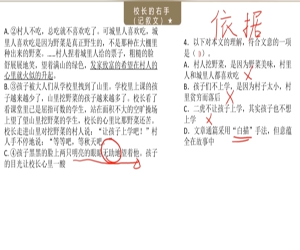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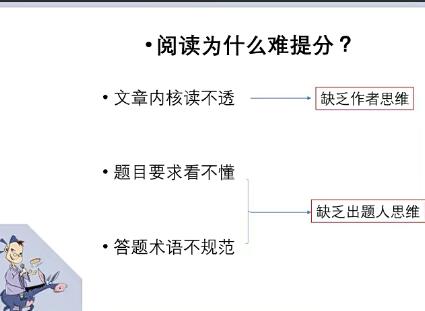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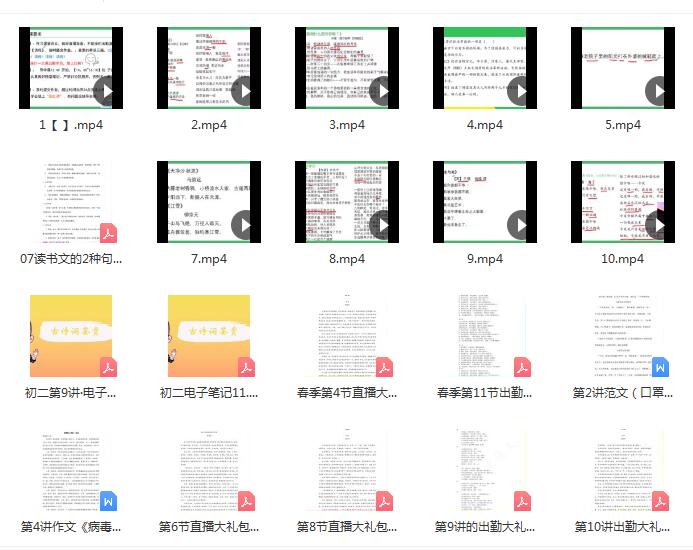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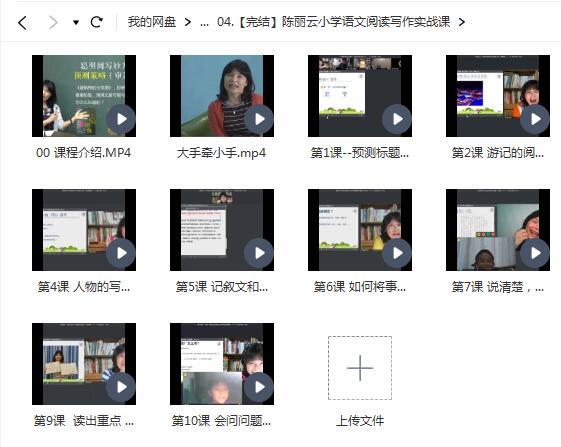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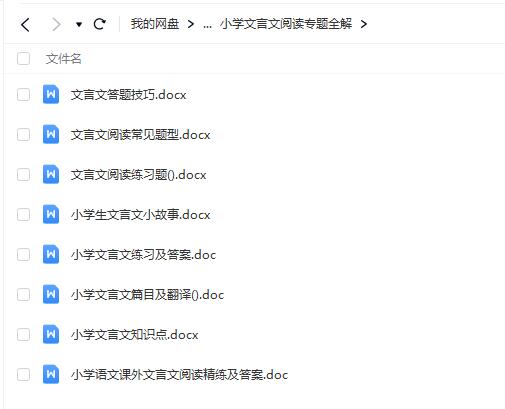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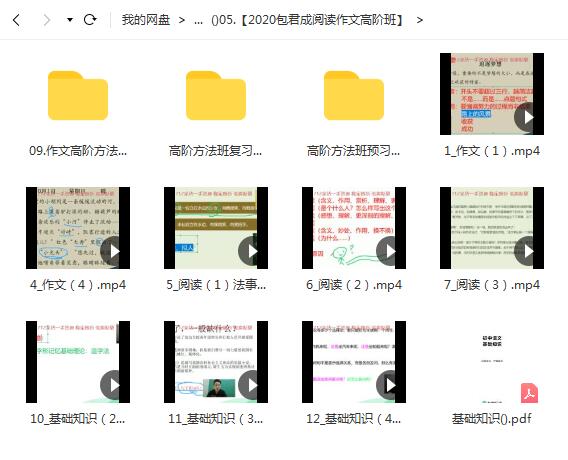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