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推荐|邹冰散文三题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12 17:26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三秦散文家散文新势力
【三秦散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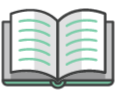
三秦散文家
《散文视野》杂志
选稿基地

本期专栏
佳作推荐
邹冰散文三题
· 目录·
· 自乐班里看秦腔
· 一叶知秋
· 那一夜的歌

邹冰,男,60年代生人,陕西乾县人,有过20年从军经历,甘肃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兰州军区话剧团编剧,2001年转业陕西省政府工作,退休之余,重拾写文章的爱好,有幸加入中国散文协会成为会员,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青年作家》《人民日报》《散文》《散文选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2020年《一个人的秦腔》荣获《中华散文》一等奖,出版散文集《特色》《雁塔物语》等。现居西安曲江新区。













(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流量为妃,我为王
三秦散文家,散文名家的家、散文作家的家。
流量时代,散文家不乏真诚,但更需虔诚:从心出发,虔诚的写我。流量为妃,我为王。
在王和妃的帝国里:
做人,上善若水,天人合一;
写文,上散若水,天我合一。
这里,是散文的家园,心灵的帝国。来,握屏筑巢,抵御浮躁,澄澈灵魂。期待心灵的核辐射,辐射三秦,辐射中国
——燕窝

投稿指南(点击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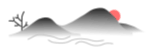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观览)
▲董信义:谁在民俗窑洞前伫立
▲吴利强:要识吴山非易事
▲韩惠民:其拒也坚,其罢也难——白居易之于“牛李党争”
▲王洁:不灭的信仰——观《重庆1949》有感
▲邹冰:沧海一粟——对关中平原小米的零散记忆
▲王志社:我与“三秦散文家”的故事
▲王铁军:散文三题
▲裴育民、阎纲、弋舟等|一碗羊肉泡馍引发的热议
▲吴兰兰:乡愁记忆
▲董信义:馥芳斋鼻烟壶——《袁家村笔记》选篇
▲王洁:八月来信
▲杜芳川:渭河,咸阳人的母亲河
▲解超:家庭焉能不讲理
▲韩惠民:且听乐天古楼吟
▲李永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诠释 ——《留住乡愁》读后
▲吕湘艳:亲情散文二题
▲李永恩:《丰碑——襄渝铁路建设纪实》 给我的三点思考
▲李进:台风烟花与德尔塔
▲史飞翔:我的家国情怀
▲杜芳川:遇见阎老
▲王志社:我打工的这三年
▲董信义:丢失的顶天寺
▲柳谋:说说我的耳朵那点事
▲秦健:又是五月麦子黄
▲姚明今: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读陈益鹏评论文集有感
▲袁国燕:每一根羽毛,都带着深情
▲王晓群:石头(三篇)
▲王洁:一梦敦煌
▲2021年二季度刊文总览
▲2021年一季度刊文总览
▲2020年平台刊文总览

2021年
9月12日

长按上面ErWeiMa我们
投稿邮箱:309733944@qq.com
主编:yanwoxian123
编辑:cyp196310
[三秦散文家]微刊团队
主管:陕西省散文学会
顾问:陈长吟、周养俊、仵埂
主编:袁国燕(燕窝)
执行主编:陈益鹏(翼鹏)
副主编:马 婷、白玉稳
郭志梅、赵攀强、杨志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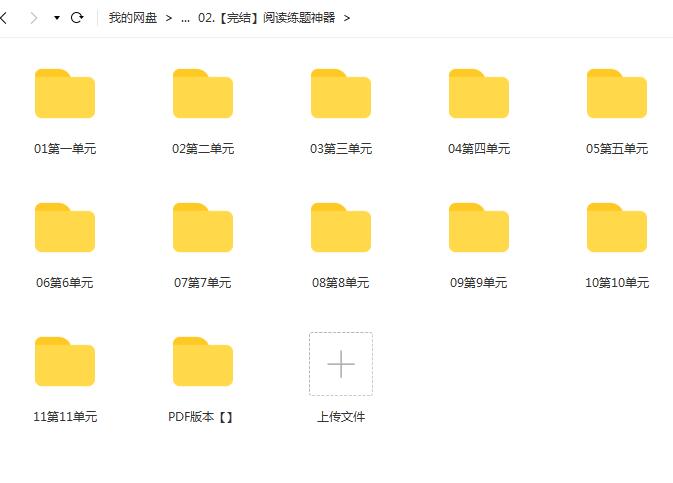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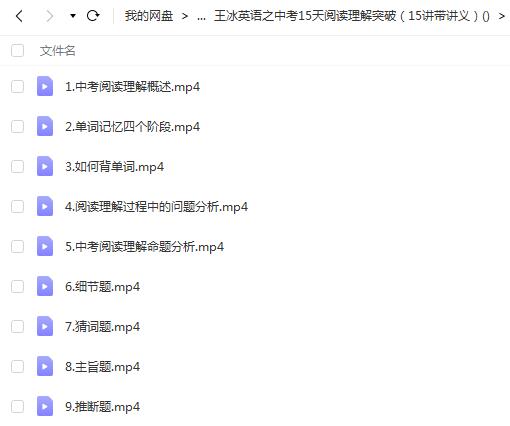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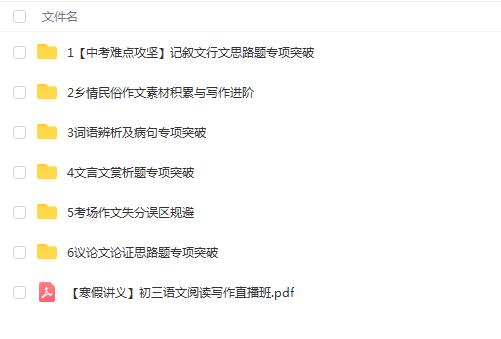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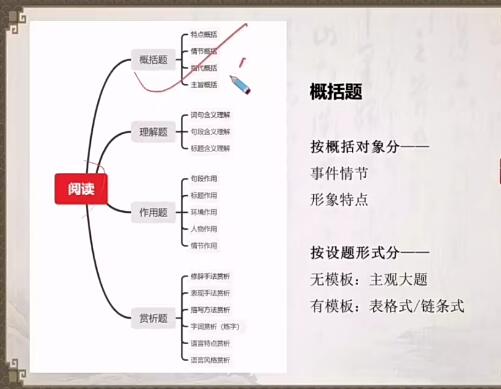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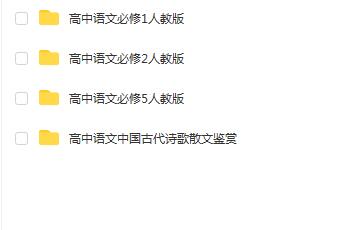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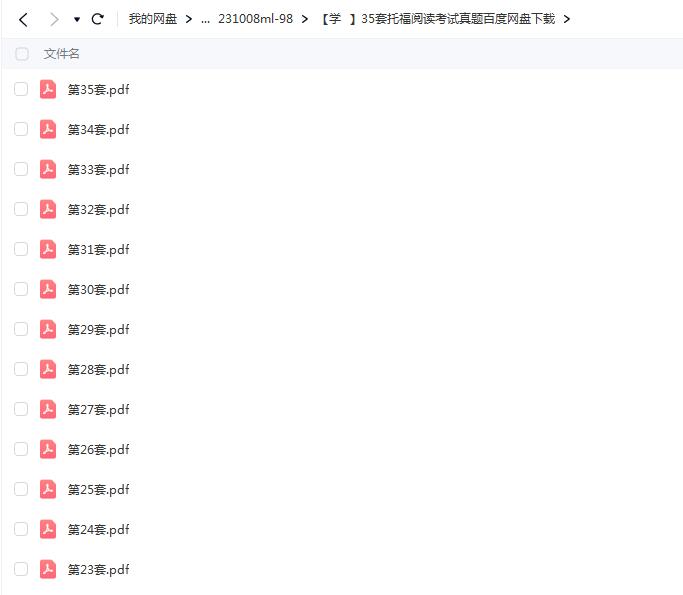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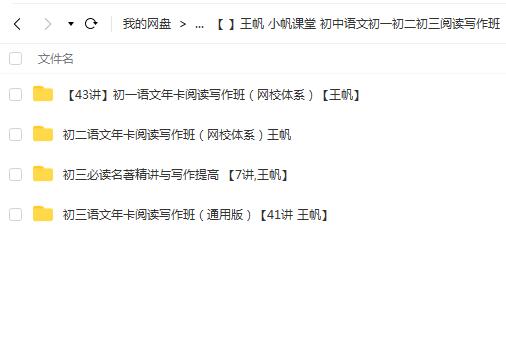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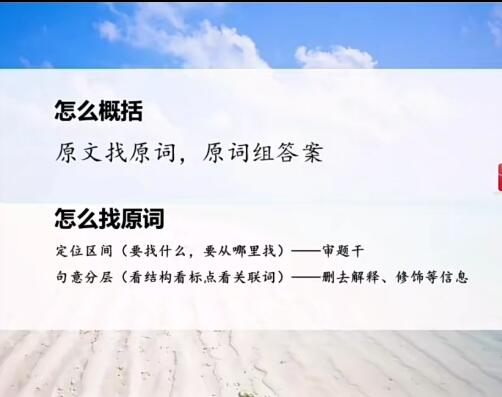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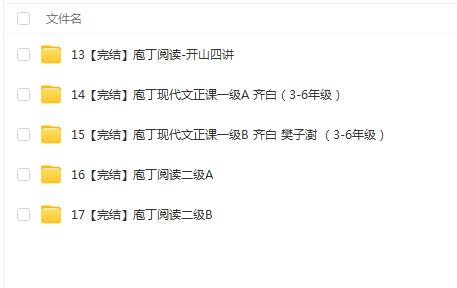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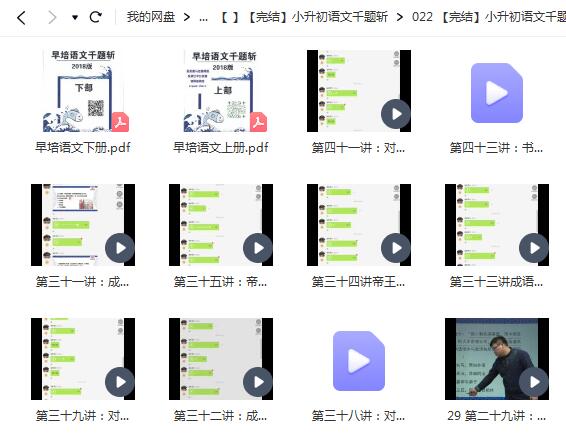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