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散文之8 永远的五月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12 17:21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我很荣幸,这辈子,能够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继母。生母给了我生命,继母养育了我。但生母过早地离去,却又是我最大的不幸,她没能看到我们的成长成家儿孙满堂,没能享受过我们一天的报恩。
听人转述,母亲是重庆秀山人,患小儿小二麻疲症,走起路来一左一右地微微摇摆,看似既要向左倒又要向右倒的样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家人逃荒到贵州做泥瓦匠糊口,经人介绍嫁给我父亲的。我小时候特淘,老粘母亲,她与全村人砍瓦柴钻刺竹林,我也跟着,浑身滚得泥巴捎带偶尔还带点刺伤的;她下河洗衣服,我也跟着,不论冬夏,满脸湿得红嘟嘟的。只是母亲自打生育了我之后,就再没有上过街赶过场。我们家住在大山沟里,无论赶哪个乡场,最少都有三十多华里,赶个场得两头黑,出门点着干葵花杆,半路放山洞里一截,回来天晚时又点着照亮回家。久未上街,母亲也想去看看城镇的变化,也想看看花花绿绿的衣裳,尽管没钱买。她每每准备去,我都哭着闹着撵去两三里路,哭声响彻满沟满山谷,母亲只好打道回府,在我屁股上拧一把,长长叹息一回。
有一首童谣这样唱的,“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啊……”生母去世时,我也才三岁。家人都外出干活了,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亲眼目睹母亲的去世,她的双眼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的留念,流露出对我们六姊妹的不舍,也有对我们未来的担忧。这是这个世界让我留下的最初最深的记忆。越是年长,这印象就越深刻。多年过去了,母亲那眼神,老在我眼前晃。家里人闻讯赶回来时,弟弟还爬到母亲边喝奶。
母亲去世时,大哥十四岁,大姐十二岁,双双回家挣工分养家活口,夏初,大姐第一次下田插秧,蚂蟥钉在腿上,大姐满田打滚哭,大哥含泪咬牙再不准大姐下田。十岁的二姐到六七里外的村里上学,负责一家人的早晚餐,还得背着我或者弟弟去学校,经常迟到,老师就骂她家里是不是用碓窝煮饭。二姐经不住骂,就赌气再不上学。父亲觉得力不从心,经常疲惫不堪。
到我确实能独自上学时,父亲试探着问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说给我们再找个母亲可以不。哥哥姐姐乃至弟弟都一致反对,生怕娶了后娘成后爷。也许是对母爱的渴望吧,唯独我举双手赞成。数天后,伯父带了个女人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新母亲,她原来那边的家里也有七个儿女。大哥大姐二哥与弟弟都不愿意叫妈妈,叫满娘,我与二姐叫妈妈。我们家对继母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叫法。直到继母去世即将关紧棺材与遗体作最后的告别前,按风俗得连叫三声妈,大哥大姐二哥才齐齐改口。这个继母与我们这个家有了二十多年的亲缘。
继母比父亲还略长几岁,但勤劳,从早到晚没见她好生休息过。从春忙到秋,从冬累到夏。金银花开了,五背子结果了,黄姜出世了,继母都去挖去采,五天一场换盐巴煤油洗衣粉钱。继母的勤巴苦挣打消了我们几兄妹对继母与父亲的顾虑。即使后来因此天灾饥荒她悄悄地给她先前那边的儿子们背过几次粮食,我们也都假装没有看见。
五黄六月的太阳真毒,稻田里的水,一河一河地扯。也晒得人睁不开眼。父亲怕田干,一天到晚就撑着个锄把,用双脚到田坎上滑。麦子熟了,继母割麦子。一刀一刀下去,一把一把麦子放倒在地上,实在累了,就跪在干裂的黄土地上,汗渍在她早已泛灰的白衬衣,在背上形成一圈一圈的汗纹,湿的,干的,层次分明。
家里人口多,饿饭的年月虽然没有经历太多,也还是有的。遇到大天干年成,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肚子一天都呱呱的叫。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吃饭时,我总是三下五除二把自己碗里的责任地率先干完,只要有一个角落没有抵饱,我就甩开嗓子嚎,父亲和继母就把他们碗里的饭倒给我,然后他们就到山林里撸一把青嫩青嫩的李子充饥。山里人勤快,总饿不死人的。
家里穷,没钱每年给家人买衣服鞋子,基本上是大的穿不得了,第二的穿,第二的穿不得了,小的接着穿,买一件衣服,看着是给老大买,其实连最小的那个眼里都盯着的。往往是还轮不到最小的来,就是补丁加补丁了,衣服原来的颜色基本上是找不着了。一双水胶鞋够我们穿好几年。时间久了,胶鞋磨得穿不成了,别的同龄人都打赤脚,可我打赤脚硬走不了路。就天天穿着继母给我做的布鞋上学,不会忘记那个夏季雨水多的五月,每天来回近三十里的上学路,我穿烂了继母给我做的四双新布鞋。
平生第一次到县城赶场,是随继母去的。我从在初中上学的二哥包里拿了他仅剩的四分钱,就跟着大人们上街了。到县城后,继母取二角钱把我交给路边一个剃头的师傅,剪了我长得像人熊的头发。趁理发的间隙,她去置办东西,免得耽搁时间,而返家时在路上黑的路更远。理好发见继母还没有到来,我就东望西望地迷失了方向。继母回到我理发的地方没见着我,她四处找,我也四处找继母,她害怕我丢失她回不了这个家,我也害怕走失离开我亲爱的父母兄弟,离开这个温馨的家。中午城里的太阳比我们山里的太阳诡异狠毒,瞪得我浑身鼓油,我狠狠心用那四分钱买了一根快融化了的冰棍。
终于,一根冰棍还没有舔完,我看到了一脸焦急的继母,奔过去,继母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巴掌,一气的责备,这一巴掌打得我心里甜滋滋,鼻头酸溜溜的,有家的温暖。继母带着我到街边一家卖粉的地方,买了一碗两角钱的肠旺粉,可把我吃得屁滚腰圆。继母坐在旁边,眼盯着我碗里的粉和猪血下去得快不快,我听得到她在不住地咽饿口水。返程的路上,继母还买了几个西瓜带着,没有带到三十多里外的家,就被我又啃得个一干二净。
这一天,我一共用了七角二分钱。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的,我记得的是继母对我的无私的爱。
揣着继母的爱,十多年后,我考上铜仁民族师范学校,我也是村子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吃国家粮的人。继母送我到学校,累了的继母坐在学校玉兰花树下的长条坐椅上,和我一样好奇地看校园的美丽。数天后的一个晚自修,学校放自制的录像,我看到了继母的身影,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继母:缀满补丁的黑青布排排衣,褶皱如川的木讷老脸,略显伛偻的身材,眼神里对我能够考起这所学校的骄傲……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
我把在电视上看到继母的事写信告诉了继母,直到我假期放学回家,邮差才把信送到,继母不识字,我和她说了这件事,继母更加高兴,笑眯眯地说在我毕业她来接我时要看看电视上的她自己。
然而她最终没能等来这一天,就在第二年的春天里,父亲上山犁田,继母冒雨上山给父亲送饭,担心家里漏雨返回时,被大雨淋成重病,不久就瘫痪在床,县内哪家医院都看过了,也没有治好。接到消息后,我赶回家里,看到继母的病情,我的内心充满了内疚与痛苦。继母,您是为这个家病倒的啊!继母说,你还没有毕业,以后的路就得自己去走了,你是寨上唯一走出山里的人,今后对寨上人和家里的人,能够帮就尽量帮上一点。我边点头,边给继母说电视上广告打得满天飞的那种药也许有效,我询问一下买些回来给她吃。听我这样说,继母很欣慰。我走出家有半里路了,继母还央村里一表叔把我叫回去,叮嘱我一定把那药给买回来,她还想在我毕业时来学校接我回家呢。她的眼里泻满了渴望和幸福。
我一下子跪在继母的床前,眼泪汪汪地说,我们一定要把她的病治好。
继母还是没有等到药寄到,就带着遗憾撒手人寰,丢下伤心欲绝的这一大家子。我们一家人对继母十分依恋,给她举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继母虽然逝去了,但她的身影留在了满山满沟里,每当我一回到家乡,仿佛她就在哪块地里,割着麦子,趁伸腰骨直起身的一刹那间,不经意间看到我们,遥望着我们归来。
(特别说明: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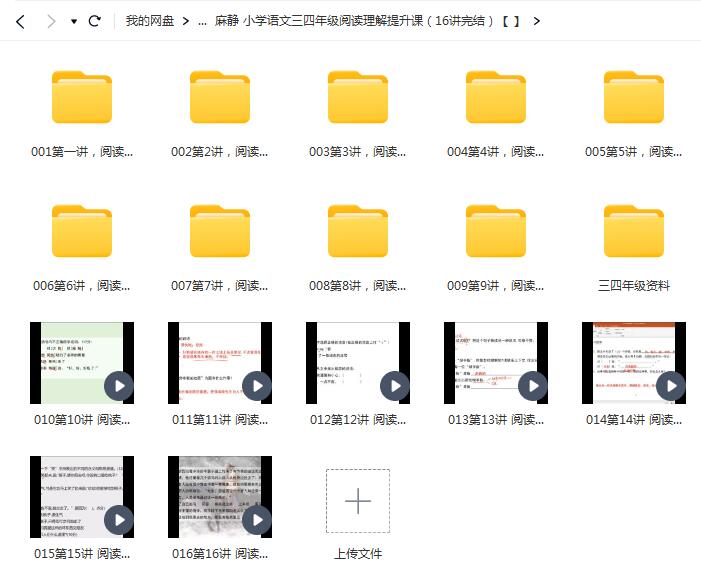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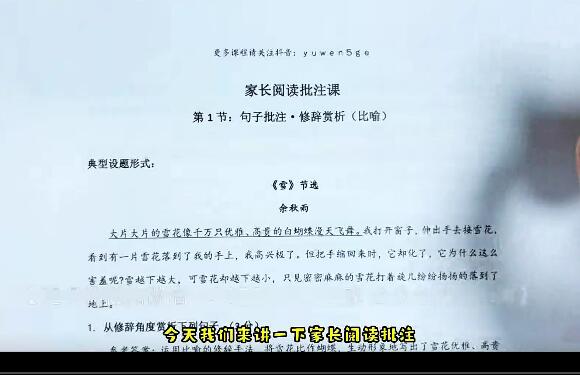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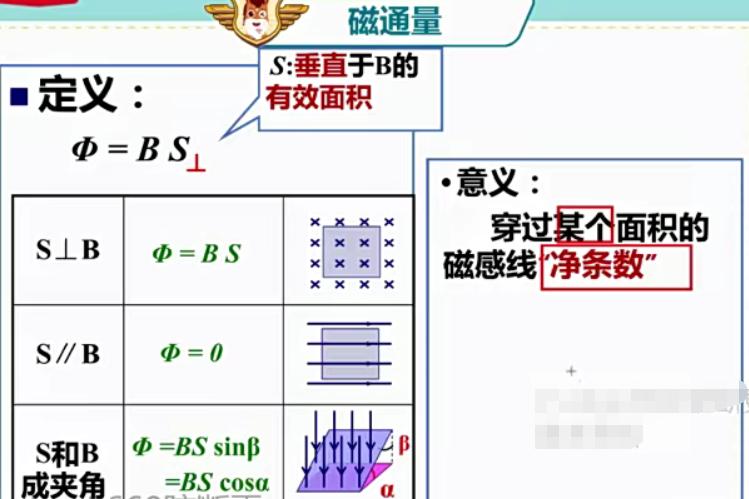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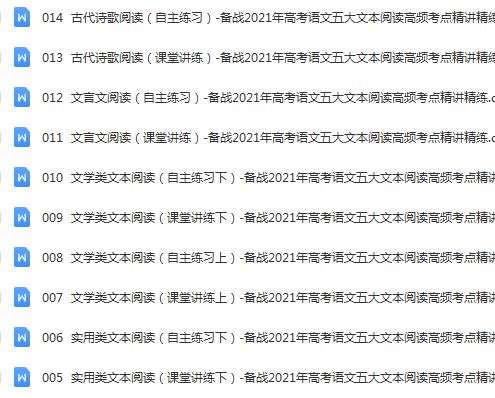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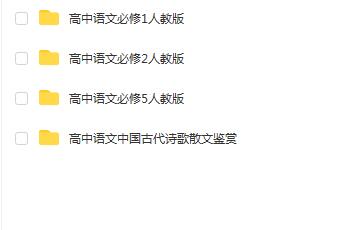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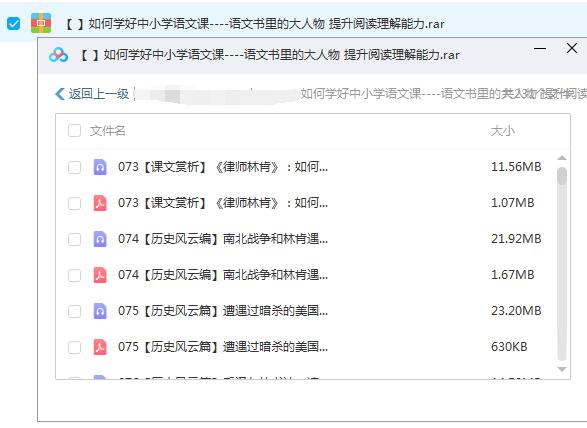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