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河文学 散文 | 檀厚云:无法抹去的记忆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12 20:13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无法抹去的记忆
◎檀厚云
我正在门口盘泥巴,鼻口挂着两条小蚯蚓,随着鼻子的抽动一升一缩。只见祖母用满是血污的手一边揩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嘟嘟囔囔从堂屋出来说:“又是个丫头片子……”我把两泥手往屁股后面一拍,欢快地跑进房间:“妈,中午吃啥饭呀!”母亲没理我,把脸别向床里,嘤嘤地抽泣着。我看见床上多了一个小肉团,粉嘟嘟的,手脚不停地挥舞着。不知什么时候,我家那条小黑狗竟然闯进来了,在房屋里四处嗅着,好似在找寻什么。
有祖母记忆的画面最早只能追溯到此,更早的记忆都是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拼接组装出来的。外曾祖父是当地一个落魄的穷秀才,有两闺女。祖母是家里的二小姐,没念过书,做得一手好茶饭,性格不急不躁。言语少,外曾祖父就把她许给了能言善辩的祖父。外曾祖父曾经收养过一个儿子,本指望他养老送终,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了两年书,孩子有思想了,竟然飞了,跑新疆参军去了。前两年还有断断续续的家书报平安,后来又过了两年,杳无音讯了。外曾祖父摇着头说:“最终是没血缘,看不家(养不住)。”最后就不了了之。
祖母一口气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两女。在那个“多生儿势力壮”的年代,祖母确实在庄上风光了好几年。接下来的日子可是愁断肠。人多力量大,人多饭量大。尽管家里紧衣缩食,一家十口人有十张嘴,偶尔还要接济自己的娘家爹妈,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家底日空。
家里还有个太太(祖父的母亲),祖母总是嫌弃老人家不够干净,沥的米饭里牙齿能被沙子硌掉(我家乡是河地,洗米是件麻烦事)。她还嫌弃老人家浆的衣服不平整,浆洗衣服如同给衣服冲个澡……后来索性一摊子杂事全揽到自己身上。慢工出细活,祖母做事不急不火,灶台边围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幼儿,祖母依然慢慢地摊着饼子,她非要煎至两面金黄才起锅,一起锅,孩子们一哄而上,哭声、闹声、抢夺声……不绝于耳。祖母依然不急不火,继续摊着煎饼,任凭孩子哭闹,稳如磐石。

“反穿羊皮袄”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听母亲提到这个词时,我大吃一惊,记忆中不总说家里穷吗?“羊皮”可是上档次的货色。母亲一一道来,孩子多,生活艰难,袄子的面子破了,白白的棉絮裸露在外面,看着似一件羊皮袄。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自嘲。
祖母一辈子没引过孙,我小的时候太太还硬朗,颠着小脚上工挣工分。祖母除了挣工分,其余的时间基本围绕锅碗瓢盆转悠。母亲要强,从不有求于祖母,我大多时间都呆在外婆家,田间地头跑着。等太太老了,基本也实行联产制了。太太大多在家“享受”重孙绕膝的生活,前两年,太太还能一手环着一个重孙,一手牵着一个重孙,衣角上还扯着一个重孙女。由于老人家年轻下力过猛,到老说衰就衰了,又过了两年,白胖重孙也抱不动了。每天院子里,放着一把椅子,一个摇窝。太太坐在椅子上,等着孙子孙媳接孩子送孩子,她的左腿上坐着一个重孙,右腿上坐着个重孙。摇窝里躺着个重孙女,太太手脚并用,一天到晚也不闲着。
祖父是“油壶少了把,只剩个嘴儿”,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就会指手画脚。祖母体恤自己的父母,总是三天两头偷偷往娘家送点东西,若被祖父撞见,祖父总是肿着脸,肿得像个大盆子,祖母因此大气不敢出,在家里自然比祖父低一等,没有一点话语权。祖父年轻的时候不出力倒省力,身子骨养得还算硬实,儿子成家分家后,祖父的日子过得更加清闲,没事时背着双手,哪儿人多往哪儿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长里短……家事国事天下事,他好似无所不晓,讲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横飞,讲得时常忘记了吃饭。祖母有时就端着个大饭碗直接送到人群堆里,惹来众人艳羡的目光,更多的是打趣的声音,老跛(年轻时熬麦芽糖,锅翻了烫伤了他的脚)这辈子值了,儿子一堆,老婆子贤惠……

后来祖父那些陈谷子乱芝麻的事已被人们听腻了,祖父一开口,人们都散了。祖父就背着手跺着方步落寞地回到家,坐在门口发呆。
后来祖父竟关心起粮食和饮牛,他会到二爹三爹的田间地头去看看庄稼的长势,不过路过我家地头他却折回腰,连头都不回。祖父牵着四爹的牛去放牛,遇到邻村的老头,祖父的话匣子想关上都难,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因为此事一家老小不知道找过多少次牛。母亲就在背后抱怨,人家是儿子,我们家就是野儿子,牛绳都不帮牵一下。
祖父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是个“坏人”一一偏心眼,祖母就是“帮凶”,她时常被祖父当枪使,在某种意义上她比祖父更坏,祖父是决策者,她就是执行者。有一次饿的不行,母亲还没收工。我端着碗偷偷溜进祖母的灶户,整个灶间弥漫着麦香味,刚把一只手伸向锅里,一巴掌狠狠地掴上来,我吓得一啰嗦,“咣当”一声我的瓷碗掉在地上裂成两半。听到响声,祖母冲进来骂:“真是饿死鬼哟。”她声音尖利。祖父的两眼更像两把锋利的剑。我吓得缩在屋角,使劲吞咽着口水,祖母喋喋不休,声音萦绕在耳边:“早分家,还往我屋里跑”“干活的人没吃,赔钱货倒抢先了……”她把手放在那张深蓝的围裙上揩了揩,从锅中拿起一个馍馍揪了一坨塞在我的手里。把我推出了灶户。
祖父祖母不待见我们姐妹俩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二爹三爹不在家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祖母的灶间吃吃喝喝,我和妹妹只能眼巴巴地盯着。
那一年,祖母生病了,开始只说头痛,头痛得要裂开了。每天就去乡诊所打打消炎针,回家照常打理一摊子杂事。我们家倾其所有在村东头又盖了新房子,离老屋远了,妹妹也大了,我也变得有骨气,能不往西头跑就不往西头跑。太太偶尔碰到我,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鸡蛋说:“回去叫你妈煮着,还是生的,别捏破了。”“不想太太吗?怎么不过来玩?”

六月的一天,听人说祖母在床上痛得打滚,还听说祖母的鼻子凹陷下去,和村边的“豁鼻子”有几分相似。父亲兄弟几个把她送到县医院,医生摇摇头说还是往大医院送吧,他们无能为力。
那个夜晚,夜死一样的寂静,祖母的呻吟声高一声低一声。沉默,许久的沉默……祖父开口了:“咱就不治了,也不折腾了,吃好喝好吧。”大伙散去后,母亲牵着我的手说:“去看看你奶奶吧。”我往母亲身后躲了躲。“去吧,去看看吧。”我进入房屋,幽暗的空间里泛着微微黄光。我怯怯地走到祖母床边,我看到她凹陷的鼻梁骨上那浑浊空洞的眼神,她伸出枯枝般的手,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她艰难地收回手,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等退岀房间,我才明白祖母那句话:“到底还是怕我。”
听说苍耳子对鼻痈有益处,周末我挎着竹篮子,跑遍漫山遍野摘了满满一篮子,野刺划破了我的裤子,刺伤了我的手。可是这一篮苍耳子最终也没挽回祖母的性命。祖母在六月末的一天走了,母亲说祖母走的时候瘦的如一把枯柴,半边脸已经塌陷。我正参加小学毕业考试,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由于天气炎热,在家停灵一天便出殡了。那天天气出奇的热,几个不谙世事的堂弟堂妹在灵前欢快地跑着、追逐着、打闹着……看着这个曾经玩闹的小院落,想着那个厉声吼叫的老妇人再也不会出现了,我的眼泪就顺着眼角滑下来了……



檀厚云,湖北枣阳人,现就职于湖北孝昌二中,偶有小作见诸报端。


“灌河文学”


阅读《云梯关》电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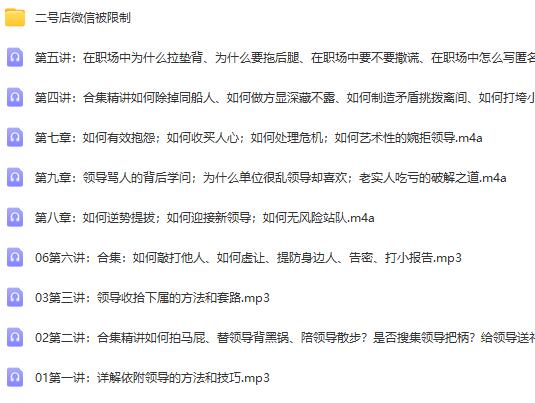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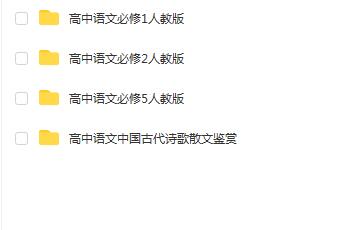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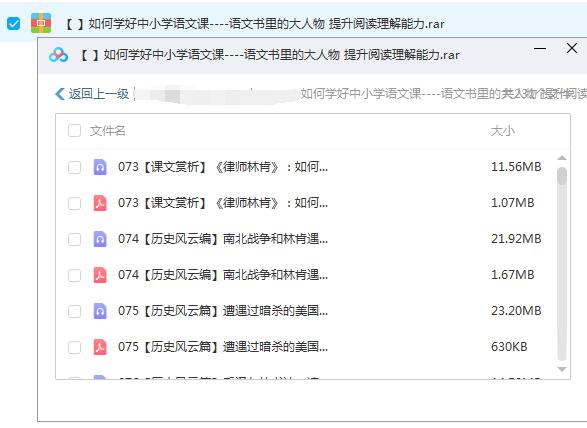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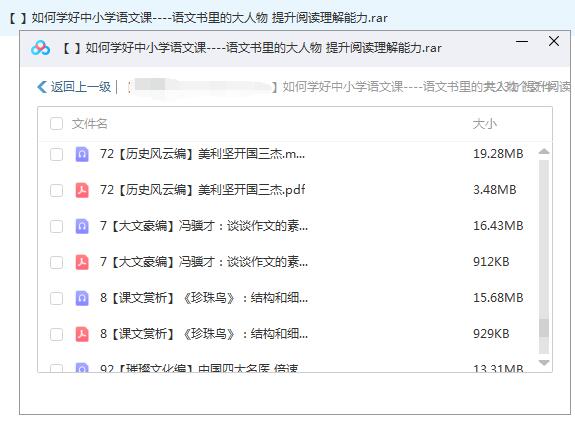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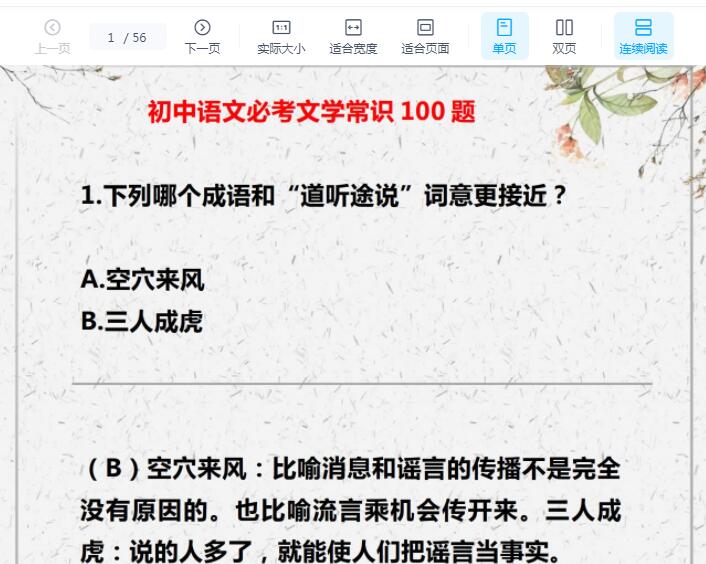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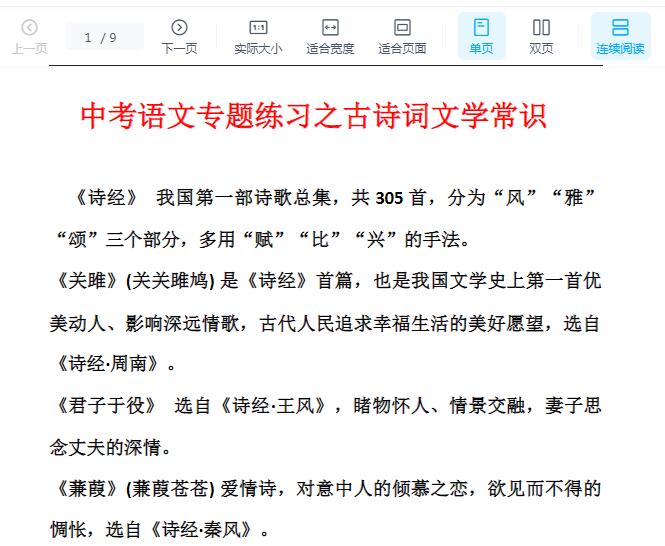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