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金乡有个大程楼
发布于 2021-11-12 09:42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金乡有个大程楼
程相崧
从金乡县城西行30里,经一个叫马庙的镇子南折,直走进这片大平原的深处,便到了一个人烟阜盛的村寨。这村子的名字叫大程楼。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他们的祖先迁徙到此,便盖了一座二层的小楼。他们在精神与血脉上,都认宋朝二程中的程颐为祖先。所以,村上人有几分像他祖先一样,讲理,也重教;在以前出了很多念书人。
村子由东向西,一共六个生产队。村南地势低洼,有一个一个断续相连的湖泊,较出名的便是官坑。村东北在解放前还有一个长方形的海子,据说那里很紧,时有水鬼出没。但是,在填平前还是有大胆的孩子到里面玩耍。因为不缺水,村中男人多识水性。夏天里,常见赤条条的半大孩子,洗完澡,光着身子从坑边往家里走。在街上碰见年轻的姑娘、媳妇,彼此脸上都难免羞惭惭的。
村中央有祠堂,是一座青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建筑。里面中堂上挂着程颢、程颐二位夫子爷的画像。并有一联曰:“一宗英豪名千古,万代子孙继二程。”村东有龙母庙,庙南不远有一座不大的土丘,人们便说那是龙母的坟冢。村东原有一大片天爷爷庙建筑群。日寇来时,扒了盖炮楼;日寇走了,炮楼的砖便又被人扒去,砌锅台垒墙头。那里从此变成一片荒芜的土坑,草木间的泥地里,偶有残砖烂瓦,给人无限的想象。
村南有一片林地,俗称老林。有巨大的石碑巍然而立,还有侧翻在地的石人石马。村东和村西又各有一座宗林,是后来新开辟的供村中人逝去后安息的地方。村东的宗林中,有一座坟,平缓巨大,如自然生成的土丘。上有一无字碑,刻字处朽烂,来历不可考。
村中在解放前有一富户,也即地主。据说他家拥有占村中绝对数量的土地。青砖青瓦的房舍院落一栋连着一栋,沿着一条细长的南北街排开。精致的门楼,门口有小小的石头狮子和浮雕精美的门枕石。这家人单是有钱,并没有出什么显赫的人物。
村中有一位农救会会长,大儿子参加了国民党,是一位文官。二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做到师长,解放后当过县里的工会主席。老三是八路军的正规军,当过骑兵连连长。由于这一家人的存在,在国共拉锯时期,村里两方面都没怎么死人。村中阶级斗争不是很尖锐,地主袒护农民,农民袒护地主的情况都有。但在最后,地主的财产还是被分了。很多年里,总有人在地主家那些屋墙的青砖上,用铁锤敲来敲去,想要发现里面藏着的金银财宝。
村人的营生除了务农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家银匠铺子,有几家染坊,有一个做煎包和肉盒儿特别出名的人。那位做煎包、肉盒的人排行第二,名字已不可考,可从前附近很多村里的孩子,在父母去赶集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能给他们捎来两个用干荷叶包着的煎包或者肉盒。那家做银器的,不叫银匠铺子,也不叫银气店,而是被人称为“银炉大院”。从这称呼上,规模可想而知。
村中染坊不止一家,所以带动了很多人家种植一种叫蓼蓝的染料作物。这种植物的叶子采摘后用水浸泡,并加入石灰,过滤后便成了纯天然的染料。这项活计俗称“打靛”,辛苦也需要技术,主人便做好吃的给打靛人吃。村里那时流行一句话:吃饱饭,打好靛。
村中的戏班子在很多年里也是远近闻名,唱的曲目是四平调、两夹弦、山东梆子。曲目开始是传统戏,后来也有了现代戏,《红灯记》啥的。据说,开国大典那天在镇子上搭台演出的,便是我们村的戏班。那时,演《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的,是一个叫阿贤的人。他演穆桂英,老太太看了都夸他真像女的。据说,在阿贤结婚的那一天,村里好多大姑娘、小媳妇都黯然神伤。她们忍不住去找同伴,伤感地一遍遍说:呀!阿贤结婚了!一定有人迎合着:是啊!人家阿贤也结婚了!
在教育方面,村里有两个人堪称功臣,他们是程鉴渊和程钦渊。程鉴渊擅长珠算,是村里珠算第一把交椅。他办过私立小学,又办过私立中学,地址就在原来的银炉大院附近。在建国初,他办的私立中学招生范围已经包括附近好几个县市,学生好几百人。在他的争取下,县里后来在原私立中学的基础上,创办了金乡三中。他在办学时为了扩大规模,建筑校舍,不惜卖房子卖田产,可以说倾尽所有。
程钦渊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子的完小当校长。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建国前平原省湖西中学的学生。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二儿子是知名的老红军,在聊城军分区干休所。他的三儿子程宝源,字大廔,是著名的书法家。如果从出人才这个角度讲,他们家算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望族”了。另外,地主子弟程汶源也办过私立小学。他和二弟程渭源都做小学教师,兄弟俩都写一手好字。程渭源写得尤其好,在家谱中都有“擅长书法”这一项专门说明。
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村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奇人。瘸子、哑巴、傻子、疯子等等,都有那么一两个;酒鬼、赌徒、色痨、亡命之徒也不乏其人;寡妇、鳏夫、孤弱、贫贱之人也隐忍地生活在大家中间。木匠、铁匠、屠夫、商贩更是在农耕之外,一日日平静地做着他们的营生。从前村北的磨坊里,还有一个人的脑袋像开动后的电磨的部件一样,一秒不停地疯狂晃动。这都让喜欢观察生活的村里人,自孩童起便从一个小村,目睹了整个世界的模样。
大家都记得一个叫彬国的老人,他住在离小学校不远的地方,以前曾在上面说的私立中学教书,不知为什么却疯掉了。他手中有《古文观止》,嘴里还念叨过“仄仄平平仄仄平”,好像对古文很有研究。他喂着一头驴子,除了赶着下地干活,有时还骑着。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他被人用棍子抹了一嘴巴的屎。他的儿子是个瘦弱且老实的人,没有办法,便用地板车拉着他,走遍了村中每一个街巷,以期望用这种方法,引起村人对伤害他父亲那人的道义谴责。
程彬国神秘、古怪而且引人同情,儿女也没有什么建树。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孙女学习极好,后来考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大夫。孙子更是聪颖过人,初中时候就学习出众,常得到老师和村人的夸赞,大约是得到了些爷爷的隔代传吧。
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文化积淀的村子,今天却似乎越来越泯然而毫无特色。银匠铺子是早已成为记忆,染布作坊的遗迹也荡然无存。大家都跟附近别的村子一样,以种植大蒜、辣椒为业;其他的手工与商业,也无不在这两样东西上做文章,千篇一律。在前几年,有人提出村子旅游开发的想法,打算将其作为县里人去白洼林场野游路上的一环。如果地主的那些大院子还在,修葺之后,似乎也蛮可以像乔家大院那样,供人一瞻的。可我们的旧建筑,总不能像西欧一些国家一样,保存至几百年而完好无损。
按说,建筑物是最易保存长久的,除非是遇到了无法抵抗的自然力或者战争。但在现实中,和火山、洪水、地震、兵燹相比,对建筑最大的戕害,却往往是人为的破坏。有意去毁掉它,当然比不慎损毁,猛烈而直接。这种破坏,往往又是毁灭性的,毁灭后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村中的那些地主院落,开始肯定是因为代表着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要被破坏;后来肯定又是不利于村子的整体规划和发展,不能给大家带来经济利益,要被破坏。在遗迹被弃置一旁甚至破坏殆尽的同时,文化和精神内核上的东西,自然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洗、大毁灭。巨大的文化和心理断层,带来惶惑的无根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村子里随之而来的变化便是,大家不再推崇文化,不再认同读书,不再津津乐道于哪个门里出了几个人才。除了由于骨子里的劣根性而产生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村干部的仰慕和追逐(惧怕他们,崇拜他们,并在有条件时,希望成为他们);他们羡慕的是谁做大蒜生意挣了大钱,成了村里的“首富”。他们把那些走歪门邪道的人捧上了天,把那些靠偶然的好运气发达的人当做了年轻人的偶像。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或者希望像祖辈那样,花了钱上了学,但找不到工作或者没找到好工作的,自然在别人的窃笑和口水中,卑微得抬不起头。
这样的村子,实在是难以自然而然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所以,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村里有弟兄俩骂架,一个说:我操你妈!另一个便学着历史上刘邦对待项羽那样,笑笑地说:我妈也是你妈,你操就操嘛!骂人的便动心思说:我操你闺女!结果,是上演了一场武打大戏。
这样一个小村,没有奇异山水,却也在自然的筛选中,发展出它独具特色的产业,也有了它稍稍出色于周围村子的事业——人才与人才的培养。这里在建国初即有人考上清华大学,北航、北邮这些名牌大学更是不乏其人。这些年,小村从风气和所推崇的来看,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同一个原本装满佳酿的瓶子,酒倒掉了,却装满了醋或其他说不上来的东西。总之,是让人觉得不对味儿。在前些年,村里是想动动祖宗的脑筋,用文化搭台,也唱一出大戏的。具体说是修了宗祠,建了牌坊,还在村口树了两根不伦不类的华表。在准备就绪之后,还搞了一个程氏的寻根问祖祭祀活动。据说在活动中,被奉为座上宾的,大约还是几个捐了款或当了官的人。虽然不大像样,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会干点儿啥呢?
这样的一个村子,渐渐活成了北中国很多乡村的缩影。


长按gongzhong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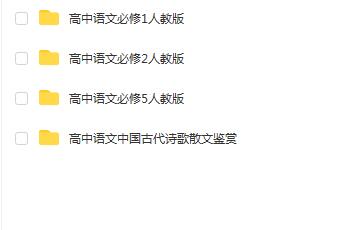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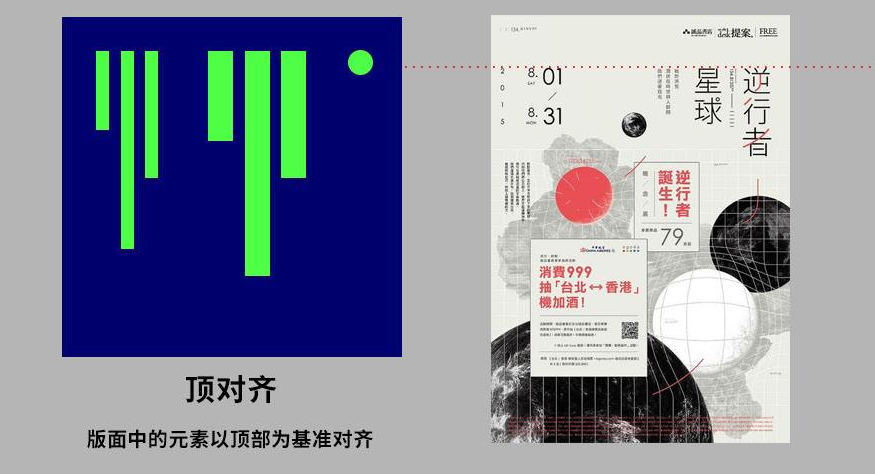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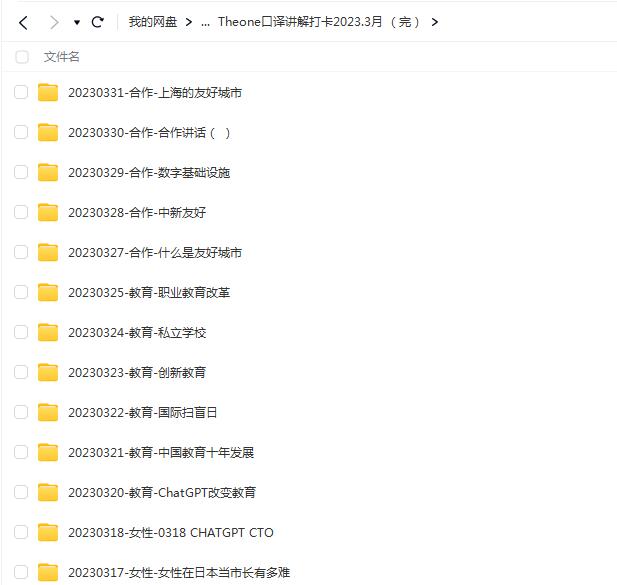
![【朱伟】高考版恋恋有词[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25ml/252-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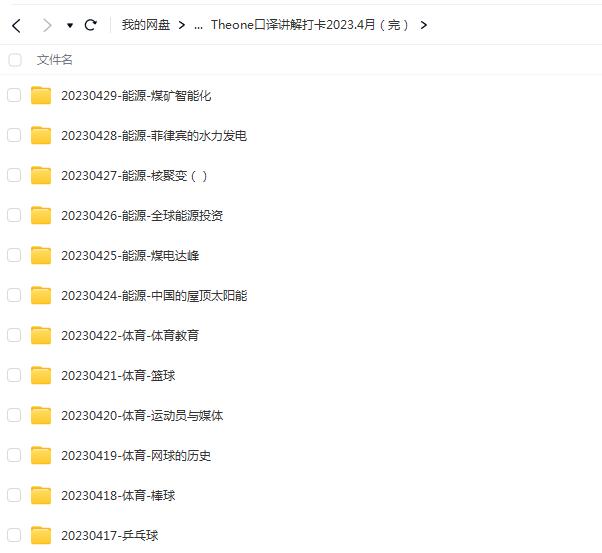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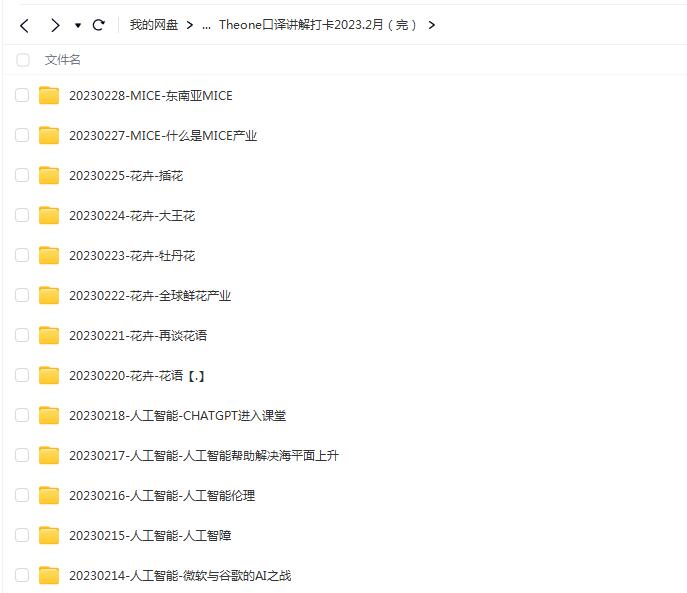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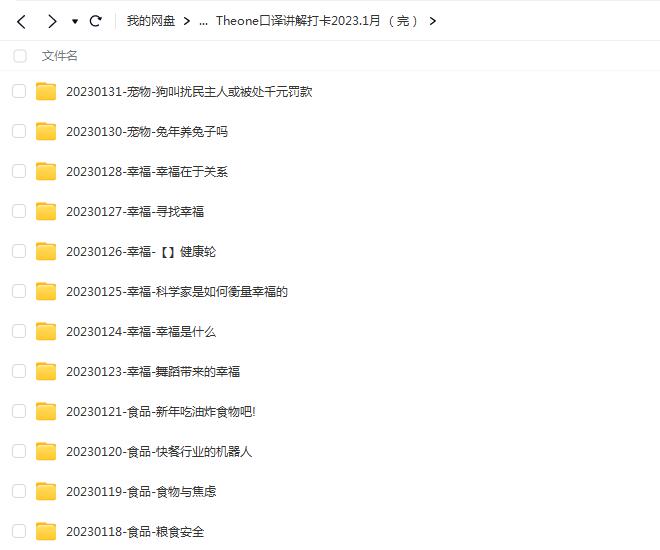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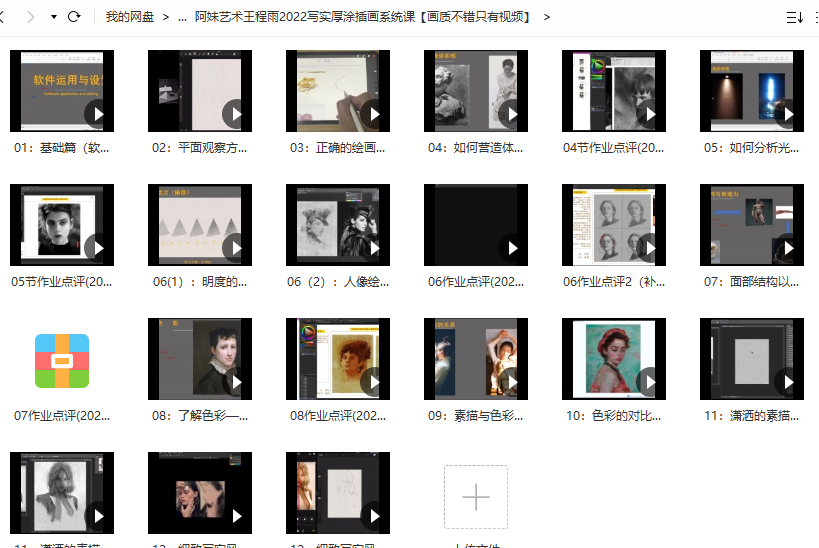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