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我的班(二)
发布于 2021-11-22 20:02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作者:陈增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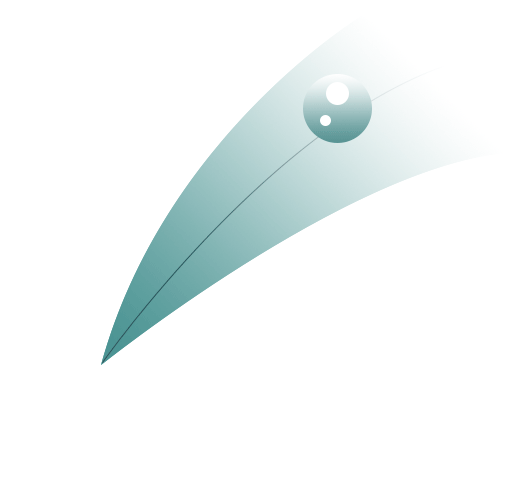
刚刚入学的一段时间,我的学习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小学整天背 “语录”,中学先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忙着揭批“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前,既无暇读书又无书可读。所以初进阅览室,骤然看到好多图书,犹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顿时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光是中国文学史,就有多种版本,刘大杰的、文研所的、郑振铎的,等等。我翻开一本,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诗人、文学现象、各种流派,评述周详,彻底颠覆了我所知的那点鸡零狗碎。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笔记本,兢兢业业地开始了摘抄大业。等我的手抄本快要竣工的时候,古代文学开课了,教材正是摘抄过的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
1982年分到邢台师专,与中文系七七级的杨东坡、潘立仿同住一排。二人讲起同窗典故,说他们班一个同学,有一部“珍贵”的《中国文学史》手抄本,成为大家的笑料。我一边感叹着吾道不孤,一边哈哈大笑,做聪明状。
“文革”甫毕,留下许多思想禁区,许多作家尝试着用文学的形式去打破一些藩篱。每有突破,人们奔走相告,一片轰动。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叶文福的《将军,不能那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戴厚英的《人啊,人》等等,无不引起人们的追捧与热议。那时的我们,吃着粗粝的饭食,住着简陋的房舍,却无不放眼世界,心忧天下。陈福民、季同欣、郑子森、贾青云、汪洋等同学,经常在一块讨论、争论、辩论。思想碰撞,学术砥砺,成为当时学习生活的一种常态。
当时人气最旺的地方就是阅览室。当时的课程安排基本上都是“干货”,多数是上午上课,下午自习。自习的时间,多数学生都涌到了阅览室,所以不等阅览室开门,长长的走廊里就挤满了人。记得有一次,拥挤得太厉害了,咣啷一声,把阅览室的两扇子大门挤倒在地,人群忽地一下,全都冲进了阅览室。现在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这要是发生踩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阅览室的座位有限,同学们想方设法,抢占座位。有人拿椅垫子占座,有人委托别人占座。记得有一次在阅览室看书,一女同学进来,左右略一扫视,噌噌噌,收起一摞子椅垫,毫不客气地丢到后头,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断,宣布了这种占座方式的破产,然后坐下来静静地学习。还有一次,中文七七级的一位杨姓学兄,一边看书,一边摇动长椅,时不时地“嘣”的一声,制造一次“地震”,并排放出一股尾气。旁边的女生一开始还皱着眉头,掩着小嘴,顽强坚持,后来实在顶不住这物理与化学的双重攻击,只好收拾细软,落荒而逃。这位学兄奸计得逞,不慌不忙地拿过书包,放在旁边,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帮死党占座的艰巨任务。
大一的时候,班里曾经出过几期墙报。编辑有李文秀等人,姜凌涛同学担任美编。我在中学时期爱好写作,作文有的登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小报上,有的被收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而我自己担任班里的板报组长,经常按葫芦画瓢,写一些《渔家傲》《水调歌头》之类的东西蒙人。上大学以后,骤脱夜郎,不啻井蛙,除了写一些小人得志的“散文”之外,还接二连三写一些所谓的“词”。蒙编辑同学不弃,张贴“发表”,沾沾自喜。后来学到诗词格律,方知古典诗词,除了字数、押韵之外,尚有“对仗”与 “平仄”之说。想起我的“大作”,不但有各班同学围观,且有各科老师“哂读”,登时冷汗涔涔,无地自容。
大学四年,我不懂音乐,不擅体育,不精写作,除了《古代汉语》考试时侥幸突破90分,名列全班第一之外,一直庸庸碌碌,默默无闻。直到北戴河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双手各攥三把暖壶,打完热水,穿过饭厅回归宿舍。饭厅的地面上有学生泼洒的稀粥,扫帚扫过以后,上面一层浮土。当时正值中午,各个饭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施施然走来,冷不防脚下一滑,以行为艺术中最酷的一个造型,趴在了地上,六把暖壶同时爆炸。沉默了四年的我,厚积而薄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河北师院的好多老师大有来头。比如我们中文系的朱泽吉先生,1938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参加沈兼士、陆宗达、周祖谟等著名学者主持的“语文学会”,颇受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学者的赏识,后来成为余先生的研究生。萧望卿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他的《陶渊明批评》由朱先生亲自作序。王学奇先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颇受先生的青睐。
其他的老师虽然师承不同,却也各有“绝活”,各擅胜场;偶有不如意处,更显其个性特点,至今回忆起来,有滋有味,情趣横生。
柴世森老师讲现代汉语,表述严谨,语气和蔼,非常有亲和力。韩阙林老师讲古代汉语,板书竖行繁体,字迹舒展大方,简直就是绵绵不断的书法表演,让人大饱眼福。白静生老师的司马迁与《史记》,汩汩滔滔,旁征博引,气场极为强大。欧阳方润老师的外国文学,王惠云老师的当代文学,逻辑严密,条分缕析,听着非常过瘾。陈淑敏老师的中共党史,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感染力极强。张祖彬老师讲授文学概论,化枯燥为生动,丝丝入扣,引人入胜。讲到兴起,白沫生焉,面色红焉,台上台下,酣然若醉。张月中老师讲元曲,激情四射,眉飞色舞,略微带“色”的地方总要渲染到淋漓尽致。许秀京老师讲“毛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讲到“原驰蜡象”一句,许老师一边以手绘形,一边以言释义:“连绵的山岭起起伏伏,就像大象的驼峰!”“大象”而有“驼峰”,许老师的思维快到错位。孙煜老师讲逻辑推理,推着推着,误入歧途,尴尬地一笑,从头开始,拎拎清楚。
尤其难忘的是胡如雷先生开讲座,大裤衩子,短袖背心,一把大蒲扇,边走边说,边摇边讲,状若市井老人而偏偏字字珠玑。马季先生作报告,外系的学生闻风而至,座位上,过道里,窗台上,挤满了人,笑声,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
大四做论文,我的指导老师是赵九兴先生,所以免不了登门求教。赵先生住一个单间,从北京搬来的书籍资料用密密的草绳捆着,一包一包地摞在一块,七八年而未曾拆开。可见“文革”期间老师们无暇治学,而赵先生对宣化也实在没有归属感。赵先生对我的选题作了详细的介绍,比如历史上有过哪些重要的争论,当今学界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等等。之后又就论文写作的立意、选材、行文格式等等,作了详尽的指导。他给我开列了一些参考书目,我专门跑到北图,才把相关的资料找全。
大学四年,我的最实际的收获有两项:毕业实习,常林炎老师训练我的职业技能,使我以后能够胜任工作,传承薪火;做论文,赵先生教给我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使我毕业之后有了追求的方向,提高的可能。
毕业后我曾到石家庄拜访过萧望卿先生。萧先生非常激动,一直在说,可惜他湘音太重,我听不太懂,只能频频点头,就像返乡的游子,充满了孺慕与感动。我在大学讲授《国学概论》,谈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说陈给他的学生戏作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梁启超是他的弟子,也是国学院的导师。王国维是大清皇帝溥仪的老师,同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此联的意思是说,你们既是圣人的再传弟子,又是皇帝的师兄弟,足以自豪了!之后我拉大旗作虎皮,弱弱地说,我的授业恩师萧望卿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几位先生。这样算起来,咱们也……话没说完,学生都笑了。
母校的老师,所任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不同,授课风格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异常敬业,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毕业几十年了,当年的学子如今发亦苍矣,齿亦摇矣。但不管我们身在何方,成就高低,老师们当年镌刻在我们心灵上的印痕,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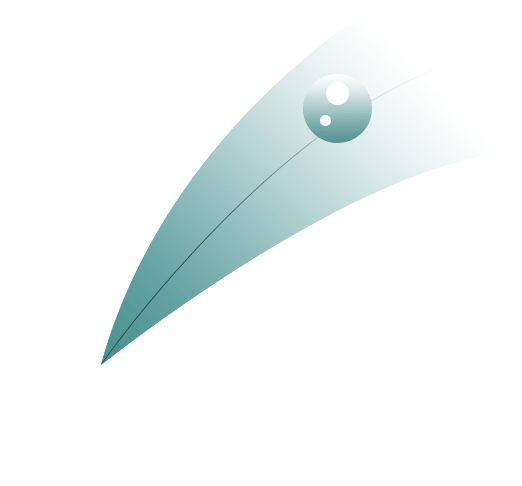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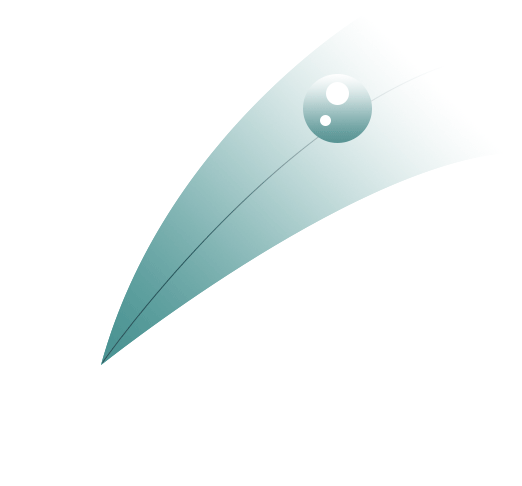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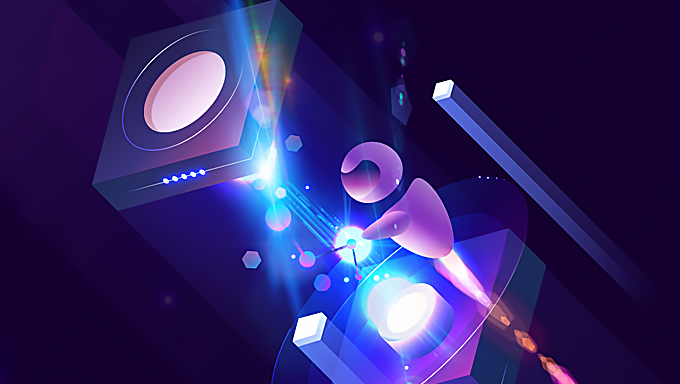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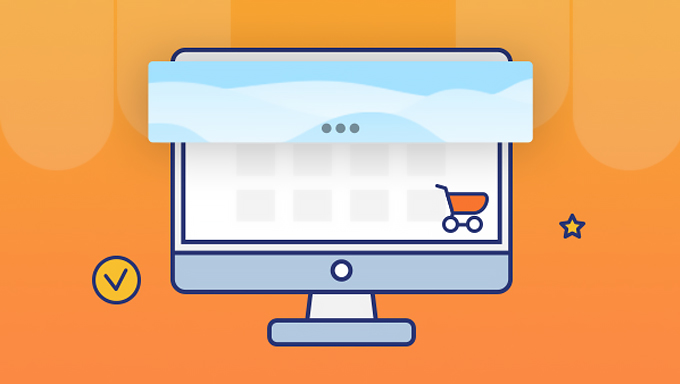






![[泡妞秘籍] 妞泡我网内部泡妞培训教程 40集 音频教程知道+doc重点笔记+素材魔术指导视频](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e295db3b2b702e6b08d32b607d777bdd.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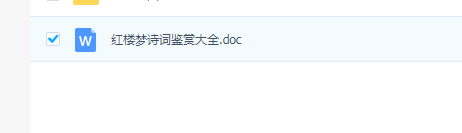

![[职场必备] 和秋叶一起学PPT、阿文新课:我懂个P、和阿文学信息图表、EXCEL表格之道专业版、阿...](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c79c0636d02149b844320d5f7d552097.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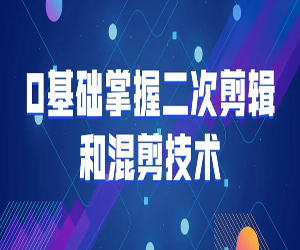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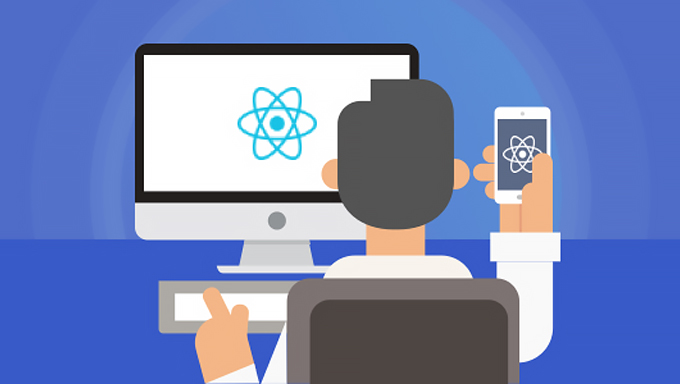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