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看到了雪,就看到了你的向死而生
发布于 2021-11-22 21:54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点击上方“蝴蝶为你朗读”我们

TO: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诗《未选择的路》写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萧红就是如此,她选了少有人走的那条,崎岖幽暗,雪花纷飞,望不见尽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识文断字的她,心性与一般女子迥然不同。她选择了自由,却被一同私奔的未婚夫将怀孕的她抛弃在旅馆。她忍辱含悲,给报馆写信求助,幸而被报馆派来的青年搭救。乱世飘萍的两人一见如故,遂发展成情侣而同居。然而,幸运只是一时的。生活的浪头一次次扑打过来,两人都处在失业状态,境遇一点也没改善。每天,郎华都出去得很早,到天黑才回来。他去找活,去赚钱买面包,然而往往所得的十几枚铜板,只够买几个雪白的馒头。只有进入幻想的世界,她才能片刻忘记忧伤,生活虽然一片狼藉,但自由之精神永不枯萎。两人自有一套精神胜利法,忘却了邻人无心的打扰,排解着生活的愁闷——今天小雪,推送蝴蝶读萧红《雪天》,愿我们像萧红那样向死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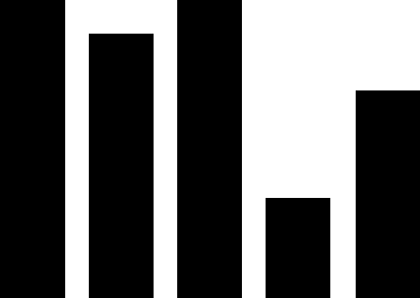
▾ 点击收听▾
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俄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象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一切街车街声在小窗外闹着。可是三层楼的过道非常寂静。每走过一个人,我留意他的脚步声,那是非常响亮的,硬底皮鞋踏过去,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有时成群的响声,男男女女穿插着过了一阵。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可是不用开门看,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
小窗那样高,囚犯住的屋子一般,我仰起头来,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地跌落,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即刻就消融了,变成水珠滚动爬行着,玻璃窗被它画成没有意义、无组织的条纹。
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萧红:《雪天》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
过道一响,我的心就非常跳,那该不是郎华的脚步?一种穿软底鞋的声音,嚓嚓来近门口,我仿佛是跳起来,我心害怕:他冻得可怜了吧?他没有带回面包来吧?
开门看时,茶房站在那里:
“包夜饭吗?”
“多少钱?”
“每份6角。包月15元。”

“……”我一点都不迟疑地摇着头,怕是他把饭送进来强迫我吃似的,怕他强迫向我要钱似的。茶房走出,门又严肃地关起来。一切别的房中的笑声,饭菜的香气都断绝了,就这样用一道门,我与人间隔离着。
一直到郎华回来,他的胶皮底鞋擦在门槛,我才止住幻想。茶房手上的托盘,盛着肉饼、炸黄的蕃薯、切成大片有弹力的面包……
郎华的夹衣上那样湿了,已湿的裤管拖着泥。鞋底通了孔,使得袜也湿了。
他上床暖一暖,脚伸在被子外面,我给他用一张破布擦着脚上冰凉的黑圈。
当他问我时,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弯:
“饿了吧?”
我几乎是哭了。我说:“不饿。”为了低头,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的脚掌。
他的衣服完全湿透,所以我到马路旁去买馒头。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着气,刷牙缸伴着我们把馒头吃完。馒头既然吃完,桌上的铜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问我:
“够不够?”
我说:“够了。”我问他:“够不够?”
他也说:“够了。”

隔壁的手风琴唱起来,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吗?手风琴凄凄凉凉地唱呀!
登上桌子,把小窗打开。这小窗是通过人间的孔道:楼顶,烟囱,飞着雪沉重而浓黑的天空,路灯,警察,街车,小贩,乞丐,一切显现在这小孔道,繁繁忙忙的市街发着响。
隔壁的手风琴在我们耳里不存在了。
本文选自萧红系列散文集《商市街》
图片来源:电影《黄金时代》


期待你的
分享
点赞
在看
编辑:时光匆匆、轻舞飞扬
管家:盛宴、浮云
音审:谛听
投稿:739255591@qq.com

长按ErWeiMa“蝴蝶为你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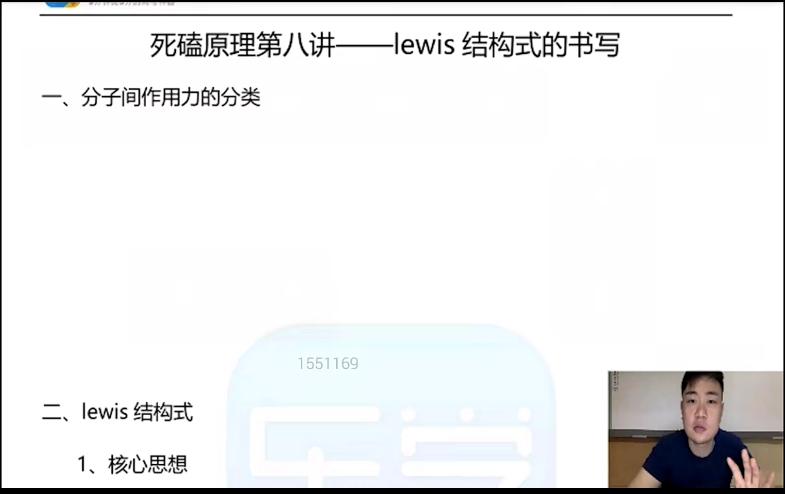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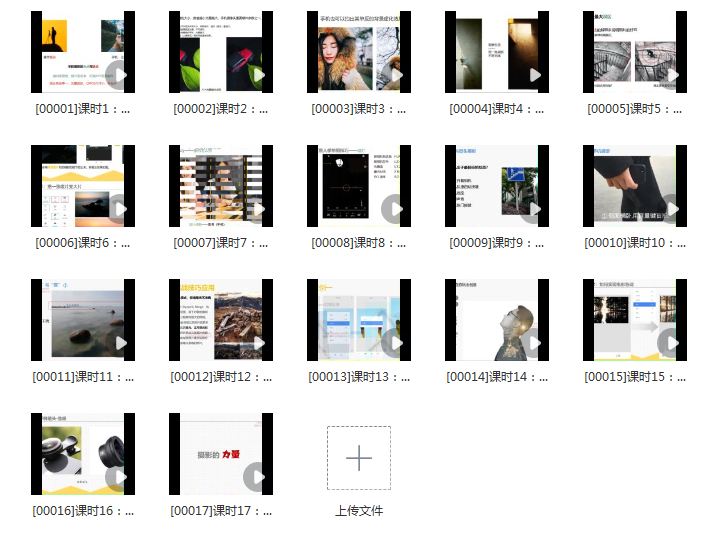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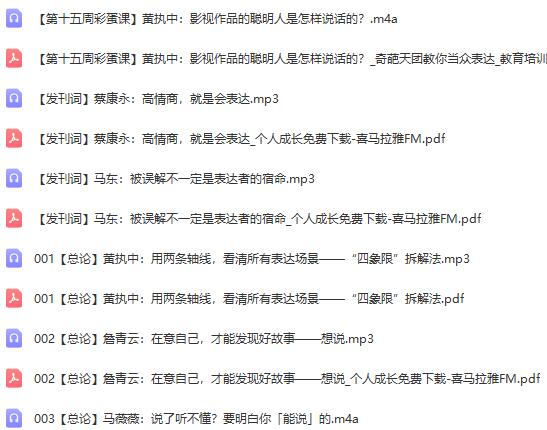
![[Web开发合集] PHP Web开发框架 laravel实战开发宝典 向军老师帮你打通PHP Web开发框架的疑难杂症](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70d4b9f114bd46480d5aa16747689329.pn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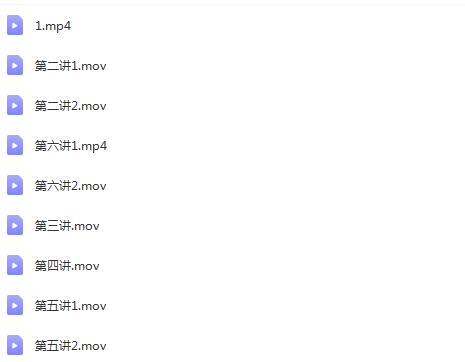


![时光暖流CATTI课,打造你的翻译梦![百度网盘分享]](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30ml/149-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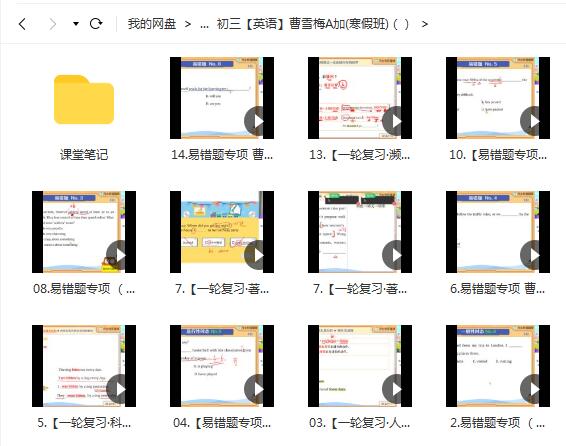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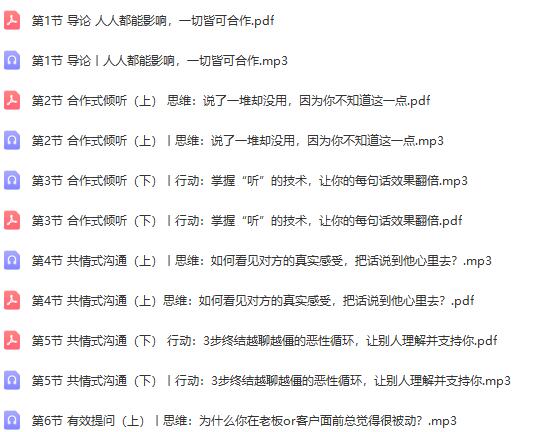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