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写|如蕤 无关时代
发布于 2021-11-29 18:43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我非常喜欢沈从文的《如蕤》,总觉得他写了一个极不常见的、令人欣喜的女性,但是又说不太清楚我的感受。这两天借着写一份作业的机会整理了一些对《如蕤》的想法,把它po出来,做一个记录。全文约3700字。
在谈《如蕤》前,我需要再简述一下小说的主要内容和引入一个讨论现代文学中“新女性”形象的说法。
如蕤是个美丽活泼、多才多艺、家境富有的都市知识女性。她向来看不起任何追求她的男性,并保持着一份孤独和高傲。如蕤在一次海中游泳时遇险,被一年轻她七岁的青年梅先生救起,遂对他生爱心。即使梅先生与她有隔阂并拒绝她,如蕤仍然保持真诚。于是三年中,“两人只在一份亲切的友谊里自重的过下去”。大学毕业后,如蕤觉得事情该有个了结,便告诉梅先生自己准备去法国留学,而梅先生无动于衷。恰巧梅先生做实验中了毒,如蕤照顾他直到出院。虽然梅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如蕤,但如蕤依然选择了离开。补充说明,小说的叙述时间是这样的:梅先生住院时——如蕤的往事、如蕤与梅先生的相遇——如蕤与梅先生的分别。
我要引入的这个讨论现代文学中“新女性”的说法则来源于赵园。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书写重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女性角色在作品发挥着批判男性中心意识的作用。而她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受男权压迫而展现苦难,二是对抗男权压迫以体现追求。而代表后一种方式的女性以“新女性”为主,即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们。赵园在《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一文中以“雄强与脆弱”对“新女性”的形象进行了概括。“雄强”是指这些“新女性”致力于摆脱传统和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脆弱”则指她们的理性不得不向情欲屈服。李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一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并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立自主、美丽性感的“正面自主型”女性的共同性格特点。但是两位学者均在话里话外对能适用于“雄强与脆弱”这一说法的“新女性”做出了另一重限定:她们“不超出革命、进步的意识形态框架”,需要“面对敌对的伦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可以理解为,在大量作品中,政治性突出的时代背景是作家提供给“新女性”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新女性”的“雄强”基于时代的鼓舞,而她们的“脆弱”也是时代中性道德新认识下的结果。
那么我的问题是:“新女性”一定要基于政治性突出的时代背景才能反映出“雄强与脆弱”吗?“雄强与脆弱”的言说空间是否可以被扩大?我认为沈从文在《如蕤》中给出了一种值得思考的答案。
先给出我的观点:
如蕤符合“雄强与脆弱”的新女性定义,同时,沈从文为如蕤搭建的爱情生活舞台也为新女性展现“雄强与脆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如蕤的“雄强”可以通过三方面体现:对部分男性的强势,对个性的坚守,对爱情的追求。这三方面并不能简单的区分,它们交织呈现,互为补注,共同实现如蕤对男性中心理念的突破和对男权的反抗。
小说中这样形容如蕤对追求她的男性的感受:“为她倾倒的人虽多,却在同样情形下露出蠢像,做出同样的事情。事故一些的先是借些别的原因同在一处,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样子,变成一只狗了。”其实如蕤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追求她的男性究竟是爱她本人,还是爱她的外貌、财富、阶级。不过这样简单地摘录容易造成对如蕤的误解,即以为她对一切男性皆是鄙夷、蔑视的态度,从而以“女性的解放也不能经由男性的被奴役而取得”等观点批判她。但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如蕤并非对所有男性如此,也并非只对男性如此。如蕤认为自己的美丽如大风,而她要寻找的、值得爱慕的是在她的美丽下如风中不动摇的大树的人,即如蕤认为男性不应当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或爱情中委曲求全、谄媚逢迎、改变自身,而应当保持自己的个性。如蕤对女性也持同样的态度,她说“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引出,个性特性是不易存在”。可以看到,如蕤对男性的批评并非源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个性”才是她评判一个人的标准,而梅先生对“个性”的保有也是如蕤爱上他的理由。不过我们不得不质疑,如蕤对梅先生的“个性”的理解是否正常,即梅先生的“拒绝”究竟是不是一种如蕤真正期待的“个性”。而如蕤对爱情的追求并非指她对梅先生展开猛烈的追求,小说也以三年中如蕤“在意外情形中成为一个失恋者”,“两人只在一份亲切的友谊里自重的过着下去”暗示如蕤行为上的局限;我想说的这种对“爱情的追求”是指,尽管有隔阂、误解,如蕤仍然爱着梅先生,她以一种无望的坚持展现着自己的个性。
如蕤的“脆弱”,即她的理性向情欲的屈服,则可以通过她与梅先生的交往经历体现。在二人海滨初识时,如蕤并没有爱上梅先生,她隐瞒了自己是“xx总长的小姐”的身份,不断逗弄这个天真的年轻男子,似乎在尝试验证自己的美丽的力量,让梅先生染上了“那点心中烦乱的爱情”。然而理性的初识之后,梅先生挣脱了,他拒绝、躲避如蕤。但如蕤“爱了他”,情欲终究打破了年龄、地位、身份的障碍,让如蕤拥有了一段自知无望的感情。理性回归,如蕤决定出国以了结感情后,却又因梅先生追问“什么时候动身”而泪眼婆娑、柔弱无力,甚至产生了犹疑。
如蕤亦是一个可被称为“雄强与脆弱”的“新女性”。但是与其他知名的“新女性”对比,比如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子君、姚木兰,如蕤的故事显然缺少了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支撑,传统观念与男性没有对其进行压迫,如蕤的爱情更没有体现所谓革命、进步上的追求,但这并不妨碍小说对女性主体性的高扬、男性中心意识的冲击和两性平等的支持。作者对如蕤“雄强”一面的极致书写就是女性在社会中应当获得自主权的最好证明,对男性在追求女性时谄媚逢迎的刻画就是将男性拉下神坛的有效方式,而对男女丧失个性的批判就是不偏私任何一种性别而支持两性平等的一种手段。这种时代、社会、男权的隐退,似乎在告诉读者,女性主体性的高扬与男女平等并不只是此时此刻、当下时代的革命、政治任务,也不是五四运动、大革命才催生的思想,而是人类应当内化的一种长久存在的认知。
沈从文将如蕤塑造成了一个自尊自重,有知识、有追求的知识女性,当时社会对女性认识的局限、外在的制度和政治背景全面隐退,给予了女性角色一个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展现自我的良好环境。结合沈从文讨论女性问题的散文《烛虚》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如蕤是沈从文心目中极为理想的女青年形象。其实光是从”如蕤”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态度,“蕤”的意思是“草木华垂貌”,引申后可指女性华美艳丽。
但是我们不应忽视沈从文塑造如蕤时反映出的一些局限,因为这些局限不仅关涉沈从文本人,更关涉整个女性群体的解放和进步。如蕤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她不仅学识丰富,还美丽动人,擅长上流社会流行的体育,能够出国留学,更是“xx总长的小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怀疑,如蕤能够批判男性和坚持自我的主体性,外在的外貌、金钱、阶级条件起了极大的助力作用。如蕤有金钱、阶级为后盾,有条件将沉浸于无望感情中的自己一把拉出,所以才能飞蛾扑火地帮助沈从文证明女子应有的形象。但这令我们反思,外在条件不如如蕤的女性应当如何成为“雄强”的自己,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即至少在《如蕤》中,沈从文描写的是一个即使在上流社会也不一定具有学习、模仿可能的女性形象。那么那些身处底层、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与她们的生活又该何去何从?难道要继续在无望中思考“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或者“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地看热闹?抑或是跟随丈夫回家又可能随时变成妓女?还是给爱人下毒?沈从文笔下,底层女性固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动人妩媚的风姿,但回归现实,她们又该如何跟上时代潮流中女性解放的步伐?我理解一切女性,但女性又当如何才能少一些这些需要“被理解”的困境中的挣扎?
上周刘老师在课上说,现在的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该在30岁前结婚,35岁前生孩子,但是这种所谓的“合理”“应该”又是从哪里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思考,为什么我们——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大多没有如蕤的勇气;为什么男性中心理念依旧存在,并不断给“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制造困境;为什么有人会执意认为“女性的解放”就是“男性的被奴役”。
最后再说一些零碎的感受。
我个人总觉得如蕤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她能对梅先生保持三年的爱已经是折损了很多骄傲的结果。如果梅先生能在她决心出国前告知如蕤自己的爱,或许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但是如果没有如蕤出国,梅先生又怎能意识到自己的爱。也许有人会疑问,为什么梅先生承认爱如蕤后如蕤还要走(有b站弹幕内味儿了),我不认同网络上说她是性单恋的说法,可能别扭的人就是这样,在没必要特别固执的事情上总有自己奇怪的坚持,所谓处在“拉不下脸”的很高段位上。(我就经常死都不改决定以至于被我妈嫌弃/爆骂过n次,所以大概勉强能理解一点点如蕤的做法。)
以及我非常喜欢小说的结尾。它是这样的:
听差拉上了门出去后,他伸手去攫取那个药瓶,药瓶中的白汁,被振荡时便发着小小泡沫。
他望着这些泡沫在振荡静止以后就消灭了,便继续摇着。
他爱她,且觉得真爱了她。
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有镜头感。
沈从文你真的很会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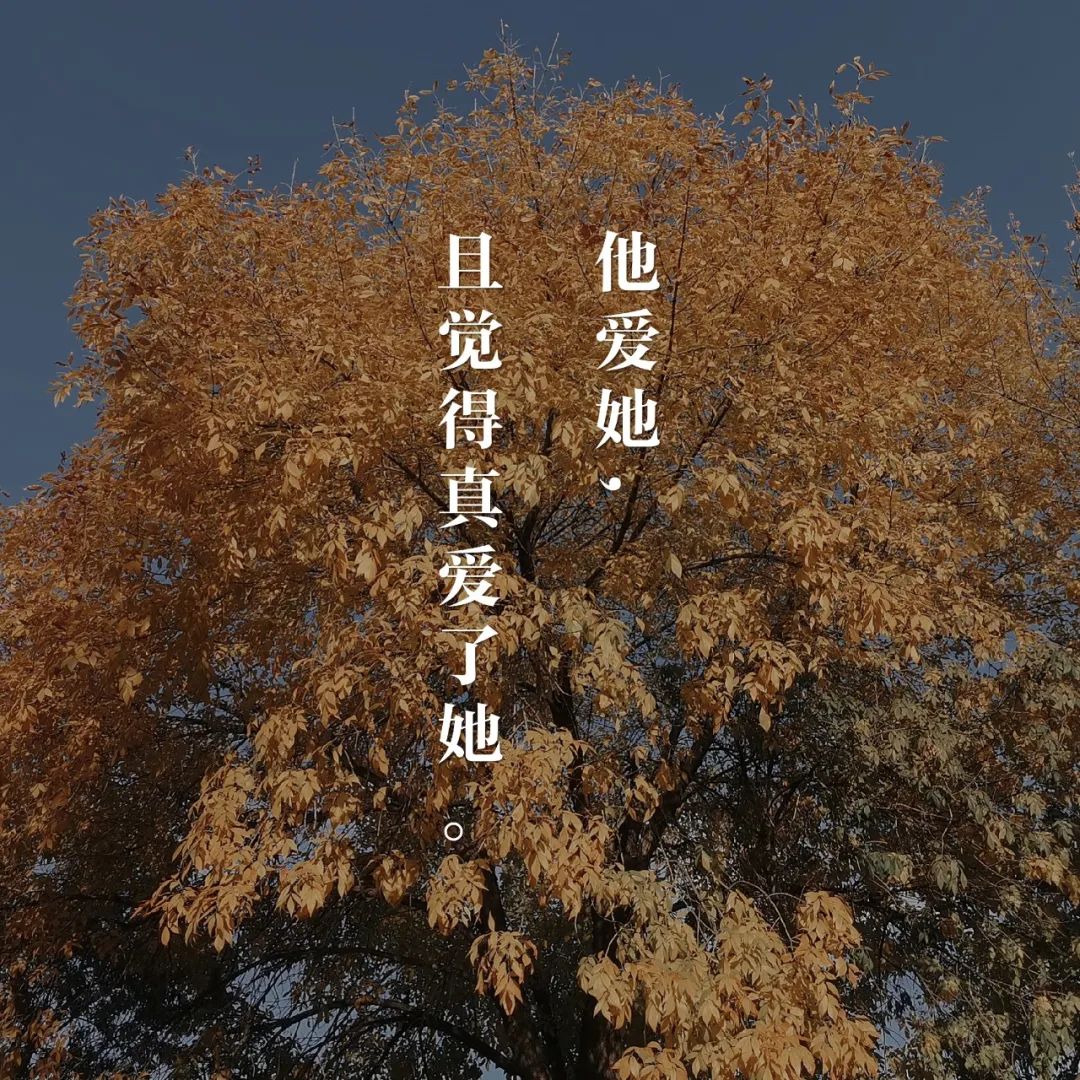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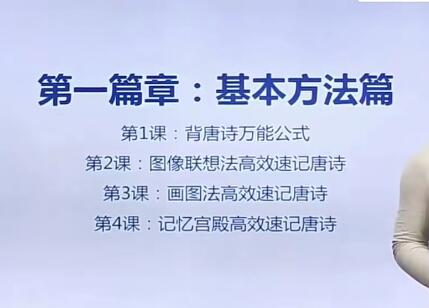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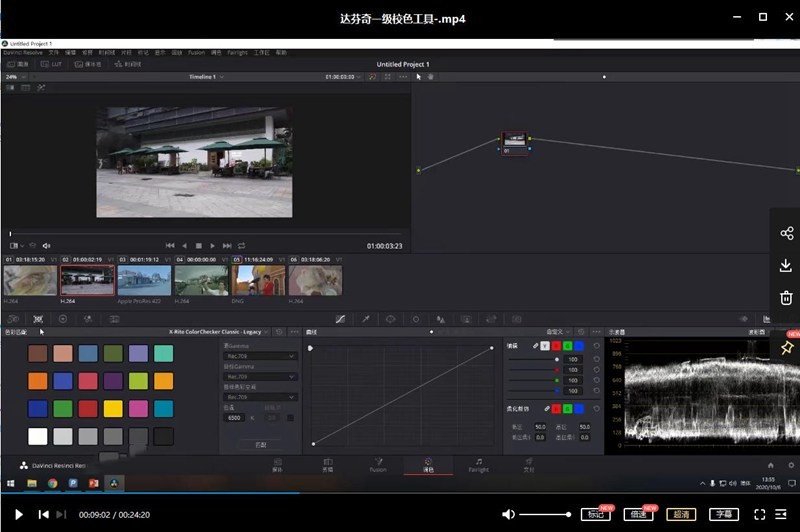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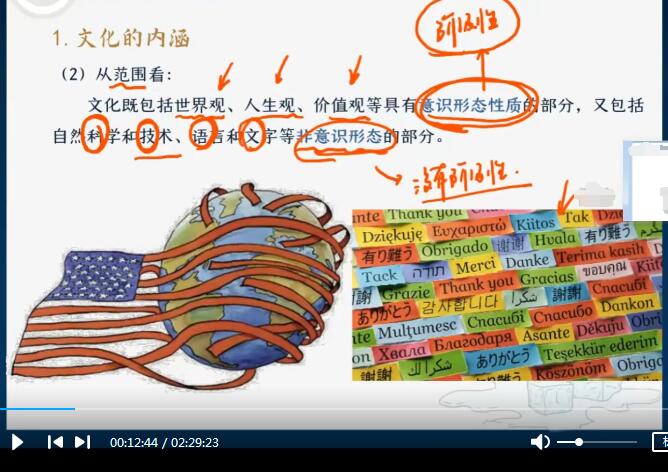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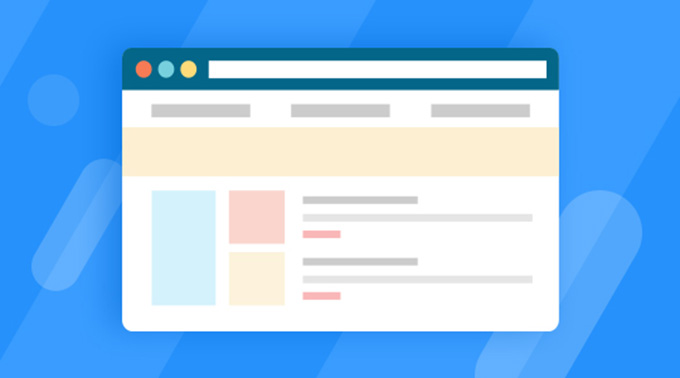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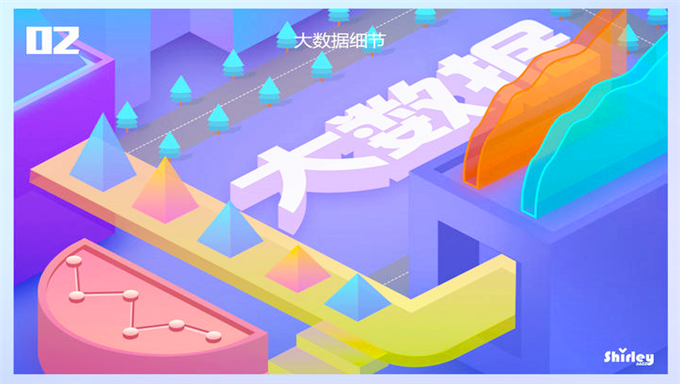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