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小说呈现”发生在某个夜晚的故事;“精彩散文”故地重游,两个不一样的海州;“诗歌矩阵“我有时为了寻找一只旧闹钟,我得翻出一个旧时代;“文学艺术”《理智与情感》:避免恋爱脑。欢迎阅读。

精彩散文
海洲游记
文|蒋冠男
我自2004年离开连云港后,整整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再去过连云港一次。连云港,古称“海洲”、“郁洲”。今“连云港”三字中的“连云”二字尚有诗意,但那“港”字总让我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堆满集装箱的码头,充斥着物欲与金钱的味道,我不喜欢。所以,我更喜欢它的古称“海洲”。2002年至2004年,我在连云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里读书。在那两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痛苦,长达两年的痛苦。所以离开后我便不愿再回到那个地方了。然而,可笑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经常梦到那个地方,那个不大的校园,那个空旷而萧条的城市。梦境中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一片。10年后,也即2014年的国庆节,我方和先生以及两周岁的女儿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游玩。十年前的痛苦已在时光中慢慢淡去,淡成了水印般模糊的印迹,但又似水墨画般悠远绵长。2016年1月,我又一次只身前往,在孔望山上的龙洞庵小住了几日,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佛法的清静,并在仁湛师父的引领下行了皈依三宝之仪。201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与妹妹一家前往连云港游玩。今年国庆,我又一次带着女儿前往了连云港。
出发
10月1日6:10我与女儿准时起床,然后洗漱,吃早饭,收拾剩余未收的随身物品。7:10我与女儿、婆婆坐上了出租车,前往堰桥地铁站(因先生在外出差,婆婆只能乘坐汽车回老家丹阳)。8:50我们乘坐的大巴准时自无锡驶出,前往连云港。无锡有直达连云港的高铁,但连云港的行程我是出行前十天才决定的,已订不到火车票,而我不喜欢开车,所以只能坐大巴前往。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还有个原因:我很想尝试简单面淡泊的生活方式。大巴未到江阴便被堵住了。我到背包中找耳塞,准备听佛学课件或音乐,却发现耳塞转换器没带,只能作罢。包中我还带了两本书——《安徒生童话》与《萧红全集1》——女儿与我的精神食粮,专为等车或休息所备。然而,车子一走一停,车内汽油味也很浓,孩子与我都有些晕车,所以书是无法看了,只能看车窗外的车流。放眼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车流,我心中不免感慨:物质的提升和欲望的兑现真的能使人获得幸福与快乐吗?三十年前,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外出只能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路远则最多坐大巴、绿皮火车、轮船,大家不急也不慢,悠然自得地生活、前行。而那些行脚僧们更是徒步出行,大好河山一草一木尽收眼底,未尝不是一种快乐。出发前我估算了一下,如果路上不太堵的话,我们下午两三点应该能抵达连云港。但一路上大巴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堵车时我便打开导航看还有多久,导航显示的抵达时间不断往后推延着,堵得最厉害时导航甚至显示半夜十一点多才能到达。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堵的路段多是近服务区处。而沿路的服务区无一例外都是一幅人山人海喧嚣鼎沸的画面。一路上我与女儿吃完了带着的一只柚子、几片芝麻糖,以及在服务区买的一网兜菱角、一杯红米粥、一只水煮蛋、一根玉米。因为无事可做,于是吃饱了便睡,睡醒了依然是看车流,看累了再混混沌沌睡去,如此循环往复。平常我总是忙忙碌碌,常常是做着手上的事,心里已在想着下面要做什么事,日程从来都是排得满满当当,从未如此空闲过,所以心里倒也轻松自在。只是缺了耳机——耳边若能有音乐则更美了。20:38我们方抵达了连云港的苏欣客运站。在我的回忆里,那客运站的大门是朝西的。夜幕下我分不清那大门的朝向,但我疑惑那似乎并不朝西。但那车站又仍旧很破旧,似乎多年未重修过——想来门的朝向应该也是没变的吧。也许我记错了也未可知。车站门口的路上车很少,出租车更少,半天才驶来一辆,也多是载了客或被人预订了的。我这才想起应该用滴滴之类的软件打车。我在支付中找到了滴滴,勾选了快车选项,半天才有个司机接了单。我看着那车的行进轨迹,最初距离我们3公里,十分钟过去了还是3公里。我有些急了,遂电话司机,司机慵懒地回复道他累了,不想跑了,让我取消订单。只能取消。我又开了个呼叫,勾选了快车、专车、拼车等所有选项,依然是半天才有个司机接了快车的单,依然是距离我们3公里,依然是半天不见那车的行进轨迹有多少变动,于是再次取消了订单。看了下时间,已近九点。我打开百度地图查了下路程,发现车站与我预订的酒店竟只距离1.3公里,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半天没人接我的单——原来这么近。其实,连云港城区的大概方位我是有些模糊的记忆的,但不确定切实距离,以为很远。可见应该先查验一下再行动,如此也就不会浪费这些时间等车了。与女儿拖着行李箱,跟着导航步行前往酒店。路上经过一广场,广场上有遛狗的、跳舞的、唱歌的,好不热闹。花了大约二十几分钟,我和女儿跟着导航,沿着我记忆中有些印迹却仍然陌生的路步行抵达了酒店。办好入住手续,我便将行李寄存在了前台,然后与女儿出去吃饭。我们住的酒店位于闹市区,周边饭馆很多。女儿要吃馄饨,我说连云港这边的馄饨是小馄饨,和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遂带着她去了步行街。我很快找到了十七年前大学同学王韵洁带我去吃的那家金陵鸭血粉丝店,它竟还在。十七年前,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所以那时韵洁带我去那家店吃粉丝的情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么一大碗竟被称作“中碗”,碗内鸭血、鸭肝、鸭肠一大堆,鲜美非常,只要4元钱。当然,那时的4元钱不算很便宜,但也并不贵。因为知道这儿民风淳朴,饭菜量都很充足(不似上海无锡一带只象征性地给一点),所以我和女儿点了两份小碗鸭血粉丝。店家告诉我鸭血没有了,问我多加点鸭肝鸭肠替代可行。我说可以。于是我原本准备加一份鸭肝与鸭肫也就只需加鸭肫了,又加了一只卤蛋。没一会儿,粉丝和加的配料都上来了,果然,满满的两大碗,粉丝上的配料依然非常充足。说实话,那粉丝及配料我如今吃起来已不觉得鲜美,但我仍硬着头皮将我的那份吃完了——为了那份回忆,同时也因为不想糟蹋食物。女儿只吃粉丝,将配料全给了我,我帮她吃了些,但吃到后来实在吃不下了,不想浪费也只能浪费了。可见,最美的还是回忆。同时,美只有在你匮乏时才会凸显出来,富足时你可能就感觉不到美了——因为缺了那份需求,所以也就没有需求被满足后的幸福感。
孔望山
10月1日晚我们抵达那家鸭血粉丝店时,我便将定位发给了韵洁。她不知我那日去连云港,于是责怪我没告诉她,不然她可以去车站接我。我说车站距离我住的酒店很近,不用接,我也正好走走路——平时很少有走路的机会。她又问我呆几天、日程如何安排等,她要陪我,同时驾车带我出行。我说不用,这次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公共交通出行的慢生活乐趣的,我们都根据自己原定的日程安排自己的生活吧。她执意要陪我,说次日她安排人来酒店接我去孔望山,她忙完孩子后来与我汇合。我玩笑说我嫌她烦,假如她让人来接我,那我就不见她了。她这才作罢。我和她都是崇尚自由个性,且不拘俗套的人,所以说话也无礼节顾忌。因为没有牵挂与顾忌,所以10月2日我与女儿睡到7:30才起床洗漱,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早餐挺丰盛,我喝了一碗红米粥,外加一个水煮蛋和一盒酸奶,女儿又给我倒了一杯热牛奶。女儿吃了点蛋炒饭,外加一杯热牛奶和一盒酸奶。她早晨喜欢吃蛋炒饭,却不喜欢吃水煮蛋,口味与我完全相反。我不太爱喝牛奶,偶尔喝一下全然因为内心的理性——觉得牛奶对健康有益。我早晨一定要喝粥——出于感性的喜欢,且要就着咸菜喝。但出了丹阳就几乎见不到咸菜了,就像出了丹阳就不要奢望酒店能有大麦粥一样,所以只能就着别的什么炒菜或榨菜喝。因为菜不同,所以那粥也全然没了就着咸菜喝时的鲜美感。对于大麦粥我也很喜欢,但尚无对咸菜般的执念,有则更好,没有,红米粥、杂粮粥甚至白粥我也能接受——只要有咸菜——当然,没有的话也只能作罢。事后想来,对于粥与咸菜的执念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这种执念会让人失去知觉上的客观。应该如对大麦粥般,拿得起也放得下方好。吃完早餐我去酒店前台问乘公交是不是一定要投币(想着如果要投币那我得准备些硬币),前台说不用,手机支付宝里有个乘车码,公交上都能刷。于是放心地牵着女儿跟着导航去站台乘公交。很快坐上了公交,没过多久便到了孔望山。进了检票口不久便见道旁有几个卖水果的大妈,柚子、丑桔、石榴等都有。我见那红柚不错便买了两个,准备带去给龙洞庵的仁湛师父尝尝。我与女儿先是去大殿和偏殿拜了诸佛,然后仁湛师父便过来了。师父微胖了一些,脸上仍是一副仁厚安详的样子。师父笑着领我们去她的住处坐。龙洞庵已于2016年重修过,师父搬到了2016年初我来此小住时供居士们暂住的一间房内。师父将室内的两把小椅子让给我和女儿坐,自己坐在了一个树桩凳上,我推辞不过只能坐下。然后师父便为我们洗杯子、煮茶,又将两把扇子递与我们扇——那日连云港的气温达到了31度,据说那温度在连云港算是高温了。我问师父目前庵中有几位修行师父,师父道现在有六个,但其中三个小师父去读佛学院了。我问那三位小师父多大年纪,师父道十八九岁。我有些疑惑,问师父她们是先学的佛学专业然后来寺庙中的,还是先来的寺庙后再去读佛学的。师父说是出家后才去读佛学的。我很惊诧,她们的父母家庭能赞同吗——毕竟世俗中对“出家”二字还是忌惮的。师父说她们的家庭都是信佛的,所以会将孩子送来出家。我想起师父曾告诉我她与另外两位常住师父也是十几二十岁便出家了——因为家中信佛,于是我不再觉得讶异,只是羡慕她们。师父道她是1987年出家的,一晃竟过去这么多年了,今年她都五十三岁了——她1969年出生的。正与师父漫无目的地聊着韵洁的电话便来了,说她已到孔望山。于是辞别师父,师父便起身送我出去。走进院子,师父指着角落里的一个房间说,那会儿你住这个房间。我说是的,感叹师父记性真好——我不过是万千个来此小住的平凡居士中的一个而已,她却还记得。见到韵洁时我们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激动与客套,似乎两人日日相见,这只是平素相见中的一见而已。我向师父介绍了韵洁,师父简单问了几句家常后我们便从龙洞庵辞别师父出来了。我们往山上走去,孔望山仍似我记忆中一样安静,无多少游客。但我记得适才师父说这十一期间人比较多,平常很少有人来。如此看来这真是个清修的好地方——不似江南的寺庙、景区那般人声嘈杂。与韵洁边走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期间在山顶上坐了会儿。回到山下已是午后一点多,韵洁说去吃饭吧。我其实不饿,但估计她和女儿已饿,于是坐上韵洁的车去往市里。由于我与女儿都吃不了辣,女儿也不太吃海鲜,韵洁照顾我们娘俩的口味因而选择面很窄。纠结了半天,便去了家日料店。虽然不太喜欢二战时的日本人,但除开此民族仇恨,对于日本的饮食及人文我还是喜欢的——日料清淡、简单,日本人自律、严谨且追求整洁。吃完午饭已近三点,正好吃饭所在的综合体内有家影院,三人遂去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看完已是晚上六点。韵洁的先生打来电话,说准备了晚饭,让我们去吃。我有些哭笑不得——刚吃完午饭3个小时,又吃晚饭了。晚饭仍然是照顾我们娘俩的江南口味,点了一堆南方菜:蛋黄虾、腰果虾、清蒸淡水蟹、鸡爪、红糖糍粑等。韵洁说胃不舒服,几乎一口没吃,她先生也只吃了两三只虾和两只蟹。他们五岁的儿子由于和我女儿比赛吃虾有了乐趣,倒是吃了几只虾。因为午饭吃得晚,所以我尽管心里不想浪费而努力吃但也吃不了多少,最后剩了一大堆。事后想想,他们不吃大约是因为他们吃不惯南方菜。果然,过了两天我跟韵洁说我不愿再与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太铺张浪费了,点那么多菜,吃不完也不打包带走,她告诉我平常他们吃不完也会选择打包,但那天的菜即便打包回去也没人吃,所以只能任其浪费。看来是我太一厢情愿了,总觉得不吃辣的人对于辣菜无法入口,而吃辣的人对于不辣的菜甚至甜味菜虽然不太喜欢但至少是可以入口的,没想到大家的喜忌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海上云台
10月3日,我与女儿依然是睡到近八点方起床,依然是女儿比我先醒。由于已向韵洁声明不要她来陪我,所以饭后我与女儿便不急不慢地按照既定日程循着导航乘坐公交前往海上云台。海上云台2017年我与妹妹一家去过一次,风景很是不错:站于山顶视野辽阔,心旷神怡,放眼望去山下海景一览无余;而那云台山腰上竹林掩映的悟道庵则更是幽静非凡,一直让我神往。悟道庵之所以让我神往,除了那处所幽静之原因外还有另外两个缘由:一是2017年我们本无心去悟道庵,也根本不知道那儿有个庵,完全是无意间经过那里时我无意一抬头撞见了不远处那写着“悟道庵”三字的山门。我走过去又回过来细品那三个字,心中隐隐似有所动——悟道庵——悟道——道不可言,得用心去悟,方能了悟。那一瞬间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通透感。第二个缘由是当我心里怀着那点恍惚走近悟道庵时,见庵前一碑上记载着此庵的来历——为一名为“了空”的法师所创建。2016年我行皈依之仪时,师父赐我法名“妙莲”,我说我已为自己想好了法名——“了空”,师父应允。虽然法名如俗世之名,重叠不稀奇,但我心里仍恍惚觉得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到达海上云台时已是中午,检票处不让游客再进,称里面人太多了,疫情防控要求不得再进。我说我是几天前就在携程上预订的票,理当是计划内的人数,说了半天方准我们进入,但告知我们不得坐观光车,只能徒步上山。徒步便徒步吧,正好运动一下。开始时路的坡度不大,后来便越来越陡了,我的腿上像灌了铅一般越来越沉重。手机显示气温只有三十度出头,但时值正午,我们又一直走动着,所以觉得酷热非常,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想来我真是低估了连云港的气温,以为毕竟这儿地处苏北,加上入秋已久天气应该不会热,所以给自己和女儿准备的都是长袖长裤,不承想这么热。一路上我与女儿走走停停,停下来便坐在台阶上吃几口柚子(柚子是前一日出孔望山时在山下买的),喝两口水,女儿间或吃几口零食充饥。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个简易的背包,每日她背自己的一瓶纯净水,我则背我的一瓶水和我们备用的一瓶水,以及点心、书,所以两天下来女儿算是帮我分担了不少分量。我是吹一吹台阶上的灰便坐下来,女儿则非常讲究地将她的简易背包垫在屁股下。我欣喜于这小姑娘总算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坐着时常有蚊子来叮我,女儿便帮我驱赶,甚至帮我拍打。我说赶走便是了,别打死。女儿说蚊子是害虫,得打死。我启发女儿道蚊子吸我们的血我们便觉得它们是害虫,那我们还吃肉吃蔬菜吃各种东西呢,对这些我们吃的动植物而言我们算不算害虫?女儿道,我们又不是虫子!唉,到底还是个孩子。讲得太玄乎了于她的成长似乎也不太好,顺其自然吧。等她长大了,也许就懂了。到了悟道庵已近两点。悟道庵是我此行连云港的目的地之一,我想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这座古刹。走进庵中我与女儿拜过诸佛,后行至院中。一个着便装的年轻女孩赠予我们两份柚子,称是供果。我道谢后虔诚接下,不禁想起2017年我与妹妹来这庵中时的情形:那日气温不似今日这么高,很是凉爽,游客也不多,一位年约三十的僧尼安静地立于院中看着我们微笑,佛珠在她指间移动着,当我和女儿跪拜完准备离开时,那僧尼拿来一只苹果,微笑着递给我女儿。两次相似的赠予际遇让我又一次心里一动,想着我与这里有着怎样的一种缘分。我与那着便装的女孩聊了几句,得知她也是居士,假期来这庵中帮忙。我问她这庵中有几位修行师父,她说不一定,常住的有两三位,又道平素这儿没什么人来,这几天人比较多。这话与仁湛师父很是相似。而在我看来,这两天这两座寺庙的游客其实都不多,只偶尔进来几个,可见平素更为清静。我们辞别那年轻居士出来,见庵前那两株千年古银杏仍繁茂如旧。我回头再看那座用石头筑成的古旧小院,忽然觉得出来得太仓促了——那院中景象我似乎并未看得很清楚,于是交待女儿在庵前等我,我复又返回庵中。我立于那院中细观,不自觉地想象自己长住于此的日常景象。再次走出悟道庵,我便去寻那“了空碑”,来回几次竟都未寻到。是改造过了吗?我心中疑惑,不禁若有所失。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日龙洞庵、悟道庵跪拜时我没再教女儿如何施礼,但眼角的余光瞥见女儿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然后循着我的方式跪拜。心中很是欣慰。与女儿走到候车点,问售票处此地离云顶还有多远,答曰还有五公里多。女儿嚷着说她爬不动了,我们坐车吧。十里路,我也爬不动了。于是买了半程票,售票员提醒我一般要等四十分钟到一小时。等就等吧。果然,一辆又一辆满载的车子从我们跟前驶过。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他已经联系了一辆车,马上就来。等到近三点半方来了一辆空车,专程来接这半山腰的二十来个游客。没一会儿我们便抵达了山顶。不知是不是因为气温高又疲惫的缘故,山顶的风景似乎没了回忆中的空旷与辽阔。我看着山下的港口,映入眼帘的尽是颜色各异的集装箱和储货建筑。我不禁想象着,假设没有这些箱子、建筑,这山下的海滩该是怎样的一副样子。应该是天然之美吧。韵洁问我几点下山,她又约我一起吃饭。我说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市区,让她别等我。她让我别急,她等我。好说歹说方打消了她要等我一起吃饭的念头。我与女儿没吃午饭,竟也不觉得饿。期间女儿在山上吃了一根烤肠,然后我们又一人吃了两小袋奥利奥。与女儿坐着景交车回到山下时天已快黑了。我们循着导航去找公交站台,半天才找到——其实景区出口处便有站台,而我没发现,多走了一站路。抵达站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打开手机电筒照了下站牌,见末班车是18:30,而彼时是18:10,方放下心来。两人站在黑漆漆的路边看着公交驶来的方向,半天也不见车来,我想大约得18:30才有车来了。我问女儿累不累,女儿说累。我忽然想起动画片《龙猫》中那姐妹俩在雨夜里等巴士等来了大龙猫的场景,觉得很是有趣,遂讲与女儿听。女儿也看过《龙猫》,遂与我开心地谈论起来。谈笑间公交便来了。我与女儿坐到中转站又转BRT,近八点方抵达市中心。女儿仍惦记着馄饨,于是去了酒店边上的一家馄饨店。问了下,果然没有大馄饨,只有小馄饨。于是要了一份肉馅的和一份鲜虾馅的,又要了两只油煎蛋和一份水煮花生米。女儿惊讶于馄饨汤中竟有小虾米,我告诉她因为连云港在海边,这里的人喜欢吃海鲜,所以汤里会放虾米。因为打定了主意想体验简单的生活,所以几天下来多是公交出行,也不像以前一样与女儿出入人均消费上百的精致餐馆。我已多年未坐公交,女儿更是几乎没坐过公交,但她即便是在人挤人的车厢里拉着吊环站着也不叫苦。好不容易有个座位,我让她坐下,她却问我累不累。我问她开心不,她总是笑着说“开心”。但站在人挤人的车厢里时,我仍不免想象着:假设我们以后的生活模式都持续这样,我能不能忍受。肉体似乎能接受,但心里也许会在意——在意他人看我与我的孩子的眼光——这个红尘世界终究是喜欢以物质为标准将人分作三六九等的。然而回头一想,这样的生活虽然看似低微,但只要自己不去攀比,其实还是自在的——拼尽全力地挣着违心的钱,换来看似富足的物质,内心何曾有过宁静的享受?吃完饭回到酒店,洗完澡,我决定把这几天的衣服洗了——堆了太多的衣服,又每天出汗,到时将这一大堆满是汗臭味的衣服塞进箱子带回去,心里终究是不太舒服。四楼有洗衣机、烘干机和熨斗,可以自助洗熨。顺利洗完了衣服,又烘了四十分钟,衣服已半干。我将衣服抱回房间时方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那么多衣架来晾衣服。于是电话问前台,前台说今日客满,所以没有多余的衣架,如果不是客满可以将没人住的房间里的衣架拿来给我用,次日她会帮我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衣架。我只能将薄一些的衣服两件摞在一起晾,将所有空间都用上方勉强晾完。整理完一应事务已是半夜十二点,女儿已熟睡——我出入房间几次,房卡拔了几次她都没醒。女儿哼哼着,我担心她是要小便,遂将她喊醒去上厕所。我看着她温顺、绵软的样子不禁觉得可爱,遂笑着跟她说妈妈衣服洗好了——她此前说怕,要跟着我去洗衣服。她迷迷糊糊地说啊,你都洗完啦?这几日都是十二点睡,因为白天步行累了,所以闭眼即睡着,睡眠质量空前的好。
连岛
10月4日,女儿七点半照例又醒了,照例又是看着我咯咯地笑,说我像猫咪或睡虫之类的话。我让她别说话,翻过身去继续睡。直到八点,我们方起床。去餐厅的路上经过布草间,我见里面有个阿姨在,遂问她有没有多余的衣架,可否借我几个——我见不远处的柜子上有一摞简易衣架。她拿了六个给我,我说能不能再给我几个,我前几天没洗衣服,昨晚一下子洗了很多。她便将那摞衣架全给了我。我道了谢,说我吃完早饭来拿。吃完早餐去取衣架时,另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三楼拐角走到底可以晒衣服。我以为是个大露台,心想我的那堆衣服今天可以全部晒干了,于是欣喜若狂道太好了。遂去那拐角的尽头看了下,没有大露台,只有一个室外楼梯,楼梯旁有两根铁丝,那大概就是那阿姨说的可以晒衣服的地方了。可以晒衣服就行,我已很满足。将那摞衣架拿回去晾衣服,竟然刚好够用:这几日的袜子因为是每天都洗,所以多数已近干,不必占用衣架拿去室外;同时因为内裤也是每天洗,又放在洗手间的通风口吹,所以也已半干,可以用夹式的衣架一个架子夹两条。晒完衣服韵洁就来接我们了。我们准备去海边,她说她也想去海边玩,我说如果她真想去玩那我们就一起,但如果她只是为了陪我或开车送我,那就作罢。她说她是真的想去海边走走。我们从服务中心坐上小火车,小火车绕了几圈后停在了离检票口不远的停车场。韵洁带着我们步行到大沙湾检票口,只见那儿人山人海,都在那儿排队检票。我已提前几天买好了两张成人票——因为携程上只有成人票买,且不贵(只需23元),估计现场的儿童票也差不了几块钱,所以干脆买了两张成人票。韵洁有年卡,所以不与我们一个通道检票。站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爸爸抱着个皮肤黝黑的一两岁的小女孩,妈妈站在边上。妈妈正在吃着一根包着巧克力的奶油冰棍,小女孩看着妈妈急得哇哇大哭,边哭边拿小脚在爸爸的肚子上蹬着。妈妈大声地说你不能吃太多,我帮你吃掉点。妈妈很快将那冰棍咬得只剩了最后一小块,然后递给孩子。孩子赌气扭头不要——嫌那冰棍剩得太少了,仍在哭着,但没过两秒钟她就扭过头来从妈妈手上拿过了冰棍,然后吃了起来。但没吃两秒,那仅剩的一小块冰棍就从那棍子上掉了下来,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一滩白色的汁水。女孩又哇哇大哭了起来,再次拿脚蹬着爸爸的肚子。妈妈拿过女孩手里那根空空的棍子,随手扔在了地上。我皱了皱眉,看向别处。终于轮到了我们检票了,我拿出ErWeiMa给检票人员刷,她却只刷了一张票便让我和女儿都进去了。女儿身高已近一米五,按规则肯定是需要买票的。我将此事说与韵洁听,她说她们这儿就这样,孩子身高超一点都不会让你去买票。说她前几日去上海迪士尼,她儿子身高还差一厘米才到买儿童票的标准却非要她买票,说如果在她们这儿是绝对不可能要买票的。我笑着说那是连云港人醇厚,在苏南或上海可不是这样——前两年我女儿身高一米三八,电影院规定儿童一米四得买票,非要我女儿持票才能进入。海滩上人很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全是花花绿绿的人,全然没了2016年初我只身来这儿看海时的空旷和寂静。女儿非要下水。出发前我原本准备了泳衣泳帽等装备,但一想带这一堆东西坐公共交通实在麻烦,而且这已经是国庆了,海边应该也冷了,所以临行时又放下了没带。不承想这儿这么热。没泳衣,只能与女儿挽起裤管下水。韵洁说她胃寒,不能下水,说她在岸边帮我们看包和鞋子,让我们放心去玩。女儿拿着韵洁在停车场给她买的网兜,学着赶海小视频中的样子在水里捕鱼虾。可此时海边除了人便是满地的人造垃圾,哪有鱼虾。海水涨潮了,水位越来越高,我们的裤管也浸湿了,只能退到岸上。我看着海滩上遍地的矿泉水瓶、废弃口罩、用过的儿童尿不湿,心里感慨万千。我将此景及检票口见到的一家三口的情形讲与韵洁听,韵洁笑了笑,说有时也不怪人们看不起那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我说是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素质都高,但高素质的概率会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些。事后我想我这也是佛家所谓的“分别心”了,其实人们的言行可能与受没受过教育无关,而与人心有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会制造垃圾,甚至由于他们收入相对高些,因而购买力也强些,所以他们在享受物质后制造的垃圾会更多,只是他们会将垃圾扔到指定的点罢了。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垃圾还是产生了。人啊,真是一群祸害万物的害虫。因为连岛这边人太多,所以我们准备沿着海边栈道前往苏马湾。在我印象中那海边栈道沿途的风光是很美的。但没走几步我们便发现栈道入口关了——在维修中。我和韵洁说要不我们回市区吧,我们去看电影。韵洁说好。于是我与女儿便赤着脚拎着鞋子去找洗手间洗脚穿鞋,可一路都没找到。韵洁说拿矿泉水冲下脚吧,地上太烫且硌脚,我说不要——我不想浪费饮用水,觉得那是罪过,而且难得有光脚走路的机会,正好让孩子体验一下。路边有很多海鲜餐馆,韵洁说要不进去洗一下,但我嫌那些餐馆地上油腻不愿进去。最后想想还有好长一段路才到停车场,不得不进了一家餐馆去洗脚。我们到达市区时已四点。韵洁带我们去吃了疙瘩汤,而后去看了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看完已19:10。韵洁说去吃晚饭吧。我笑着说五点吃的不是晚饭?这一场电影的工夫又吃了?我反正不饿。韵洁说她也不饿,可孩子饿啊。我问女儿饿不饿,女儿说饿。我说你这么一会儿工夫又饿了,是嘴馋了吧?她笑了。小孩子总是分不清嘴馋和肚子饿的不同。韵洁将我们送到了酒店边上,将车停下来,从车里拿出一盒凤鹅非要我带回家。我说不要——一则我每次来她都极尽周到地招待我,还让我们带一堆东西走,我实在不好意思老这样;二则此番前来我本着“极简”的宗旨,所以不愿拎东西;三则我也确实不爱吃那烤鸡卤鹅之类的东西。但她非要塞给我,我趁她不注意拉开车门将那凤鹅放进了她车子后排的座位上。临走前她又交待我不要去买土特产,她会帮我买好,明天她去送我。我说不要她送,但她执意要送。好吧,这会儿说了也没用,明天再说吧。回到酒店,收回上午晒出的衣服,发现衣服已全部干了,很开心。洗澡,收拾东西,照例又是忙到近十二点,女儿照例已睡熟。
归程
依然是八点方起床。这一天我们没有游玩行程,所以很是放松。我梳了下头发,漱了下口,洗了下眼睛便与女儿去吃早餐了。我与女儿都没换衣服,直接穿着睡衣去了餐厅——因为想着吃完早饭后就呆在房间里不出去了,省得来回换衣服麻烦。当然,我们穿的睡衣其实是有袖子、胸前带卡通图案的家居服,不是吊带裙或带碎花图案的真正意义上的“睡衣”。女儿从动画频道里找到《龙猫》,调出来看,我收拾完也凑过来看。两人坐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吃前一天晚上韵洁走后我们从零食店买来的坚果,很是自在。看到近十二点,我们拖着行李去退房。退完房我将行李寄存在了前台,只在女儿的简易背包里装了两瓶水,准备背着那两瓶水去看电影。可是一看影讯我想看的片子时间都不凑巧,只能作罢。于是跟女儿说要不去步行街上走走吧,女儿说好,两人便去了步行街。两人在步行街上从最东头走到最西头,又从最西头走到最东头。看看时间一点出头了,问女儿饿不饿,女儿说饿,于是找了家日料店点了份牛肉饭和一份豚骨面。我一点都不饿,所以只吃了几口;女儿大约也并不十分饿——上午她吃了很多香蕉片,所以也没有吃多少。韵洁没有找我们,因为我前一日便跟她说次日我们自由活动,我想睡到自然醒,让她别找我。吃完午饭,一看时间已午后两点,我们是近四点的火车,所以决定去火车站。在去火站前,我们又去零食店买了两袋栗子,准备带回家给家人尝尝——那味道很不错。不到两点半,我们便抵达了火车站。看着那“连云港站”四个字,我觉得陌生而亲切——我上一次来这车站还是2004年来办转学手续时,一晃竟过去十七年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十七年前这车站的样子了,只隐约记得从苍悟路来车站需要经过解放路,解放路两旁栽满梧桐,与南京的老街很相似。公交一路过来,我特意留意着路边的路标,发现自己的记忆没错,果然要经过解放路,解放路两旁也果然是梧桐成荫。这两日与韵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很多,聊的多是2004年前的事。昔日不喜欢的那些人和事而今聊起来竟已没感觉了,只觉得好笑,甚至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人生可不就是这样,身在其中时总觉得那快乐和痛苦如天一般大,包裹了你的全部情绪,而当你跳出那情境时会发现那些快乐和痛苦其实根本不值一提。我与女儿很快进了站,然后我便给韵洁发说我们已进站,让她别来送我们,人很多,我们进出很不方便。她说怎么这么早就去车站了。我说早来早安心。她说也好,保重。18:43,火车准点抵达无锡。我向仁湛师父报了平安,而后便与女儿乘地铁去往堰桥,先生已开着车在那等我们。原本他说要去火车站接我们,我说地铁很方便,何必绕去火车站接,还没地方停车。到了家中,晚饭已摆在桌上:一盘炒鸡蛋,一盘韭菜炒青豆子,一份油焖虾,一碗丝瓜青豆鸡蛋烫。韭菜、青豆大约是婆婆从老家带来的,虾估计也是公公做好的。我将菜拍了张照片发与韵洁,告诉她我已到家,准备吃饭了,让她看看我们这儿的口味。她道,开眼了,每个地方的吃法还真是不一样。
往期精彩↓↓↓
【精彩散文】毛琴芳:监考
【精彩散文】郦金兰:一位能干利落的妈妈
【精彩散文】郦金兰:一位能干利落的妈妈
【精彩散文】王晓明:误入冬季的海棠花
【精彩散文】吉浩源:书窗秋暮
【精彩散文】陈建华:俄罗斯掠影
【精彩散文】钱建军:桂子花开
【精彩散文】章晓兰:不虚此行
【精彩散文】朱娟娟:独驾的感受
【精彩散文】蔡竹良:太极锁芳华
【精彩散文】王晓明:喝茶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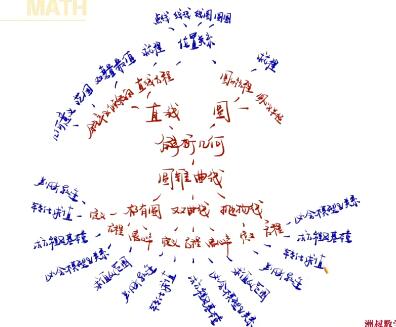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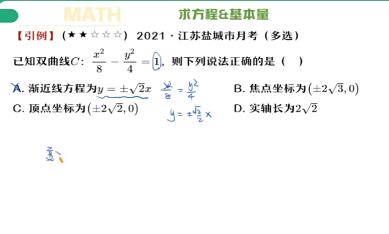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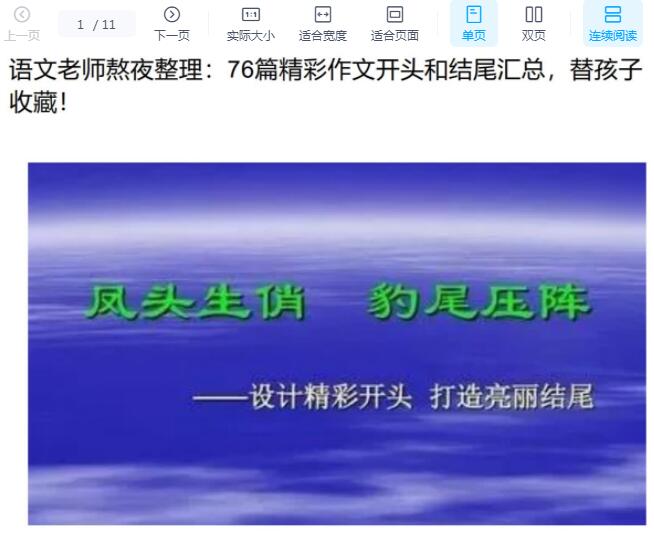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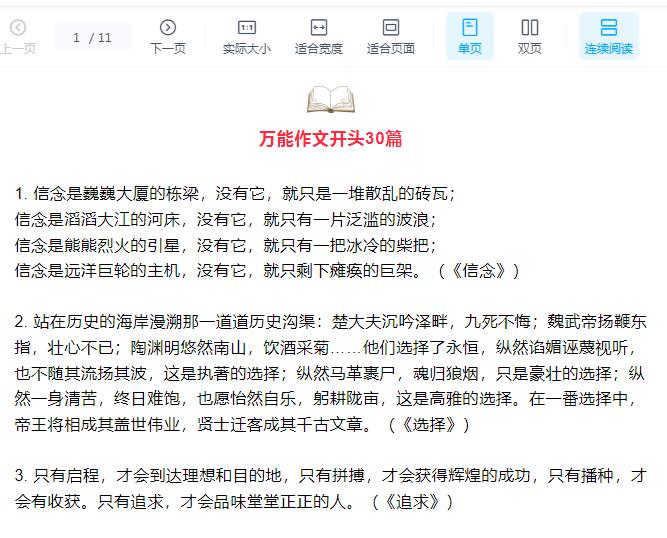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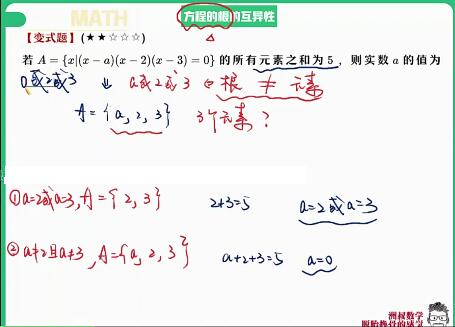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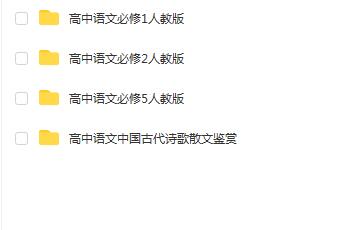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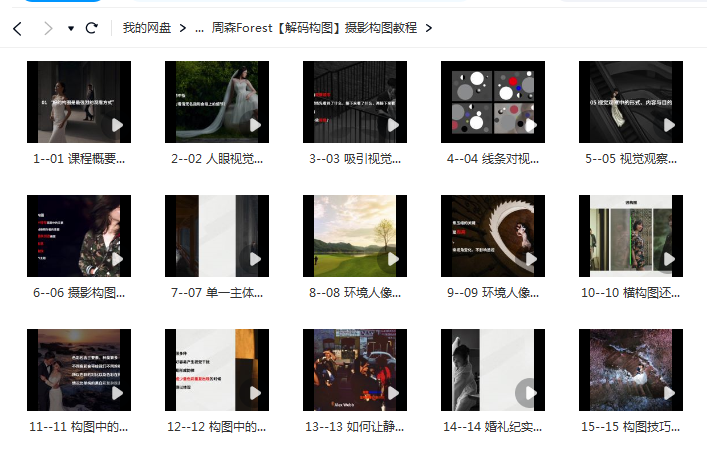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