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6期(总第481期)|卡伦散文|彭意辉 (湖南)| 那条鱼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06 11:52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6期(总第481期)彭意辉(湖南)散文那条鱼




主 编:梁冬梅
本期编辑:丁万良
那条鱼
彭意辉(湖南)
记忆的火炉里,那条鱼已烤了四十多年了。但一直没有烤熟,它早已成了记忆里的鱼,成了我的记忆,也成了不再消失的故事。

一、记忆
说起鱼,你不会陌生。草鱼、鲫鱼、鳊鱼、鲤鱼、游笔子、黄Y鼓、桂鱼、财鱼、麻脑壳、瞎抛子、千年老、万年任,至于泥鳅、鳝鱼、脚鱼、乌龟等等。生活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的人,不用去解释,也不用去把这种叫法换成书面语。都晓得哪种鱼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
过年了,我们家家都有鱼。
过年的鱼是:年鱼、鲫鱼、财鱼、鲤鱼。当然有桂鱼更好,但那桂鱼是非常稀少的。
关于鱼,你一定要懂:鲤鱼音通礼鱼,过年有鲤鱼,是表示在新一年里都文质彬彬,讲礼貌;年鱼呢,这鱼就音余,表示年年有余;那么鲫鱼,财鱼呢?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它,连起来就是:年年余积财!
过年的时候,到我们农村来做客,饭桌上一定会有鱼。你若爱吃鱼,劝你不要去吃鱼头与鱼尾,过年的鱼头鱼尾是不能吃的。吃了,亲戚朋友家是不会高兴的,因为那是农村人的一种希望:希望一年到头,有头有尾,办事有始有终。
时至今天遇上过年,当然是不用顾忌鱼头鱼尾不能吃了。但若是在别人家做客,还是忍住嘴巴的快活为好。
烤了四十多年的鱼,没有烤熟,那是记忆的犹新,没熟,不能吃,那是童心不灭,少年的不老!
四十多年了,那时的:人民公社,大队部、生产队。供销社、粮管站、肉食站、邮政所、兽医站、木站、卫生院、代销店、打米厂……,还在眼前象放电影一样声音影像俱全。
那时候,粮田是队上的,沟渠,水塘,队屋…都是队上的。
只有自家的土砖茅屋子,茅屋子屋前屋后不大的地方才是自家的。屋前屋后的树木就是炮桐树、鸭婆子树、腊树,桔皮树,土地刺树,桃树还有楠竹,青竹,水竹,是自家的。其它沟塘边的毛桃树,杨柳树。谁栽谁扦谁得利。

杨柳树一到春天,扦插技条,很容易活,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活,它不怕水淹,也不管环境,生长速度快。二年就可以劈下枝条做柴烧,再过四五年又可以做家具,也可以做水车的车叶子,所以很受农民喜爱。
我也很爱杨柳树,先不说唐朝诗人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单就那杨柳菌,就让你回味无穷,一直充满少年的乐趣。寻杨柳菌,爬树,用枝条撮高枝处的杨柳菌,那都是寻柳菌、摘柳菌的喜悦。杨柳菌是一种很好吃的美食菜,那清香野味的鲜美,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春天来了,捉哼蛾,这也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哼蛾最爱附在桃树、杨柳树、桔皮树、土地刺树的腐烂处,它们愛吃这上面的东西。在这几种树上寻哼蛾是不费力的,很快就能找着。哼蛾捉来后,就偷一些大人的鞋线,或缝衣线,拴住哼蛾的一只脚,拉住绳子的另一头,然后放飞它,让它使劲的飞。看它,听着它的叫。等它飞到没有劲了,一头栽了下来,不停的发着哼哼声,挣扎不停,心里才似乎觉得高兴。一天玩到天黑,在大人的喊吃晚饭声里,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第二天天亮,只要不下雨,又约上小伙伴去捉。有时候,也一个人去捉,自玩自乐。直到读书去了,作业越来越多了,不知不觉中就再也没去玩哼蛾了。当然那时哼蛾被玩断腿,玩死的也有不少。
好几年的春天都是捉它玩。小朋友的那种玩法,哼蛾不死不伤是不可能的。
但最惨的还是臭屁虫,只要被小伙伴们遇上了,就会直接搞死,棍子打,泥巴坨活埋,那是惨不忍睹。这大概都是臭屁虫,臭的缘故。碰了它,没碰它,都感觉它臭。偶尓也有男孩拿它来吓女小伙伴,也有女小伙伴拿来吓男小伙伴,相互取乐。有时候有的女小伙伴吓哭了。应该不是吓哭了,是被那臭屁虫臭哭的。臭屁虫弄到身上,只能用小棍子或小竹枝等挑开,不能直接用手去捏或手打,那样的话,手,身上与那臭屁虫接触处,会臭上好几天。
不管是真哭还是假哭,到了第二天,大家又笑到一起来了。但是,那臭屁虫早就不幸了,被搞成粉身碎骨了。
玩了一天的小伙伴,屁股、脸、身上都处都脏透了,从头到脚就只剩那滴滴溜溜的眼睛了,活像八卦炉里出来的孙悟空。

我们六、七岁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穿的衩裆裤,地也是泥巴地。下一场雨,那泥巴地是很久都是湿湿的,用来揉泥团,办饭饭席,那是最好的。
我们常常把这不干不湿的泥巴做成泥巴碗,锅,杯子,用小树枝做筷子,学着大人的样子办席面。把小伙伴扮成一对对新婚夫妻,搞得有模有样。大家也都愿意,一天换了他,一天又换了她,总是那么不厌。当然也有做了夫妻,还想做的,也有做了,第二天要跟另外一个做的。都可以,只要有人相互愿意做,我们就做得更起劲。假装的吹锣打鼓,假装的席面,一直在笑声里存久。
泥巴地,若是干了,出太阳了,地上的泥灰有寸把厚,稍微在上面跑动,尘土飞扬。小伙伴们都不怕,不管男女,偏要在这泥灰多的地方玩。一屁股坐到地上,那还有什么肉屁股喽,全是小灰菩萨了。
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不会怪你,只是把你抓到水塘边上,一顿好洗,在嬉嬉哈哈中,赤身裸体,转回原形。大一点的小伙伴回家后,就象哪咤闹海一样,在塘里翻江倒海,(不用担心淹死,农村里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早就练出了哪咤闹海的本领)不一会儿,就洗出清秀面目。
夕阳西下,余辉照人,喷香的饭菜早已好了。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呵斥下,三下二下就吃完了饭。吃完饭,又秀气地玩一会,上床睡觉了。

夜里脸上的微笑,很快地迎来了新来的天亮。
那时候,最广谱的小吃零食是:红姜、瓜子、花生、红薯烫糕、红薯片子、题完几,但这些对农村的孩子来说都是稀罕货。不管城里、农村、山村。那时候能把肚子吃饱的,农村里的孩子就是吃野菱角、鸡灵Y、藕肠子、藕。那是可以尽情的吃,每次可以吃到肚子撑破。只要自己勤快,自勤自食,没有人说你不该的。山里的孩子呢,经常吃紅薯,听说吃得要哭呢,差不多天天吃红薯,吃到他们心生厌恶,一听又吃红薯,还想作呕。
环境不同,交通不便,走亲戚,农村的到山区去,搞几个红薯到农村,我们当成宝贝。曾记得父亲说过要找个山里媳妇,多半是有些爱那红薯、花生;当然山里的人应该也是相反的想法,他们渴望农村的生活。总之都想自己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
那时候几角钱的红姜、瓜子、花生,有些小伙伴能吃上二、三天。给小伙伴们吃,红姜是撕得象线条一样的,有时搞一点点,几乎连眼睛都看不见,也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还要用舌子舔下嘴唇,有时连接过姜线的手也不放过,也要放嘴里舔一舔,生怕还裁落了点点灰灰。
瓜子,花生是一粒一粒的数着发给小伙伴们吃的。当然能吃到这些东西,那关系的好彼此不用说的,都是好得很的小伙伴。当然这好得很,今天可能是你,明天或许又是另外一个小伙伴了。小时的小伙伴任何时候,那是不可能好到天长地久的。小伙伴们的脸也象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有好玩的不一起玩,有好吃的不给吃,变得快,更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不过都不要紧,没多久外交关系又搞好了,好到鼻子眼睛笑到一起。小时候,桔子罐头、油饺子、胡椒饼、猫耳朵、发饼都成了小伙伴炫耀的食本。
玩耍的时候,吃了小伙伴的东西,你千万不可以得罪他(她)。如果有一天,若是闹僵了。小伙伴会当众马上提醒你:某年某月某日,给了东西给你吃,给你玩。而且是反复提醒,或者是哭着告诉你。那一会儿,将是你前所未有的尴尬。你也无力的反驳。说:下次吃东西还给他(她),还没有还,一段时间后谁也不记得还没还,只有天爹爹晓得了。好多年后其实也不要紧了,只是在每一个人的成长中,数十年坚定地告诫自己:再也不要吃别人的东西,玩别人的东西,哪怕是最好的朋友真诚给的东西。
虽然今天时常遇见小伙伴,或者旧相识,我也没有再听听他们谈起过这些儿时,光屁股的事了。
但彼此相遇时的惊讶:应该是都记着了从前,要不又会是一刹那间的人流擦肩,彼此又消失在人流的烟幕中。
那瞬间停下的脚步,加个电话,添个。存留着那份彼此的时光,但又谁曾想到,这些又彼此成了空设。因为彼此那少得可怜的拨通与聊微早已作了说明。不要问原因,你也懂。若不懂,那是你所走的路还不够长,再长点,你会比现在懂的人更懂。又一段时间,不拨不微,早已丢失在手机角落里多年。通与不通,早已不知道那个号码是否在还是不在了。
我记忆火炉里的那条鱼,也正是这样!不过那条鱼没有烤熟,我一直在烤,等着他(她)的熟和香!

二、趁戡与干塘
要想知道那条鱼,追到熟和香,才可以知道它的味!你就要知道趁戡。趁戡,你也不要去查字典弄懂趁戡的意思,更不要去查经据典,你是查不到的。只有到农村来生活,你才会知道。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等到七、八十年代的这批人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你就会真的不知道:趁戡了!如果不到农村来,又想弄懂那条鱼在趁戡里的来由。那你就只有耐着性子,看完以下的文字。其实看了或读了,对你都有好处:经历过了的人,你会更加珍惜还在过来的时光,会更爱自己的亲人朋友。没有经历过的人,你看了或读了,会知道今天你们的幸福生活就是在长辈们的日常生活中垒起来的,尊敬长辈,热爱生活,关爱他(她)人,不为私欲,更加勇往直前!趁戡,它是农村里的俗成语。说白点就是地方土话。嘿嘿嘿,咳咳咳,慢慢地喝上一壶茶,扶一扶戴在眼睛上的老花镜,摸摸干瘪的肚子,你就会知道:趁戡是什么滋味了。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趁戡一般都是在冬天。而且是每年的冬天,快要过新年了的那十几天,才能趁戡。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农村的人们才有空干塘。趁戡是不分远近的,只要你捕捉了信息,你就去趁戡是的。一般别队的人是没有时间来趁戡的,他们同样要忙自己队里的事。当然去趁戡是文明的,这是队里的权威人喊了趁戡,才去趁戡,才叫趁戡。如果没有喊,就去趁戡,那叫抢塘!抢塘是不文明的,未得到允许。当然抢塘是很少发生的。不过某段时间也多。抢塘公平与不公,那肯定是不公的,家里劳力多的,做好了准备抢塘,那自然是抢到的鱼最多,这抢塘,抢的是大鱼。就是队里干塘了,这鱼还未捞上去一半,或半把,鱼塘岸上准备或还没准备趁戡的人,在抢塘人的一哄而下塘的情况下,就都变成了抢塘。那形势一来,就象上了战场一样,不管男的、老的、女的、少的、只要不是残疾,或老到不能动,幼到不能走的,能下塘的全部上了。那管什么寒风刺骨,冰块凉心,那抢塘的热火全然没有半点冷。(抢塘的人,也大多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偶尔也有邻队的人抢塘的,)抢来抢去,就这样塘里的鱼很快就抢完了。

干塘,必定是忙完了冬修。我们小时候的农村,一年里就是:一春修,春耕生产,秋收,冬修,那是年年都非常 热闹的事情,也是全国人民热火朝天的日子。要不然,如今的大垸,小垸,农场,宽广的堤子,都是那个时期的长辈们用肩膀挑出来。
临近过年了,冬修也忙完了。男女劳力都回来了,于是,架起水车干塘捞鱼过年。那是每一个生产队必干的大事情。
队上的干部、社员,齐心协力搬的搬水车,扛的扛锄头,耙头,一同去架车车水。
那时候,队里是没有抽水机的,连养鸡养鸭养猪的都非常少,一年的粮食都吃不上一年,左借右借,黄花菜,白菜苔子拌饭,红薯煨饭、鸡灵Y蔸子煨饭,那都是不错的美餐。一年四季就靠些野菜淌了过来。干塘是农民生活的迫切需要。
干塘,看热闹,这也是小朋友最爱的。可以干塘了,水里的鱼儿在干了的塘里做猛的乱游,时而溅出一梭的泥水,鱼嘴不停地开合,随着塘干水浅,塘里的鱼更加惊慌得乱游乱蹦.
干塘这个时候,在冬天里冷得要命,手脚拿出来就会冻得不晓得知觉。而且只要一下雪,那山川河流,就成了《沁园春.雪》一样的美画诗章。沟塘里甩泥坨,泥坨会在沟塘的冰上滑很远很远。如果下一日一夜的大雪,雪就会有六、七岁小孩子衩裆深。
越是下大雪的夜,小孩子越不会怕,想着耍戏,打戏仗,堆雪人,还生怕下雪不够大,生怕天亮得慢。
那时候水车,车干一个塘的水,三台水车同时也要三、四天。车干一个大塘,那更需要多些天。有时候队里吩咐轮班车水。
车水也是一种技能货呢,没有本事。:你是根本无法去车水的。 车水最怕的就是:“吊麻鬼"。“吊麻鬼”那是时有的事情。队友与队友之间,时常是喑里比赛。这车水搞不好,掉下来了,不残也受伤呢。但那时,沒有人因此变残废,他们都是技术能手。
“吊麻鬼”.“吊蛙公”在农村那也是最让人笑话的。车水搞不赢了,双手就牢牢地抓住水车架的横杆,双脚悬空,这就是:“吊麻公”了,吊了“麻公”,不要慌,也不要急,让那几个水车上的英雄狂蹬几下水车就没事了。因为他们一边笑,一边蹬水车是坚持不了二分钟的,马上就会没劲了,停下来。这时候,“吊麻鬼”的人,趁机顺势而下来蹬水车,又可以以一胜三呢!就这样又有队友“吊麻鬼”,“掉蛙公”(这钓麻公,就是用一根小木棍或者小竹棍,都可以,用绳子绑住小棍子一头,绳子的另一端系一小坨棉花,去钓青蛙,青蛙一伸嘴咬住,就会被钓者,钓起来,钓起来的青蛙,那一瞬间,四脚无靠,乱蹬乱踢,样子很滑稽。车水落空,也正象钓青蛙,故而农村把车水脚落空,叫做“吊麻鬼”或“掉麻公”。青蛙爱叫,也爱蹦,又时候,一不小心,吓人一跑,所以农村的人就把它叫作“麻鬼”,或者“麻公”,绿色的青蛙就叫“绿麻鬼”),笑死人。
“吊麻公”惹出的一次又一次的笑声,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忘记了疲劳。让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小朋友,也跟着傻笑,有时也跟着呐喊,助威着自己心中的明星。 就这样,水塘在笑声里,一寸一寸地干了。我们心里不忘的趁戡,嘶喊着明星们赶紧车水。

说到车水,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水车。农村的水车,有三种:一种是手车又叫手叉,一种是座车,还有一种是站车。
如果,你还不懂,有空的话,就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周立波作家的故乡去看看,那里有当年的水车,风车,打稻机,簑衣,扁担,箩筐……。座车,一般是两个人坐着车水,也叫夫妻车。
一段时间后,农村分田到户了,家里条件好点的就请木匠师傅做了座车。座车是要多耗些木材的。前面说过,农村就只那几种树,
这几种树有的重,有的弯曲,有的不经水浸,都不是做水车的好材料。那时木材稀缺,而且又要是农闲,河里涨水的时候,要排古老放排,到公社木材站拿到木材票,才可以买到木头,即使有木头买,你也没钱。所以不管何种水车,那都是很贵气的。最常用的水车就是站车,有三人站车,也有四人站车。
队上的水车,大都是四人站车,车水的也都是高手,队里专门选出高手,专门负责车水,白天,他们除了吃三歺饭,上厕所,晚上回家睡觉,基本上都是在水车上过的。因为队里的那些需要水的稻田,基本上都是他们车的水。故此,水车还有个迷语:一只黑鸡婆,带窝黑崽几,港子里来,港子里现,港子里埋,你猜是什么?不要猜了,这就是农村的水车。
农村的水塘基本都很深,有些有三、四米深,都是修堤护垸人工锄头、耙头、锹挖的,有些是挑塘泥肥挖的。那时候化肥是很少的,大部分是挖塘泥,腐草皮做肥料。水车农忙干塘用完了,就要冲洗干净,凉干,刷上青漆或者刷上桐油,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护水车的使用寿命。水车是农业生产的宝贝,是不能马虎的,大家都很爱护它。刷油也要多刷几次,如今这些东西早就成了不值钱的废物。不做用了,大部分都不见了。
那时候趁戡,大多数的小朋友是找根小竹杆,用细小的绳子绑个伞骨了做的钩子在小竹杆的顶端。看见了鱼就去勾一下,勾中了,就把勾到的鱼用树钩穿起来。会勾的,会钩一串树钩的鱼。这小竹钩只适合我们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钩着玩。

趁戡,那个年代,农村里的男孩女孩都一样,爱趁戡。
等到水车把塘里的水车干了,队里面的会抓鱼的就派上用场了,他们用网捞把鱼捞到箩筐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就一担一担地挑上岸来,放到宽敞的地坪上,负责地坪上的队员就提水冲洗上坪的鱼,活蹦乱跳的鱼在水的冲洗下,好多跳出了箩筐,但它们又象逃跑的敌人一样,被抓到箩筐里去了。等到水塘里面的鱼,被捉得只剩下些:盘皮弄公、小鲫鱼、雕子鱼了。队长就一声喊:趁戡了。于是木桶、木盆、撮箕、箢箕、戳箕、簸箕、筲箕、粪箕……,只要能抓鱼的精良武器都用上了。顿时,泥水溅飞,盘皮弄公,虾子鱼在无力地挣扎中进入了队员们的木桶、木盆、撮箕、箢箕……里。
“这里有一条财鱼,那里有一大鲫鱼”,岸上看热闹的大声叫喊着:“背后,前面,裤裆边”,喊声不绝。一波人顺着喊声,不管是真是假,迈着齐腰身的泥水,箭一般地冲过来,争抢着那财鱼、鲫鱼。当然财鱼也不是好捕的,它行动敏捷,刹又跑掉了。趁戡的人,随着又是一阵追抢,那斤来重的财鱼落入了一个人的筲箕里,被人抓去了。
十来分钟过去了,趁戡人们早已不是先前的人们了,个个都成了泥人,只剩下那两个眼睛眨啊眨,才知道他们不是泥塑雕像。干塘的岸上生起了几堆小火,那是队里做公事的几个人在烤火。
又过了四、五分钟,队长又一声喊:“开月口了!”于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挖开了月口,隔塘的冰水随着月口的破开,象洪水一样迅速奔腾而来。趁戡的人们,才感觉到一股直冷袭来,迅速护好自己的战利品走向塘岸上来。不可恋战,毕竟冬天里的塘水,不是闹着玩的,冰得要命,何况人,早已冷冻十几分钟了。
毫不留恋,随便洗下脚手,揣着那几斤盘皮弄公、小鲫鱼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回去了。偶尔几条大点的鱼都是在为逃命,藏到杂草,淤泥里,不想又一来一波象鸬子一样的趁戡人,无幸都成了他们手中的俘虏。
队长吩咐放水是必要的,因为来年的水塘里要有幸存的小鱼小虾,下年的干塘还要有鱼的丰收。
干塘里,一边放水进来的时候,为队里干塘的队员就冲洗箩筐,拆水车,把水车搬到下一个要干的塘去。
年轻的小伙子挑着最后的几担鱼,高兴地放到地坪上的鱼一起。
地坪上从起鱼的那一刻起,队里的长寿老者早就守在这里。
他们拄着拐杖,摸摸雪白的头发,在那没有了牙齿的笑声里,自言自语地说着:“好鱼。”
分鱼了,几个干练的小伙子协助着队长,会计的秤称着鱼。会计的珠算打得飞快!只听得珠子响过,象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那数就出来了。
按人口分鱼,历年来都是这样。鱼的大小等级搭匀,再按总斤两,人匀分,这是队里形成的公平,不论年长少幼,都沒有意见。很快鱼就分好了,家家各自拿着自家的鱼回家了。当然,队里的五保户,孤老都有份,有时候还特殊给他多分点好些的鱼。也有队员还送些自己趁戡的小鱼给他们,让他们煮黄菜吃。
冬天里,小鱼煮黄菜,非常好吃。黄菜就是把摘采回来的青菜:如白菜、萝卜菜、芥菜……,放刚烧开的开水里烫一下,就成了黄菜。根据个人喜好,有时让这烫菜在这烫水里久放几天,这时菜叶菜杆都变黄了,放出酸味来,这就是真正的黄菜了。
水车(水叉)干塘,抢塘,趁戡你也听了。分鱼,鱼煮黄菜已入了味。你似乎还在云里雾里,因为没有找到那条鱼。

三、鱼在哪里
那条鱼在哪里,在这里。
我家住在农村,我也生活在农村。父亲兄弟姊妹多。五兄弟,八姊妹,父亲最小,自然排行老满。母亲呢,平起平坐,兄弟姐妹八人,排行老四。你也不用笑,不用哇地惊叫。那时候父亲母亲的兄弟姐妹多,那是司空见惯的。就是因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多,小时候,才可以到处为非作歹,别误会,这个为非作歹不是那个为非作歹!这个为非作歹在农村是非常调皮的意思。何况母亲的娘家也就在邻队,所以调皮的活动空间那是相当大。迈出一脚,自己队,邻队那都是亲戚呀,即使有几个外姓在队里,那也都成了亲戚,婚嫁连姻呀。所以在外公外婆家的日子,那要用许多年做单位才可以表述。因此,那条鱼,也生长在外公外婆家的队上。
小时候的记忆里,自己队上干塘,趁戡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的,因为盘皮弄公看到的机会都少。倒是好几个伯母经常来我来借钱,借米,借布票、借粮票,伯父,堂兄砍我家竹子……的甚多。记忆里借的次数多,但还过来的非常少。关于竹子,还记得好几根竹子上我都歪歪斜斜刻过字;不经允许,不准砍我家的竹子。那时候,四伯父还笑着说:嗯,不错,晓得管家了。
父亲爱竹子,他种有楠竹,水竹,青竹。而且这三种竹子都长得特别好。屋后,屋旁长了三处,形成了三山。因为有竹,每年队上的人,邻队的人,来砍竹子的特别多。不过那都是白砍,对待砍竹子的人,父亲母亲都是笑脸相迎,时常是冬天有热茶,夏天有凉茶。毎每都是砍了竹子的人,肩着竹子一路笑着回去了。
当然小客也不少,那些都是我和弟弟、妹妹的小伙伴或同队,邻队玩得好的大哥,大姐,有时候也有同学。放学了,在我家竹山里玩爬竹子,翻竹子,那是个个练得猴精,比孙悟空还灵变。小客砍钓鱼杆那也是不缺的年岁。
自爱自选,选正那一根做钓鱼杆,就砍哪一根,随他们。有些小伙伴一年要砍好几回。
有了竹子,做趁戡的挂钩,那就容易多了。当然这也只是十来岁左右大的,甚至还大一些孩子的一种调皮玩耍乐趣。真能钩很多鱼,那是少得可怜的。
不过,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小男孩基本上都爱搞这个。由于年龄小,个子不高,干了水的塘,下去趁戡,那等于是毛爷爷带领红军过草地,淤泥淹没头。何况,那时的冬天结冰,树枝都可以冰断,所以搞根小竹杆绑个自制的伞骨勾在上面,钩塘岸边的小鱼那是常有的事。
我也不例外,也爱这个,求这个小伙伴,那个大哥哥,好不容易弄了根雨伞骨,象李白遇见的老奶奶铁棒磨针一样,经过几天的磨砺,把伞骨子磨出了钩尖,再把它插到门缝里或铜锁里,才好不容易做成了挂钩。做成了竹杆挂钩,那就是迫不及待的试钩了。烂鞋子丢到堤坡下,试着去钩,还蛮行,十有八九中。现在想来,不中也不行,那烂鞋子又不会跑,小竹杆又刚好够得着。哼,最好还是钩真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快又到了一年的干塘时间。
那条鱼,想想,正好是我九岁的那年冬天。
那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都冷,不知是不是下过了几场小雪的原因,还是我穿衣服,穿得太薄的原因。后者应该不是,我比别的小伙伴穿得更多,而且还穿着父亲母亲给我新做的小棉大衣。看小伙伴们穿着单衣,光着冻得通红的小脚,我应该是不冷的。

干塘了,干塘了。小伙伴们用那冻得哆嗦的嘴,高兴地叫喊着。
我和几个小伙伴站在塘边一个小洲上,拿着那新做的小竹杆钩子,左一下右一下地划着竹杆伞骨鱼钩。
水车上,车水的更卖力,飞快地用脚蹬着水车。塘里的水越来越少了,大鱼开始露出来了。捞捕鱼的队员,抓紧捞鱼,挑鱼的一担一担运上岸。趁戡的群众紧紧围上塘边,捞鱼队员的抓紧防守,不时的用擅斗子装点淤泥撒向下塘而来的趁戡者,让那撒去的淤泥落在身边。其实这些趁戡者,不是别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堂客,崽女,伯伯,叔叔,堂兄堂弟堂们……,生人趁戡那是很少的。
忽然,淤泥撒向了我们这边,一些淤泥落到了我的新小棉大衣上。我生气了,把小竹杆钩很肩上一肩,跑到挑上坪的鱼堆旁,选了一条大草鱼,气鼓鼓地拖着它回家了。
把鱼拖回家,我一放下,就拿把刀把那鱼开起剖来。母亲在家打鞋底,听见有响声,似乎知道是我回家了。
马上就出来了,看见我剖鱼,问我鱼从哪里来的。其实不问也知道那鱼是从哪里来的,邻队干塘那么大的消息,又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我哭着说,是泼泥巴到我身上了。母亲没说什么,或许连我眼角挂上了眼泪都没有看,就拿起那条鱼走了,当然是送回原处了。
从那次后,任何地方水车,车水干塘,我也不再用小竹杆钩去钩鱼了,也不去看热闹,包括任何热闹。
随后来的日子是分田到戸,农民下海打工,闯荡江湖。我也随着父亲、母亲的工作迁动,一步一步离开了那远去的生产队;也随着读书一步一步进入高校学习。那水车车水的年岁,早已换成了电动水泵,水塘也分到了每家每户,干塘也不再有人去看热闹,那小竹杆钩与趁戡,抢塘,都随着岁月的装点……像那粉身碎骨的臭屁虫一样消失了。那条鱼在母亲的仁德中变成“多味鱼”。

【作者简介】彭意辉,男,生于1970年1月,湖南益阳人。笔名东剑,又名十豆三先生。
◆卡伦湖文学是综合性纯文学平台,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题材作品。
◆卡伦湖的朵朵浪花揉着我们的情感和爱,卡伦湖的日出灿烂了我的梦,卡伦湖的星光月影有着唐诗宋词的韵脚,卡伦湖的美丽自然风光,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在这里犁田种诗,畅读大千世界,感受真善美带给我们的快乐,用文学点燃心中爱的火炬。
◆《卡伦湖文学》作品要感情求真,角度求新,视野求广,语言求美;坚守唯原创,唯精品,杜绝侵权,文责自负。
◆《卡伦湖文学》接受诗词(格律诗、散文诗、现代诗)赋、散文、微型小说、微型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其中,格律诗须符合平水韵、词林正韵、中华新韵要求。编辑部对投稿作品有修改权。
◆《卡伦湖文学》作品需原创首发,作品如已在其它平台发表,请勿再投,避免弹幕。
◆《卡伦湖文学》为非营利性平台,文章属于阅读分享性质,所有录用稿件无报酬。
◆《卡伦湖文学》投稿信息包括作品文本、作者简介、作者生活高清照片。《卡伦湖文学》使用的照片,除作者提供外,其它均来自网络,请不要和正文对号入座。如有侵权,请联系发布者删除。
◆《卡伦湖文学》稿件择优录用。来稿必须以word文档方式发送附件到专用邮箱。对话框只作文字沟通平台,一律不收稿。
◆《卡伦湖文学》微平台推出的作品,择优收录《卡伦湖文学》优秀作品辑,赠作者样书,不再另附稿酬。
◆投稿邮箱:klhwx2020@163.com;联系人:梁冬梅,:1310873197。
往期精彩
【卡伦湖文学】第329期总第(433期)||热烈庆祝首届“卡伦湖杯"华语文学奖征文大赛颁奖典礼胜利召开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58期(总第463期)|热烈祝贺《卡伦湖文学》创刊一周年专辑|主编寄语|贺词/贺诗/书法作品
【卡伦湖文学】梁冬梅(吉林)|远山的呼唤—读鲁奖获得者任林举报告文学《虎啸》有感(散文)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5期(总第480期)|卡伦散文|李凤志(吉林)| 拜水都江堰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4期|卡伦诗歌|蓝帆 (辽宁) | 我忧伤河南没有泪(外二首)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3期|卡伦散文| 郭勇卫(江苏) | 幸福的王小明——《事说师生关系》阅读札记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2期|卡伦散文|王忠生(吉林)| 木棉花开
【卡伦湖文学】2021年第371期(总第476期)||卡伦散文||甄春延(吉林)|| 学校生活往事
总顾问:王 强 傅天琳
凌鼎年 陈小青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曾令琪 赵培光
任林举 思 宇
马永辉 纪洪平
吴耀辉 李凤志
主 编:梁冬梅
副主编:赵秋实
编委会:赵秋实 李洪军
静 川许 放
高智敏 张丽艳
裴凯茹聂子明
方明元何桂年
马海洋
编辑部
主 任:赵秋实
编 辑:丁万良朱杰
朗诵部
主 播:芷 兰 紫 陌
沫非 夕 颜
暴新宇


纸刊支持:文学季刊《西南文学》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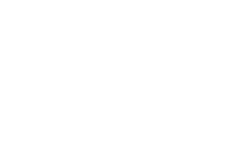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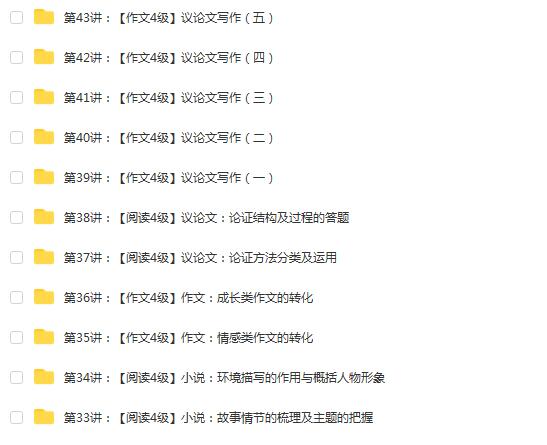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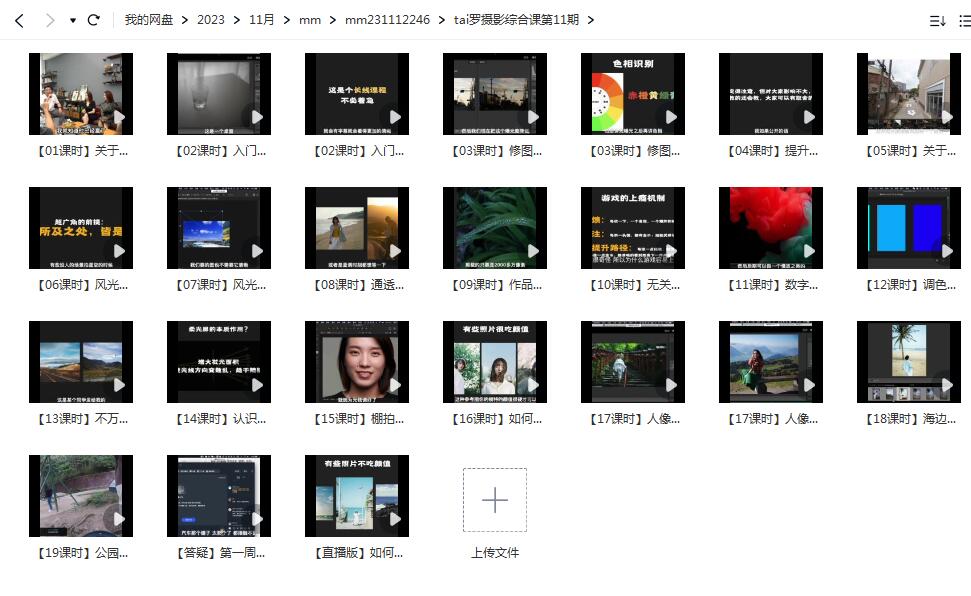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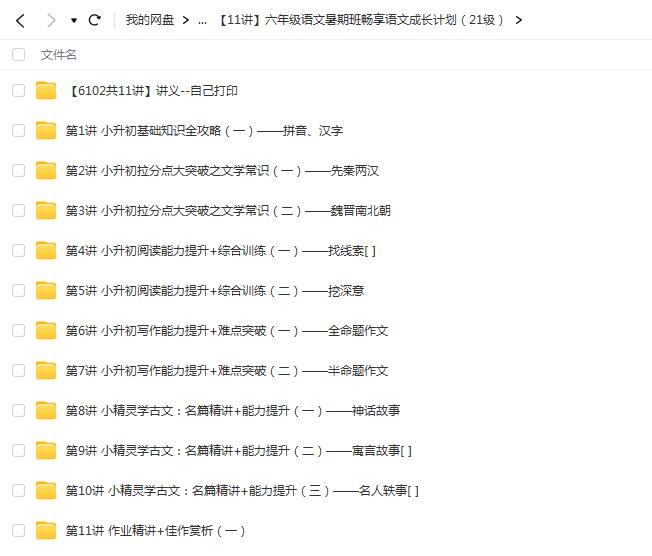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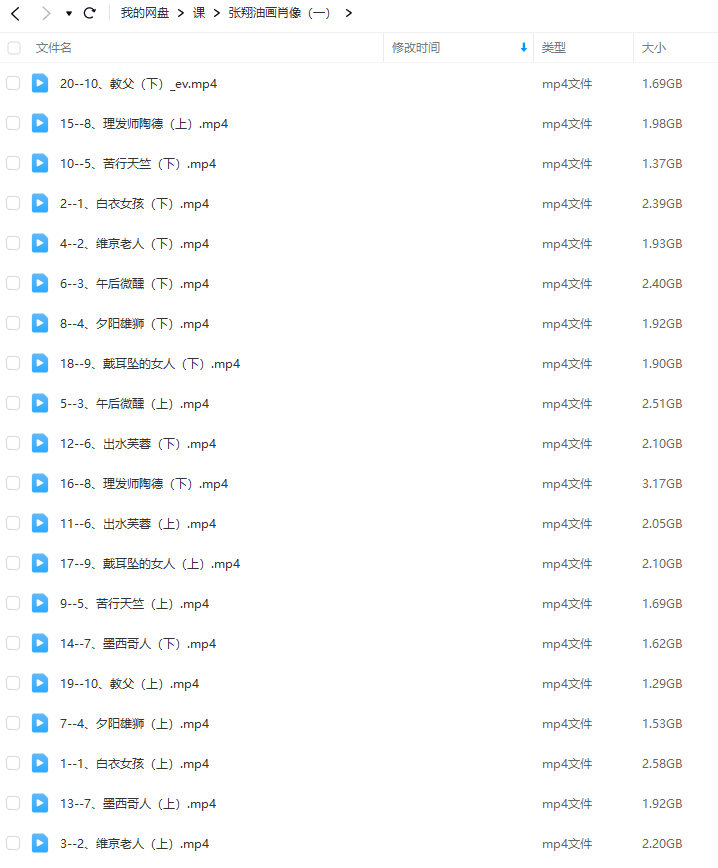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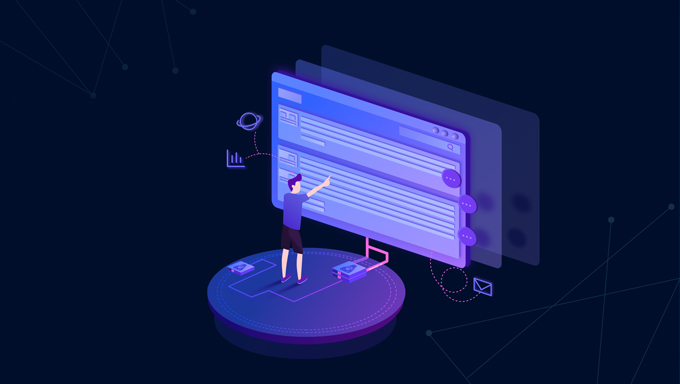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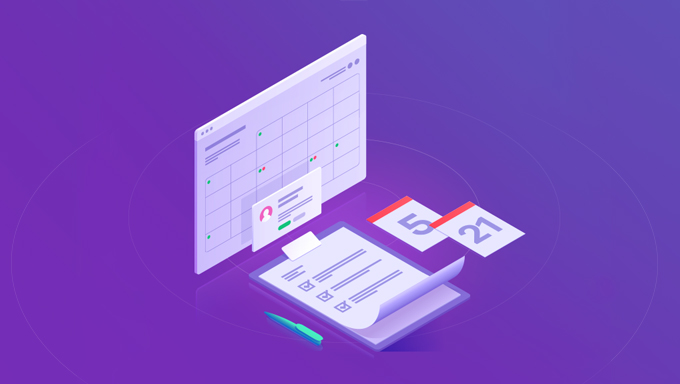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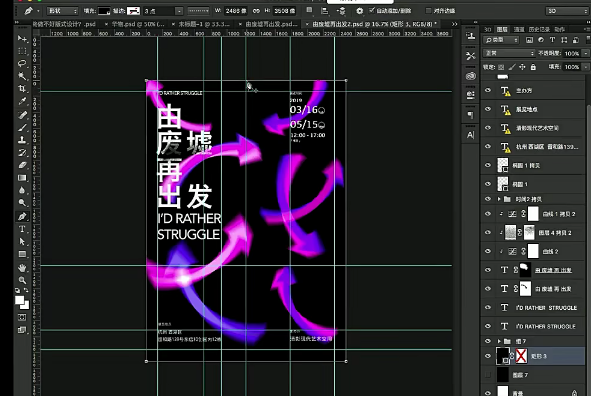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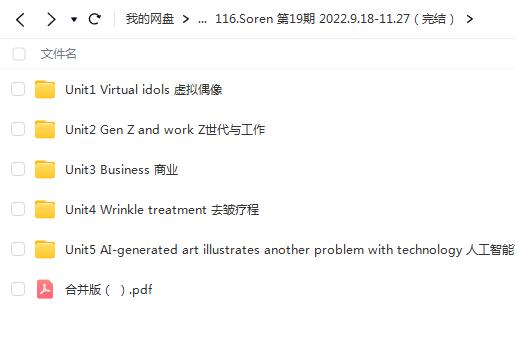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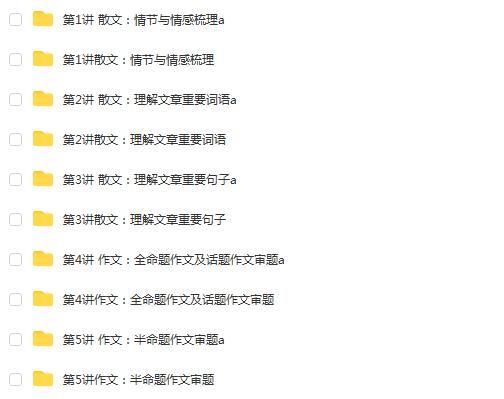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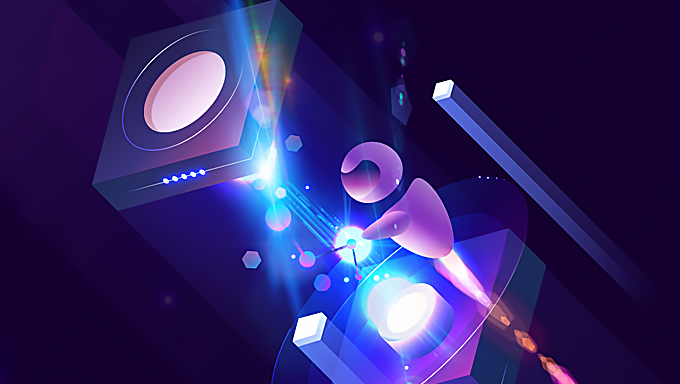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