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小城童年》(连载二十五)_语文阅读
发布于 2021-09-12 18:43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图:丰子恺
秋 天
秋天头来咧,弄堂里会有很多人家做新衣裳,晾晒棉花,扯新布料,箱柜底里的樟脑丸味道。秋风一吹,街巷仿佛又成了新的街巷。热天乘凉搁门板洗冷浴的痕迹被打扫得清清爽爽,夏天没有了,连同那些烈日下面赤着脚“咚咚咚”跑过的小人声音。我一觉困醒,发觉妈妈脸上神色快乐轻松多了,她再也不用为出门出汗,穿什么短袖子烦恼;而学堂又要开学。我开始想念学堂上课时金属的摇铃声音。学堂操场,靠围墙一侧全是梧桐树,我曾在哪段文字提到过,学校雇的摇铃的老太太,传说解放前是哪个大资本家里念过书的小姐。她一天八九次,替我们挨教室摇铃,已经是人老珠黄,一生未嫁的老处女,可她脸上总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严峻沉思,泄
露着她非凡的身世、乱世的经历。她用一只教堂用的手摇铜铃替学堂报时,精确守时如同一只西洋进口的老式自鸣钟里通过机械装置按时跳脱出来的鹦鹉。我突然发觉,我已经一个热天头没有看见她了。与此同时,我在学堂整整五年,从未碰见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也包括跟学堂成百上千的学生。她的出现就像一名哑巴……。醒在大清老早的小床上,想起她,感觉秋天就更加洇凉更加神幻莫测了。
江阴话说一年四季,从不说简单的“春夏秋冬”,也不说“春天、秋天”,而要在所有“天”字后面,加一个“头”的发音,头脑的“头”,变成“冬天头、秋天头、热天头、春晒头……”弄堂人家要做的事体,就更多了,碗橱抬到闸桥河里清洗。蚊帐收起来,床架,地板刷洗,老棉絮晒晒。去年的旧衣裳一件件摊开,看看还能不能再穿。家里老大的两用衫传给老二,老二的书包传给老三,都有一个新旧事物的传承。秋天来了,于是市井之间一套秘密的日常仪式庄重自如地展开,仪式的主题,有关成长、祖先、记忆和人性。所有小孩出门时,拍拍身上缀了补丁的衣裳,都要大大方方闻闻干净衣裳的味道,衣裳上往往也吸带上了所有家庭里那些针线储物抽屉甚至过期药丸的味道。因此,有一个星期左右,弄堂里全是穿两用衫、长袖,百货店的味道。在一阵阵风吹梧桐树声音里,秋天正像一个古老的戏班子,在小城的荒僻处上演如仪。
拆蚊帐时,帐顶掉落下来的没有被拍死的死蚊子,已经被屋里屋外的秋风吹瘪了,小孩子会看着那蚊子发愣。现实世界中,蚊子简直太讨厌了,总是一拍一包血,总是在你好不容易熬过暑热,快要入睡时在你额头耳朵边上“嗡嗡”飞近。听它不紧不慢的声音,它对自己的偷袭计划很有把握呢,除了你想拍死它时它惹出来的汗,在你眼前紊乱逃遁的小黑影,你对蚊子的印象全是断残、歪曲的。你身体上留下各种各样被拍打过的死蚊子的尸体、印渍,有时像一颗溅落的雨点,有时像一粒芝麻,剩下几根断肢……于是赶紧把它从手臂弯,从腿上抹去。然后,乍一看见一只只完整的蚊子尸体,就像博物馆里古代人的干尸,你惊诧自己看到了另一种更加秘密、不为人知的现实,跟夏夜中拍打死的那种蚊子的现实不大一样。这些干枯的蚊虫,看来死得那么忧伤、整洁,全部翅膀触须都蜷曲着,仿佛一个个做着好梦的婴儿……它们怎么没去咬着人就死了呢?或者,咬着了,飞回来躲在屋梁灰尘里暗自忏悔了?这种蚊帐顶上轻飘飘掸落的死蚊子,就像蚊子中的诗人,给人一种华美幽咽的感觉,但也很决绝。人家房间里巨大白色的帐子顶,成了它们自绝于人世时签署下的自白书,一份骄傲的遗嘱,专等我们这些秋风中的小孩子闹嚷嚷拥进来,骤然间撞见它们唯美的结局。我们咬了咬嘴唇,转过身来,秋天如此明媚温馨地已经在窗外,在妈妈喊我们的嗓音里。
落 雨
落雨落得地上的砖头地全变绿了,慢慢生满苔藓。落雨的天气里蹲在屋檐头看,小孩翘着屁股老半天不动那姿式,叫“孵”,形容像母鸡孵小鸡,十分相像。我小辰光孵在雨地里,天上打雷也不怕的。痴痴地看雨脚,看水花,看阴沟水慢流时的白皙,再看屋檐滴下的檐雨,颗粒要比露天的雨点略大,如同杨梅相比较杏子罢。有时在人家天井,在街边边上,竟看到一尾尾的小鱼,相约尾随,仿佛正欢喜于前方是茫茫东海。雨中的蝌蚪颇是常见,黑色的一尾尾,有时雨点被风一散,黑的蝌蚪身子竟闪出白亮。然后看砖头地上的青苔,想:雨落得快还是苔藓长得快呢?反正雨一落了,苔藓明显增多。整个院子、院墙、人家房前台阶,全被一层绿绿暗暗的砖头地光泽笼罩,使人好像再也走不出去。砖头原本就是有些旧年头的薄青砖,后来又逐年生长苔藓,你说绿到什么程度呢?雨到弄堂人家,全变成青绿色的了,这种境界,仿佛传说中的幽灵鬼魅最欢喜罢——鬼魂们全在雨中集体出行,额手称庆了。我这样孵在那里,慢慢地会觉得自己头颅很大,雨很大,天更大,大到头脑、雨雾、天空像混沌的三兄弟,亲密无间到分不出彼此——所以妈妈来喊我,屡次走到过道上,喊我来吃夜饭,可能喊给雨听见了,天空和我全无知觉,也可能喊到了我,没喊那些渣渣出声的入夜的雨,于是雨也不情愿,外面迷蒙的天空,就更不乐意了!我们中间总有一个,马上就沉下脸,不高兴起来!我仍旧继续孵着,吸一口气,把砖头的味道跟围墙味道,在嗅觉中区分开来。雨中最苦的味道是墙上扁豆藤,这种藤蔓,好像又名牵牛花,在小辰光北门人家院子弄堂,多到随处可见。开紫色花。想想,中上向没菜了,家里要靠它们捋一把来顺手做一道菜呢。难得一个夏天里吃到两顿以上扁豆烧肉,一般全是扁豆清炒炒,但放点酱油的,也放糖,味道喷香,正好配以一碗冬瓜海带汤。我想这是我小辰光夏天最理想完备的菜肴了。吃时,炎炎烈日仿佛仍在扁豆,冬瓜味道里存留着,久久萦绕不去。一直让孩子们吃到院墙、窗台、山墙上的泥土味道吃到干躁的冬瓜地里的暑气。但一场大雨倾盆,扁豆这种植物似乎不大性喜雨天的。我低下头,都能闻得见一名孩子挨打时嚎啕大哭;闻见小孩啜泣一样的扁豆藤的微弱气味,雨把这类,还有其他各种植物的气味冲走,又落回来,再冲走…… 形成各种繁复数不清的气味的秘密甬道,仿佛一瞬间同时有千百条河流在一个江南人家天井这么大的空间里交汇重叠……。万物生命,正通过雨的暗道蓬勃滋润着,不管哭丧着脸不乐意,还是像阴沟水里的小蝌蚪们一样欢天喜地;也不管我脚孵在那里孵到多么酸麻发胀。于是离开绿绒绒的砖头地,满脸满身凉丝丝的雨腥气——直到在夜饭桌上坐好,像个呆人一样拿了筷儿一动不动(想来我大概跟天空一样阴沉着脸呢),耳朵才忽然火烧火燎刺痛起来。原来,再三喊了不听之后,妈妈才忍无可忍一把耳朵将雨的干儿子一样的我揪到里屋去了。一家人全坐好了,哥哥已经闷头扒了小半碗饭,并且吃掉了一只面筋塞肉。父亲面前仍旧竖一张当天——1969年或1971年某日——的《参考消息》。父亲只订读这份报纸。1977年圣诞节后,我就是从这份报纸一小块豆腐干文字上念到我心爱的银幕大师查理•卓别林去世的讣告的。有一段时间,父亲还读《文汇报》,继而《解放日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全放弃了,家里再也看不到上述两种大的报纸,只有版面小一号了的《参考消息》,因此,落雨那天,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只看得见黄黄电灯光下他坐的位置有一张超现实的竖直的报纸,就好像报纸也有腰身,两只脚,可以站立,行走,端坐下来。不管怎么说,我的目光突然被饭桌子对面那版正对直我的报纸标题吸引住了。父亲的形象,使我暂时忘记了耳朵疼,妈妈的愠怒,并且从大雨倾盆、苔藓生长的神奇现实中走出了一步,走到了今夜此刻。我有没有真正坐在那张饭桌跟前,和我的仿佛古时候人一样的家人坐在一起?时至今日,他们全去了哪里?如果我伸出筷儿搛菜——那盆引起我食欲的面筋塞肉还真的在吗?父亲座位上的《参考消息》上的黑体标题,写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不再能够复述甚至——瞪大了眼睛看见?比方说:“中苏边境苏联军队集结……”,“印度旁遮普邦数年干旱导致灾民万人游行”这样真实时间中的文字?
——而文字、雨、童年、古老的家庭,这一切全真的存在,真的有过的吗?
电影院
弄堂口出来是厕所,厕所再过去是电影院,然后才是卖熟花生和瓜籽的摊点。这些摊点通常在水泥砌的售票窗口靠外面一点点,紧紧围绕着窗口附近东张西望的那些准观众。那些年放映的电影寥寥无几,观众却很多。一个月里大概只有四天电影院里大门畅开。全是礼拜天什么的,而且还是在夜里。除了革命样板戏之外,放映的片名稀奇古怪。有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有朝鲜电影,惟独没听说过后来满天世界的香港电影或好莱坞大片。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其实肇始于一部记不大清片目的电影;这座城市的巨变也起始于电影院门口开始有小人书摊。开始铺浇上水泥或者开始有外地(比方说:安徽)人摆摊卖瓜籽。更早些时候电影院门口是没有瓜籽卖的,没有什么炒熟的香喷喷的葵瓜籽。只有标语和墙上宣传栏里的告示、枪毙人的布告什么的。只有一大片的烂泥地。城里年纪大点的都叫电影院那块地方叫“荒场”。这是由来己久的习称。人们都在那块荒地上聚集。冬天泥泞遍野,夏日里尘土飞扬。但是县城范围思想和体格活跃一点的人士仍旧习惯了晚上纳凉时自发聚集到这里,一段时间以来把电影院这个地方弄得像是未及命名的广场或是某处学校的操场。不明事理的外地人初来乍到,还以为是轮船站呢。可是又没有轮船,长江航道也远在十几里外的港口。有一天,他们来说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已经被拍摄成电影了,快要来县城公映了。又有一天,一个古怪的电影片名开始频繁出现在市民们嘴边上:《巴士奇遇结良缘》。公正一点说,变化是从另一部名叫《桔颂》的香港电影开始的。流行歌曲、邓丽君、两喇叭四喇叭的录音机之类走私或舶来货品还是后来的事情。一部讲述古代诗人屈原的香港片。我甚至闹不清是影片中的插曲还是电影名字就叫《枯颂》,总之,外面大街上的生活开始流动、变幻,如同河流被缓缓解冻,人们脸上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表情。《巴士奇遇结良缘》。什么叫“良缘”?很多人的眼睛为之一愣。“巴士”又是哪种古怪国家的产物?城里人有人读作:巴士奇——遇结良缘。有的读成:巴士——奇遇——结良缘。很多年过后,这座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挤在人群堆里轧闹猛的小伙子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老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回想起来,才依稀领悟读懂了当年在县城里显著的位置上张贴海报的这场电影的一部分朦胧含意。是的,“奇遇”!正是这个词。这个词,这场电影的片名的出现是一个信号,一场噩梦——噩梦中的噩梦——开始的漫长片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几乎没有“零食”这一说。市场、商店里根本没有现在的炒花生、瓜籽可买。只有逢年过节,人家家里才有瓜籽好吃,而且全是县城每家每户自己炒熟了捧出来的。政府不是反复提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深挖洞,广积粮”吗?甚至一开始还没有炒花生、葵瓜籽,只有炒蚕豆。花生瓜籽简直都是奢侈品!可是,有一天,或者不如说,在某一年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街头——尤其是电影院门口——开始出现随处可见的炒熟了的带壳花生、瓜籽卖,只要你有钱,你可以随时买来兜在手里剥了来吃,一天24小时,每分每秒,你手心里都有可能有吃在嘴里糯香糯甜的花生仁。于是县城大街上开始出现一批新的闲人,他们脸上总是挂着饥饿、渴念着的、梦游般的表情。他们的目光总是朝向街道两旁的小吃店、熟食摊,朝着电影院门口空荡荡的那块书写片名的大黑板或宣传栏。他们总是期待着一部不知名的影片可能的公映。他们的到来,或聚或散,使得电影院一带的空气发出饥肠辘辘的声音。他们茫然瞪视着前方。瞪视着电影院门前那几级年复一年残缺了的台阶。那些台阶仿佛是一种愿望实现了的幸福的标志。影片开映!那是多么神奇的时刻啊!偌大的银白色幕布,藏在楼座墙后神秘的放映机。胶卷的“格格”、“咯咯”、“滋滋”声。片头音乐、交响乐、开始。银幕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个雄纠纠的大字。或者“长春”、“上海”等电影厂家光闪闪的雕塑标志。大放异彩的感觉,黑暗的观众席上,观众们个个全像一棵棵闪电击中的树一样笔挺端坐,巍然屹立,一个个活着经历了闪电。
电影院每周放映一部电影。曾几何时,每月只放映一部,甚至同一部影片轮流放映,达半年之久。后来改成一个月四部。终于有一天,县城里的居民等来了如同外星球居民降临的某一个国家的影片,美国影片:《摩登时代》。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古老的市井百姓而言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在这之后,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电影全都陆续开始放映了,于是,又一个来自银幕世界的新鲜词汇成了新时代到来冉冉升起的信号——:“摩登”。这个词,如同前面谈及的那部“奇遇”字样的香港电影一样的令人费解,经久不衰而又耐人寻味。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新时代的开端。
国家的命运从一个词上面,开始改头换面。
弄堂口出来是厕所。
实际上,那些年里水泥楼板搭建的简易公厕在县城显著的位置,也就是如今说的中心地带并不显得太招眼或难看。厕所看起来很平常,也不臭。不算很臭。因为是一半露天的,敞墙式的,蚊子苍蝇多点而已。冬天头是一点也不臭的,底下粪池老早板结住了。就一天里的时辰计,只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弄堂人家倒马桶时段略臭些。你想想,那么多人家的马桶云集,一齐拎出来倒在粪池里,味道难免不堪些。每月的几号,环卫所定期有组织安排的粪车负责前来清理。把粪便挖出来运到附近蔬菜大队,或更远处乡里的人民公社,也算是居民为社会主义略作一点贡献罢。那时候弄堂人家的树多,天井和院子多,旧房子多。自然把分散在县城各处的厕所味道过滤掉了不少。我跑来跑去,从倒塌了的旧城墙一直到城里最古老的(北宋年间)宝塔院,脑筋过一遍:青果巷、庙巷、东平庙巷、火车弄、蒋家宅基、北门、南门、石子街、忠义街、涌塔庵……统共也不过十几家厕所,跟相同位置的粮站、混堂、煤球店数目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电影院侧门边上那家厕所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去的趟数太多。仅次于我家在北门丁家弄位置上那爿厕所了。
就式样和蹲坑的舒适程度,有句说句,电影院弄口那家厕所,还不及丁家弄那爿好呢。后者显得更为大方、宽绰,虽然蹲坑板上的泥浆、积粪、痰迹和各种垃圾呕吐物也一样多。记得那些年里的呕吐物、积粪、痰迹里往往夹杂着一些旧报纸,有些用撕下来的杂志盖住,有的粪便里露出一角生报纸,让人疑心起世界的终极问题,例如先有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
有几年光景,我甚至怀疑自己记错了。因为电影院里面本身有一家厕所的,在那个年代,往往也是除县委机关之外的县城最高级的拉屎的地方。对呀,为什么电影院内部有一家,电影院大门口一侧还会有一家呢?这从道理上讲不拢头呀!可是后来我又问了城里许多人,许多四十岁朝上的人,他们全都记得比我还清爽呢。比如厕所外墙有一侧是红砖头。比如敞墙式的公厕,男的能够听见隔壁女厕所声音。男女相隔的厕所中间一堵墙只有两米多一点高。再比如厕所顶上蛛网纵横的人字形梁柱……小便池里漫出来的粪便,地上堑着一块块的砖头才能平安抵达也干净不到哪里去的蹲坑板上……
你不记得啦?很多闹猛的电影观众暴满。很多人一看不到电影,就先抢占位置进来拉屎、边蹲坑边听听电影院里的声音也好,解解馋。电影里飞机大炮的声音,厕所里蹲坑的人也跟着一脸的英雄豪气……
你不会真不记得吧?电影院排队买票,队伍把男厕所的围墙一只角也轧塌掉啦!那是1975年,1976年的大热天?那是场什么电影?《甲午风云》!
“天哪——苍天啊!”林则徐在电影里喊。
——“轰”地一声,外面的厕所坍塌下来。
电影院进去阴森森的,左右两侧向下的过道,中间一大排位置。有着县城最显赫的建筑风格,又高又大的围墙,深不可侧的前台搭着巨幅的白色幕布。没有观众时这些幕布也会在梦幻似的空气里微微飘曳,一个武侠世界,一场不幸的恋爱,一次宫廷政变,格斗、战争、流亡、杀戮……随时会随观众脑后的高墙另一头迸射的一束光柱中粲然浮现。没有性别的灯光幕布,不计年代的黑暗。银幕世界诞生自两种绝然不同的因素:黑与白、光明与黑暗,现实和梦境……很多幽灵。观众的幽灵,银幕内心的幽灵和故事的幽灵在此汇聚。有着真实中的真实,虚空的虚空。一排排空旷无人的座位上拂起一股神秘的气流使得前台那一大块幕布微微翕动,仿佛朝向永恒世界微微掀动的嘴唇,电影的巨唇,一遍遍述说着人类的孤寂,男男女女,不舍昼夜。从亚洲到非洲,再从欧洲到南美洲……银幕上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脉,贴近辽阔一望无垠的潘帕斯大草原。画面上的东北军,不真实地贴上了义和团式的面具和旗帜,爱尔兰矿工、朝鲜武士、白脸的丹麦王子、修道院、精神病科医师、皮卡迪利大街雨中的间谍。据说他们手里的雨伞的伞尖是特制的,含有某种当场致人于死地的毒液。风中眼镜王蛇的嘶嘶声。丛林雨季。雨像一场场漫天大火席袭着战火中的亚特兰大城。更多的被挖成秘密地道的中国北方的村庄。更多的埋下去炸人的地雷。多瑙河上游漂下来的水雷,以及总是抽着烟的游击队员、南京大屠杀、中世纪欧洲的僧侣……全部人类的记忆仿佛历经了一场洗劫,电影胶卷的洗劫,无情的闪光,无情的黑影。人们看见,仿佛为了再次遗忘,再一次地经过那场哗哗泻落的倾盆大雨……
《甲午风云》放映之前一个月,我就晓得快要公映《甲午风云》了。以我当时十二、三岁的年纪,我已经早一个月得知了消息,那么那些满城满大街做父母上班的大人们,该是早上三个月、半年就晓得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晓得他们是如何闭得牢他们的嘴巴的。那个年代里这一类的消息传播得最快。除了过年国家供应的年货品种数量,例如:几斤鸡蛋,每户多少肉类,多少油,多少烟,豆腐百页券,粉丝券之外,就数电影放映的消息最得人心了。我记得那年的暑假快到了,我大概是初一的学生罢,学校组织去看的一场电影,片名我已经忘了,科教纪录片一类的。我们出电影院大门时照例乱哄哄。我们挤在大门口不肯出去,老师在跟影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交谈,我们本能地凑上身去,想偷听得点什么激动人心的小道消息。倒不一定是非要跟电影有关的,随便什么大人的事情都行。我被人群挤在外围,糊里糊涂什么也弄不清爽,突然一个声音,一个名词清晰地传出来,里面有很多嘴巴在说,在喃喃传递,只有一个同学的嘴巴朝准我,并且声音很响地大喊:
“——《甲午风云》!”
好像他是多年以后报纸上着意渲染的那名中奖者。
我至今仍记得他闪亮的、迷惑但近乎于狂热的眼神,一名夏日少年的眼神。就像他刚刚手掀帐篷,从正在表演的场面热腾腾的马戏团现场走出来,刚刚目睹了某个汗孜孜的奇迹。那奇迹的声音、形象、力量还停留在他稍显稚嫩的耳廓、眼瞳、呼吸之间。他晓得我欢喜电影(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谁又会拒绝自己成为银幕世界的宠儿呢?)。对于电影,他也跟我一样狂热、无知、兴奋。他说话时把他嘴里那一口呼吸喷吐到我脸上。啊,多么美妙的夏天!“《甲午风云》……”我喃喃自语道,侧过脸去,已经被身旁更多的同学挤轧到了大厅的侧门边上。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黄海上,在吴淞口,在广州外海流域奔突驰骋,鸦片战争,我们不仅一天之内知道了历史上有鸦片战争,我们还知道了1840年,1850年这一类古怪费解的数字。这是什么意思,表明了什么?以我们十一、二岁时的历史知识,比较有把握说得出口的人类纪元,或某重大年代的数字,第一要数1949年了。这四个数字仿佛是用铁锤洋钉敲打到了我们那一代人的脑袋瓜里,此外我们还知道1958(伟大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1951年(“抗美援朝”)。我们还知道中共成立的1921年。对1937年这个数字也不陌生,因为抗日战争(“地道战”)。此外,学上得好,书念得不笨的初中生还约略知道——最多了——点1919年,那是相对业余的候补知识,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剩下的,人类纪元仿佛就是从“19”这个数字开始的,从不晓得,也无从关心“19”之外的数字。因而,猛一听说一个什么“18……”宛如挨了一记当头棒喝!怎么啦?难道人类之前还有人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被蒙骗——我们受骗了!这不,现在来了个《甲午风云》!“甲午”这两字,什么意思?“鸦片战争”的“鸦片”又是什么劳什子?再一看电影:清朝人的装束,“顶戴花翎”,皇宫的华丽……看电影的同学们,仿佛全在各自的座椅晕头转向地梦游。那场电影,从此成了我少年时代乘坐的一架名符其实成功穿越了复杂隧道的时空机器。我仿佛一下子就脱离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重心,掉落到了一个全新而怪异的世界里——走出电影院时,我有身上的某些东西一下子长大成人的感觉……既孤独,又懵懵懂懂……走到外面马路上,看着那弄堂口的厕所,水泥砌的售票窗口,闻到平常熟悉的粪坑和老街味道,就像一个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茫然懵懂,觉得走路时候两只大腿也不听使唤了。马路突然变成了陷阱似的泥沼。放眼望去,县城停滞的空间景观仿佛突然被一道眩目的极光击中了似的。整个城市、年代、记忆、生活慢慢从街道中心开始裂开了,就像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艘沉船。起先,这艘巨大的游轮还在航行,但是突然间灾祸来临,意外发生了……总之,我身上某些东西仿佛被粘在了那场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的银幕上。同样的我,散场以后要走出电影院走到外面马路上去变得艰难异常。我吃力地加倍想一些问题,意识到一些问题。仿佛大冬天的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电影有意无意所暗示给我们的那段历史包含着的现实跟我生长其中的那种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钟表开始“滴嗒滴嗒”在我体内响起。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认为我们是史无前例、崭新的一代,我们是“红小兵”,个个肩负着某种“红色中国”的使命。可是,那天下午,在走出放映《甲午风云》影片的那家影院大门一刹那,我身上有一种超乎寻常,远比我自己更加伟大的心跳降临了,它在我胸腔里,在我身上,听起来那么清晰、深沉——我听到了真实的人类的心脏!

摄影:杨键
庞培 1962年生,诗人,散文家。1980年代开始写作,1990年代编辑民刊《北门杂志》。散文著作有:《低语》、《五种回忆》、《乡村肖像》、《黑暗中的晕眩》、《旅馆》、《帕米尔花》、《少女像》等。诗集《四分之三雨水》(台湾唐山)、《数行诗》(上海文艺),等;2005年发起并主持(和友人)“三月三诗会”凡十七届,“江阴民谣诗歌节”暨无锡“大运河民谣诗歌节”十二届。被誉为九十年代“新散文”代表作者。现居江苏江阴。
转载请联系后台
商务合作请添加:cstaozui


微店:按左下方“”
往期推荐

《少女像》 (连载)
《少女像》 (连载二)
《少女像》 (连载三)
《少女像》 (连载四)
《少女像》 (连载五)
《少女像》 (连载六)
《吹笛人之诗》
《到金沙江去》
《少女像》 (连载七)
《旅行的黑颜色》
《和鬼魅同在》
《蔷薇之舞》(外一篇)
《飞行棋》(外一篇)
《南游记》(连载一)
《南游记》(连载二)
《南游记》(连载三)
《南游记》(连载四)
《翘辫子的鲥鱼》
钱穆:八十忆双亲(上篇)
钱穆:八十忆双亲(下篇)
《小城童年》(连载一)
《小城童年》(连载二)
《小城童年》(连载三)
《小城童年》(连载四)
《小城童年》(连载五)
《小城童年》(连载六)
《小城童年》(连载七)
《小城童年》(连载八)
《小城童年》(连载九)
《小城童年》(连载十)
《小城童年》(连载十一)
《小城童年》(连载十二)
《小城童年》(连载十三)
《小城童年》(连载十四)
《小城童年》(连载十五)
《小城童年》(连载十六)
《小城童年》(连载十七)
《小城童年》(连载十八)
《小城童年》(连载十九)
《小城童年》(连载二十)
《小城童年》(连载二十一)
《小城童年》(连载二十二)
《小城童年》(连载二十三)
《小城童年》(连载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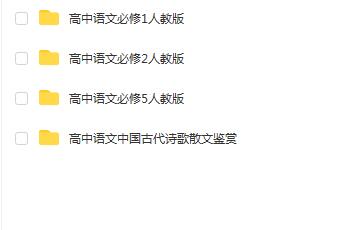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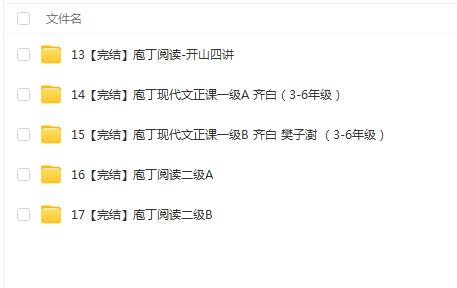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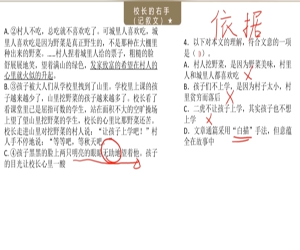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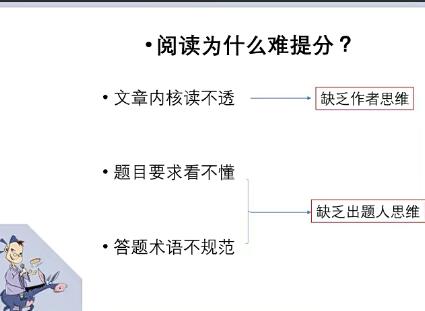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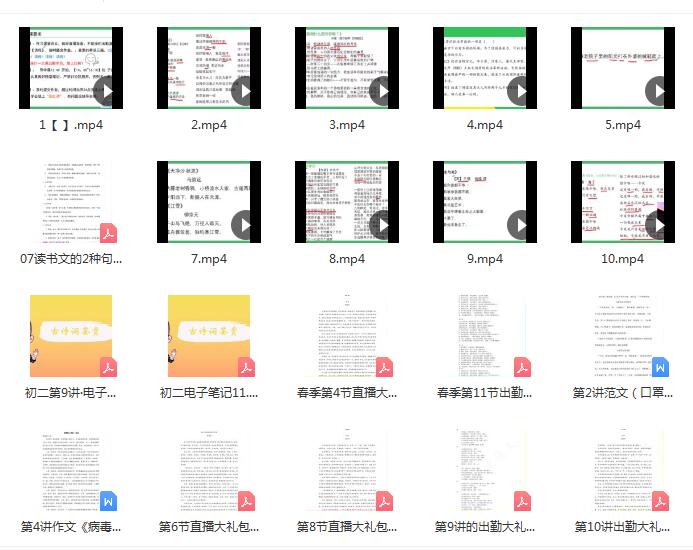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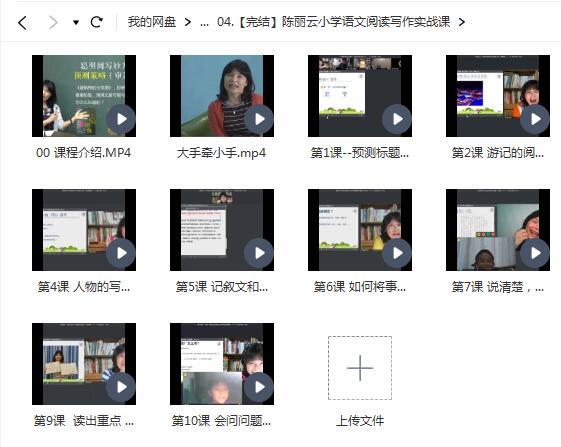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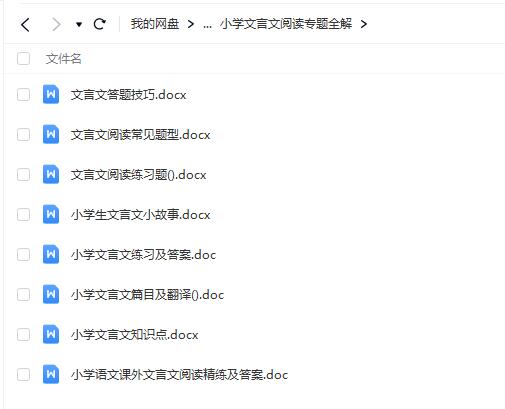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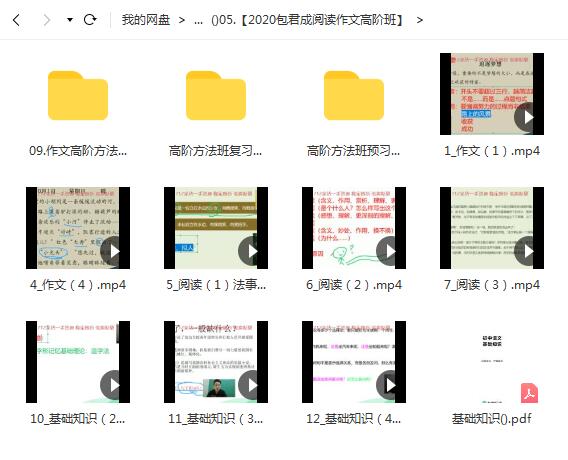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