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围城、无法超越的轮回宿命
发布于 2021-11-29 19:38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生的围城、无法超越的轮回宿命
—论夏目漱石的第二夜
冉秀
摘要:《梦十夜》蕴含着夏目漱石对人生存困境的各种思考。尤其是在《第二夜》中对武士悟道过程的描述,更是将人在生存过程中遇到的无法逃避的各种围城的、轮回的困境深刻地呈现给读者。《第二夜》中的“我”拘泥于自己的武士身份,想以此身份为原点参悟禅道,以期能缓解作为武士生存的苦恼。但是,在经过一番苦苦挣扎终于得以悟道的瞬间,“我”本能地再次回到以武士为原点的下一个轮回。夏目漱石通过梦境告诉人们:人在生存过程中,根本无法彻底超越自我,最终也只能是重复着一个又一个无法改变的轮回。这种人生轮回的宿命观贯穿于《第二夜》的始末也显示出漱石对人生宿命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第二夜;禅宗;悟道;围城;轮回
一.前言
《梦十夜》是夏目漱石应《朝日新闻》社的邀稿于1908年7月25日至8月5日连载在《朝日新闻》上的,由10篇描写离奇怪诞梦境的小说组成的短篇集。《梦十夜》与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1906)相比,在文体风格和主题意蕴上略有不同。《我是猫》通过主人公猫来观察人类社会。猫认为主人犯有人类通有的“胃溃疡”病,以讥讽的语调侃述人类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虚伪和敷衍。夏目漱石通过《猫》批评了当时日本采取抛弃日本传统文明,几乎全盘西学的风气,主张本国文明对西洋文明的合理吸收。这种主张在时隔一年后发表的《梦十夜》中也有所体现。但在《梦十夜》的10篇中,可以看到其中某些篇目的主题已经慢慢地发生转向,从人生存的外部环境转向人的内部。在《猫》之后《梦十夜》之前的1907年,夏目漱石辞掉了学校的教职,开始专职写作时曾经说过:“准备去除历年来积存的污垢”[1]。对于“陈年的污垢”,日本学者大久保纯一郎认为这是指作家开始放弃批判日本国家的西化思想,而将笔触转向人生内部的禅意识[2]。的确,这种禅意识体现在夏目漱石于1907年至1908年发表的如《文鸟》《坑夫》《永日小品》《梦十夜》等一系列作品中。尤其在《梦十夜》的《第二夜》中有很好的体现。《第二夜》通过“武士与禅”的原初矛盾来深刻揭示人类生存的种种“轮回”困境。
《第二夜》的大致情节是:武士久不得悟,去向师傅求教。师傅勃然大怒,认为武士觉悟性不高,否则不会不开悟。所以师傅怒斥他不配做一名武士。武士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中,继续禅坐悟道,他所坐的的蒲团旁边,藏着他的武士身份的象征—─ 短刀。他一面想着悟道,另一面却想着要不辱自己的武士身份。对于自己久不悟道,心中十分懊恼,但同时他又十分痛恨师傅蔑视自己的武士名节。为了证明自己作为武士也能悟道,他决心要在时钟敲响下一个钟点前开悟,然后再砍下师傅的人头作为自己开悟的奖赏。如果真如师傅所言不得开悟,武士决定以自杀来守住自己的武士名节。最后,在时钟敲响下一钟点的瞬间,武士正好进入“一切皆无”的“悟道”状态。但武士最终却悟道失败,他听到时钟敲响的那一瞬间,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手摸向藏在蒲团下面的短刀。
《第二夜》中看似简单的一个武士悟道的故事,却蕴含了漱石对人生存过程中的深刻思考。
对《第二夜》中体现的漱石的思想方面的研究,有学者从作品内容出发认为《第二夜》体现了“夏目漱石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扭曲现象的批判”[3]。武士最后的悟道失败,暗示了“日本不能盲目地完全西化,而对传统文化的不抛弃,不放弃。传统文化的回归,才能使日本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往正确的道路上行走”[4]。有学者试图将《梦十夜》放在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教中去解释作品思想。他们认为《第二夜》中的武士坐禅,一方面与夏目漱石自身的坐禅经历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释教文化的底蕴和释教美学的思考。”武士要悟的境界“无”,来源于中国唐朝时期的赵州禅师,本意是叫人放下一切,保持平常心。后来由王阳明系统为“心意知物”的“四无思想”,由此成为中国哲学的精髓。有学者认为《第二夜》中的这个“无”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是小说深部的潜在主题”[5]。日本学者也大多以禅道意识为视点来解释《第二夜》的作品主题。学者大久保纯一郎认为,第二夜中的武士悟道的过程,与夏目漱石在1906年至1907年到京都游历,在加茂禅堂跟着师傅学习打坐悟禅的经历有关。漱石将他在加茂禅堂悟道过程中的感悟投射到《第二夜》中。在探究漱石作品中的禅意的研究方面,马英萍认为,夏目漱石在作品中投射的禅意源自于他在《草枕》中表达的“非人情”的创作意识。其主要表达了提倡日本本民族文学创作[6]的思想。
梦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日本学者入江隆则在解释《梦十夜》时与前述大久保纯一郎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第二夜虽然难懂,但无不与夏目漱石自身的参禅经历有关。但在作品的内容安排上,武士悟道的最后时刻进入似悟非悟的模糊状态。漱石将这种状态描写得模棱两可。证明了他自身对悟道都没有彻底明白。比如武士最后要悟的那一瞬间,眼前到底出现了什么,他悟道了什么,等方面的表达都较为模糊。由于漱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对禅道到底领悟至何种程度[7],所以无法写出武士悟道那一瞬间的详细情形。入江隆则继续在其论文中阐述到,武士与悟道的关系就像个体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一样,整个宇宙在被个体认识的过程中,就是一种无意识形态。在武士似悟非悟的瞬间,时钟敲响,实际上是宇宙在我们大脑中的闪现。这种闪现是那么地短暂,让人无法捕获。但是个人在那一瞬间得到了完全地释放[8]。这就是第二夜的作品主题。
归结中日两国学者对《第二夜》的解释,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将作品的主题理解为夏目漱石作家内面的矛盾冲突;另一类是将武士与师傅的对立看作是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并批判日本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的失败。
诚如上述学者所述,《第二夜》中蕴含非常深奥难解的哲学意义,也包含着漱石对人的生存困境、人生存做面临放入各种内部矛盾冲突、以及人生存的内外环境冲突等方面的思索。理解《第二夜》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武士为什么要悟道?武士悟道过程中存在何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作品所要揭示的深刻主题在何处?究明了以上三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第二夜》的作品内涵。下文将围绕上述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索出《第二夜》的作品内涵。
二.道与师傅
《第二夜》的文本中,“我”要悟的道是赵州禅师的“无”。赵州禅师的“无”实际上是叫人放下自我和一切欲望,遵循平常心。那是一种超我的境界,就是“无心”“无欲”“无我”“无物”[9]的境界,并不完全是前述学者提到的“西方文明”,也不应将“无”理解成武士的精神--武士道。“无我”即放下一切“有”及自我,不要拘泥于自我,具有随时能超越自我的觉悟。这种“无我”的觉悟就是“我”要参悟的道。简而言之就是要求参禅者“我”能将武士道化为“无”的道。那就要求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我”,要舍弃武士身份,顺乎自然,放下一切名誉得失,将所有的已经有的东西淡化为“无”。正所谓“心体留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前着不得些子尘沙”[10]。
武士自他成为武士之日起,就具备了克己守礼、舍身取义、仁、智、忠、信、孝、节等武士道的觉悟。即便是不悟道的武士,也能放下自我成就仁、能使自己的言行公正符合道义;能够克制欲望以成就大义;能够舍弃小我,成就藩主和君王的大我,成为志公无私的人、是能够用平常心去接受外界事物的人。武士的这种特征与禅道提倡的“放下一切,顺乎自然”之道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因此禅堂的师傅认为“我”既是武士,“不可能無法開悟。”对于“我”久久拘泥于自己的武士身份而无法开悟,师傅认为“大概不是武士”。
师傅认为的道与武士的关系,类似于菊池宽的小说《形》所描述的主题[11]。《形》的主人公是松山新介(日本地名)的武大将中村新兵卫,是闻名于畿内地区的大豪族武士。他作战勇猛,每上战场,必定穿戴他的猩猩绯铠甲和唐冠缨金头盔。敌方看见穿着猩猩绯铠甲(战袍)和头戴唐冠缨金(头盔)的他时,都吓得不战而退。所以,猩猩绯和唐冠缨金就成了中村新兵卫的标志。它让敌人望而胆颤,让战友信赖,也让新兵卫自己觉得自豪。但是当新兵卫将猩猩绯和唐冠缨金让给藩主的儿子后,藩主的儿子瞬间被当作新兵卫。而自己穿上普通士兵的黑铠甲出战敌方的时候,却被敌军毫不留情地用刺刀刺进心脏。在敌军眼里,猩猩绯和唐冠缨金不管穿在何人身上,都是勇猛无敌,力大无比、不可战胜的象征。《第二夜》中的“我”因为有了武士身份被师傅认为理应悟道,就正如《形》中那猩猩绯铠甲和唐冠缨金头盔一样。“我”的武士外壳,就等于具有能舍弃自我,放下小我,成就自然之之道,能够进入“无”的境界一样。
师傅所说的道,正类似于中国的孔儒老庄之道。即人如果遵循了老子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样的自然之道,就能做到“无善”“无恶”“无心”“无念”,“为无为,则无不至”[12]。由此可知,师傅所指之道首先就是老庄的自然之道。即人无需特意为之,天生就具备了体察万物的能力。看似复杂抽象的道,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13],万事遵道于自然之后,方能成为自然之人,方能使本体与道合二为一。
师傅的“武士不悟道就是人类的渣滓”中的 “不悟道”,就是不悟孔孟老庄之道,即所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人不先“正己”,就“无”法直立,“无”法直立就“无”法顺乎自然,不顺乎自然当然就不能成为自然人。因此,武士不悟道从根本上说就是武士不尊“自然之道”,不能将自己心中的“有”放下,让其成为自然之“有”。这样就违背了自然的法则。所谓“人类的渣滓”,指的是不遵守“人道”的人。孟子曾经用“思诚者,人之道也”[14]道出了人之道的根本。人若为人,就要遵循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绳,反之就不成为人,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的渣滓”。
禅堂的师傅是极少的能悟到“无私无欲无心无物”的悟道之士。他能站在高处评价人生存的困惑。师傅认识到“我”之所以无法悟道,是因为“我”无法舍弃“我”作为武士的“有”,无法超越“我”自己。师傅已经洞察出我一边在极力修炼“无我”,极力想摆脱“自我”,可另一边又死守着自己作为武士的名节。这样的“我”就算一时得悟,也会不由自主地回到本能的自我。就算是觉悟较高的武士,也无法达到平常心,也极难彻底超脱而得道。所以自然也做不了顺乎自然之人,只能成为被各种“有”包围的芸芸众生之一。
三.“我”与道的纠葛
“我”在悟道的过程中,至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武士,并且自始至终都希望能作为武士参悟。想证明即使是威武无比的武士也能放下一切自我,回到平常心的状态。“我”一边念着自己的武士身份,一边想着悟道,另一边还想着悟道以后要杀人。这就注定了“我”的悟道过程中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以及“我”悟道最终会失败的宿命。因此了解“我”在悟道的过程中面临矛盾冲突,就更容易理解“我”悟道失败的根源。
3.1“静”与“动”的矛盾
《第二夜》的大部分内容在描写“我”的悟道的过程。梦境从几个方面叙述了“我”的难以超越自我的命运。最后“我”抽刀自尽,可以说是作为武士无法逃避的命运。人在禅悟的过程中,要求参悟之人自己的内心要安静下来。所谓的“人心要虚,惟虚集道,长使胸中豁豁,无些子积滞”[15]便是如此。可是“我”所面临的只是“我”的外部的寂到极致的静。而“我”的内面却是暗流涌动的“动”。这是“我”面临的第一对矛盾冲突。
3.1.1 “我”外部的“静”
禅道的“无”,是参禅悟道之人追求的心灵境界。它要求参禅之人静坐,以放松入静,排除杂念,呼吸自然。驱除自身外部的一切杂物。这是为了让参禅之人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后进入忘“我”的境地,为了能给参禅之士提供悟道的理想场所。“我”参悟的禅堂四周出奇的静。“偌大的寺庙,附近一带万籁俱寂,冷森森地毫无人迹。“我”的房间里,昏黄的坐灯亮着,其“花形的丁香油噗咚掉落在朱漆的灯台上,弥漫的残香更加让人体会到静无声的坐禅环境。行灯的“圆形灯座的影子映照在黑漆漆的天花板”上,让“我”总觉得行灯的影子“活像是有生命似的”。灯的巨大的影子更加衬托出房间的寂静宽敞。
“我”坐悟的房间,空寂清静,使“我”在寂静之处感到身处一种随处可见的“动”中。这种“动”反而映衬除了禅堂的至寂至静的状态。其次是在“我”的房间的内部布局上也处处显示出寂静的气氛。与谢芜村(1717-1783,日本江户时期有名的画家和俳人)的画,浓淡分明的柳树,时远时近地点缀在画中;打着哆嗦的渔夫更让人联想到一种秋风萧索易水寒的萧杀寥寂的画面。而且,房间内的“壁龛上挂着文殊菩萨的挂轴,让人立即进入一种静穆的禅意识氛围中。在一般常人看来,文殊菩萨能为每一位参悟之人开行引路。文殊菩萨身上的宝剑能斩断参悟之人的一切俗念,使参悟之人放下一切,开启自己的悟道之门。最终使参悟之人达到纯洁无染,顺利进入悟道境界。上述的行灯、与谢芜村的画、禅堂四周的寂静,都为“我”的静坐悟道提供了与参禅环境相应的外部环境。
3.2.2 “我”的内部的“动”
与禅堂的“静”的环境相比,“我”的内心却是极不宁静,甚至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动荡不安。简言之,在“我”的心里首先有越来越强的“我要悟道”的欲念。“我”的内里面的“动荡不安”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我”的内心充满了要守住“武士名节”的念想。“我”将“恪守武士的名份” 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并且不断地转化成“我要去实现”的意念。
其次,“我”的内心还有着“我要悟道”“我要取师傅的人头”的欲望。因为如果不悟道,就会被师傅蔑视,就会侮辱武士的名节。可以说,“我”想参悟的意念因为师父的话语而不断得到强化,甚至变得越来越强烈。
因此,“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武士之名的眷念和对和尚的愤怒,“我”根本做不到静坐,甚至是“单膝跪在坐垫上”,嘴里“咬牙切齒地”骂着臭和尚,并且不时回想起师傅的话语时心里愤愤不平。我心里一边念着自己是一名武士,一边渴望着能悟道给师傅看。所以内心越发不能平静下来。非但如此,“我”甚至还下决心以“悟道换取和尚的人头”。“我”的“牙齿咬得的”很用力,“我”的鼻孔“直冒热气”,太阳穴“抽筋得很痛”。想悟道的欲念已经使“我”的双眼也“睁得比平常大了两倍” 。此时的“我”因心中充满着太多的杂念而“无”法让自己进入宁静的禅坐氛围里,也与“无”无缘。
“我”一边在与“我”的外部各种因素冲突挣扎,一边在与“我”自己内部的各种矛盾因素斗争。“我”又不得不直面“我”自己内部更多的矛盾冲突。
3.2“无”与“有”的对决
赵州和尚[16]所说的“无”,就是所谓的“平常心”,就是要把自己心里所有的对立面全抛开,否定一切的一切,进入“无”的境界。“无”是参禅之人摧毁一切“我知”,“我见”的最锐利的武器。可是,“我”在通往赵州和尚所说的“无”的进程中,所见所闻所嗅所感的,全是与“无” 相对立的“有”。“我”看得到挂轴,看得到坐灯,看得到榻榻米,更看得见师傅的光头,甚至听得到师傅咧嘴嘲笑的声音。“我”的舌根不停地念着“无”“无”。明明心里知道在念着“无”,可“我”还是能够闻到房间里的香味。“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搞什么鬼”,“我”的“无”在哪里。“我”的心越有意于求“无”,而越不觉“无”。
“我”的内部有太多的“我知”和“我见”。首先“我知”的部分有:“我”心里装着“我”是一名武士的名份,也认为具有师傅认为的武士悟道的能力。即就是说“我”自身认识到自己具有武士的一切属性——“有”。而且“我”心里还有藏在身边的短刀,“我”认为它是能证明“我”是武士的最佳手段。“我”如果能悟道,就能用短刀证明“我”的武士身份,也能用它来结束师傅的生命;但如果不能悟道,“我”也能用短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我”是武士。因此可以说,短刀是哽在“我”与“无”之间的最大障碍。它时时刻刻让“我”觉得 “有”的存在,也阻止了“我”走向“无”的境界。
梦境中的“我”在悟道过程中所经历的身体上的变化表明,“我”在与“无”的对立面“有”进行搏斗之后,进入了一种“有”与“无”相互搏斗的混沌状态。佛家有云:当人禅坐到一定程度,即到了“启齿神气散,意动火功寒”的程度以后(南怀瑾《花雨满天,维摩说法》),此时若做到六根关闭,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再受到干扰,人自身所聚集的“无”的份量就会不断增长,从人体中脉往上走,一直到头顶。可是头顶又无法打开让“有”释放出去的时候,就与人体内的“无”产生搏斗。人的感觉就是 :头脑里面又放光,又炸雷又头痛,眩晕呕吐。这种“有”“无”一直在头里面相互博弈,弄得让人天旋地转。这时候如果能得到一个声音的刺激,人就能猛然间得以开悟。
试看文中描述的“我”悟道过程中的体验。
我突然握紧拳头猛砸自己的头,嘴里“呀!呀!”地嚎叫。后槽牙咬得咯吱咯吱乱响,腋下冒出冷汗。脊梁背儿僵直得像根棍子,膝关节剧痛。“就算膝盖骨折了又有什么呢?”我这样想。”可是,疼死了,难受死了。“无”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只要一有“无”来临的感觉,便立刻疼痛难忍。愠色现于面上,癫狂一触即发。我满腹委屈,不禁热泪潸潸。真想一狠心撞到巨石上,来个粉身碎骨。尽管如此,我还是克制住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心中按捺住难以忍受的痛楚。那痛楚,像是要从下面提起我体内的肌肉,又急冲冲地欲从汗毛孔冒出来、冒出来,然而到处都水泄不通,连一根可以排泄的汗毛孔也没有,憋得我难受到了极点。(夏目漱石《文鸟·梦十夜》第31页)
对照前述的坐禅开悟的经历来看,“我”在悟道的过程中正好也体验了上述开悟的全部过程。这证明“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已经顺利进入参悟的最后阶段。而时钟“啪”的敲响声也正好刺激了混沌中的“我”,成为“我”猛然间开悟的“发令枪”[17]。由此得以证明我在时钟敲响的那一霎那终于得以开悟。
四.回到原点
如前节所述,“我”经历了各种痛苦到达悟道的最后阶段--“无”的状态,可是还没法完全开悟。“我”的“无”已经到达最紧要关头,正是天旋地转,头疼难忍,癫狂如痴的状态。“我”开始变得“神志不清”了。眼前的落地纸灯笼、芜村的画、榻榻米、左右交错的搁板在“我”眼里时“有”时“无”,若隐若现。这时,时钟“啪”的一声响,瞬间将“我”带入了悟道的状态。“我”此时能被钟声惊吓,表明“我”的内心已经进入了寂静,进入了“无”的状态。只有在“静”与“无”的状态中,“我”才会有“大吃一惊”的反应。有的学者认为:“我”听到钟敲响的那一刹那,手不由自主地伸向短刀,“一方面表明“我”参悟的失败,另一方面又为武士的继续开悟叩响了发令枪”[18]。也有人认为:“我”的开悟是一种假象,钟的响声,反而将隐藏在“我”内部的“贪,嗔,痴”暴露出来,反而唤醒了“我杀戮的本能”[19]。也有人认为,“我”最后悟道的失败,暗示着“日本不能盲目地完全西化,而是对日本传统文化的不抛弃,不放弃,传统文化的回归才能使日本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往正确的方向行走”[20]。
上述的种种解释,其结论大体上都归于“我”的悟道失败。这些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都难以让人完全信服。从梦境的层次和篇章结构的安排可以推断:“我”在一心想领悟赵州禅的“无”的过程中,经历了坐禅到开悟的每个阶段。“我”在最后时刻也到达了将自身体内所有的“有”推到了一个排泄口的程度。而此时时钟的响声正好成为“我”开悟的阀门。那一瞬间“我”得以开悟。可是悲剧的是,我得以开悟的那一瞬间,“我”又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藏在身边的短刀。“我”的这一行为表明“我”心里又涌现出了“有”——武士的名份。“我”不由自主地“摸”向蒲团下面的短刀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认为“我”开悟失败而摸刀自杀。二是“我”得以开悟摸刀去杀和尚。当不管是哪一种含义,都表明了“我”又回到“有”的原点。一方面,“我”不得不重新做回武士,重新开始参悟的痛苦历程。另一方面,即使“我”得以悟道,上升到“无”的境界,但是“我”的心中却装着杀和尚的“有”的欲念。所以,无论做后结果如何,“我”都无法超越真正的“我”。只能是在“无”与“有”之间重复和循环。这就是“我”真正痛苦的根源。
总而言之,“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悟,达到了“万物皆空,平常心即是道”(赵州禅精髓)的境界时,并不是会继续前行,进入彻底的“无我”境界。等待“我”的下一站竟然是“我”最初的原点-武士。这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在武士生命中的投影。“我”最终又本能地回到生存苦闷的原点,绝望地走向新的轮回。“我”对于这种命运的轮回,毫无办法反抗,也无法逃避。这就是“我”作为人的宿命。
五.漱石的思考
大部分学者将“我”与作者夏目漱石等同起来分析,认为《第二夜》中渗透着漱石在1905-1908之间的个人经历(大久保纯一郎,1974)。也有人认为,整个《梦十夜》就是漱石对人生存的原罪不安的反应,是夏目漱石儒释道思想的集中体现(孙树林,1999)。但如果从文本对“我”悟道的阶段性体验的描写来分析,夏目漱石在其中表达出了比上述学者观点更深层的意义。这与其说是夏目漱石对人生存的原罪的苦恼,还不如说是漱石对人生存中无法回避的各种轮回、各种围城现象的痛苦思索。具体而言,漱石的《第二夜》通过悟道的经历,揭示了人生存环境中无法躲避的轮回和围城现象。漱石再文中对这些人生困苦进行了深刻地探讨。就拿武士来说,武士自成为武士以来,他就不断在寻找能超越自己的出口。漱石是想通过他的系列作品告诉我们,人在生存的过程中,总是不停地在寻找苦闷生活的出口,总是在寻找能超越当下、超越自我的契机。可是人为解决生存困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人在生存过程中总是不由自主地从一个轮回进入到下一个轮回,在自设的围城中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能被迫地接受一个又一个人生围城轮回的怪圈。
归结起来,人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地自设围城,然后不断地寻找方法冲破围城。但是在冲破围城的那一霎那,人又本能地回到最初的原点。这就是人的宿命。漱石在他的不同作品中曾多次提到人的这种宿命。比如,在《第十夜》中,庄太郎每天坐在门口观察外面的世界,总想寻找一种让自己走出屋外的动机。有一天终于在一个女人的带领下走出了自己的小屋,在经过七天七夜的与外界融合的过程中,庄太郎不停地从一个轮回走向另一个轮回。他在山崖边不停地与猪搏斗,最后累倒在山崖边。最终,庄太郎又回到自己的小屋。这就是庄太郎无法逃避的宿命。再比如,在《永日小品》[21]的《心》中,作者描述了“我”与小鸟在相互试探中走进彼此心里以后,竟无法再往前走一步。“我”在潜意识里又退缩到远处来观察小鸟。人始终在寻找自己能与外界融合的接触点而苦苦求索。但是可悲的是,人就算找到了与外界的接触点以后,人又本能地回缩回到原点。
六.结语
夏目漱石在《第二夜》中,分层次分阶段地对梦境进行了描述。其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生存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各种轮回式的、围城般的人类命运。人总是在想超越目前的自己,但是在超越的那一瞬间又本能地回到原点,进入下一个围城。这就是人生存过程中无法改变的宿命。《第二夜》中的主人公“我”被困于武士这一名份,极力想通过悟道来使自己的各种欲望淡化,使自己归于平常心。当“我”经历了重重苦难,终于得悟的那一瞬间,“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藏在身边的短刀。这就意味着“我”又本能地回到自己的武士的名份中。这使得我不得不面对先一个痛苦的围城。这种生命过程中的各种围城现象,是人类自身无法控制的,只能无奈地跟着一步一步地走。就像庄太郎明明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把扑面而来的黑压压的猪群全部推下山去,可是他还是本能地不断地努力。这也是庄太郎无法抗拒的生命历程。这是夏目漱石《第二夜》中所要揭示的深刻主题。
参考文献:
[1]大久保纯一郎.漱石とその思想[M].日本:荒竹出版株式会社,1974. 214-219.
[2]同上
[3]高鹏飞、高歌.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二夜解析[J].读书文摘,2016(02):001-002.
[4]高鹏飞、高歌.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二夜解析[J].读书文摘,2016(02):001-002.
[5]孙树林.梦十夜与儒释道[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1):54-55.
[6]马英萍.非人情与禅——论夏目漱石《草枕》[J].江淮论坛,2006(4):181-182.
[7]入江隆则.《讲座夏目漱石》第二卷漱石の作品(上).日本: 有斐阁,1981.259-260.
[8]同上.
[9]宿亦铭.王阳明全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36-93.
[10]宿亦铭.王阳明全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36-93.
[11]村上林造编.近代日本短篇小说选集[M].日本山口市:山口大学教育学部村上林造研究室,2015. 51-52.
[12]邓启铜.老子·大学·中庸[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05.
[13]宿亦铭.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 36-93.
[14]此语出自《孟子,离娄上》的词句.
[15]宿亦铭.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 36-93.
[16]赵州和尚,“我”国唐末著名高僧。俗姓郝氏,为曹州(今山东曹县)郝乡人。因晚年久居赵州观音院,故时人以“赵州”敬称。(778-897).
[17]肖书文.夏目漱石梦十夜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8(10):60-64.
[18]金开龙.苦梦方知悟道难--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二夜》解读[J].东京文学,2012(03):99-100.
[19]肖书文.夏目漱石梦十夜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8(10):60-64.
[20]高鹏飞、高歌.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二夜解析[J].读书文摘,2016(02):001-002.
[21]夏目漱石1909年1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题为《永日小品》短篇散文集二十四篇.
作者简介:
冉秀,文学博士,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日近现代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数据库] 经典之作 无法超越 2011版李兴华主讲-ORACLE实战 56集](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7bd8952148d6da7051eb6d246ec47872.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Python] [经典 无法超越]2013年老男孩录制 从零开始学python编程课程57集](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0ceab0a2df5e4d63fda958d69ac7f18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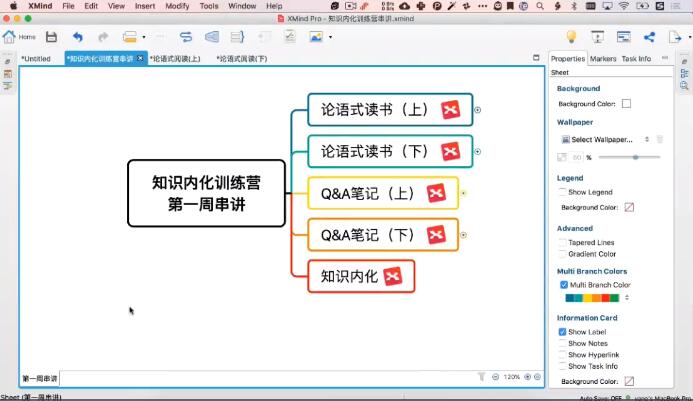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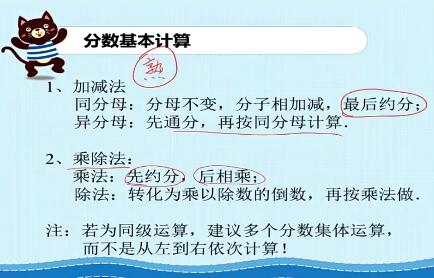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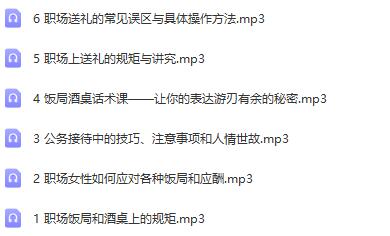

![[php基础] 解决PHP中的Bug,搞定PHP的错误体系的各种问题](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fd5a6305469616cdc05c47fa0e881d00.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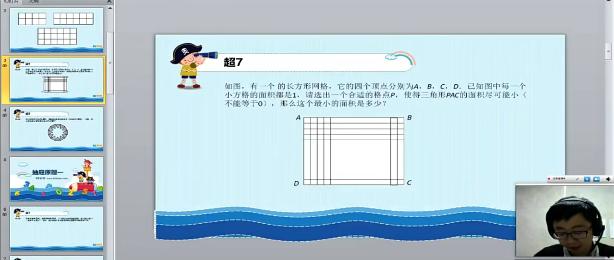





![[Hadoop] 新版视频下载 hbase 是hadoop的重要组件 分布式的、面向列的开源数据库](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c5ca5ce9c087063421b806fd24132729.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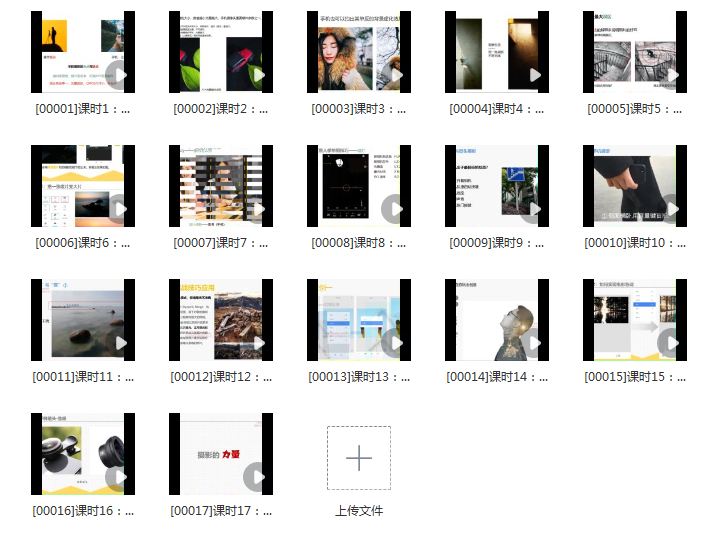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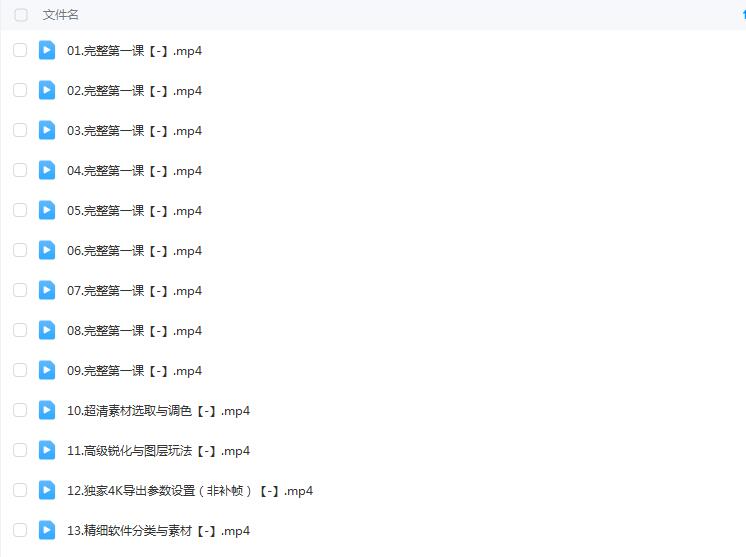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