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散文两题 || 作者 杨进荣
发布于 2021-11-30 14:22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点上方蓝字【天南地北会宁人】免费
纪实散文两题
作者 ‖ 杨进荣

一、 一碗浆水面
今天,老乡约见,在他家吃了一碗浆水面。老乡很是热情,佐以猪手排骨,韭菜炒鸡蛋。吃罢,不能说不香,也不能说不好。然而,多年后每有浆水面的餐桌,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想起八十年代前的一碗浆水面。

那是一九八O年初夏,我还在会宁一中读高中。虽说已经包产到户了,但因我家陈年旧帐多,家底瘠薄,吃饱饭还是有点困难,玉米糊糊,就是家常便饭。
暑假,乘班车回家,车到会宁草滩乡路沟村,突遇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土路,瞬间被山洪冲毁,每人退了一元钱,只有步行、泥泞回家了。好多人前去路边人家避雨,我因饥肠辘辘,两天未曾吃饭,便冒雨到该村油房沟社二姐婆家,希图填饱肚子,再回那个穷得前心贴后背的老家。
二姐的公公在新疆,一二十年没有回家。婆婆独自拉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记事起,大儿子(姐夫)和女儿成了家,其余两个儿子,已是小伙,还未娶妻。
两三里路程,连滚带爬地走了近两个小时,到姨娘家大门洞时,湿泥地看不出衣裳穿的是啥,两只烂布鞋已经裂绑,不得不抱在怀里,右脚被瓦渣划了一下,血透过烂泥,泛出红色。喊了声姨娘,我没哭,跑出来的姨娘先哭了:唉呀,我地蛋蛋,这么大的雨,你从哪里来呀?快,快往屋里走……
姨娘拿来了一套烂衣服,让我赶紧换上,端了半盆水,洗了手脸,让我再把脚上的泥洗掉。她撕了一疙瘩棉花,烧成灰,敷在划破的口子上,让我立马上炕,把被子拽过来给我捂上……
姨娘是一位干炼的老人,平常衣服穿的干净整洁,为人贤淑善良,话语温润委婉,做得一手好针线茶饭。

过了有半个小时,姨娘用盘子端来了一碗浆水面,盘子里放了三个小碟子,一个盛盐,一个盛咸韭菜,一个盛油波辣子。
我忘了文明礼貌,端起碗就吃。姨娘说:狗娃慢慢吃,调上一点辣子,下上一口咸菜。我嗯嗯地应承着,三下五除二,一碗浆水面下肚,辣椒和咸菜碟都被打着地光光的了。酸辣爽口,满嘴余香。姨娘又端来了一碗汤:狗娃,你再喝些汤,你姐夫寻粮去了,前面缸缸里只扫了一把面,你姐夫寻来了,咱们吃长面……
我端起的汤碗停在嘴边,哽咽着说,姨娘我都给你没让!姨娘摸着我的头说,你超子说啥呢,姨娘是大人……
雷雨后的夜晚,天空格外晴朗,满天的繁星特别明亮。我陪姨娘睡在上窑的窗户下,姨娘从墙洼里取下一把破旧的三根弦木琴,弹了一首曲子,那曲子悲伤忧郁,年少的我更难入梦乡,不明白姨娘为何要翻来覆去地去弹它呢?
后来,才知那首曲子名叫《王家的歌》,系流行于甘肃定西会宁一带的民歌。与陕北民歌《拉手手》《蓝花花》等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来自憨厚的黄土地,以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唱咏相思之苦,男女爱情!
长大后,终于明白,当年姨娘不是在弹琴,而是借助夜色,倾诉思念之苦,思夫之情啊!
生在陇上,吃浆水面是经常。后来求学谋生至城市,间接到挂有乡土牌子的饭馆去吃浆水面,但无论怎样吃,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还是吃不出、品味不到,那年姨娘给我做的那碗浆水面的纯正酸香!
浆水面哟,那碗浆水面!
二、 一双毛袜子
至少在十五岁前,春夏秋三季,我是没有穿过袜子的。

有钱人家,夏季穿一身料子(化纤)衣裳,脚登一双有袜垫子的毛底条绒鞋。冬天披一件有绒领的大裹托,脚穿一双白白的羊毛线挑制成的毛袜子,那种穿戴,用现在时髦的词叫帅呆了,酷毙了。

好象就是我十六岁的冬天,二姨和三舅来我家浪门子,三舅拿着一个羊毛线杆,嘴里叼着旱烟锅,一边和父母亲聊天,一边帮二姨捻线。
线杆,一般左手拿一疙瘩质量最差的羊毛,常常是生产队春秋两季剪下的羊毛,好的挑拣后交给收购组,羊小腿及屁股周围短且脏的分给私人,就这不是谁家都能分到的。人们把分到的羊毛,经过手撕挑拣,拣出屎渣垢饼,然后找个一尺长的、筷子一般粗的细棍或竹杆,杆的下面连一小块砖石,左手拿上整松软的羊毛,右手提线杆,线杆不断扭转,羊毛不断相续,就能捻成挑毛袜子的羊毛线。
线捻成后,找来五根签子(签子有的用竹棍,有的用铁丝),双手掏捥,便能织成毛袜子、毛裤之类。
三舅是想给自己织双新毛袜的,但经二姨劝说,便决定把新毛袜织给我。
是阴历九月九,生产队宰杀了十多只羊,分到几百口子人手中,每家只有两三斤。好似我把一块肉都夹给了三舅,以报给我挑毛袜之恩!
毛袜子挑成后,不能立即去穿。天还不冷,烧的穿不成。母亲说。
盼啊盼,天空飘起了雪花,母亲才把那双毛袜子从墙洼挂着的纸背子中取下,让我下雪穿上,天晴了就脱下。
我的脚是汗脚,光脚穿鞋,走一截路,脚底都感到湿滑,穿上毛袜子后,那个热,好象双脚伸入热炕上一般。不几天,天亮最怕穿它。因流汗袜子底部结荚,初穿冰凉。穿热又出汗。若洗了,冬夜无法晾干。
半个月后,毛袜的后跟开了洞,我看到袜子烂了,十分心疼难过。洗净,偷偷塞入炕角的席垫下面。谁知睡觉时,被母亲发现了,责怪我一番后,拿到灯盏下看:我得个大呀,你咋把新袜子一下给穿烂了……?母亲接着说,去取针线蒲篮子去,我给你敹上!

谁知,敹过的毛袜子,穿上不再耐实,本来母亲都是用旧破布敹的。
好象那个冬天,过三四天,母亲都要给我敹袜子。结果袜子越敹越厚,沓沓落落,不时脚底被茬子磨出水泡,没人的地方一跛一跳,有人了还要装得一本正经,不敢给大人说是袜底子磨出了水泡。
那双毛袜子穿了三年,直到袜袜腰都不能再补相连!
穿过毛袜子已经多年,至今想来,母亲为给我敹袜子,没有少受破烦!当时若懂事,还不如不穿!


 分享到:
分享到: QQ空间
QQ空间 朋友圈
朋友圈 ↓
↓



![【古荣荣】2022高二英语秋季尖端[百度网盘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25ml/119-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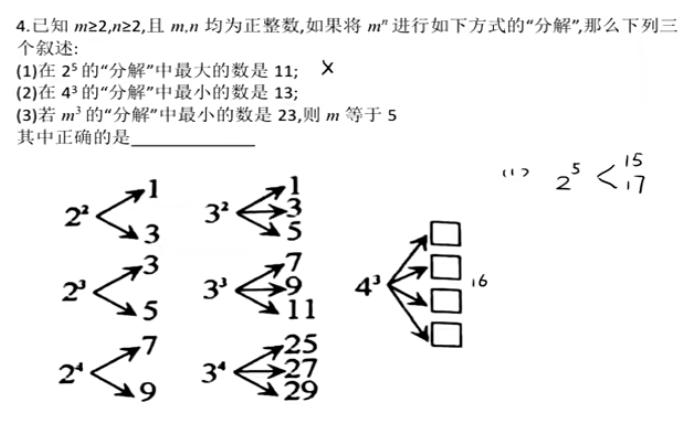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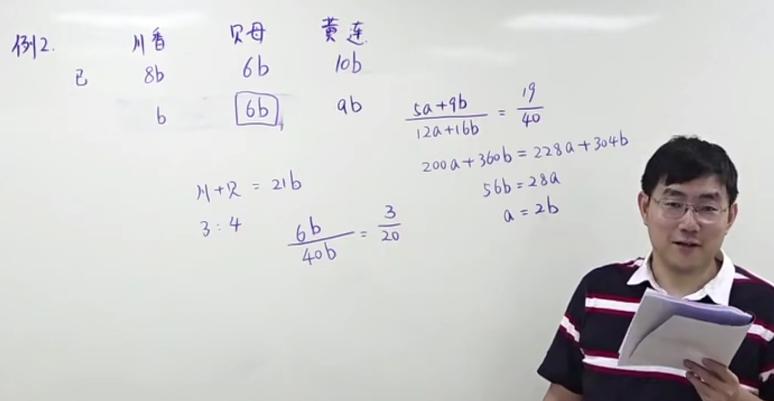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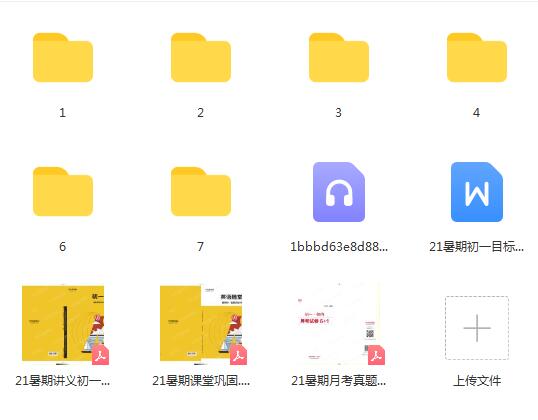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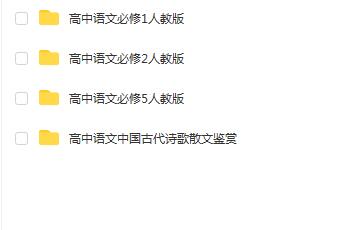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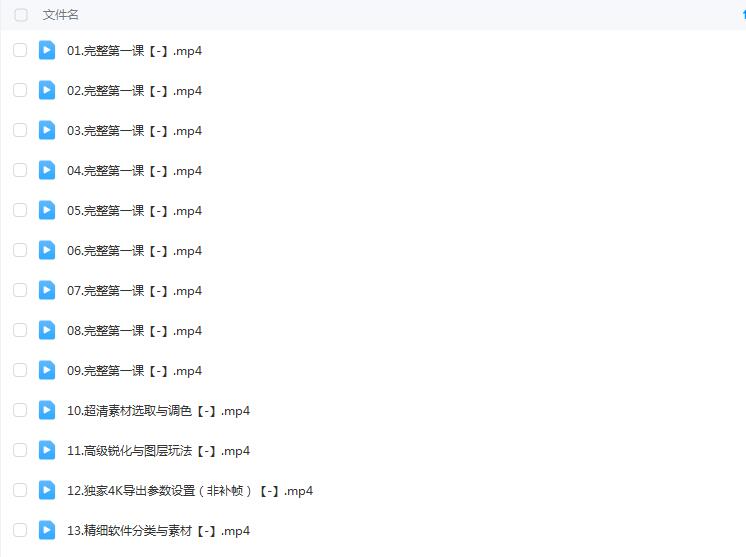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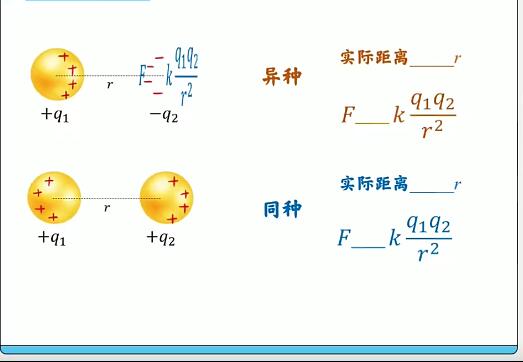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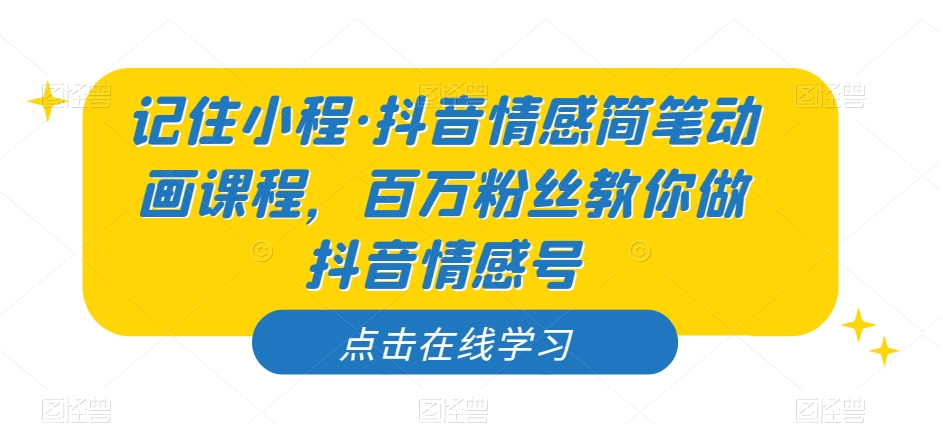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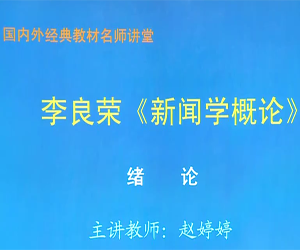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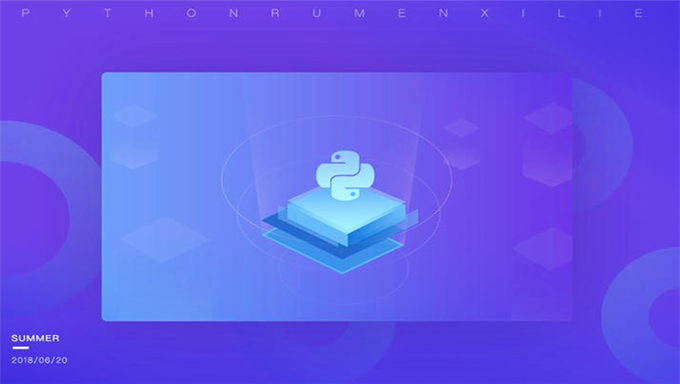
![数据库] 某培训机构价值进2w元的经典oracle学习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ae33ca341490af8c0023ebf3bec5b83c.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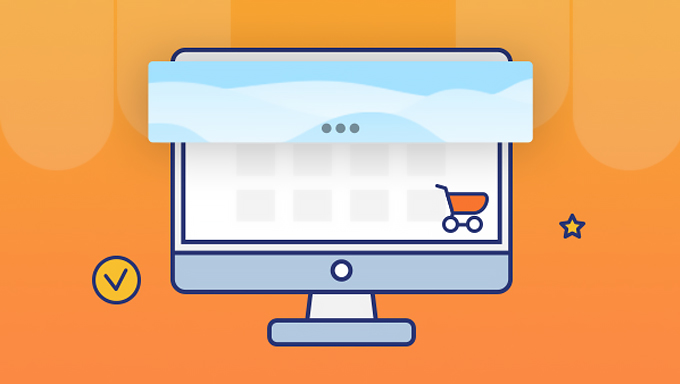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