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春节期间,庚子疫情暴发,世界进一步分化,人们围绕不圆作家的日记展开互撕。在不知道明天与新冠哪个先到的焦虑中,唯有读书可以让我回归平静。我反反复复地读卡夫卡作品集与《美丽新世界》。卡夫卡与赫胥黎两位天才预言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看透了权力与科技主宰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至今,疫情仍在继续。人心仍在撕裂,人性仍在异化。

从个体异化到群体异化
——从《变形记》到《美丽新世界》
文/石凌
卡夫卡的《变形记》历来被视为后工业时代个体命运的杰出寓言。“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燥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他仰卧着,后背坚硬得像铁甲一般,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变成了棕褐色,高高隆起,表面分割成许多弧形的硬片,在肚子的最高处,被子已经盖不住,就要完全滑落下来。他长着许多条腿,这些腿与巨大的身躯相比显得很细,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扑腾着。”《变形记》的这个开头成为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经典之一,无数作家从这部中篇小说中汲取过营养。作家阎连科说:“《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的启示和变化,无异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满布各国的一片粮禾,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变形记》的魅力不仅在于卡夫卡以天才的想象力,把个人在工业社会里被挤压变形的过程具体化、细节化,而且在于它对后现代社会里人的精神异化的高度概括与精准描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前,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衣料推销员,他拼命工作,赚钱养家。在公司,格里高尔对老板的要求惟命是从,“他是老板的一条狗,既没有脊梁骨,也没有头脑。”在社会上,格里高尔只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枚螺丝钉,没有自我,他变形前后一心想的是工作,从未对自己为何变成甲虫进行反思,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在家庭中,格里高尔是顶梁柱,他一心想的是赚更多的钱还债,让一家四口过上体面的生活:父亲可以拄着手杖悠闲地散步、看报;母亲可以指挥女佣干活,而不用自己辛劳;妹妹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浸于少女梦想,自由自在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甲虫,不仅粉碎了他自己的梦想,也把一家人的生活打回“解放前”。首先,家里失去了一个挣钱养家的机器,他们面临着沉沦到社会底层的危险。接着,他们感觉变形以后的格里高尔是一家人的累赘,是影响他们正常生活的障碍,他们百般虐待他,希望他尽快从家里消失。比起格里高尔的肉身变形,家人的精神变形表现得更为激烈而持久。长时间得不到食物,又受到家人虐待的格里高尔终于疲累而死。一家人如释重负,完全解脱。《变形记》是一面照妖镜。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与他的家人、老板互为镜子。卡夫卡以他天才的想象使变形人的生活具体化、细微化,通过变形人的眼反观正常人的变化。无论是变形前后,格里高尔都一如既往地爱着他的父母与妹妹,他想挣更多的钱让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想让父母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格里高尔起早贪黑到处奔波做推销,累到身体变形,他的亲人立即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父亲始终未正眼瞧过变形人,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与父亲唯一一次在客厅相遇,被父亲咒骂,砸伤。在父亲眼前,那个变形人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一个怪物。母亲因绝望而尖叫,因对格里高尔恢复正常失望而冷漠,既而要把他当作累赘抛弃。妹妹之所以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初还表现出一点点耐心,给他食物,是因为妹妹还未品尝过工作的辛劳与穷人的辛酸,她的善良源于她的单纯,当妹妹不得不出去工作,遇到老板的刁难,感受到挣钱的不易后,态度立即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弯,率先提出要把格里高尔处置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哪怕是亲人也不例外。 卡夫卡以变形人格里高尔的眼审视当时的社会,把工业社会中人的冷酷无情,人的残忍程度,人的忍耐极限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格里高尔的变形对公司而言是失去了一个能干的职员,对家庭而言,则是导致了“宁静平和、富裕舒适、心满意足的日子现在要可怕地结束,那会是什么情形呢?”格里高尔正常的时候,人人需要他,关心他。他变成甲虫以后,人人嫌弃他,虐待他,没有人记得他曾为家里付出了多少,人们只意识到失去这个赚钱机器以后他们会失去什么。卡夫卡通过格里高尔的眼,看清了人世的炎凉。以前,格里高尔养家糊口,一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全家人都不工作,靠他养活。当格里高尔变形后,家里没有了指望,不仅年迈的父母,而且以前一直衣食无忧的妹妹也坚强起来。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现在挺直了身板,一件银行的勤杂工一类人穿的镶着金色纽扣的蓝制服紧绷在身上,高高的制服硬领托着他那又肥又大的双层下巴,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原先蓬乱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中间留着分头。”格里高尔的变形让父亲重新出去工作,恢复了朝气与活力,但父亲一点儿也不感谢他。曾经养尊处优的母亲在格里高尔变形后,不得不为一家服装店缝制做工细密的内衣,挣钱养活自己。母亲没有意识到失去儿子以后,她变得强大起来,反而把他当作怪物与累赘。一直游手好闲的妹妹在格里高尔变形后找了一份售货员工作,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以便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妹妹没有意识到格里高尔的变形使她迅速长大,反而让她的心变得跟父母一样坚硬。《变形记》是试金石,在检验人类的忍耐极限,也在检验人类自救的能力。而格里高尔即使变成甲虫,在心底里仍然深爱着他的家人,仍然想着要按时上班,完成老板交待的任务。他知道自己的变形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不仅家里人希望他尽快消失,他自己也希望他消失。“他充满爱心,深情地回忆他的家人。他必须从家里消失,这个看法在他身上比在妹妹身上更坚定。他就这样一直处于平静的、朦胧的沉思状态中,直到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3点。窗外天刚刚发亮时他还清醒,还看到了朦胧的晨曦。然后,他的脑袋就不由自主地完全耷拉下来,从鼻孔里微微呼出最后一口气。”卡夫卡不仅用极大的耐心写出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的生活,写出了家人虐待、折磨格里高尔的过程,也写出了变形人死后家人的反应。变形人的死让一家人如释重负,家里无人为他悲伤,都在规划新的未来。卡夫卡以他天才的预测力,描述了后工业社会压力下人的变异。细细思量,人在工业社会的挤压下,无一不在变形,格里高尔是工业生产链条上的一个机器,这个机器整日满负荷劳动,劳累过度,被工业文明与攫取利益的重担压得变了形。卡夫卡以无限悲凉的笔触细腻地描述家人对格里高尔变形以后的态度,从最初的惊恐,到最后的憎恶,要把它处置掉,无不体现出利益对人的操纵。在卡夫卡时代,人被社会挤压变形还只是个体现象,变形人即使肉身变异,但仍然头脑清楚,充满人的爱心,具有人的灵魂。人的变异到了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笔下,就成了群体事件,赫胥黎的著名小说《美丽新世界》,描述了人类被科学技术与权力改造的过程与结果,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有被成批生产出来的人不懂痛苦,没有思想,人成了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蛆,人的变异就成了群体行为。与卡夫卡个体生命在后工业社会里的变形不同,赫胥黎虚构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一幢只有三十四层楼的矮墩墩的灰色建筑物。大门口上方有几个字: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一块牌子上写着世界邦的箴言:共有、划一、安定。”人就是通过这个孵育暨制约中心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至少有一百五十个成熟的卵。再加以受精和波氏化——换言之,再乘上七十二——那么你就可以在两年之内,由一百五十批孪生子平均得到大约一万一千个同年龄的兄弟姐妹。”“由一百八十九批孪生子培育出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人。”为了减少生育麻烦,他们“允许百分之三十的雌性胚胎正常发育。其他的则在其后的路程上每隔二十四米就加入一剂雄性激素。结果是:她们倾注出来就是个不育女——构造上十分正常,但绝对没有生育能力。”对这些人造孪生儿,他们进行胚胎干预,让其中绝大多数胚胎间歇性缺氧,他们认为,“阶级愈低,氧气愈少。”如此,使这些胚胎百分之七十成为侏儒,甚至怪物。而对极少数胚胎,他们允许正常生长,成为高人一等的统治者与社会管理者。通过一系列干预,使人成为在艰苦环境中劳动的苦工,“一切制约的目的皆在于:使得人们喜欢他们无可逃避的社会命运。”“美丽新世界”是关于一个未来世界的谎言,维持谎言存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一是禁书。胚胎室里,人成批地生产,没有父亲和母亲。在育婴室,更多的干预措施让婴儿只能适应一种情况,心甘情愿地做权力的奴隶。他们先给婴儿书本与花朵,接着施以电击,使这些孩子“怀着一份心理学家曾经称之为对书本和花朵‘本能’的厌憎而长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低层阶级的人们在书本上浪费掉社会的时间,而且读书总会使他们有解除掉某个制约的危险。”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每天一百二十遍,每周三天,如此三十个月”对孩子进行同一内容的催眠教学,让这种暗示长进人的大脑,再也不用思考。在“美丽新世界”,人们安于命运安排,过着物质共有、性爱共享、整齐划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种成批生产的人还叫人吗?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人还能称其为人吗?看看眼下的世界,无不朝着美丽新世界大步迈进,人类在掌握了克隆技术与体外受孕以后,一切皆有可能,发达国家组织科学家不断进行人体基因研究与实验,企图通过改变某些种族的基因使之成为富有阶级驱使的工具,从而使自己变成为所欲为的上等人。“美丽新世界”中,一切文学、哲学书籍都成了禁书,只有元首可以阅读,其他人活在现世,不思考,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按时满足生理需要,对元首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从不反抗。元首认为,尽可能地使人类免于激情,“世界就万事如意了。”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制造白痴,因为元首希望这种“美丽新世界”能够永远“安定”。为了制造这种“安定”假象,他们不让人一刻闲着,“老年人工作、老年人性交、老年人没有闲工夫,忙着享乐,没有一刻能坐下来思考——纵使不巧碰到他们那团烦恼的固体张大了时间的隙缝,总还是有索麻。”所谓索麻就是一种可以麻醉人神经的毒药,有了索麻,一切痛苦就可以忍受。表面上看起来,“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安定、幸福的世界,因为干预,人早已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个由极权与科技维持的欢乐世界只是一种假象。对于三个因工作人员疏忽,基因改变不彻底的人,“美丽新世界”根本容不下他们,两人被流放荒岛,唯一一个读了莎士比亚作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他们眼里是“野人”。“野人”通过阅读学会了思考,知道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食物短缺,而是失去思考能力。因为思考,野人心中产生了仇恨,对这个“美丽新世界”新新人类的憎恶让他苦恼。野人“发现了时间、死亡和神。”在《变形记》中,变形人保持着人的爱心与思考能力,却被亲人当怪物与累赘除掉。在《美丽新世界》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野人”被当成异类,他不满足于感观的刺激,他要继承人类的智慧,他向统治“世界邦”的元首讨要自由。“野人”指出,那种表面上划一、精神形同人蛆的生活是对人的奴役,他要反抗这种精神捆绑,“如果我能自由——而不是做我自身制约的奴隶。”在他看来,人类安于其中的“美丽新世界”是人类的一场噩梦。他竭尽全力制止人们服用索麻,但没有人相信他。他告诉人们,索麻“不仅是肉体,更是灵魂的毒药。”当他为了别人的自由呼吁时,却被他要拯救的人打伤。这就像鲁迅的小说《药》中的夏瑜,为了拯救蒙昧的人牺牲了自己,却不能阻止那些蒙昧的人们拿馒头蘸他的血吃。“美丽新世界”的缔造者——元首告诉野人,人之所以要被改造成这样的白痴与侏儒,就是被统治者不希望有人反抗他们做出的决定,“不希望自己的喉咙被割断。”,所以他们造的人“他是不自由的,他是被命定了。”当“野人”要求流放荒岛的愿望被元首否决后,他逃到了一座废弃的塔顶,为赎罪不断地鞭打自己,使自己处于警醒状态,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比照现实,对人类的原罪进行反思,但他的行为在所谓的文明人看来,只是娱乐的一个焦点。在这里,严肃与戏谑、反智与冥思、喧嚣与孤独、蒙昧与救赎……诸多对立的情感与社会众生相集中到一起。“野人”在废弃灯塔上寻求隐居的生活先是被记者偷窥,公之于众,继而又遭到众人围观,一场严肃的救赎诞生了一场群虻的狂欢。由此构成了巨大的反讽。习惯了“美丽新世界”社会秩序的人们对“野人”寻求自我救赎的意义完全不懂,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寻欢作乐,不存在痛苦,因为他们从胚胎开始就被训练成一批批白痴,元首禁书使他们无从知晓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的哲学、文学与艺术。追求灵魂自由要进行自我救赎的“野人”最终被一群被规训的群盲围绞而死。赫胥黎生活的时代,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论调甚嚣尘上的时代,作家一方面以巨大的耐心描述了科技进步对人类自身的改变,人在技术控制面前的变形,一方面通过“野人”这唯一的人类智慧与经验的传承者被围殴自杀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社会的担忧与悲观态度,对技术与权力结合,改变人类命运的恐惧。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的再版序言中写道:“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的手段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管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需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从被迫变形到心甘情愿地变形,人类走过的路不到百年。两位天才作家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寓言式的解构。今天的世界,无不向着“美丽新世界“狂奔,权贵与资本结合,少数人操纵绝大多数的命运已是事实。富人穷奢极欲,忙于寻欢作乐,不愿意思考;穷人忙于生计,疲于奔命,没功夫思考。纵观世界,资本操纵下的媒体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人进行不间断地轰炸式洗脑,还有多少人在思考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在对人类犯下的罪行进行救赎?卡夫卡是绝望的,他让变形人死于亲人的虐待下;赫胥黎也是绝望的,他让唯一具有独立思考意识与自我救赎能力的“野人”死于众人狂欢式的围殴。他们是天才的寓言家,他们早早看透人类未来的命运,一旦科技与权力结合,人就被迫变形,从肉身到灵魂,从个体到群体。自庚子除夕至今,一场席卷全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人类的杀手,这既是人类自作自受的恶果,也是对科技进步的最大嘲讽。人类自以为掌握了科学技术就可以控制世界,控制其它生物的生命,却对小小的病毒束手无策。在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的当下,人类需要更多像《美丽新世界》中的“野人”一样的思考者,对人的不义行为进行反思与自我救赎,而不是相互指责,内讧,做病毒的帮凶。【作者简介】石凌:甘肃灵台人。在《北京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奔流》《边疆文学》《延河》《朔方》《飞天》《作品》《散文世界》《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报刊发表作品,10多篇散文入编多部书籍,已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长篇小说《支离歌》。
卡夫卡以变形人格里高尔的眼审视当时的社会,把工业社会中人的冷酷无情,人的残忍程度,人的忍耐极限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格里高尔的变形对公司而言是失去了一个能干的职员,对家庭而言,则是导致了“宁静平和、富裕舒适、心满意足的日子现在要可怕地结束,那会是什么情形呢?”格里高尔正常的时候,人人需要他,关心他。他变成甲虫以后,人人嫌弃他,虐待他,没有人记得他曾为家里付出了多少,人们只意识到失去这个赚钱机器以后他们会失去什么。卡夫卡通过格里高尔的眼,看清了人世的炎凉。以前,格里高尔养家糊口,一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全家人都不工作,靠他养活。当格里高尔变形后,家里没有了指望,不仅年迈的父母,而且以前一直衣食无忧的妹妹也坚强起来。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现在挺直了身板,一件银行的勤杂工一类人穿的镶着金色纽扣的蓝制服紧绷在身上,高高的制服硬领托着他那又肥又大的双层下巴,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原先蓬乱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中间留着分头。”格里高尔的变形让父亲重新出去工作,恢复了朝气与活力,但父亲一点儿也不感谢他。曾经养尊处优的母亲在格里高尔变形后,不得不为一家服装店缝制做工细密的内衣,挣钱养活自己。母亲没有意识到失去儿子以后,她变得强大起来,反而把他当作怪物与累赘。一直游手好闲的妹妹在格里高尔变形后找了一份售货员工作,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以便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妹妹没有意识到格里高尔的变形使她迅速长大,反而让她的心变得跟父母一样坚硬。《变形记》是试金石,在检验人类的忍耐极限,也在检验人类自救的能力。而格里高尔即使变成甲虫,在心底里仍然深爱着他的家人,仍然想着要按时上班,完成老板交待的任务。他知道自己的变形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不仅家里人希望他尽快消失,他自己也希望他消失。“他充满爱心,深情地回忆他的家人。他必须从家里消失,这个看法在他身上比在妹妹身上更坚定。他就这样一直处于平静的、朦胧的沉思状态中,直到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3点。窗外天刚刚发亮时他还清醒,还看到了朦胧的晨曦。然后,他的脑袋就不由自主地完全耷拉下来,从鼻孔里微微呼出最后一口气。”卡夫卡不仅用极大的耐心写出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的生活,写出了家人虐待、折磨格里高尔的过程,也写出了变形人死后家人的反应。变形人的死让一家人如释重负,家里无人为他悲伤,都在规划新的未来。卡夫卡以他天才的预测力,描述了后工业社会压力下人的变异。细细思量,人在工业社会的挤压下,无一不在变形,格里高尔是工业生产链条上的一个机器,这个机器整日满负荷劳动,劳累过度,被工业文明与攫取利益的重担压得变了形。卡夫卡以无限悲凉的笔触细腻地描述家人对格里高尔变形以后的态度,从最初的惊恐,到最后的憎恶,要把它处置掉,无不体现出利益对人的操纵。在卡夫卡时代,人被社会挤压变形还只是个体现象,变形人即使肉身变异,但仍然头脑清楚,充满人的爱心,具有人的灵魂。人的变异到了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笔下,就成了群体事件,赫胥黎的著名小说《美丽新世界》,描述了人类被科学技术与权力改造的过程与结果,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有被成批生产出来的人不懂痛苦,没有思想,人成了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蛆,人的变异就成了群体行为。与卡夫卡个体生命在后工业社会里的变形不同,赫胥黎虚构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一幢只有三十四层楼的矮墩墩的灰色建筑物。大门口上方有几个字: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一块牌子上写着世界邦的箴言:共有、划一、安定。”人就是通过这个孵育暨制约中心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至少有一百五十个成熟的卵。再加以受精和波氏化——换言之,再乘上七十二——那么你就可以在两年之内,由一百五十批孪生子平均得到大约一万一千个同年龄的兄弟姐妹。”“由一百八十九批孪生子培育出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人。”为了减少生育麻烦,他们“允许百分之三十的雌性胚胎正常发育。其他的则在其后的路程上每隔二十四米就加入一剂雄性激素。结果是:她们倾注出来就是个不育女——构造上十分正常,但绝对没有生育能力。”对这些人造孪生儿,他们进行胚胎干预,让其中绝大多数胚胎间歇性缺氧,他们认为,“阶级愈低,氧气愈少。”如此,使这些胚胎百分之七十成为侏儒,甚至怪物。而对极少数胚胎,他们允许正常生长,成为高人一等的统治者与社会管理者。通过一系列干预,使人成为在艰苦环境中劳动的苦工,“一切制约的目的皆在于:使得人们喜欢他们无可逃避的社会命运。”“美丽新世界”是关于一个未来世界的谎言,维持谎言存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一是禁书。胚胎室里,人成批地生产,没有父亲和母亲。在育婴室,更多的干预措施让婴儿只能适应一种情况,心甘情愿地做权力的奴隶。他们先给婴儿书本与花朵,接着施以电击,使这些孩子“怀着一份心理学家曾经称之为对书本和花朵‘本能’的厌憎而长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低层阶级的人们在书本上浪费掉社会的时间,而且读书总会使他们有解除掉某个制约的危险。”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每天一百二十遍,每周三天,如此三十个月”对孩子进行同一内容的催眠教学,让这种暗示长进人的大脑,再也不用思考。在“美丽新世界”,人们安于命运安排,过着物质共有、性爱共享、整齐划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种成批生产的人还叫人吗?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人还能称其为人吗?看看眼下的世界,无不朝着美丽新世界大步迈进,人类在掌握了克隆技术与体外受孕以后,一切皆有可能,发达国家组织科学家不断进行人体基因研究与实验,企图通过改变某些种族的基因使之成为富有阶级驱使的工具,从而使自己变成为所欲为的上等人。“美丽新世界”中,一切文学、哲学书籍都成了禁书,只有元首可以阅读,其他人活在现世,不思考,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按时满足生理需要,对元首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从不反抗。元首认为,尽可能地使人类免于激情,“世界就万事如意了。”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制造白痴,因为元首希望这种“美丽新世界”能够永远“安定”。为了制造这种“安定”假象,他们不让人一刻闲着,“老年人工作、老年人性交、老年人没有闲工夫,忙着享乐,没有一刻能坐下来思考——纵使不巧碰到他们那团烦恼的固体张大了时间的隙缝,总还是有索麻。”所谓索麻就是一种可以麻醉人神经的毒药,有了索麻,一切痛苦就可以忍受。表面上看起来,“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安定、幸福的世界,因为干预,人早已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个由极权与科技维持的欢乐世界只是一种假象。对于三个因工作人员疏忽,基因改变不彻底的人,“美丽新世界”根本容不下他们,两人被流放荒岛,唯一一个读了莎士比亚作品,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他们眼里是“野人”。“野人”通过阅读学会了思考,知道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食物短缺,而是失去思考能力。因为思考,野人心中产生了仇恨,对这个“美丽新世界”新新人类的憎恶让他苦恼。野人“发现了时间、死亡和神。”在《变形记》中,变形人保持着人的爱心与思考能力,却被亲人当怪物与累赘除掉。在《美丽新世界》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野人”被当成异类,他不满足于感观的刺激,他要继承人类的智慧,他向统治“世界邦”的元首讨要自由。“野人”指出,那种表面上划一、精神形同人蛆的生活是对人的奴役,他要反抗这种精神捆绑,“如果我能自由——而不是做我自身制约的奴隶。”在他看来,人类安于其中的“美丽新世界”是人类的一场噩梦。他竭尽全力制止人们服用索麻,但没有人相信他。他告诉人们,索麻“不仅是肉体,更是灵魂的毒药。”当他为了别人的自由呼吁时,却被他要拯救的人打伤。这就像鲁迅的小说《药》中的夏瑜,为了拯救蒙昧的人牺牲了自己,却不能阻止那些蒙昧的人们拿馒头蘸他的血吃。“美丽新世界”的缔造者——元首告诉野人,人之所以要被改造成这样的白痴与侏儒,就是被统治者不希望有人反抗他们做出的决定,“不希望自己的喉咙被割断。”,所以他们造的人“他是不自由的,他是被命定了。”当“野人”要求流放荒岛的愿望被元首否决后,他逃到了一座废弃的塔顶,为赎罪不断地鞭打自己,使自己处于警醒状态,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比照现实,对人类的原罪进行反思,但他的行为在所谓的文明人看来,只是娱乐的一个焦点。在这里,严肃与戏谑、反智与冥思、喧嚣与孤独、蒙昧与救赎……诸多对立的情感与社会众生相集中到一起。“野人”在废弃灯塔上寻求隐居的生活先是被记者偷窥,公之于众,继而又遭到众人围观,一场严肃的救赎诞生了一场群虻的狂欢。由此构成了巨大的反讽。习惯了“美丽新世界”社会秩序的人们对“野人”寻求自我救赎的意义完全不懂,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寻欢作乐,不存在痛苦,因为他们从胚胎开始就被训练成一批批白痴,元首禁书使他们无从知晓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的哲学、文学与艺术。追求灵魂自由要进行自我救赎的“野人”最终被一群被规训的群盲围绞而死。赫胥黎生活的时代,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论调甚嚣尘上的时代,作家一方面以巨大的耐心描述了科技进步对人类自身的改变,人在技术控制面前的变形,一方面通过“野人”这唯一的人类智慧与经验的传承者被围殴自杀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社会的担忧与悲观态度,对技术与权力结合,改变人类命运的恐惧。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的再版序言中写道:“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的手段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管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需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从被迫变形到心甘情愿地变形,人类走过的路不到百年。两位天才作家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寓言式的解构。今天的世界,无不向着“美丽新世界“狂奔,权贵与资本结合,少数人操纵绝大多数的命运已是事实。富人穷奢极欲,忙于寻欢作乐,不愿意思考;穷人忙于生计,疲于奔命,没功夫思考。纵观世界,资本操纵下的媒体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人进行不间断地轰炸式洗脑,还有多少人在思考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在对人类犯下的罪行进行救赎?卡夫卡是绝望的,他让变形人死于亲人的虐待下;赫胥黎也是绝望的,他让唯一具有独立思考意识与自我救赎能力的“野人”死于众人狂欢式的围殴。他们是天才的寓言家,他们早早看透人类未来的命运,一旦科技与权力结合,人就被迫变形,从肉身到灵魂,从个体到群体。自庚子除夕至今,一场席卷全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人类的杀手,这既是人类自作自受的恶果,也是对科技进步的最大嘲讽。人类自以为掌握了科学技术就可以控制世界,控制其它生物的生命,却对小小的病毒束手无策。在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的当下,人类需要更多像《美丽新世界》中的“野人”一样的思考者,对人的不义行为进行反思与自我救赎,而不是相互指责,内讧,做病毒的帮凶。【作者简介】石凌:甘肃灵台人。在《北京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奔流》《边疆文学》《延河》《朔方》《飞天》《作品》《散文世界》《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报刊发表作品,10多篇散文入编多部书籍,已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长篇小说《支离歌》。石凌|地火奔涌(钱理群印象)
在烈焰中奔突——张承志散文印象
被漠视与被遮蔽的——纪念王小波
读大先生:寒湖埋浊身,冷月葬士成
撕开历史面纱 血还没干
评论|| 寻求救赎之路——阿富汗作家笔下的塔利班
《生死疲劳》,戏谑之下全是泪
莫言小说《蛙》的现实主义特质及其历史意义
布衣情怀 高士操守——评安杰人物传记《皇甫谧传》
走近卡夫卡之一:饥饿也是艺术吗?
石凌评刊||诗意的回望与深情的追寻
皇帝宠爱的女人为啥都没好下场
石凌| 夜莺是怎样变成啄木鸟的
现实主义的叙述宽度——读石凌长篇小说《支离歌》
石凌 |一场严肃的救赎变成了群虻的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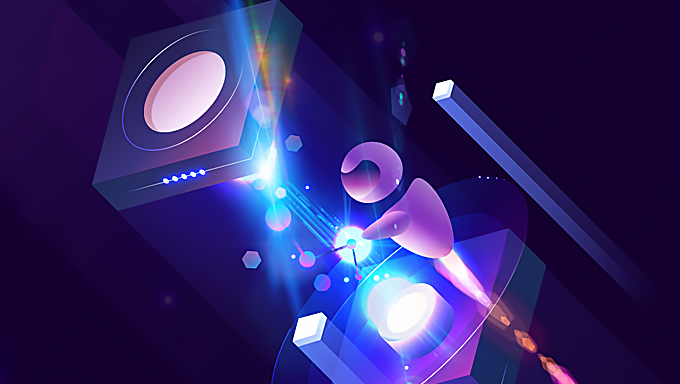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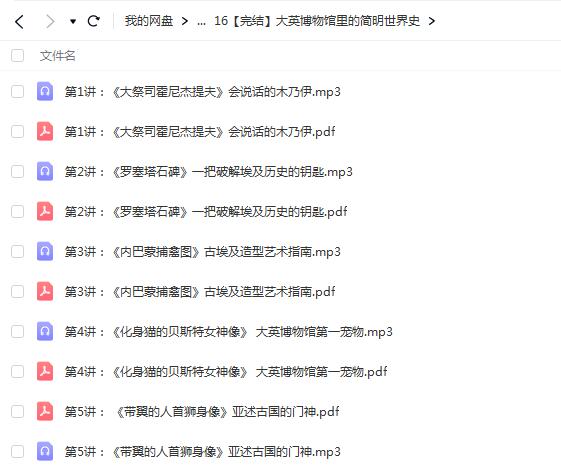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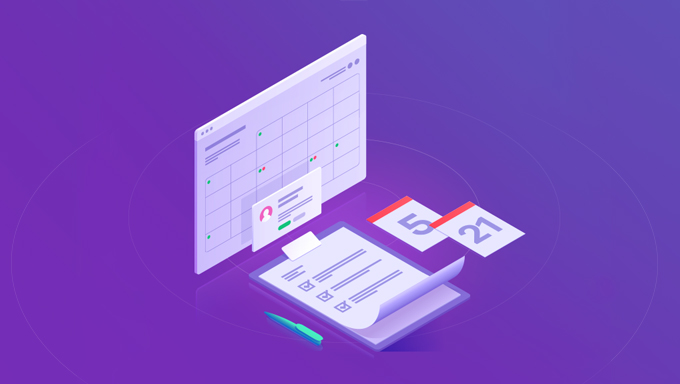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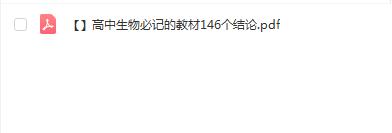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