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 汤雅洪:越剧名家竺水招母女的悲欢人生
发布于 2021-05-13 11:06 ,所属分类:戏曲剧目学习资料

越剧名家竺水招母女的悲欢人生
汤雅洪
想找一段网友制作的水袖集锦,找不到了……
只能用俺做的这么粗糙的充数……
同时,本文感谢【@君子啊】整理!
只要提起经典越剧影片《柳毅传书》,人们就会想起柳毅的扮演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竺水招。然而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这位备受观众喜爱的戏剧名家在她艺术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却被“文革”浩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今年5月26日是竺水招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越剧名家竺水招,笔者近日特地采访了她的亲友和知情人,追忆她不平凡的艺术人生。
竺水招之名是用她生命换来的
虽说竺水招(1921-1968)的名字享誉梨园,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当年取名时还曾有过一段惊险而传奇的故事。
竺水招的老家在浙江嵊县金庭乡的灵鹅村。1921年4月15日,竺水招降临人间时,她的父亲竺朝见很不开心,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相当严重,而且,在她之前母亲生的也都是女儿,因此她的出生让盼子心切的父亲大失所望,真可谓生不逢时。于是,在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后,她母亲一气之下,狠了心叫接生婆将刚出生的竺水招扔进附近的河里去。接生婆来到河边感到非常为难,实在不忍心将这刚出生的孩子扔到河中,为了不伤害这个小生命,接生婆将她丢在了小河边。时隔不久,幸亏竺水招的姨妈在河边发现了她,又将她抱了回去。后来,竺水招一阵阵清脆的啼哭声唤起了父母的怜悯之心,父母才不再嫌弃她。
竺水招满月后又白又胖,人见人爱。每天听到乡邻们夸自己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竺水招的父母心中自然非常开心。为给漂亮的女儿起个好听的名字,竺水招的父母特地找当地一位算命先生为女儿取名。此人掐指一算,开口说,这个丫头命中注定缺水,而且她的命是从河边拣回来的,再说,她今后或许能为竺家招来男孩子,招来好运气,她的名字干脆就叫竺水招吧。
令竺水招的父母喜出望外的是,后来,竺水招还真的“招”来了两个弟弟。
血染冰雪,依然苦练越剧基本功
竺水招家乡浙江嵊县,是名闻遐迩的越剧之乡。竺水招和我国许多老一辈的越剧名角就是从嵊县的小村庄迈向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戏剧大舞台。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浙江嵊县学演戏的农村女孩子非常多,因为当地农村贫困家庭女孩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给人家当童养媳;第二,去到外地当童工;第三,就是进戏班学唱戏。竺水招12岁那年产生了学唱戏、挣钱改变家庭困境的想法,但是,她父亲却认为女孩子去当戏子会让人瞧不起,坚决不同意。幸好竺水招的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意,于1932年冬季的一天瞒着丈夫,牵着竺水招的小手,迎着萧瑟的寒风,悄悄地将她送到了离家七里开外的后山村白佛堂的“吉庆舞台”,拜唱旦角的越剧男艺人竺焕全为师,学唱越戏。
竺水招从小学戏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没有练功房,她一年四季常在户外苦练基本功,在寒冷的季节更加辛苦,数九寒冬季节,她就在冰天雪地里练“拿顶”、“小翻”、“喊嗓子”,而且稍有失误,师傅手上的藤条就会抽到身上。
后来,竺水招从“吉庆舞台”转到“瑞云舞台”学戏,得到著名的“越剧三花”之一——赵瑞花的器重与栽培,对她以后的演艺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瑞云舞台”班主赵瑞花文武不拘,戏路宽广,扮演《孟丽君》《碧玉簪》等传统剧目中的花旦,都是赵瑞花的拿手好戏,竺水招虚心地向她学会了一招一式的表演技巧。赵瑞花在《碧玉簪》中演李秀英有个“绝技”最为出彩,她在演这部戏跑“圆场”时,拿衣服的双手颤抖不止,而下身穿的褶裙却纹丝不动。竺水招为了学会这种高难度的表演绝技,曾冒着风雪在冰上苦练,她一次次地滑倒,又一次次地站起,鞋子磨破了,脚上的冻疮破裂了,地上的冰雪被她脚上流出的血水染红了,但是,竺水招依然咬紧牙关坚持着,在冰上一遍又一遍地练跑“圆场”。经过反复苦练,她终于将这一动作练得像模像样。
性格刚毅的她,视金银珠宝如粪土
天生丽质的竺水招扮相很俊美,演技很全面。她不仅在舞台上反串《张文祥刺马》《双枪陆文龙》中的张文祥、陆文龙等武生角色英俊洒脱,功夫不凡,而且,她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为人豪爽、果断刚毅的坚强性格。解放前,唱红上海滩的竺水招曾多次机智勇敢地摆脱土匪恶霸的欺辱与纠缠,成为戏剧界的一大美谈。1939 年,竺水招与一批越剧小姐妹从浙江嵊县农村迈上了上海滩的大舞台,当年,在灯红酒绿的繁荣大都市,有的女艺人贪图享受,做了资本家的姨太太,有的女艺人甚至成了恶霸流氓的摇钱树。但是竺水招一贯洁身自好,不落圈套。
有一天晚上,上海滩黑社会的一个头目去看竺水招演的古装戏。当晚散戏后,这个家伙不怀好意,来到后台找到竺水招,厚颜无耻地要招她做“干女儿”,并且将装有金银首饰的饼干盒和一把手枪一起放在了她的面前,要求正在卸装的竺水招跪下来喊他一声“干爹”,这些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就全归她所有,否则就自食苦果。
当时现场气氛相当紧张,大家都为竺水招的艰险处境感到十分担心。然而,生来刚毅倔强的竺水招对眼前闪光的金银珠宝视如粪土,她态度很干脆地告诉此人:“我自己有爹有妈,凭什么要喊你干爹?凭什么要给你下跪?”话音刚落,竺水招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剧场。竺水招的这一举动让黑社会的头目一下子愣住了,他绝没想到外表看似柔弱的竺水招竟然有如此的胆量。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对竺水招果断勇敢的举动既感到十分惊讶,又非常佩服!
与金陵结缘,创办南京越剧团1949年5月27日,为庆祝上海解放,竺水招兴高采烈地与越剧界的姐妹们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当时,她头戴阔边呢帽,身穿米色风衣,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在彩旗的映衬下,英姿飒爽地行进在越剧界方阵的最前面,可想而知,解放后获得新生的她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快乐!那时候,听说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越剧姐妹们的民营剧团改编为解放军总政越剧团,与她们共称为“越剧十姐妹”的竺水招也期盼着将自己组建的民营剧团“云华越剧团”改为国营剧团。
1954年11月,竺水招率“云华越剧团”从上海来到南京,在当时的明星大戏院连续演出了《柳毅传书》、《文天祥》、《南冠草》、《范蠡与西施》等剧目,场场爆满,非常轰动。当时彭冲、徐步等南京市委领导观看竺水招主演的《范蠡与西施》这部爱国历史剧后,非常赞赏,建议南京市文化局对该团给予关怀与重视。几天之后,南京市文化局特地派人和竺水招洽谈,准备吸收“云华越剧团”为民营公助性质的南京实验越剧团,竺水招非常爽快地同意了。
1956年春节前夕,实验越剧团又正式改为国营体制的南京越剧团,首任团长竺水招在该团成立大会上心情激动万分,她认为一个在旧社会被人轻视、遭人欺凌的女艺人,如今当上了国家干部,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在她的带动下,商芳臣、筱水招、蒋鸿鳌等主要演员,都将私有的演出服装与用品全部捐献给新成立的南京越剧团。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她感到开心无比
竺水招生前曾多次率团赴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经典越剧,其中为周总理演出她感到最激动,最开心!
1956年的春季,竺水招率南京越剧团到北京整整演了两个月。一天晚上,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观看她主演的越剧《南冠草》之后,特地到后台看望了剧团全体演职人员。当时,郭沫若握着竺水招的手高兴地说“你在《南冠草》中扮演的古代英雄夏完淳和我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完全一样,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于立群告诉竺水招:“看你在舞台上演出时,郭老和我都激动地流泪了,因为观看这部戏使我们想起了抗战时期在重庆度过的艰苦岁月。你们不知道当年郭老是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与迫害下,非常艰难地完成了话剧《南冠草》的创作。如今你们将该剧搬上了越剧舞台,我们要特别地感谢你们!
相隔十几天后,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特地邀请南京越剧团到政协礼堂演出《南冠草》,招待在京开会的全国科学家们。这一天,竺水招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邓颖超和中央其他几位首长。周总理看完演出后亲切接见了南京越剧团全体演员。当周总理来到竺水招的面前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表示祝贺时,竺水招的心激动得仿佛要跳出来,此时此刻,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时隔不久,周总理又邀请南京越剧团到中南海紫光阁演出越剧《南冠草》,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竺水招等演员,并且和演员们畅谈许久,让大家格外兴奋。当时,周总理对竺水招等主要演员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坚持演出有教育意义的爱国历史剧,这很好!今后,你们还要演出现代戏,还可以向男女合演的方向发展。”后来,竺水招按照周总理的这番教诲,在舞台上既演《柳毅传书》、《碧玉簪》等传统剧目,又演《南冠草》、《孔雀胆》、《蔡文姬》等历史剧,还演《江姐》、《阿庆嫂》等现代戏,使演出的越剧剧目更加丰富多彩。
“文革”中遭迫害,她坚贞不屈以死抗争
竺水招在戏剧舞台上,曾经以缠绵悱恻、委婉动听的唱腔,俊美潇洒、形神兼备的扮相,为广大观众完美塑造了蔡文姬、夏完淳、江姐、阿庆嫂等一个个从古到今、光彩照人的戏剧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戏剧人物的艺术长廊。1962年,随着彩色越剧戏曲片《柳毅传书》亮相银幕,在影片中扮演柳毅的竺水招,备受海内外观众的赞扬。那个时期,她的演艺人生更加辉煌,不仅荣获越来越多的荣誉和奖项,而且,还于1964年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于1965年3月实现了她人生最美好的愿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然而, 1966年爆发的“文革”浩劫,将竺水招从艺术巅峰冲击到万丈深渊!“文革”发生后不久,竺水招被红卫兵与造反派罗织了一大堆的罪名,什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黑线人物”等等,这些罪名就像一座座大山重重地压在竺水招的身上,让她难以承受。后来她的罪名又逐步升级,甚至被无中生有地扣上了“文化特务”的帽子,无数次地被游街批斗。
随着“文革”的狂风越刮越猛,他们全家遭受的打击越来越严重。家中物品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先后查抄了5次,珍贵的戏剧资料、珍藏的心爱之物几乎都被抄光。
1967年的冬季格外寒冷。有一天,在呼啸的寒风中,竺水招被“专案组”隔离审查,关进了由剧团仓库改成的“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她的三个女儿年龄还小,对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
1968年5月的一天,小女儿非常想妈妈,哭着去找母亲竺水招,当时竺水招刚刚挑过水,打扫过卫生,她一眼看到很久未见面的小女儿,赶紧擦去手上的灰尘,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从头摸到脚,她心中似乎有千言万语想对女儿叮嘱,但心情难受说不出口,只对女儿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个好孩子。”然后,竺水招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滴在了女儿身上。
然而,年纪幼小的女儿决不会想到,妈妈嘱咐她的话竟然成了一句遗言!1968年5月26日中午,竺水招为了永远摆脱精神与肉体上的摧残与折磨,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她含愤自杀被人发现后,被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抢救,但是由于失血过多,当天下午17时29分,竺水招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终年48岁。一个曾经深受亿万观众喜爱的越剧名家,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人间。她逝世后,身边没有哀乐,没有鲜花,没有一个亲人!
母亲离世后,女儿带着骨灰盒下放到农村

竺水招不幸离世后,她本人和家人遭受的迫害却并没有减轻。有一天,造反派竟然在黑板上画上竺水招漫画像进行批斗,并且将她的丈夫拉上台进行陪斗。有个人还恶狠狠地对竺水招的大女儿、越剧演员竺小招说“竺水招是畏罪自杀,你们都要与她划清界限,肃清余毒!”突然失去母亲的竺小招虽然非常伤心,但是,当时她却不敢流泪,更不敢哭出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与母亲划不清界限而罪加一等。
经受了一次次的折磨,竺小招突然觉得自己变得非常懂事了。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就是: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两个妹妹又幼小,假如自己遭遇不测,两个妹妹就更加可怜了。
到了1969 年,南京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的浪潮。那时候许多人怕下放、躲下放,害怕到农村吃苦,但是,竺小招却主动要求跟随家人下放到苏北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不少亲友对竺小招的选择很不理解,认为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然而,他们哪里知道竺小招的内心苦衷呢?当时她认为“长女如母”,自己虽然不在下放范围之内,但是失去母亲后,一定要帮助父亲撑起这个家。那么,既然一家人在城市里遭受冷落与歧视,不如到农村去换一换环境。后来,他们全家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南京下放落户到苏北灌云县的东辛公社。下放到灌云农村的那几年,虽然生活条件比原先想象的更困难,每天几乎见不到大米白面,吃的都是杂粮与山芋,但是,竺小招感到农村的空气非常新鲜,和善良的农民们相处精神上很愉快。
鲜为人知的是,竺小招下放到苏北灌云时,特地将母亲竺水招的骨灰盒也带到了农村,安放在自己床头旁的一个木箱中。竺小招当时之所以打破让母亲竺水招的骨灰“入土为安”的世俗,一是考虑到母亲生前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虽然当了演员有了名气, 但千万不能忘本,永远不能忘记农村。”二是因为竺小招从小就对母亲太爱戴了,虽然母女永远不能相见,但是,让母亲的骨灰盒天天陪伴着自己,这样做会觉得与母亲依然没有分开。
竺小招对母亲竺水招的爱是默默而又深厚的。后来,竺小招从农村返城后,又将她母亲的骨灰盒带回南京,放置在床头柜中,让母亲竺水招依然日夜和她在一起。直到1983年11月母亲竺水招被平反昭雪,其骨灰盒才由南京政府部门安放在南京清凉山骨灰堂。1997年,竺小招的父亲去世后,竺小招将父母的骨灰一同安葬在苍松环抱的南京白龙山公墓,入土为安。
为“竺派艺术”,历经周折重返舞台
很多越剧观众都觉得竺水招与竺小招母女俩的名字很特别,但是,却不知道竺小招之名也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从1951年在上海出生直到1975年从农村返城,竺小招的名字都叫刘克美,“竺小招”这个名字是父亲在1979年为她重返越剧舞台而起的一个艺名。在女儿重返越剧舞台前夕,父亲想到应该为她取一个有意义的艺名,她的父亲当时认为“你已经许多年没登台演出了,现在不知道演出效果怎么样?如今就上台小试几招吧。”然而,她父亲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自己萌生了灵感,于是,就根据这句话为女儿取了“竺小招”这个不一般的艺名。那时候,竺小招虽然多年未登台演戏,但是由于表演功底扎实,所以,她重返越剧舞台主演的第一部戏《双玉蝉》,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观众感慨地说,我们简直都分不清台上是水招还是小招了。
然而,竺小招重返越剧舞台却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应当说,竺小招是深爱越剧艺术的,与越剧的情缘也是很特殊、很深厚的,在“中国越剧十姐妹”的子女中,继承自己母亲表演艺术的唯有她一人;在竺家三姐妹中,从事越剧表演的也唯独只有她一人。可以说,自9岁那年母亲带她报考南京戏校,得到学校老师与母亲的双重培养,以及1962年与母亲首次在大华电影院同台演出越剧《莫愁女》后,她对越剧艺术产生的感情就越来越深。
但是,自从母亲因唱越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及母亲离世前后全家遭受那么严重的打击,都促使竺小招对越剧艺术由爱到“恨”。尤其在“文革”时期和下放到苏北农村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越剧”这两个字不是他们全家的荣誉和骄傲,而是一个巨大的“伤疤”,那时候,一家人谁都不愿意再提起它!
因此,当竺小招1975年从苏北灌云农村返回南京工作时,虽然南京文艺界许多老领导都希望她再回到下放前所在的南京越剧团,继承母亲竺水招的演艺事业,从事传统剧目的复排与新剧目的创作,但是,竺小招始终表示不愿意,因为她怕回到剧团,再看到母亲生前化妆与排戏的场所,她怕再见到母亲生前被批斗的地方,总之一句话:她怕再回到越剧团,想起曾发生过的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
由于竺小招不愿重返越剧舞台的态度十分坚决,南京市文化局领导只好将她分配到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于是,越剧演员竺小招就在该单位当了几年考古工作者,与同事们完成了明朝名臣徐达玄孙之墓的挖掘等多项考古任务。
但是,后来竺小招的思想经过一番斗争,还是有了改变,终于对越剧艺术由“恨”到爱。促使竺小招思想与情感发生转变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她考虑到母亲生前呕心沥血造就的“竺派唱腔”应当后继有人。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天,竺小招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十姐妹的昨天与今天》的文章,当她读到“著名越剧演员尹桂芳腿都站不稳还坚持上台演出”这一句话时,眼含热泪,读不下去了,老一辈越剧表演艺术家如此敬业的精神,让竺小招内心深受震动。于是,为了越剧艺术的明天,竺小招放弃了一切个人恩怨,于1979年春季主动向南京文化局的领导提出要求,愿意回到离别多年的南京市越剧团。
竺小招回到南京市越剧团之后,与陶琪等越剧名角为广大观众演出了一部部传统与新编的剧目。观众最爱看竺小招主演的剧目当然是《柳毅传书》,由于竺小招与母亲的形象与演技颇为相似,因此,人们在舞台上一看到竺小招,就仿佛又见到了竺水招的身影。
2006年,中国越剧节在浙江绍兴举办期间,竺小招和陶琪主演的大型神话越剧《柳毅传书》荣获金奖,她俩均被评为当届艺术节的“十佳演员”。
“清清白白做人”,是母亲留给女儿宝贵的精神财富
越剧名家竺水招生前生活朴素,为人真诚。她虽然是一位著名演员,但平时最爱穿很普通的布衣布鞋,冬天喜爱围一条洁白的围巾。1964年,竺水招参加第三届人代会期间,得知国家主席刘少奇每月工资300元,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每个月拿296元工资显得太高了。于是从北京返回南京越剧团之后,竺水招主动向越剧团领导提出,将她的工资减去100元。自己主动要求降低工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恐怕都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母亲竺水招高尚的艺德与品行,对女儿竺小招的为艺为人影响很大。近年来,虽然竺小招参加新戏创作、舞台演出和拍摄戏曲专题片十分繁忙,但是为了越剧艺术后继有人,她抽出时间精心培养郑飞儿、孙静、段瑞芬、孙婷涯等越剧弟子,不仅向她们毫无保留地传授表演技巧,而且还经常用母亲竺水招生前常说的一段话教育她们:“学戏要先学会做人,要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当然,竺小招在对弟子们言传身教时,更加注重以身作则。竺小招带领南京越剧团演员到杭州参加“全国越剧大奖赛”那一年,在金奖的入选演员中,她的得意弟子孙静与本剧团的另一名女演员得分竟然完全一致,然而按照大赛规定与获奖名额,两人必须要有一人落选。“我作为大奖赛的评委,当然希望她们都能得到这项最高的荣誉,但事实上是绝不可能的。”于是,竺小招就主动向大奖赛的主任评委建议:如果两人要取消一个,那就取消我的弟子孙静。评委们听她这么说,都感到出乎意料。当孙静得知恩师竺小招的这一想法后,当然思想有情绪,感到怎么也想不通。孙静认为:“我是你竺小招的弟子,怎么一点光也沾不上呢?”为做好弟子的思想工作,竺小招耐心地开导孙静,让孙静知道平时在剧团辅导会尽心尽力帮助你,但在这个时候,我竺小招是决不会为你提供任何帮助的,谁让你是竺小招的弟子呢
当这次大奖赛结束回到南京后,竺小招继续鼓励弟子孙静,加倍地向她传授表演技巧。时隔不久,孙静在“江苏省戏曲大奖赛”上获得了金奖,后来,她又以优异的演技,在“全国‘红梅杯’戏曲大奖赛”上,荣获了大奖赛的最高奖——“红梅奖”。
(作者单位:《江苏工人报》社,江苏南京210024)
惯例碎碎念:
这篇文章是2008年的,我当时没有看到,只是2015年以后重归越剧圈子,媒体太发达了,才看到的。
上半部分基本不用看,下半部分其实她有时候也谈到过,有些则从未提过。
和很多那个时代的子女不一样,她对于这部分往事基本上处于一种关闭心态,如果不是引导,她就不提。但我觉得引导太残酷了,有些部分让往事逝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她给她父母的墓上面也只一副对联,连她妈妈是“唱越剧的”,都只字未提,实在是很……很好。

(一)
那么之所以忽然又提到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引导。2005前后有一篇文章,一个电视采访相当有名的,不知有没人有些印象。言清卿回忆他的母亲,很小的孩子,突然间没有了母亲,他认为继父并不曾做到许诺的那样,一个人茫茫然在外飘荡。有一天飘到了殡仪馆,用其母亲的原名,得回了她的骨灰。自那以后,他把言慧珠的骨灰放在床中间,日日夜夜,母子都在一起。言清卿说:后来给走掉的人做追悼会,像上官云珠等都只衣冠而已,可他还是有妈妈的。
这系列采访是和章女士一篇《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差不多时候一起出来的,章女士写得好,而言清卿的回忆在当时颇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因为那个时代,渐渐的,在我们记忆中,早已模糊,远去,淡忘,……甚至无人知晓原本模样。
小招老师这篇回忆恰好在这个以后出炉的,所以我不得不因此怀疑,她其实是受到了些许引导,有了些许触动,才会愿意把沉封在千尺之下的事情透露一点点。但她照样儿不肯煽情,她说,这么做是考虑到母亲生前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虽然当了演员有了名气, 但千万不能忘本,永远不能忘记农村。”
一点点心酸,一点点曲衷。我就想到86年的时候,帮尹桂芳办流派演唱会,她自己脚上挂着几十斤重的压铁来支撑重心,彩排时看到戚雅仙叫着“先生”跑上台来,顿时哈哈大笑。她还笑得忘记把小话筒摘下来,彩排有很多观众进场,戚雅仙抚额:倒底笑什么?你要是明天正式演出,也这样笑就好看了。……她笑了半天,说:那时演《屈原》,你的婵娟叫着“先生”跑上台来,多年轻多苗条啊,现在你发福好厉害啊。
大抵这话太直率了,她觉得不妥,严肃的补充:我们这样大年纪,还能上台演出,感谢党感谢祖国呀。
但是没什么,小招老师经过这一次引导,以后的态度,似乎就是:说都说了,再说一遍不是问题。我后来似乎在别的地方也曾看到过。算是一种变相的“打开”了。
(二)
言清卿的叙述是第一次冲击,老虎也这样说,我又看到潘虹的自述——她10岁,在上海龙华领到其父骨灰,万里迢迢一路捧回哈尔滨。
心里似乎有了一种做梦都能做到实处的沉甸甸:哦,那是那样一个时代呀。
就是人死灯未灭,依然你在右我在左,划清界限,不可混淆。人性的幽微,在此时并不需要。
(三)
到了八十年代,却当真人死灯寂灭。
竺水招,已经回不来了。

中国三四十年代黄金年华的一整代艺术家
大约是整个时空中最坚强、最有韧性、也最善于寻找真我的一代艺术家
不要忘记她们,她们书写并阐释了崭新的中国艺术史
代表了最后具备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积极美学
她们不写“阴翳”,不存在“迷惘的一代”,她们流光溢彩

扫描或长按ErWeiMa“竺音清响”
点击右上角|转发或者分享朋友圈
【为gongzhong号能在信息流里及时呈现,请
顺手点一下右下方的“在看”,谢谢!】
欢迎戏曲稿件,加我:muruojingf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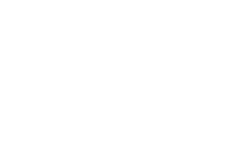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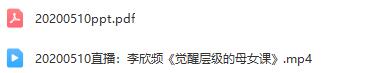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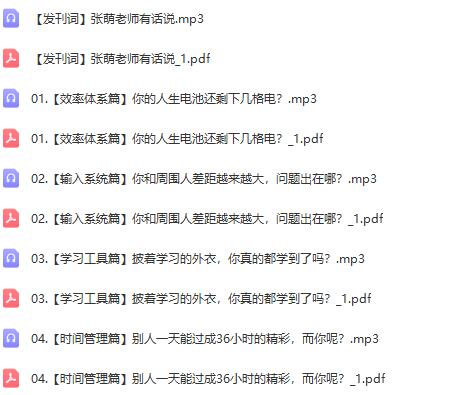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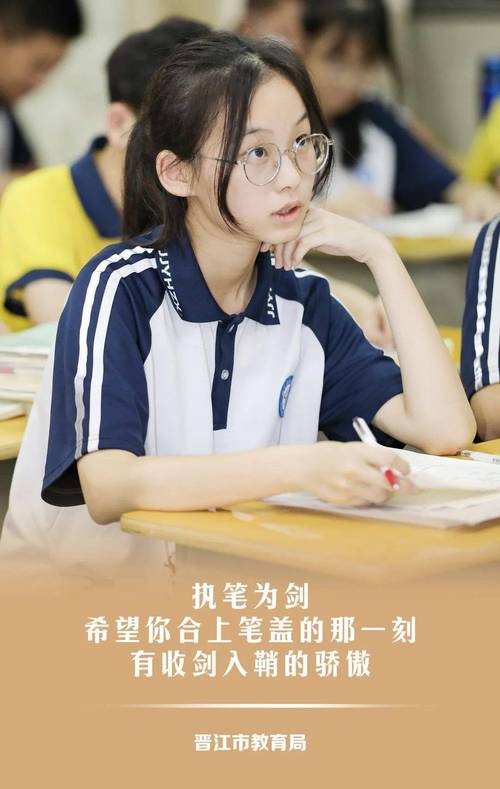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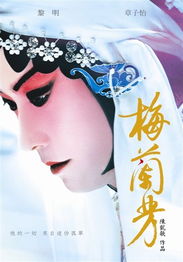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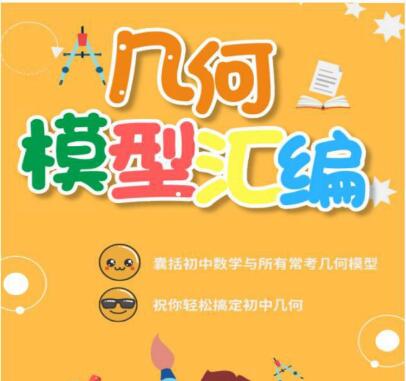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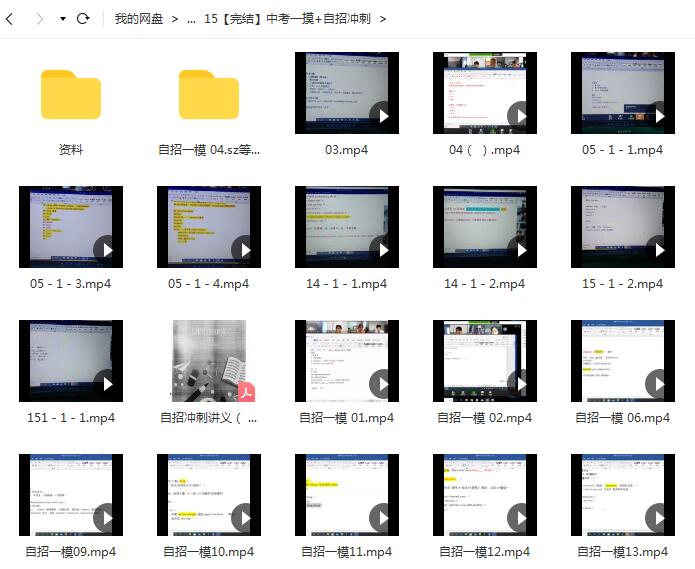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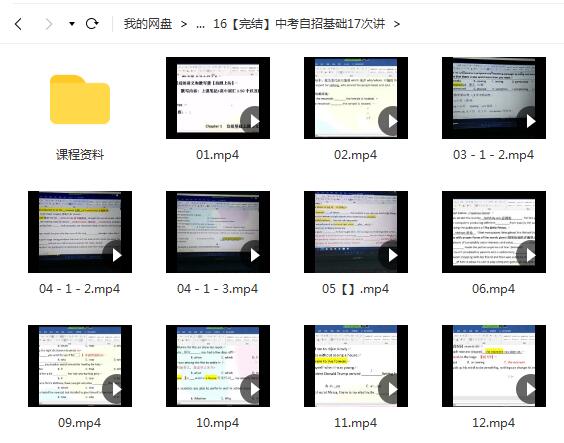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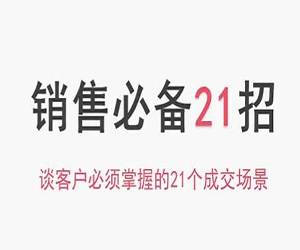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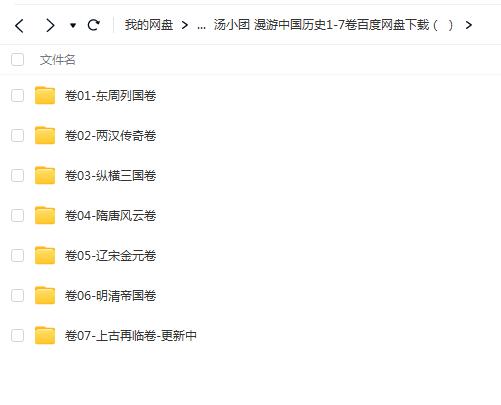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