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对丁玲的一次访谈
发布于 2021-11-29 17:39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新文学史料》2021.4期登载拙文“1984年我对丁玲的一次访谈”,编辑部高度重视这篇珍存37年的访谈记录文本,对所涉史料进行了缜密考订、在“历史现场”栏刊发全文。谨向《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致诚挚谢忱,即此照发,以飨本号订户和广大读者朋友。


1984年我对丁玲的一次访谈
张国祯
编者按:这是关于30多年前一次访谈的回顾,受访者所谈内容大多在今天已不是新史料了,然而言谈间丁玲的气息却扑面而来——这是历史现场,访谈者的设问也留有那时印记。为此“现场”呈现,以备研究。
80年代初,我读研毕业后仍在闽省电视台就职,负责文学组筹建电视剧部,多联络省内外作家组稿创作。1984年6月上旬,厦门文事密集季,我出差住在鼓浪屿幽静的省干休所,一早服务员小姑娘告诉我:作家丁玲就住在我们后面的小楼里呢,还有她丈夫陈明和另一位作家。我闻讯大喜,我想如能求得两三小时,和重回文学界的前辈重要人物丁玲作访谈,追溯新文学三人行,岂非甲子一遇良机? 当即毫不迟疑、前去拜访求教。
叩开丁玲前辈的房门,我持记者证,说明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期盼就前辈的文学历程、胡也频文学成就等向丁玲老师求教访谈。安然质朴的丁玲老前辈,花白头发,神态安祥,双目明亮有神,对我这不速之客似在端详审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请求。陈明老师说,他们此次是应邀到厦大参加“丁玲创作学术研讨会”,他对我有问有答,不使冷场,并介绍那位身材壮硕的作家是安徽省作协的陈登科,他俩无拘束地照样聊着北京作协轶事什么的。少顷丁玲问我原本就是福州人吗,像对这一点较有兴趣。
我看她似乎不会有什么明确反应,便告辞退出。此时,丁玲虽已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政协亮相,从政坛和文艺界报道高层恢复职务的情况看,丁玲的身份似还有些许模糊之感。是否因为如此,她还未完全恢复自如呢?
回到福州一周多后,我忽接省作协办公室张是廉主任来电,说:丁玲同志从厦门到了福州,明天下午准备安排时间和你谈谈,你不是找过她吗。我惊喜地问,是她本人主动和你们说的吗?张是廉告诉我:丁玲到福州后向省作协了解你个人情况,我们告诉她你是我会会员,现代文学研究做得不错的,是省电视台文学组组长,她听了挺高兴,马上就表示要和你谈,会详谈你想了解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丁玲是项南书记请来厦门疗养和写作的,三年前她刚平反项南就请她到厦门来,在鼓浪屿住了几个月写了不少文章、资料;这次再来出席在厦大开的丁玲创作研讨会,返程特地再来福州看看。然后老张郑重地给我布置了任务:帮丁玲同志找找胡也频故居,她想去看看,但不想惊动太多、特别是不要惊动胡家的人,你就把她的这次访问给安排好吧!
我心里顿时明朗而神思联翩。三年前项南书记才到福建上任几天,就邀请刚平反的老作家丁玲来厦门住,表现出作为改革开放杰出领导人反“左”纠偏的鲜明立场、高度尊重文艺家的政治家胸怀器度;也更能理解老作家的笃定信念、清醒警觉又不懈进取的精神。
于是,我如约来到省府温泉宾馆拜访老作家丁玲,作了两次半天访谈,并陪同她夜访胡也频故居。
丁玲一改初见时的沉静少言,放开思路侃侃而谈新文学往事,语速流畅,显出文坛宿将博览世事、强记从容、举重若轻的本色,陈明则始终在旁不时插话、不断作些解释说明。
访谈记录当时谨遵访主之嘱,“近期不必示于若干人”(主要指胡家亲属),并说到一些具体原因;不觉之间30年过去了。

胡也频故居
情系胡也频:丁胡结合真实经过
丁: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我上一次在厦门没有和你多谈,是因为不了解而有顾虑,顾虑很多的啊(笑)!以前我也没有机会来过也频的故乡故居,听说有一些亲属事情也会不少,也频在的时候就交代过我,我以前的文章里也写到过我们当年遇到他家人的一些事情。
这次我到福州来和省作协的同志了解了(你的)情况,就放心了,我可以和你充分地谈你想了解的事,一个半天肯定不够,两个半天,谈不完还可以接着再谈。你已经知道也频故居在哪了是吗,好啊!回头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带我们到故居去看看吧。
张:好的,太感谢您了!能有这个学习机会,听您来充分回忆、追述几十年前文学上的宝贵历程,我觉得真是太幸运了!您能先谈谈您最早和胡也频怎么认识的吗,还有沈从文,那时候你们都是什么样的文学青年呢?
丁:嗯,我认识胡也频是在1925年,在北京的一些文学青年组织了文学社团“无须社”活动的时候,胡也频是“无须社”最热心的一个成员啦。这些文学青年,很多是在北大所在的北京东城沙滩附近住,住在银闸公寓、小胡同里,很冷的,也在那里聚会,或者在北海聚会。成员有王森然、于赓虞、焦菊隐和许超远(许超远是也频的福州中学同学)等等,前面几位是北大学生。我有时也参加的。那时候我不爱讲话。我们有时到北大听课,那时(校外青年)到北大听课是自由的。
张:您到北京的时候已经上过上海大学了吧?您那时的思想比无须社成员是不是更激进一些?
丁:是的。我那时在北京听课学习曾经想学做电影。思想上面,我当时是一直在求索,有点一切都要怀疑,什么都不轻信,也可以说是更激进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就认识了胡也频。那时候的胡也频瘦瘦的,很清秀,平时看起来挺温和,其实他内里性格很暴烈,爱打抱不平,朋友给他起的绰号叫“霹雳火”,但是他从来不讲朋友的坏话,别人对他说某熟人如何如何、对他怎么不好什么的,他都只是笑笑、并不去理会的。
张:您在文章里说的他上海军学校之前当过“小有天”酒店的学徒,我找了当年在这家店做事的老人了解,“小有天”是福州老板开的,在福州和上海都有店铺,我找到了我家附近街道有位80多岁老人是胡也频当学徒时的工友,我要再找他聊聊。
丁:嗯,那好。也频说过那时他还很小,年纪大的学徒爱欺负师弟。他在上海时曾经回福州去过,他们听说他成名了,到上海来谋生的还来找过他,他对他们都很好。(据胡当年工友谈话证实,胡也频在上海办刊物的时候确实回福州去过,那些人认为胡“出仕”了。——张注) 那时候经过胡也频,我也认识了沈从文,确实是通过胡也频认识的。胡也频那时先后给《京报副刊》《晨报副刊》都当过兼职编辑,当然首先是自己写稿创作,投得多了、人家让他当兼职编辑。1925年初他在当《京报副刊》编辑时,发表了沈从文(笔名“休芸芸”)的一篇稿子,这是沈从文的文章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两人因此认识了,成为好朋友。他很高兴地请沈从文吃饭,胡也频就是这么个热心人。这时胡的朋友中荆有麟是个很活动的人物,办《京报副刊》主要是他活动搞起来的。听说后来是军统解放后被处决了。沈从文那时也结识不少文学青年,燕京大学学生张采真,就是他与胡也频的好朋友,张采真很有才华,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如愿》等很多作品——《如愿》到解放后再版还是用的张采真翻译的文本,张采真后来在武汉参加革命,很年轻就担任过中共的重要职务、二十几岁就牺牲了;那时张的思想倾向就是左翼的(这里讲的“左翼”指共产党——张注)。但沈从文那时是中翼的,后来也一直是;胡也频的思想在那时候也还是中翼。我自己那时常有愤激的情绪,比他们还要激烈一些,但也不是共产党。沈从文很佩服革命者张采真,他一直是佩服。
张:从作品看,沈从文那时总体是不如您激进,他是表现乡土人物情感更多、更细吧。我读到的胡也频的作品挺有激情的,短篇小说写的多是清贫的写作人、或是青年艺术家形象,文笔清新流利,写得很好。
丁:是的,那些短篇小说不错。但是胡也频这个人在交往中有他的狂士风度。他虽然给京报、晨报做副刊编辑,但他和晨报主编陈博生、报社大股东刘老板(某电灯公司老板)相处也从来不逢迎,都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
胡也频是诗人气质,他平时话不多,爱读外国诗。我认为他新诗写得好。他爱看歌德、席勒的诗。胡也频开始写诗的时候就喜欢象征派风格,但那时象征派诗歌译成中文的并不多啊,他认识李金发,很欣赏李金发的象征派诗作,胡也频的诗歌创作受到李金发诗的影响,他没事时经常揣摩李的诗作。他和李金发好像曾在一起办过一段报纸副刊(是不是一起办京报副刊,记不大清楚了),那时还曾和邵飘萍(著名的进步报人)接触交往过,邵飘萍很有才。
张:我前一段主要研究现代小说,我觉得胡也频的抒情小说写得很好,在现代文学里排得上,现在大学中文系教材现代小说选里就有他的两篇。
丁:胡也频小说、散文、诗歌都写,都写得好的;我认为胡也频的现代诗是写得更好的,他个人气质主要是诗人,他的诗是有象征派味道,又比李金发的好懂,更好一些。胡也频的主要文学成就应该是他的诗歌创作,我看至今对他的诗作研究得还是很不够的。(我注意到当提及胡的创作整体评价时,丁强调诗作,没有提她曾强调胡后来的理想主义中长篇小说作品。——张注)
沈从文这时候对我们俩的关系其实并不很清楚,他在写的文章(指“记胡也频”、“记丁玲”——张注)里说,“这时候(1926)他们已同居(指结婚了)”,文章里说“前年我问丁玲,她不置可否”,还说我们是回湖南老家我妈妈“给办的喜事”……。其实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崇尚独立,不要传统俗套,新潮人士、新文学青年一般都不要“结婚”(不办),头两年我们就是朋友、并没有“结婚”,他到我家找我、也根本没有办什么喜事,并不像外边说的那样。(这是丁玲重要补白,说明并非胡到常德他们才结合。——张注)我原以为胡也频和我同岁(他看起来很年轻),后来看材料上才知他是1903年的,比我还大一岁。
1926年我和胡也频同返北京。那时(指和胡要好之前—张注)我本并不想恋爱,我对他的好感主要就是他的纯真。在那之前(指和胡到香山公开同居前—张注),有很多朋友来和我说:何必要找他呢?一个个的这么说,我因此被激怒了,就干脆带他一起到香山去租房子住了。
我说的这些朋友主要都是女子补习学校的同学,有左须知、曹孟君、王佩群、周登馥等等,这几个后来都是国民党的,还有夏之栩,她后来好像叫丁琪(这个要查证一下)。(笔者查证丁玲所提她当年几位女伴以及前述“无须社”诸成员姓名均无误,甚为佩服丁玲八旬老人之强记——张注)
张:您是说去常德之前,你们已经要好了?几位女友劝阻过您,而您根本不为所动是吗?
丁:是的,我有我的判断、我的选择,不会听从别人的。

胡、丁、沈之新文学三人行
张:我看史料,是不是那时有一次您给鲁迅先生写信,鲁迅以为是沈从文居然化名女子给他写信,文章还说到这“很无聊”?
丁:是有这么回事。我那时思想上看不到前景嘛,就想向鲁迅这样我崇敬的有思想的人问询和抒发,没什么具体的。我那时还没发表什么作品、鲁迅不会知道我的;沈从文投稿多,他的字别人觉得秀气,鲁迅看了我信上的字觉得像沈的字了,在文章里捎带讽刺一下(笑)。胡也频因此为沈从文打抱不平,他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说明信,说这信确实是一名叫丁玲的女子写的、说自己就是丁玲弟弟,和沈从文无关,鲁迅没再回答,当时也许更不高兴吧!也频就爱打抱不平,别人不会去管的,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张:你们当时都已经崭露头角,是不是在一起酝酿过成立一个文学社呢?
丁:当时我们的创作倾向和《语丝》很接近,但是《语丝》那时没有稿费、是同人刊物,他们(胡、沈)觉得不好意思再插进去,不是人家不要,思想上并没有隔阂的;《晨副》多少能解决生活困难,稿费从2元、5元起,最多到一个月能到50元。
张:那很不少了啊!
丁:那是不稳定的啊。我们住在香山的时候曾经很苦闷。他不要写诗了,有个爱人就很满足,那时他好像是这样的。我更苦闷。也频感情上很单纯,也可以说感情上比较狭小一点。他平时没多少话,有时很内向,发起脾气又很火爆。有时我们也会吵架。前面我说他有“狂士”的一面,其实他更“狷”得很,对我是如同对神仙一般。
张:您是说他有狂狷之气,像狂士又更像狷者吗?
丁:是的。但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后来他母亲(来上海)见到我,拿金戒指要给我,他见了马上对她母亲疾言厉色地给推了回去,他是不让像传统老规矩对待新过门儿媳妇那样对待我。
那时侯我们认识了刘开渠等多位学艺术的朋友,几个人后来都对我更好。
也频一直很勤奋做事,很勤奋地写象征派风格的现代诗,勤奋地做编辑、创作。
歧路口:徘徊与奔突
丁:1926到1927年那段时间,我是最感寂寞的,自己常苦思冥想,也不怎么参加胡也频他们与报刊编辑们的交往活动。我来北京有自己的理想,本来曾在中国大学学艺术学的。我那时是想要学做电影的。后来在那休学了。这门课当时大学里开得很少。
我之前曾参加拍过一次电影。1926年春,我从北京到上海去了一趟,是洪深导演答应让我去,要给我介绍拍电影的事,但是到上海转了一阵,影戏公司、南国社都去看了,都不行,没有事可以做。我好生气。
张:您找的就是田汉、洪深他们那个创作戏剧的南国社吧?
丁:是的。到后来我看出他们自己做得也是挺难的。可是那时候我不这么想,我就想你既然答应我、来了又不能兑现,算怎么回事呢?气得我回头就走了。我再也不想理他们了。(这是丁玲主动谈到她最早参与拍电影的经历,以及她的演艺工作为何没有继续下去。——张注)可我这时又不想再到北京去了,就让也频一个人返回北京去。他到了北京又不断来信,不断地催我去北京。
这时候我曾想去找共产党,但是一时又没找到关系,因为从1924年我离开上海到北京以后,和共产党里的朋友一时都没了联系。那时也频还没想去找共产党。
在也频一再催促下,我还是先返回北京,再作安排。有了前一段的寻路的经历,催生了我写《梦珂》和早期几篇小说。《小说月报》(1927年)郑振铎、叶圣陶很快给发表了。
张:您的作品当时影响就挺大,虽比他们后发一点、引起的度却更高?20年代末您和胡也频、沈从文都参加文学研究会了吧?
丁:我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以来,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叶圣陶他们经常会给扶植照顾。从一开始他们给我的稿酬就是3元/千字。《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发在《小说月报》上的。胡也频沈从文他们俩比我先发过,1元、2元都拿过。这也可能跟你说的受情况有关吧!
文学研究会那时是相对松散型的社团,它联络了很多作者,(最多的时候据说名册上有一百七八十人吧)。我和胡也频那时也没参加别的社团,列名在文学研究会是它的后期阶段了。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是郑振铎给了胡也频不少支持,他主持的《东方》杂志给胡也频作品发表过连载。他们给我们出版作品小册子(出集子),也是给了大力支持的。
我这时期开始文章逐渐写得更勤了、密集发表得也多了。
我们写作,总的来说是以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为主的,但对真正的方向和出路那时并不是很清楚。对早期共产党人思想上钦佩,主要是敬佩。我们俩写作精神上总的是写实主义的,写得比较敏感、更敏锐一点。
张:那时你们两位的创作和文学研究会一些作者比起来感觉要更前卫,沈雁冰评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发出了“负着五四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啊!您那时真实是什么样一种精神状态,再后来又是怎么完成转型的呢?
丁:我写莎菲女士是写这么个苦闷悲观到了极点的女子,她当然是个文学典型形象;后来有些人说“莎菲”就是丁玲,这个说法很荒唐。我在那时是有苦闷,那是还没找到正确道路的苦闷,我在不断苦思,但我自己当然不会像“莎菲女士”那样悲观到要自杀。那时我有那么个女同学,就是抑郁而死。我要是那样怎么能走到左联道路上呢?
接下来那段时间(1927年),我敬佩的向警予牺牲了,张采真牺牲了……我的很多亲戚、很多共产党里边的朋友都死了。胡也频也有共产党里的朋友牺牲了,他这时也有了这想法,(想去参加革命),不过还不大明确。这就是我们那时的思想状态。
夜访胡家故居
在温泉宾馆那个下午访谈之后,翌日傍晚,遵丁玲老师之嘱,我和福建广播电视报摄影记者小谢开车作为丁玲、陈明老师轿车的前导,带领寻访老城区胡也频故居。车辆在乌山东南麓紧窄的街巷左盘右转,来到城边街一条短巷“卖鸡弄”里的一座老厝。之前丁玲老师对我说过,胡也频向她描述过童年故居和乌山的美好记忆,此时她的眼前定是浮现着那位乌山少年吧。
丁玲老人下车环顾短巷老墙,走进这颇显古旧而保存尚好的宅院,端详这座清末单进木构民居。厅堂里两家居民刚在收拾起饭桌,热情招呼远来的稀客。我们已了解证实,胡家虽自清末起两代人曾为宅主,但民初胡家经济渐走下坡、20年代末就已将此宅售出,丁玲来时这里住户几经迁易、早已和胡家完全没有关系。两户老人只是听说一点胡也频烈士和他家族的事。丁玲老人安然坐在厅堂的藤椅上、仔细打量四周,饶有兴味地向惊喜的居民们询问老屋的事。

1984年6月丁玲夜访福州胡也频故居。谢思秋摄,张国祯供图
一个甲子前从这宅院走出的那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志士,和当年明眸睿思的丁玲结识相知、叱咤风云,7年后他又流星般离去53年了……饱经风霜的她,说起胡也频来仍是一往情深、有血有肉真实而富有个性的伴侣。此时用心悄然寻找到胡家故居,像阔别重返的燕子眷恋着老屋,观之听之令人动容。
丁玲和住户居民亲切地聊了近一个小时,关心地问到这座烈士故居的变迁、保护情况和前景。她没有许愿,只是希望住户能配合政府保护好烈士故居老屋。丁玲来访离闽后项南书记指示福州市有关部门研究保护这座故居事宜。
从北京到沪上:丁胡沈创作路/合办“红黑”
张:上次您说到1927、28年您和胡也频在苦思、奔突着往前行。
丁:是的。1927年底,连沈从文都到上海去了。北京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我们终于相约南下。让我们下这决心之一的,有冯雪峰和我们的一次谈话。
这年冬天,我们俩在北京朋友王三辛那里见到冯雪峰,冯建议我们南下,他对形势有一番分析。我们挺为他的建议所动。本来我们就在反复考虑的。后来我们一起到和平里王会悟(李达夫人)住处那一起商量过。我们到了杭州一段后,冯雪峰主动给我们在杭州找了个住的地方。
过年我们就南下,也频和沈从文在南方见了面,又商量起合办文学园地了。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明确地想要革命。这时的冯雪峰并没有和我们谈什么革命的事,他是分析新文化运动的走向、新文学的发展,重心正在移到南方。
然后这一段,我们是在杭州—上海这边从事写作活动的。这时我也在连续写作,在不断发文章、出集子了,不是光是也频在发文章,小家庭的生活就比较好过了些。
我们后来曾经在西湖附近小山旁租了房子住。冯雪峰1928年初那时候来过,他和我们俩有交往,原来在北京就熟悉的。后来我们到上海是租住在淮海路一带、离瑞金二路医院近,冯雪峰住北四川路,离得比较远,来往不多。
张:这时候冒头的青年作家是不是创作都在分化呢,您、胡也频、沈从文在文学方面都受什么影响比较多?
丁:嗯,有各种趋势吧。各人的背景都不相同。我们到上海,这时看的外国书比较多了,对创作研究更深入了。胡也频看翻译作品看得更多了,前面说过的。后来翻译的文艺理论书他也看的更多了。
我看外国作品比他们看得要更仔细一些,我不是一览而过的,我注意的作品会深入去琢磨透。
沈从文以前看中国书、看史传多,他特别佩服湘西将领陈渠珍。沈从文年轻时在湘西军队当兵、在陈渠珍手下当过两三年军部书记(文书),很受陈的熏陶。后来他特别佩服陈写的《艽野尘梦》。沈从文的发展受陈渠珍对他影响很深。
这时期沈对外国小说也看得多些了,曾见他常看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李霁野的翻译作品。
张:我确实在沈从文文章里看他不止一两次提到过这些,他说过从传奇性的作品《艽野尘梦》里学到很多。也说过他写短篇小说从莫泊桑作品学讲故事。你们发展的趋向好像并不完全一样,那为什么会合办起文学副刊和刊物的呢?
丁:那时我们三人一起来办副刊,出《红黑》、《人间》期刊,自己做出版,也叫“红黑”出版社。当时的想法,最主要的是不要受书商、资本家的剥削,自己干自己要做的文学事业。《红黑》是从“中央日报”承包版面出来办文艺副刊;起名“红黑”,是湖南话,横竖要干、死活都要干的意思,表示坚决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组稿写稿三人一起做,组织工作、事务性的事情是也频为主来做。也频他有凝聚力。
这时我们在上海淮海路相邻的瑞金二路医院附近租住了那一处小房子,我们自己戏称“花园房”,我们用一个打气的煤油炉做菜,沈从文有时也搭伙。在上海生活,都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吃菜的,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经常就是熬熬菜,胡也频有时还像福州老百姓那样、没什么菜就用猪油拌饭吃。
张:这种饭我们在福州小时候是没什么菜时才要吃的。你们是在艰苦创业啊!
丁:我们手头并没什么可以周转的资金。沈从文是不大会理财的。他还念念不忘培养他的九妹,为培养他的九妹他是竭尽全力的。也频承担了外面广泛联络和报刊理财的各种事情。胡也频这个人和一般文人不大一样,他是凡事都能顶起来的,里里外外、文的武的,包括工人做的那些事他都做得来。
沈从文后来又受聘到中国公学去教书(胡适就任校长后聘任沈教课)。
沈从文佩服革命者;沈并非胡适他们培养的
张:办“红黑”时间也不太长吧?结束了“红黑”的工作以后,和沈从文就不在一起了吧?后来胡也频被捕、被秘密杀害以后,沈从文写了《记胡也频》,还陪送您和孩子回湖南了吗?
丁:是的。也频牺牲以后,我就带着孩子搬到李达家去住,是在租界里面、淡水路;李达夫人王会悟给沈从文写信,告知他这个情况,王会悟建议沈把我母亲从湖南接来告状,控告他们秘密绑架杀害作家、文化界人士。
张:胡崇轩(胡也频)是沈从文最早的文学知己,沈从文文章里总是称他“海军学生”,我从当年报纸读到连载的原作,感觉他虽然不能像胡也频那样英勇,但还是很钦敬、赞美胡也频的;他失去了这位原先的伙伴,看得出来当时也很难过的啊。
丁:他是钦佩胡也频,他做不了也频的事,就像更早时对张采真那样。当时他也对外声明,自己和胡是不同政治观点的。沈从文来和我们商量后,决定陪送我带孩子回湖南常德我母亲那去。回去的盘缠费用,是郑振铎立即派人借给我们的200元。沈从文一路送我们乘车回到湖南,在我家住了两天。
张:哦,是这样的啊!我看民国那时的报刊,当年支持保护您、后来发动营救您的文化界人士很多的啊!
丁:是的。也频刚被捕的时候沈从文是参加奔走活动过。胡也频和沈从文一起做事时间不少。也频对我说,我看到的湖南人,男人都像女人、女人做事反倒又像男人?这话是从我们朋友唐友仁(湖南人)讲起来,也是讲沈从文。他说沈从文有时显得懦弱、有时又有点糊涂。沈从文有自卑感,是有心理学上的“自卑情结”。有时候很胆小,解放初那时风声鹤唳,有一阵差点要不行了(要自杀)。(—他以为共产党要跟他算账呢。)那时候经过安慰开导了他才好了。沈从文后来还谈到张采真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一直对张是很崇敬,自愧不如,但他自己不能去做的。
沈从文后来由于生活上的原因,跟胡适、徐志摩新月派他们接近,胡适聘他到中国公学教课、讲新文学。《新月》发了一些沈从文的文章。但是新月社声称是他们发现和扶植了青年作者沈从文,其实并不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发沈从文的文章要更早、更多。也频和我和胡、徐不接近。
张:郁达夫也更早过沈从文吧,他作为编辑不是1924年冬就去访问过这个年轻作者,看他缩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写稿子,回来写了《致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吗?
丁(点头):是的。郁达夫和新月社徐志摩他们不是一派的。
张:您是说沈从文成为作家,并不是靠胡适徐志摩扶植的是吧?
丁:对。胡适、徐志摩其实对沈从文并没有像对朱湘、陈梦家那样重视,他们是把朱湘、陈梦家看成是他们发现扶植的真正“新星”,那才是他们心里真正的“文坛新秀”。他们对沈从文文章的欣赏,是有些猎奇的成分,并没有那么重视。1928年在上海,胡适、徐志摩到沈从文住处去看他,沈从文显得非常拘谨。他心里还是羡慕他们的。朱湘在生活上和胡适徐志摩他们更接近。
张:是啊,我觉得沈从文最大的文学成就是在乡土小说和乡土散文创作方面,这些和新月派并没有什么关联。他也许曾经希望在政治方面保持超党派的中立?
丁:嗯。沈从文也不会成为胡适、徐志摩那样的洋派绅士。沈从文自己从来都穿中山装、中式服装,从不穿西装的,他不是西派的。可他对他的九妹极娇宠的,一心要培养她成为上海现代闺秀。
沈从文创作的路子和新月派徐志摩他们也并不一样的。
沈从文以前是想超然不介入党派。
沈从文到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写了一些新文学的论文,结合教书吧,有的见解不一定正确,对《阿Q正传》这样受果戈里影响的文学作品就不理解。
沈从文后来和王平陵主办的《文艺月刊》较密切,常在这刊物上发表作品和评论。王平陵办《文艺月刊》态度看起来是取中间路线、也讲兼收并蓄。但王他实际上还是受国民党领导的,虽然他声明要做纯正的文艺。后来他的结局也很惨,到台湾去惨淡经营、60年代就累得病故了。
张:不过在严重白色恐怖的那时,从原版文章看沈从文对胡也频和您作为革命者都是怀有很崇敬之情,出书是遭到大删的、都接不起来啦。
丁:嗯,那时上海国民党当局新闻审查是控制很严。他的文章有的就寄到北平那边去发表,那边管的相对松一些。《记丁玲》最先就发在北平报纸副刊上吧。
张:是发表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了十来期的,我当时对比着抄录了,删改最多的一则达一两百字,凡是赞扬革命者的、讽刺当局的话都被删掉。
丁:嗯,你看得蛮仔细。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去了一趟,他让几个学生去看望了我母亲。他自己没来。
胡也频支撑办“红黑”和胡家的事
张:您说胡也频作为他家长子是很想给弟弟们开创道路的?
丁:是这样。才到杭州不久,也频一次和我在西湖岳坟那边散步,看到一个小孩很像他的小弟弟,也频说他弟弟在福州不会有出息的,他想把小弟弟带出来培养。没想到不久他的小弟弟(四弟)和母亲、还有三弟,真的来找他了!她以为我们已经自立门户、能照顾、提携家人了呢,就一直是凭她的想象啊。他们是先到的上海,住在一家福州人开的旅馆,然后随着我们的行程也来了杭州,我们到杭州开头还是住旅馆,他们也住到旅馆房间,也频本想搭个行军床,一起挤挤住下吧,他母亲说“睡帆布床会得肺病”,只好另开房间,呆了两天只好把他们送回去了。——刚好那几天我收到小说《阿毛姑娘》的稿费(提前付的),还能顶上这次接待家人的花费。
待我们开始做《红黑》、《人间》的时候,正好也频的父亲到上海来了一趟,他是带了凑上的1,000元钱,记得他是想到“小有天”来入股的,“小有天”是小有名气的菜馆,老板是福州人、也频父亲和他算是老朋友,—你知道也频少年时在福州“小有天”也做过短期的小伙计。这时也频和他父亲商量,先把这笔钱借给我们做出版资金,每月寄回30元利息回福州。从1928年末到29年,才半年钱就差不多花完了。后来到济南去,一方面也是为了去教书挣钱来还借款,在济南我们挣了钱就寄给也频父亲还钱。我母亲是大力支持我们的,她实际是从她的好朋友那凑的钱,寄来了350元钱,我们凑上还给也频的父亲。(胡家亲属八九十年代后写的回忆文章,还写到胡也频向他父亲借了多少还了多少钱,办红黑出版社盈亏的事。—张注)

胡也频故居-胡也频像
走向革命:胡也频非常适合做革命
张:那在这个阶段,胡也频和您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参加革命的呢?
丁:冯雪峰开始的时候(1927、28年)只是鼓励我们创作,并没有说让我们参加革命,我曾经当他面说要去干革命,他反问:你是小资产阶级,怎么参加革命呢?
我们是后来读了鲁迅、冯雪峰他们编译的那些文艺理论丛书,才真正理解了文化战线的革命。开始的时候冯雪峰他们和鲁迅也不一致,当时地下党在上海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思想论调都比较“左”,创造社还攻击鲁迅、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冯雪峰写评论的笔名是“画室”,“画室”开始的文章调子和鲁迅观点也不一样,有过交锋。后来上面(中共中央)叫他们要团结鲁迅,依靠鲁迅。鲁迅是通过柔石才认识了“画室”,后来“画室”和鲁迅相互了解、走到一起了,成为了同志和战友。
1928-29年之间,完成了这个关系的转变。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这时都被封闭了。进步文化界开始酝酿组织“左联”。也频和我的思想也在完成飞跃。筹备成立左联开始时,冯雪峰有一次来找胡也频,他俩单独谈了很久;开始他们对我还有所保密,后来就也不瞒我了。那是在胡也频要到济南去之前。
张:您是说胡也频实际上在济南表现完成了他朝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
丁:是的。去济南,胡也频冬天先去的,然后开春我也去了。是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俩教授推荐到省立济南高中去教书,有董每戡(研究戏剧理论的同仁)等人同去。北大毕业的作家董秋芳此时也到济南高中教国文。也频到济南高中大力宣传普罗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了青年学生拥戴的新思想新文学的亮星,和那边的众多学生、学生会主席冯毅之等人都相处得很融洽很好。他一改沉默少言的性格、变得活跃起来,要组织学生们成立进步文化组织“文学研究会”。
胡也频等于在那里做了学生运动,还支持了进步教授张默生当校长(这个人后来也并非变得不好、以前我对他曾有一点误会,后来我到四川特地向他表达了歉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抗。我去济南呆了一段、那年“五四”就在那,发现也频在那有着强大的影响啊。认识当时那里一名学生李士钊,后到上海学音乐、参加革命,写过这一段回忆(他研究蒲松龄、写过《武训先生传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其实并不向着国民党,何跟张默生通气、透露当局要抓胡也频等“赤共分子”的消息,张立即给了200元路费,资助保护了也频等人脱网。也频马上和冯毅之一起先到青岛、再一同乘船脱险回到上海。
也频1929年写的小说《到莫斯科去》,那是第一部这样的书,红色封面上印着大字。当时对革命者生活活动还不很熟悉。《光明在我们前面》写得更好一点,就有亲身感受到的革命者斗争的气氛了,当时还是很感人的。
我看到胡也频参加革命的表现,我对他说:你这一着又对了!你真的就适合做革命!也频这一段非常活跃,做了很多事情、效率特别高。党在上海筹组左联他先是选为“执委”,后来居然又被选上“工农文化委员会主席”、担任这个(职务)本来是要到江西苏区去参加会议的,听说原先的人选是冯乃超,冯这人性格比较温和(他的观点是很激进),由自由大同盟、左联、社科联几家组织一起选这个苏维埃的代表,可能觉得胡也频更像工农的代表吧!他当选了这个,就非常认真地不断到东方旅社去看何时开会、何时有事,本来准备2月27号开,后来一直延到11月才开。过不久,他就是又到那去开内部会时,被当局特务捕快一下子抓走了,损失了那一批党的重要干部。
张:胡也频和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他们左联五烈士就是这次牺牲的,进步文化阵线损失惨重啊!
丁:嗯,是啊。以前那段历史,内容非常丰富,有待你们去进一步挖掘、研究了!
——对了,我们早上接到通知,要提前返回北京,我们这次谈话只好暂告一个段落,回头继续保持联系吧!
现在研究工作的困难是伪史很多。比如有的人写自传就把自己什么功绩吹得很过分,这样的情况现在太多了,研究者一定要作细密研究,分清真假、弄清楚哪些是水分,去伪存真才行。
我这次和你谈的,都是我自己仔细回忆起来的真实材料,供你做研究参考,近期不要急于发表,这方面我回忆的情况你多研究就会理解了吧。
丁玲前辈最后介绍了冯夏熊、杨桂欣、王中忱几位研究者,还提到广州军区有老同志万正(解放初曾在公安部工作),他说有个黄理文(涉另一案子)、还有林肖霞,收集过三四十年代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和一些案子的很多历史资料,希望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他们。

编后记 丁玲、萧红,都是从民国一直“热”到当下的女作家。丁玲1984年接受采访,言谈举止,在采访者张国祯记录下,颇具“现场感”;……
作者的话:拨乱反正的70年代末由新文学史家发起、诸多前辈作家支持创办的《新文学史料》,四十多年来坚持高水准、纯学术、高信息量、高还原度,开卷令人如临史场,如闻先驱其声、如见前辈其人,是笔者学习现代文学以来心中的圣地。访谈录得以在此刊发,一遂夙愿!惟尽力将自己研究之经历和研习心得继续奉献给同道和读者朋友!再谢读者朋友们的热忱鼓励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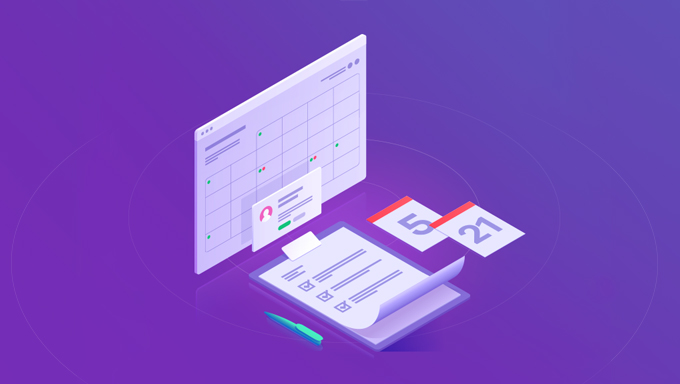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数据库] Oracle全套学习资料(88GB)绝对真实有效 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分享](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827e8782b7986957a2e8c6bbd10cf1ca.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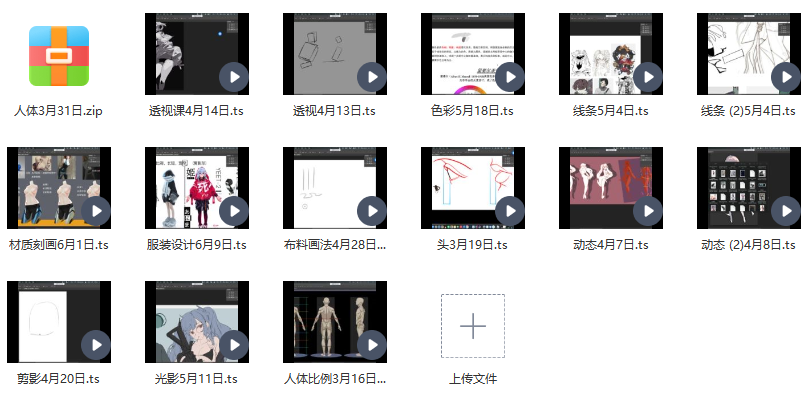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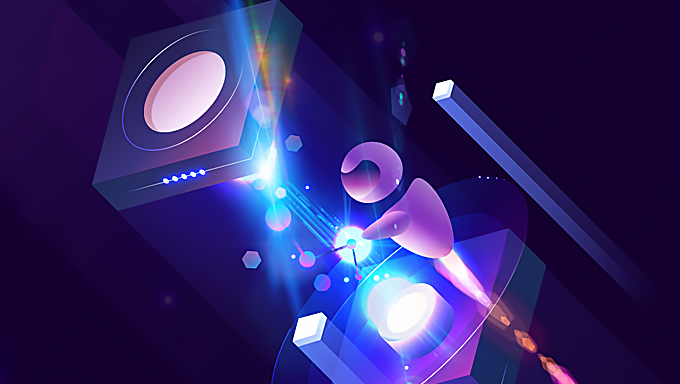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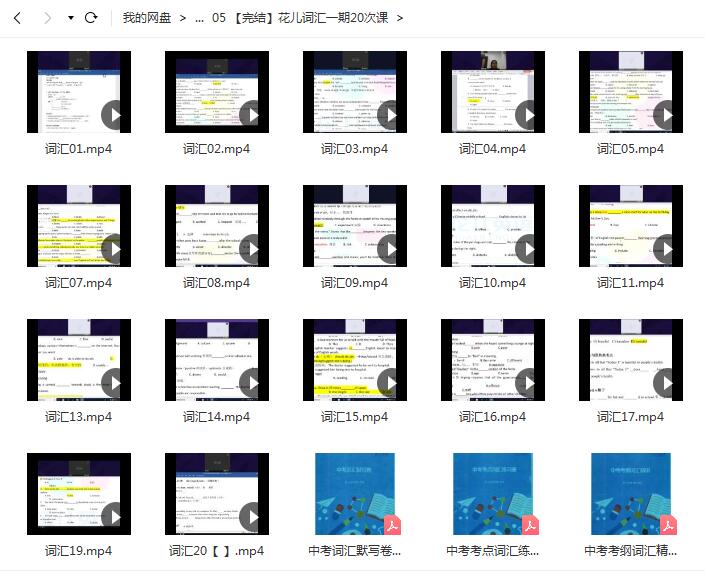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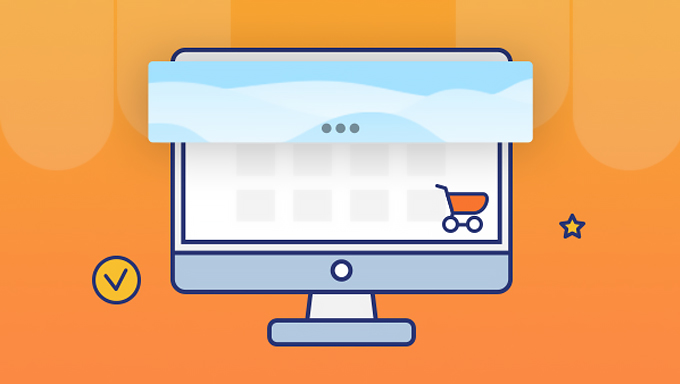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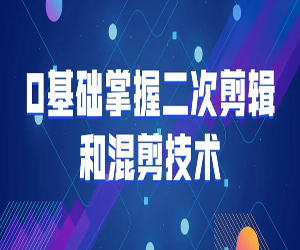


![【杨雅静】16次课搞定新概念一册语法16讲[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425ml/244-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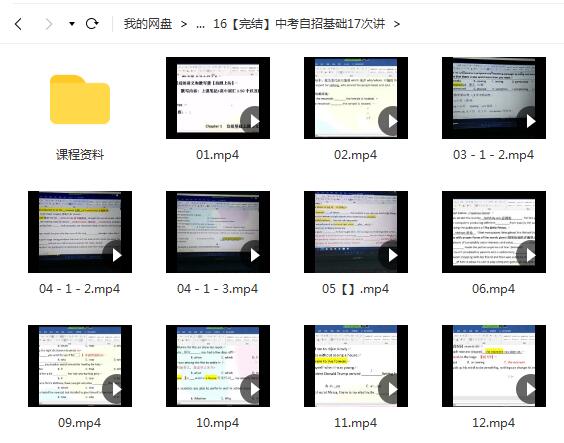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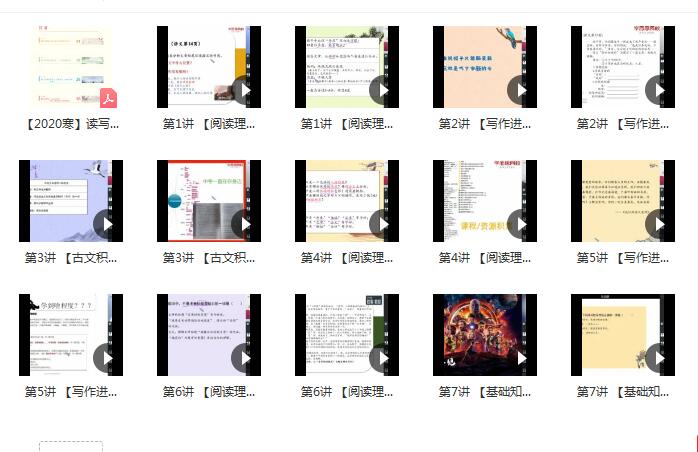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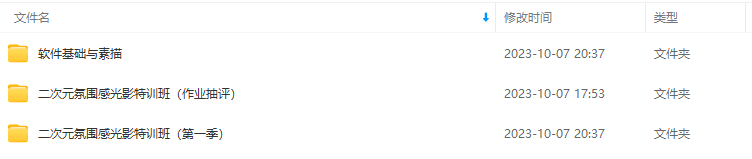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