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文学】鸟洲(第四章 碎发时代14)
发布于 2021-11-30 12:45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本平台联系号:378072574 欢迎转发分享给更多爱好者
然后在那一次的调位事件中怪兽和我坐到了中间组的第三排又或者是第四排,反正就是酱子的,那一次我们又多了一个同桌木木。木木那一年是从三中转来二中读高四的,说来也抽象,木木居然是我的学前班同学,十多年后我们再次坐在同一个教室去挤那座六月的桥。也是在那一次的调位事件中,虹虹、亚丫、一鸣再次成为我们的前排邻居。大颠也就酱子出其不意地坐到了我们的后排,那时节和大颠同桌的好像是金哥,可大颠的另一个同桌在好多年之后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一开始我是不认识大颠的,也没留意大颠是啥时候跑到我后排来的,后来听到友哥叫他大颠,我这才知道他是大颠。然后他也叫友哥做傻友,他们俩一个大颠一个傻友,真的是一对活宝。

大颠据说是学美术的,那时他们刚从外面写生回来,回来复习文化课。大颠他还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成员,他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他的口头禅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继续努力和周星星的别人笑我太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这别人是无法干涉的,但他老是在赞这个党而贬那个党则令我不能不时不时地和他辩论一下下。
不过我和大颠那些关于历史真理的大讨论通常都是不能达成一致的见解的,所以搞得我不得不再化了更多的时间去和他继续那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可是越论却越没定论。其实那会儿我是很自信我的历史知识,所以我一定要驳倒大颠。可都驳了N次还驳他不倒真的让我有点躁火。而最让我觉得抽象的是,每次在和怪兽或王王她们讨论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达成一致的见解,为什么这些东东搬到了大颠的思维里却来了另一个解读呢。我就酱子乱七八糟地和大颠扯了一大通历史的东东,然后怪兽终于发现我走火入魔了就一把拉住了我把我的元神拉了回来。是怪兽的那句话使我清醒了过来的,怪兽说他本来就是大颠,我们正常人和这种口味的人是沟通不来的。

所以那一次我就以一道历史填空题终结了我和大颠之间关于历史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我说,我绝对有理由怀疑你不是学历史的,酱子抽象的理论也能给你搞出来。既然你那么推崇你的那个党,那你说现在是民国几年。
唔——唔,民国八十七年,不对,应该是民国九十一年,是不是?大颠这一把可真被历史忽悠住了。
民国九十三年——这是在历史题上的说法,我们是说公元2004年或建国55周年。如果你不能确定就去问历史老班,他会很乐意为你们美术界的精英传道授业解惑的。记住了,下次别丢了你所谓的那个什么党的什么革命会的脸。

然后我和大颠关于历史真理的大讨论才酱子告了一段落。而当大颠在下午第三节自习课闲着没事的时候再来找我开片的时候我都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再见。直到那一次历史老班在班会课上发表其关于征收资料费的演讲,大颠就老班的一些过激言论也发表了一下下他的见解,我这才发现大颠有时候也会说些人话,然后才又和他继续那些天马行空的讨论。这一把我和他的看法倒大多时候是一致的。只要我能憋着不和大颠讨论那些这个党那个党的东东,很多时候我们的话题都是放得开也收得回来。
不过我总感觉大颠也不像是学美术的人。虽然我没见过他的真迹,不过在我的想像中老觉得大颠画的画应该就和《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个竹枝山画的那幅“小鸡叨米图”或华武的那幅石榴姐漫画差不多口味的东东。

其实我酱子说是很有根据的。我还记得那是鸟洲的一个春天里的一个下雨天,那也是鸟洲的第一场春雨,然后我种了一年多的那盆下雨花冬眠了一个冬天终于在这场春雨中开花了。那一盆白色的小花开得很审美,它是在我的高三时开花的。这盆下雨花也就是王王在她的《这么近 那么远》里所叙述到的“还有不知谁摆在讲台上的那一盆淡淡清香的无名小花”,在此我要说明的是,讲台上的那一盆淡淡清香的无名小花是我摆上去的,那是我和怪兽种的一盆下雨花,它不是无名小花,它叫下雨花。所以在它开花的那一天果真下雨了。
然后我就叫大颠给我的那盆下雨花画张像,因为那时节的数码技术还没普及要不我会给我的下雨花拍张相的酱子就简单多了。理论上讲大颠是学美术的叫他即场来张画应该是没什么技术难度的吧,因为那天中午我就在座位旁边看到那盆下雨花的画像,又因为那画像上有一个脚印我才没捡起来收藏,所以我想大颠应该也具有这种技术的。而且大颠他一直都在忽悠我给他讲解数学题或历史选择题最抽象的是他居然还忽悠我给他查一模的标准分,而我现在只是忽悠他给我画一幅下雨花我想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可大颠这只家伙最后还是忽悠了我,后来在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他还是没给我把那画画出来。早知酱子我就叫Jian来画这个画了。不过那时节Jian已经给我画过一幅西洋倩女图了就不好意思再麻烦她了。大颠说那下雨花他没给我画出来,不过他会帮我画另一幅画,等过了那个六月给我。然后我就说那时我们都不在这个破教室了他还怎么给我。他说反正他有办法就是啦。我说那好,这次不要画花,要给我画一棵树。

那棵树就是我和王王在上学路上看到的在沿江路上的那棵不知名的树。关于那棵树我和王王在放学路上是常讨论的,王王说那是她发现的一棵树,而且是一棵正在慢慢长大的树,在冬天的时候它只是一树的虬枝给人一种好冬天的感觉,而春天来了它就会吐出嫩芽再慢慢地长成一树繁密的绿叶。那时节我和王王有时会讨论的还有桥头上面的另一棵不知名的树,那棵树就是我发现的了。我对王王说,等那棵树开出一树像凤凰一样火红的繁花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小城了。现在看来,我想那一树应该是鸟洲的凤凰花。
就在我和大颠狂聊天的那会儿,一鸣突然问我为什么不下棋。然后虹虹就说我已经被大颠迷得差不多了,哪儿还会想到下棋。对于虹虹的个人见解我是不准备发表什么见解的,不过我很确定大颠没有迷倒我,在我的正是高三时,是没有哪个人能迷倒我的,只有历史能迷倒我。而且那时节我感觉自己的鸟洲象棋已经下到了最高境界,所以对下棋也就不怎么感冒。其实有时候我做好多东东都只能维持三分钟热度。
好多年之后,当我在回忆我们的高三那一段时光,最使我抽象的是,我们的另一壮举——象棋居然能下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们下的象棋和中国象棋不同,这个是地道的鸟洲象棋,只需用半个棋盘,棋子是盖着的,以“消灭敌人的人生力量为目标”,谁把对方的棋子都杀光就算赢。

我们的象棋开战场面是酱子的,一到课间,一鸣和亚丫就杀开了,然后我和虹虹也加了进来,有时怪兽也会掺上一腿,再有时候王王也会在一旁静静地边听周杰伦的歌边看我们开战。所以说一盘棋不是两个人下,而是几个人一起下,观棋不语真君子在这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到高考前夕,那棋盘已给我们磨得很光滑的了。然后我才想到那个象棋是小笨在开学初送我的生日礼物。
在那一年的下棋事件中,我也悟到了一些棋道,那可是我在那个非常时期所悟到的一些很珍贵的棋道。其实鸟洲棋道也是很讲求技术的,虽然那棋在开局的时候是暗棋,运气占有一定的概率,但是在棋逢敌手的时候绝不是一个运气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要不放弃,充分利用手中的棋子,即使一开局那个将军就瓜了也不会影响整局棋的胜负,最后也有可能反败为胜,要不也能来个和局。这也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下鸟洲象棋的原因。因为鸟洲的象棋任何一个棋子都是很重要的,这不像中国象棋,常会被对手来一招弃车保帅,而在这象棋里,将帅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时在残局的时候不是来一招弃车保帅,而是来个弃帅保士。最抽象的是,即使没了将军也没关系,棋局仍在继续,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谁赢。当然,在鸟洲象棋中,我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表面看似是运气占主导地位的棋局其实最终还是由技术决定胜负,而这种棋艺就是一种不放弃的棋艺。而且在这种口味的象棋里,棋逢敌手的最终结果就是和局。
不过说来也抽象,在那一年里我们疯狂地下象棋。可是过了那一场传说中的高考,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我也再没下过那种鸟洲口味的象棋。可能是再也找不到那种棋逢敌手的感觉了吧。

感谢,持续更新中,原创不易,欢迎点评。
笔者简介
笔者名(网名)相里虫虫,女,1984年出生,广东省吴川市人。2008年7月大学毕业于大理学院(大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粤西乡村中学的一名教师。笔者长期扎根在粤西乡村基层,自称是一条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摆脱愚昧走向未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认真向上的蜡烛。业余爱好写作、旅游、烹饪、栽花种草。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民俗文学家,并以此为契机在十年间(主要创作期在2009年至2013年间)陆续搜集整理及创作了上百万字关于粤西民俗文化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如对吴川的民间故事收集整理和吴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田艾文化等进行收集整理并写成报告文学等,其中以吴川本地为主的粤西民俗文化为基础创作了代表作有合集《鸟洲》和《鸟语虫言》(均未出版,只是曾在相关网站发表过,并引起过一定的反响),文集中相关的篇目如《韩田氏族》、《红颜》、《送嫁姨》、《碎发时代》、《风花雪月》、《试论田艾的前世今生及穿越》、《虚构与现实的叙事圈套——记王小波<白银时代>》、《舌尖上的童年——民间故事篇》等在文学领域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形成了新的网络加粤西民俗的文学模式。
2019年《番薯者,飞薯也》入选由洪三泰、林育春、陈通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发行的《番薯崛起》。
2020年《给小红的一封信》获湛江市第二届中学语文教师下水作文竞赛评比活动二等奖。
2021年被吸收为本地作家协会会员,2021年8月底开通gongzhong号继续进行创作。
尊重小编,转载请注明出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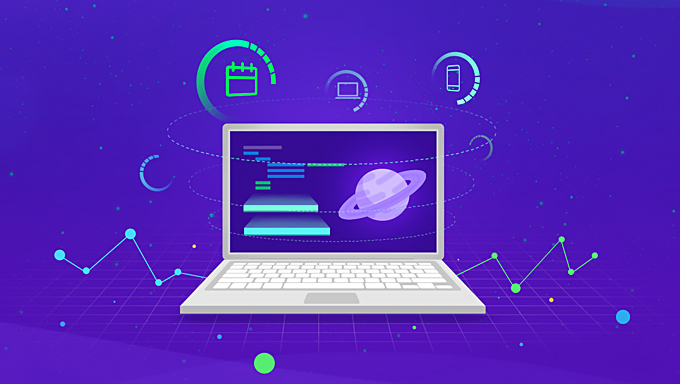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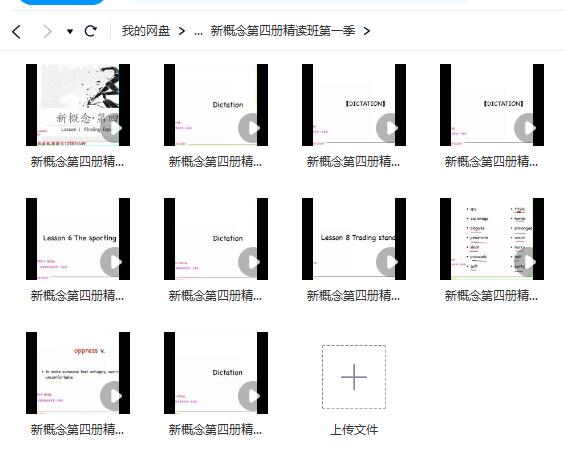
![【刘勖雯】2023高三高考历史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百度云资源]](https://static.kouhao8.com/cunchu/cunchu7/2023-05-18/UpFile/defaultuploadfile/230505ml2/90-1.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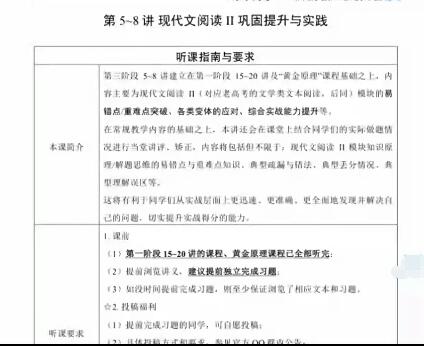
![[全套视频] IOS培训班第四期 基础+就业班 完整高清版](https://static.kouhao8.com/sucaidashi/xkbb/57e981572d8ab32df30394459e6df27b.jpg?x-oss-process=image/format,webp/resize,w_88/crop,w_88,h_88,g_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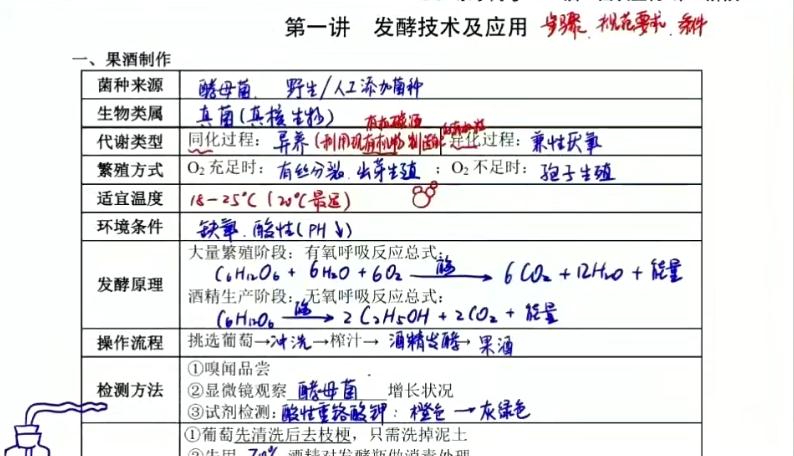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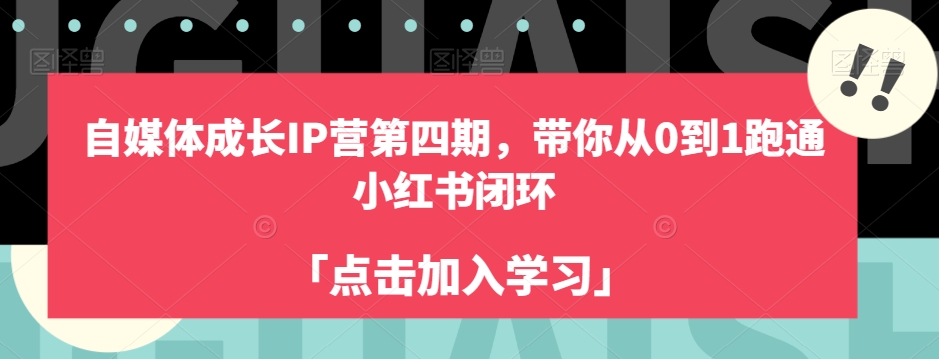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