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彼 岸(魏冶)
发布于 2021-11-11 18:04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 舟山 图片源于网络
彼 岸
文/魏 冶
一
首先是水,无涯无际的水。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想象中被过度开采的海洋宝库,中国三大渔场之首的舟山群岛,却气质安静,海水碧蓝。
深蓝的海水并未掺入太多可见的杂质,一波波朝外洋接连涌去。
阴雨蒙蒙,我乘船自沈家门出发,往海中的普陀山里去。
甲板上,天色阴沉,打着伞,我出神地凝望着船后被切割成无数菱形又重新汇聚的海水,螺旋桨搅起的泡沫浮出水面,又散尽在波浪中,陆地正朝我们远去。
颠簸之下,凝视海面过久的我几乎要把飞溅的海浪和飘散的雨水混同在一起,我稍稍倾开半盖雨伞,让雨丝飘落到我的脸上,加深这不安的氛围,这一刻我几乎以为我已是惊涛骇浪中的一片树叶,不知道是否还能顺利到达对岸。
然而理智告诉我,脚下现代化的机械船能够在三五倍的风浪之下毫发未损地抵达。
但幽蓝的海水却像在发问,五百年前,一千年前,同样的海域上,乘坐简陋木舟的漂流者心中有着怎样的惊疑和恐惧?
我不由想起了普陀山“不肯去观音”的传说,这个传说如此富有戏剧色彩乃至不下于任何小说,南宋宝庆二年(1226),由罗拔、胡渠修等编写的浙江宁波地区方志《(宝庆)四明志》卷一一《寺院·十方律院六》开元寺条记载 :
又有不肯去观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惠锷诣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见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锷即肩舁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锷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锷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唐长吏韦绚尝记其事。
不难想象,坐在舟中的惠锷面对难测的天威,为了满船人的性命,即便万分不舍,也只好就地将观音像放置在普陀山。这一神迹让舟山的信众们笃信,为了能够庇护百姓,观音选择留在舟山,镇守海疆。秉持这个信念的渔民相信即使一叶扁舟,惊涛骇浪,也必定能从海上平安归来,于是普陀山下,千帆竞发。
不到水上来,不会发现,水,才是菩萨无边无际的道场。
二
雨渐渐停了,碧空如洗,普陀山在望。
同为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比起九华山、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地方狭小,孤悬海外,交通不易,却香火最盛,是何缘由?
彼岸。
东来千年,佛教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什么?生死轮回的论说?明心见性的体悟?综而言之,佛教最大的贡献,是为深具务实精神的中国人提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们可谓之彼岸。
《大智度论》十二云:“以生死为此岸,以涅盘为彼岸”,对比即生即灭的此岸,逃脱了尘世烦恼的彼岸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之地。在丛林修建中,为了能更加切近佛典中的境界,僧众把佛寺筑在深林之中,白云之上,意欲以白云为屏障,隔绝两界,营造出尘意味。
对惯见山林平原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没有哪里比大海更像一个不生不灭之地,那里的海浪无论飞溅起多高,终究要落回到海底,这些历千载不变的海水,仅仅在一个大范围之内流转着,面向阔大无垠的海洋,陆地上的居民们感觉到浩浩汤汤的气概和超脱生死的气质,而越过这片海洋,一方幽静的岛屿突出洋面,岛上山势挺拔清幽,山泉淙流,绿草如茵,瑞兽漫步,这难道不是典籍里佛国乐土的再现吗?普陀,这孤悬海外的一方秀屿,遂成为了信众心中彼岸在人间的再现,也无可争议地成了为在中国有着最广泛影响力的菩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在这人间的彼岸上,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天光海影的风味,海市蜃楼的奇景,几乎所有居住在普陀及周边岛屿上的居民都能言之凿凿地说出自己目睹这些奇观的经历,并把它视为菩萨显灵的瑞相。这种神秘而迷人的氛围绝非是山民妄语,就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游览之后口述的《游普陀志奇》里,也讲述了同行人皆无所见,惟自己遭遇“宝幡舞风”“奇僧数十”海市蜃楼的见闻,惊异地感叹:“余脑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普陀山的神秘可见一斑。
也许就因如此,在主张见性成佛、佛教仪式简洁的禅宗丛林里,普陀山的信仰力之绵密是罕见的。行走普陀山,你时常会见到身披黄衫的僧人或者身形各异的信众,随地匍匐,行五体投地的顶礼。这种信仰之深,有时竟达到了让人不忍的程度。据传在唐宣宗年间,有梵僧到普陀山梵音洞前,自燔十指,而见观音现身。千载之下,即便稍微想象十根手指在烟火中一一烧尽的场景,也觉得周身寒冷。但神奇的传说引来了络绎不绝的追随信众,自残乃至舍生者络绎不绝,迫使明清的地方官屡立《禁止舍身燃指》碑和《舍身戒》碑等劝世碑文,这股自残的风潮才慢慢息止下去。
船即将到码头,细雨飘落中,甲板上的两个阿姨望着黛青的山色,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口诵阿弥陀佛不止,她们心中的佛国到了。
三
初登普陀岸,我抱着要把普陀山的寺庙古迹一一仔细游览的兴味,但很快发现这只是空想。这方小小的岛屿上,各式各样的寺庙、佛堂、僧舍等数以百计,密度之大令人惊异,正所谓“三大寺、六院、八十八庵、一百二十八茅棚,有言皆寺院,遇人即僧侣”,行走岛上,会发觉明人徐如翰“山当曲处皆藏寺,路遇穷时又逢僧”的描述已经不足描绘现时普陀山的香火旺盛了。我只能加快步伐,期望对普陀山的寺庙有一通观的印象。
在走马观花的漫步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雨寺。
法雨寺,三字匾额探出绿树之时,似乎万籁都寂,惟有这三个字造成的回响在我心头盘旋。似乎恰因今天有着蒙蒙细雨,如烟如雾,而我柳暗花明又一程,撞见法雨寺,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细雨直下,不用一言我已经懂得它的内涵,雨丝自然飘落在万物之上,不分高低贵贱,它既飘落在顶礼者那样的信众身上,也飘落在我这样的行走者身上,既飘落在井水里,也飘落在坟墓上,既不以飘落在汪洋大海里自惭渺小,也不因飘落在龟裂的田地里自矜功高,它持续飘落着,如同佛法无所不覆,无处不达。
这不得不让我再次叹服佛教说理的艺术——世界上任何宗教都在说理,但绝少有像佛教这样说得别开生面,一片主观,但又充满意蕴,让人感觉清新烂漫,天真无暇。
雨让一切都清晰,也干净了,法雨寺前后的参天古树静默着,如同参禅的居士。亮晶晶的路面上,僧舍向上延伸,和尚们时隐时现,轻轻地走着,仿佛与这佛寺融为一体。而这寺、这僧,仿佛也辨认不出年代,黄墙绿树之下,他们似乎从古代的庭院里迈入,又随时要从未来的大殿中迈出,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历千百年而不变的简洁禅居生活。
如果愿意翻阅一些普陀山建寺以来的典籍和吟咏的篇章,会发现僧侣是普陀山诗文中不可忽视的一脉,他们用文字记录下清洁简朴的生活和参禅悟道的体会。其中尤以释海观的《山居偈》组诗最为朴素动人:
“清晨上磐石,观兹旭日辉”、“闲涉松竹林,捡拾朱红菌”、“荡钵群猿捧,经颂众鸟亲”、“山路适樵子,斋头转古帖”——《山居偈》
这些描绘岑寂禅意生活的诗句,把人带回到诗人描述的时代,也帮助我们理解了现时普陀山充满禅意的生活。虽然年代变易,但在这彼岸之上,一种精神气质依旧完整地保留着,持续地撩动来访者的一丝幻梦,让他们忍不住想割舍上船前的一切,在这里度过余生。
但禅意广大,并不代表着不问世事乃至与世隔绝,抗日战争时期,东部的抗日前线上忽然出现了一拨特殊的医护人员,他们衣着简朴,头颅浑圆,带着慈悲的面容,极富耐心地救治伤员,仿佛一股清流。他们是普陀山应抗日旗帜号召奔赴前线的百名青年僧侣,也许是禅居的生活令他们相信,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也未必无法变为静谧和平的乐园。
四
正午抵达南海观音立像,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打消了上去的念头。
金沙滩上,观音和我一同望着辽阔无涯的大海,正午阳光直泻而下。强烈的阳光刺激我的视网膜,恍惚中我似乎看见海天相接的尽头出现了几个小黑点,并且愈显愈大,我心下揪紧,那是否是黑色的军舰?
军舰乘风破浪而来,巨型炮塔指向天空,浑黄海水在四周搅动,海鸟惊散,我似乎已经隐约听见炮弹在地面的炸裂声,黑烟漫过天际,人群四下奔逃,就像历史上普陀山遭逢多次灾难一样……
我急忙揉了揉眼睛,海风爽人,人群自在走动,观音像依旧含笑向洋,海平面上空空荡荡,这一切不过只是我的臆想。
原谅学历史出身我的臆想频出,但我又怕这臆想不仅仅只是臆想。
普陀山紧邻舟山群岛的最大岛舟山岛,背靠宁波,是海路要道。从唐代始,明州港(今宁波)就是重要的转道港口,普陀山作为出入明州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了海上要冲。开山建寺、大兴土木亦从唐代徐启大幕。这样一个从古开始就传扬佛法,与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文化关系密切的胜地,真的能简单视为人间的彼岸吗?
我不知道,当皇家进香车辇在普陀山上行进,当士人大夫对着海浪吟咏,他们有没有想过,在看似平静的大洋之外,隐藏着怎样的世界,怎样的人群,海洋会永远平静吗?当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人跨洋而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战而胜之,我们又是否真的具有将普陀山永远作为一个海天佛国祥和之地的能力呢?
但我能想到的是,在转述“不肯去观音”故事的时候,无论是士绅大夫,还是农人渔民,必定心中充满了文化优越感——华夏之外的地方,皆是文化弱势群体,他们是需要来中国“求”文化的,至于求不求得到,拿不拿得走,还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比如佛法不肯远渡东洋就是如此——神话映照制造者的思想,东海波涛里的不肯去观音传说,除了映照出神秘和禅意,也映照出民族的自大心理。或许我们忘了,禅宗固然是基于中国本土加以结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但它的思想根源来自异国,我们何尝不得益于吸收异域的文化?可是从东汉开始垂千年,我们却逐渐停止了大规模吸收异域文化的过程,自我眼界膨胀的同时,对外洋懵然无知,从这个意义上,普陀山确实是一个彼岸,是我们画地为牢的界限。
于是让人不忍提起的事情终于发生,英国的军舰洋洋得意地来到东海水面,简单交战之下是帝国羞耻的溃败,第一批被迫向洋开放的口岸里赫然标着:宁波。虽然因为疟疾等原因,英国将割让舟山转为索要香港岛,但硝烟未散、血迹未干的定海,标志着这块福地和平自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然而历史是否是在鸦片战争时才显示出迹象呢?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当大明王朝被满洲的铁骑冲的七零八落之际,南明的朝廷退据舟山作为基地,拿着大量的佛学经典为筹码,准备去日本乞师勤王,却无功而返。对比于唐代菩萨不肯东渡,这一次佛典漂洋过海却被人拒之门外,难道不够给时人以警醒吗?普陀依旧是海天佛国,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只要焚香跪拜,默诵佛号,就可以脱身尘世之外,甚至与人间彻底隔绝,一次次在王朝更迭之下屡废屡兴的普陀山说明,普陀山是国家兴衰的缩影,想让它的佛教文化焕发更大的光彩,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它为和平环绕,也必须时时保持对世界动态的观察和思考。想想普陀山开山建寺的时代吧,当普陀山伐木筑基,预备种下灵根的时候,风雪里,韩愈因为谏迎佛骨的反佛思想行走在贬谪的路上。我们不去争论谁对谁错,但我们必须认识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思想的多元才能保持思想的活力和警惕,才能不陈腐而健康。
带着这凝思,我侧身再看这座大观音像,似乎又悟出一些今人塑此巨像的寄托,这一尊高耸入云的观音,能在洋面上远远望见,散播佛号,它无疑是渔民得以心安的灯塔;而它面向东海伫立,能观普天世情,眺望水天极处的面孔上,则是永远凝视外洋八方的深邃目光。

本文刊载于《延平文学》
2021年 第3期

来稿可联系:18905091313(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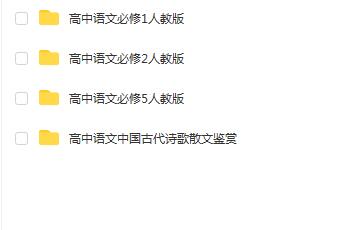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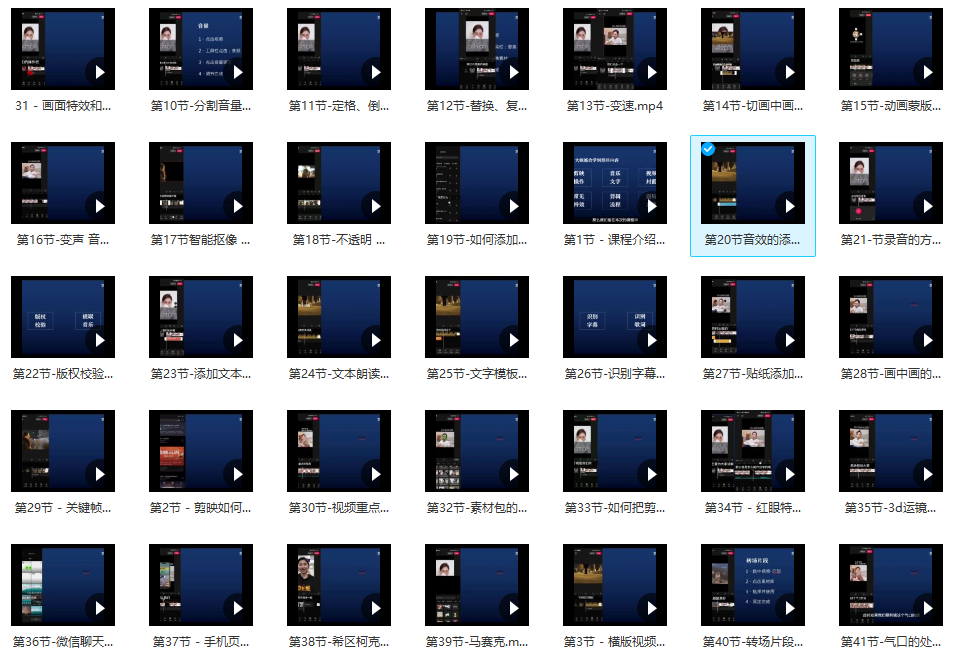

相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