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旧文拾掇 庙与学校(六) 2021年第103期(总700期)
发布于 2021-11-26 19:05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化处全景周光容摄

庙与学校(六)

宋茨林
十八
前文说我最终摆脱源自古庙深处的梦魇是因“一次惊人的发现”,此说实是一种夸张一种噱头,但也并非专为制造“悬念”。
照理说,读书之人教书之人应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但在浩劫之年,不要说是好书,就是一般可读之书也大多被打入另册,就连教科书也曾一度断种,可见“大革文化命”之彻底。
课余无书可读,我用三个办法打发时间:一是批改作业如皇上批奏章,如挑花绣朵针脚细密;二是如老僧静坐古庙深思默想,常作参禅状但却心猿意马难拴;三是走村串寨交朋结友,让宝贵光阴在唠七诨八中悲惨流逝。
从我在其间教书的胡家弯古庙出发,翻过南面的山冈再往西走,便是化处火车站。火车站北侧是一个叫播仁的村寨。播仁小学里有一些可以谈心的教师。从播仁往西去便是六枝县的地盘了。在播仁南面,隔着铁路的田坝中央,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村寨叫底播。底播系六枝县属,那里有一位在化处做民办教师的、出身为“地主”的年轻知识分子,姓王,可以交往。

胡家弯周光容摄
从古庙出发,向北下山,便是化处场坝。进入场坝前得先路过又一座古庙叫“仙人寺”。庙前亦有两株高大的银杏树,庙内亦有学校,底播那位家庭出身为“地主”的王老师就在这个学校任教。据传这个王老师很有学问。村里人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后证实他在外地读过两年中专。我慕他名,去仙人寺里听他讲课,想通过“观摩教学”学习教学经验。我发现他教学能力不强,与我相距远矣!但他的学生却在场坝上四处散布流言,说我这个胡家弯小学的老师是他们王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而我的学生则愤愤不平地为我四处辟谣,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些许安慰。

仙人寺 周光容摄

仙人寺周光容摄

仙人寺远景周光容摄
后来,我又陆续认识了水母小学的邱老师、华老师以及在场坝小学代课的王老师等等。
各个学校的老师们似乎也很无聊,便决定排演样板戏《红灯记》——“整本”!实话实说,作为“样板”,《红灯记》的艺术水准是很高的,演出难度也很大;“样板”中的演员照现在的说法,都应属“国家一级”;“样板”中的唱做念打、音乐、舞美等等,要求很高,岂是一伙乡村教师所能完成的——而且是“整本”!老师们热情很高,场坝上的王老师毛遂自荐出演李玉和。王老师身材瘦小,出演叛徒王连举还差不多,但他坚决要演英雄李玉和,其他老师们也都同意了并力邀我演鬼子鸩山。我想,有我这样漂亮的鬼子吗?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但我经常参观他们排戏。他们排的戏,像川戏、像地戏、像花灯、又像是某种从未见过的“说唱”,反正不像京戏,更不像“样板戏”。然而他们很认真、很快乐,而且很快就在场坝的土台子上“正式演出”了!演出时看的人很多,很热闹。如果以“样板戏”为“文革伟大成果之一”的江青得知,不知是要恼怒还是要欣喜。是要褒奖还是要痛斥?

样板戏《红灯记》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演员”给沉闷的场坝带来了笑声,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略带苦味的欢乐。而更主要的,是我与其中的一位“演员”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这个朋友神秘地问我知不知道我教书的那个古庙曾办过农中,我说知道。他考虑了半天后对我说,庙里有间空房,里面有个柜子,柜子里有宝贝!我问他哪间屋子哪样宝贝。他说是做过农中保管室的那间屋子,什么宝贝打开屋子打开柜子就知道了。
这位朋友是喝了点酒才说这番话的,说话时神神怪怪,与庙里的气氛十分吻合,我当时并不在意。但有时路过那间“藏有宝贝”的屋子时心里怪怪的。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夕阳的余晖照着那间神秘的屋子,我从门缝往里窥视,果然有个柜子。静极了,夕阳透过西窗射入屋内,阳光映着微尘,形成一道斜而笔直的光柱。仿佛这光柱正发出一种神秘的激光微响弥漫在整个庙中,使整座古庙更加寂寥。我立即想起了许多关于剑仙,关于大侠和关于鬼狐的故事。而此时只有我一人在此庙中。
我反复劝说自己不要造次,但一种探宝寻秘的冲动使我做出了平生最英勇的决定——我使用敲钟的铁锤击落了门上的锈锁,闯进了那间神秘的屋子。
十九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我麻起胆子破门进入那间布满灰尘的屋子。那个柜子——那个据场坝小学的老师讲藏有宝物的柜子静静地立在我的面前。我不希图什么宝物,在这样的荒山野庙中能有什么宝物?但是,这里曾经办过农中。因此我的心中扑腾着一个强烈的希望——打开柜门,便是满满一柜子“禁书”——满满一柜子!金圣叹说“雪夜读禁书一大乐事” ;“古庙读禁书”岂不更乐?
但我突然后悔起来,我这不是做贼吗?背上贼的罪名,不但会丢掉吃“转转饭”的饭碗,而且可能还会遭到造反派无法无天的处罚。这个念头一出现,耳朵里立即响起一种极细微但又极强烈的声音,像是天边的海啸,又像是大山的呼吸,极模糊而又极真切,在古庙中四处弥漫。似乎又有一个声音响在我的耳际:“读书人窃书,能算偷么?”这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说话。那么,动手吧!
后山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像一滴强力洗洁精,滴落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切都立即清晰洁净起来,“海啸”消失了,幻听消失了。这是一个平安而又美好的黄昏呀!
但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宋老师,你在找哪样?”
这不是幻听,这是人的声音,像一声炸雷,令我猝不及防,惊得我魂飞魄散。
我缓缓转过身子,面对我的,是一个瘦高个男人,长腿长脸长下巴,形如图画上的朱元璋,弯弯的小眼睛里盈溢出善良的笑意。他叫王义元,是胡家弯大队的会计,我的朋友。
王义元是学校的热心支持者,常常在队里替我说话。他的娃娃还小,没有来读书,但他希望我教下去,以后把他的小儿子教成才。王义元上过几天农中,农中也是中学,因此他认为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而且只有我与他有“共同语言”。王义元很善良,是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农民。与我同在胡家弯教书的那位知青的母亲去世时,王义元出了大力,他领着我挨家挨户地收“酒票”,提了一大塑料桶包谷酒到安顺送礼,解了办丧事的难题。在那个年月,这种朋友是十分可贵的。

双凤山寺 周光容摄
面对笑眯眯的王义元,我完全放下心来。我问他上山来做哪样?他说来叫我去吃饭。我说你家娃儿又不读书转不到你家。他说今天不吃转转饭了,去王XX家吃满月酒。我说我没有礼送。他说不要你送礼,请你给他娃儿取个学名就得了。我说你是大队干部,你不会取?他说我的学问赶得了你宋老师的脚丫巴?是人家瞧得起你!
王义元说:“你要找哪样?我帮你找!”
我说找点教学用具,他说找得到个干㞗,像样点的样什早百年就遭狗日的些掳光了,还落到你来?
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忽地一下把柜子门打开了,我立即凑上前看,希望“早百年狗日的些掳光”的不是书,也就是说,希望柜子里装满了书。
然而我失望了。柜子的上面几层是空的,只有最下一层堆着些旧资料,王义元扒开那些积满灰尘的旧资料,露出了几本书!
王义元说:“拿走!送你!”好像是他的东西。
走出那间屋子,王义元把掉在地上的锁挂在门上,又骂了声干㞗!
书一共四本,最厚的一本像块砖头,叫《教育诗》,第二厚的一本叫《堂·吉诃德》;两本薄的都是白皮红字,一本叫《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另一本叫《反杜林论》。在曾经办过农中的古庙里找到四本书,而且不是偷的,也不是“窃”的,是大队会计兼共产党员再兼好朋友王义元“送”给我的,哈哈!
王义元说:“走,喝酒去!”
我一边跟王义元下山一边寻思,“狗日的些”为什么会留下这四本我从未读过的书?可能是农中教师水平低不识货?可能是因为书中人的名字太长太难记?很可能!《教育诗》是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的著作,《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则是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读起来十分吃力,犹如读“天书”!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图片来源网络
是的,这些外国人写的外国书真不好读,首先是人的名字难记,就连我这样记忆力极强的人也是记了好久才记住了塞万提斯的全名,叫做: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是的,在这个古庙里,我将要努力记住许多人的十分难记的名字,我将要孤独地与他们在油灯下逐一会晤。
那天,我给刚刚满月的那个男婴取了一个十分好记的名字——“书海”!
二十
《堂·吉诃德》是一本十分有趣的小说,极富喜剧色彩。1605年出版第一部,1615年第二部问世。400年以后,这部小说成为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堂·吉诃德也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在世界向前发展之时,吉诃德逆潮流而动,偏要扮演中世纪的游侠骑士,闹出了许多笑话。吉诃德的怪异行为使我想起了化处场坝上那些“反潮流”的造反派,我在古庙的油灯下一边读一边笑出声来。我这个人在“官场上”永不成熟,但在“政治上”却自认为是早熟的;当我读到吉诃德向巨大的风车发起进攻的那一段时,我不禁掩卷沉思起来,并在油灯下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挥舞长矛催动瘦马/向风车发起进攻/地球的这边正在日落/孤影拉长在夕照中/他背对太阳狂歌/理想让他发疯/他错把自己的影子当成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
题目是《给堂·吉诃德画像》。我自认为诗写得不错,而且抓住了小说的要害,事隔多年,才知道并非如此。最近我读到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索飒的一篇论文《挑战风车的巨人是谁:塞万提斯再研究》。这篇论文援引上世纪学者马埃斯图的观点:“真实性不可或缺,把风车当成巨人不只是一种幻视,更是一种罪过。”而索飒研究员在梳理了20世纪西班牙语学术界对塞万提斯研究的成果,客观而审慎地排列诸家所说之后得出了他自己的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堂·吉诃德》这部世界名著之中充斥着对当时西班牙所执的宗教压迫和血统清除国策的控诉。”

《唐·吉诃德》图片来源网络
可见,当年在胡家弯古庙里教书吃“转转饭”的年轻教师“自认为在政治上早熟”是多么的可笑。然而,今天对《堂·吉诃德》的进一步的政治解读却与当年在古庙里的秉烛夜读有着血脉上的关联。在当年,即便是世事洞明的资深学者们,谁又能指出吉诃德的“幻视”和“罪过”,谁又能讨伐“血统清除国策”的反动走向呢?
当年我在古庙中对吉诃德形象的思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80 年代对《射雕英雄传》中“西毒”欧阳峰这一艺术形象的哲学探讨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欧阳峰武功盖世天下无敌,但终因走火入魔,竟与自己的影子作拼死之斗,最后心力交瘁而死。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只有他有力量自己消灭自己否定自己。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凭恐龙之巨大,谁敢与之争锋?但正是因其过于巨大而终至毁灭。
产生这些力不能及的思索,与在庙里读的那两本书有关。《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真理是一个相对的、无限发展的联系的过程,只有骗子才会谎说“绝对的终极顶峰”。《反杜林论》则告诉我:封闭的体系是不存在的,要凭借有限的个人力量来建立一个永恒不变的封闭体系是徒劳的。当然,这两本书所阐述的远不止这些。这两本书的译笔真好,特别是(反杜林论》注释部分所引普列汉诺夫的精彩思辨更是令我如醉如痴。另外,说来叫人瞧不起,我是在安顺的花街书市上买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拿到胡家弯的古庙里来读的。那书的第一句就让我震撼、让我吃惊、让我感到绝美——“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我在原安顺地区二中读高二时就应业师王鼎三校长之命写过题为《论全世界都要走十月革命之路》的“论文”,写作之前竟没有完整地读过《共产党宣言》,更没有读过《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感到既对不起鼎三先生又叫人瞧不起。在胡家弯的庙里读这三本书,体味了一种思辨的快乐。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所说的“惊人的发现”。我说这“惊人的发现”使我摆脱了独宿古庙“夜半惊魂的梦魇”,确实有故弄玄虚制造“悬念”吸引读者的欺诈嫌疑。但宽厚的读者应当承认,这也确乎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作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曾使我们一度陷入空前的“梦魔”;凭借什么摆脱这个“梦魔”呢?只能凭借理性的思辨,只能凭借对真理的探寻与解读!

《共产党宣言》图片来源网络
至于在庙里读的另一本书《教育诗》,那真是一部奇书,一部辉煌的改造灵魂挽救灵魂的史诗。在我心目中,其作者马卡连柯(前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在苦难中创办“工读中学”,把“少年犯”培养成工程师、飞行员、教师、诗人和作家。其中的故事,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使我在孤独、寂寞和苦难中感受到教师的伟大和教育的重要,使我认识到“停课闹革命”的罪过,使我在庙与学校中坚守着人类的尊严。
二十一
在胡家弯的庙与学校中,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我只有两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教书,另一件便是读书。并非我特别敬业特别好学而不爱玩,而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时间无处可去无处可玩;即使是在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其他节假日,我也很少回安顺。那时的安顺城口号连天派仗不断使人厌倦,而胡家弯除山清水秀之外还有“转转饭"可吃,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存身避乱的好地方。
每到夜里,空空落落的大庙里一片死寂,但在死寂之中却有生命的跃动。在那盏马灯的映照下,我很快就读完了王义元“送”给我的那四本书。其中《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了不下十遍,虽然至今年过天命都尚未读懂但我认为这本书阐释的是“真理中的真理”,对我的影响是难以言喻的。

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更没有卡拉OK和舞厅,八个“样板戏”已全部看过。化处场坝上偶尔放电影,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剩下的时间只有读书,在孤独寂寞中读得很细。有一次回安顺城,发现市七小的那条街冒出了一个旧书市场,大家称为“花街书市”。书市上摆放的是“红宝书”一类无可指责的“革命书籍”,但背底里却有人在干着出售“禁书”的“勾当”。先是向一位姓葛的老师购得一部《古文观止》和一部《诗词例话》。《古文观止》后来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诗词例话》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 年9月北京第一版,周振甫著“官价”8角6分。这两部书较之今天那些装帧华丽乃至花里胡哨的图书而言,纸张差之远矣,但朴实无华,难得的是几乎没有错讹,编校者的专业水准和文化精神令人怀念,特别是读到现而今某些错漏百出的盗版书甚至正版书时更是如此。把这两部书带到胡家弯的古庙里去细读、背诵,与那里的环境协调极了。细读这两部书,使我既领略了传统文化的精深,又体味到了汉语言的美妙。

《古文观止》图片来源网络
出让这两部书给我的葛老师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瘦男子。他之所以出卖藏书是因为他作为“右派分子”贫病交加;而他的藏书之所以未被查抄据说是因为他的一位学生是办事处的工宣队队长,暗中保护了他。我与他逐渐熟悉之后曾到过他家位于安顺西城小街的祖居屋,在那里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等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有的购得,有的借阅,都是在胡家弯的庙与学校里读完的。
后来听说这位葛老师终因贫病交加,忧愤去世,“右派”帽子始终没有摘掉。人且不保,书何以存?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均为世事左右。
后来我又认识了两位年长的朋友,当然都是男性。一位姓彭,平坝天龙人氏,西南师范学院高才生,以英国文学见长,但也是个“右派分子”。这个“右派”比上述姓葛的“右派”更年轻,仅30来岁,当时在跳蹬场中学代课,常常被人欺辱,另外一位姓杨,是个医者,爱好诗与哲学,写过上千首“十四行诗”,细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下百遍。我在他们那里读到了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他们则从我这里读到了胡家弯的古庙与青山——他们曾先后到胡家弯的庙与学校看过我,与我一起吃过学生家的“转转饭”。
说句实话,我之所以对近一个时期的一些畅销书包括《廊桥遗梦》之类不以为然,乃是因为这些书与我在庙与学校里读过的那些优秀作品特别是与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我之所以对某些眼下走红的人存有不敬之心,绝非我对他们心存嫉妒,而是因为这些人与我曾经相识相遇的那些身处逆境而能率真做人、历经磨难仍存天真之心的人们相比,实在不敢恭维。
二十二
这篇“纪实散文”写得够长了,应该打住了。但打住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算是“后记”罢。
最早动念写这篇长文,是源自钱理群教授的启发。钱先生对“新历史主义”的理念甚为重视,他认为,个人的经历以及无数平凡人的遭遇,往往能够折射出时代的特点,丰富历史的血肉,并以个案佐证乃至纠正历史的结论。钱先生作为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以及“拨乱反正”之后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不仅十分重视文学的“本质真实”,而且十分重视原生形态的“个案记录”。他在自京返安的几次学术活动中,都曾当面赐教于我,提倡“纪实文学”及“非类型化”写作。我常常这样想,像我这把年纪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后虽无轰轰烈烈的壮举和生生死死的传奇,但我们在物质匮乏和精神崩裂的“浩劫”中最终没有成为“垮掉的一代”,不能不感谢“十七年”的基础教育和中外优秀文化的滋养。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这个“石”,这个“火种”,应该就是科学教育和人文精神。正因为千千万万的平凡青年虽历尽磨难而没有丧失良知,这才铸就了民族复兴的“群众基础”,这就是“百姓故事”的意义,也是我要写《庙与学校》的初衷。

本文作者(右)与钱理群先生(左)《文化安顺》编辑部摄
后来,我把这个“初衷”告诉了郑正强先生。郑先生是作家、书法家、地方文史专家,是散文大家。他曾赠我一本书叫《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并嘱我精研细读,使我获得了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我曾多次说“郑老师教我学文化”,虽有“戏说”成分,但确有感激之情。郑先生在听我摆谈了《庙与学校》的构思后,不嫌故事琐屑,认为很有意义,要我认真去写,要写出一个边远贫困地区平凡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或许正因为平凡,才能够反映出一代人的遭遇和心声。
而今,钱理群先生年逾花甲仍在“追寻生存之根”,而郑正强先生却英年早逝令人哀婉。《庙与学校》作为一份学生作业,算是对生者的感谢,对逝者的追怀吧!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庙与学校”作为“物质文化”形态是一种物质结构,但又是许多“非物质文化”赖以产生的摇篮,因此又可理解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学、艺术和宗教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元素。宗教列入其间可能很犯忌讳,但百家争鸣、有容乃大,富强盛世应当有宽容精神。
这使我想起了弘一法师李叔同。
我在庙里读书和教书时不知李叔同为何人。有一次在安顺的花街书市购得一本旧书,书中夹有一个纸片,原书主用漂亮的毛笔小楷在纸片上写了如下的句子——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意境凄清苦寒,词句令人肠断,但不知何人所作,后来才知道是文化大师李叔同的《送别》,再后来从李晓先生处借阅《弘一法师传》,才又了解到李叔同的生平。李叔同是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法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和师范教育家。他出生于天津富户,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国立杭州师范学校任教。他的学生丰子恺和刘质平都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作为老师的李叔同更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艺术大师。令人不解的是,在物质和文化上均处于社会上层的李叔同竟心恋佛门,时时往来于杭州的庙与学校之间,最后竟在39岁时遁入空门,落发为僧,号为弘一,成为佛教律宗派大师,留下了我国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 图片来源网络
李叔同作为“优秀教师”和艺术大师最后皈依佛门,使我深为震惊,也使我深感庙与学校的紧密关联极其复杂和神秘,绝不可作简单粗率的论断。
我想,在旧时中国,庙与学校有着许多关联,孔庙就是教育与宗教色彩兼有的“物质文化”形态,的确需要作出特殊的解读。
学校,是培育科学精神的摇篮,而在真理面前,是否需要宗教般的虔诚?
庙与学校所孕育的人文精神,是否会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永远存续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
(2005年6月~8月)
(完)
· 作者简介
2021年11月
值班编辑:宋兴平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长按上方ErWeiMa《文化安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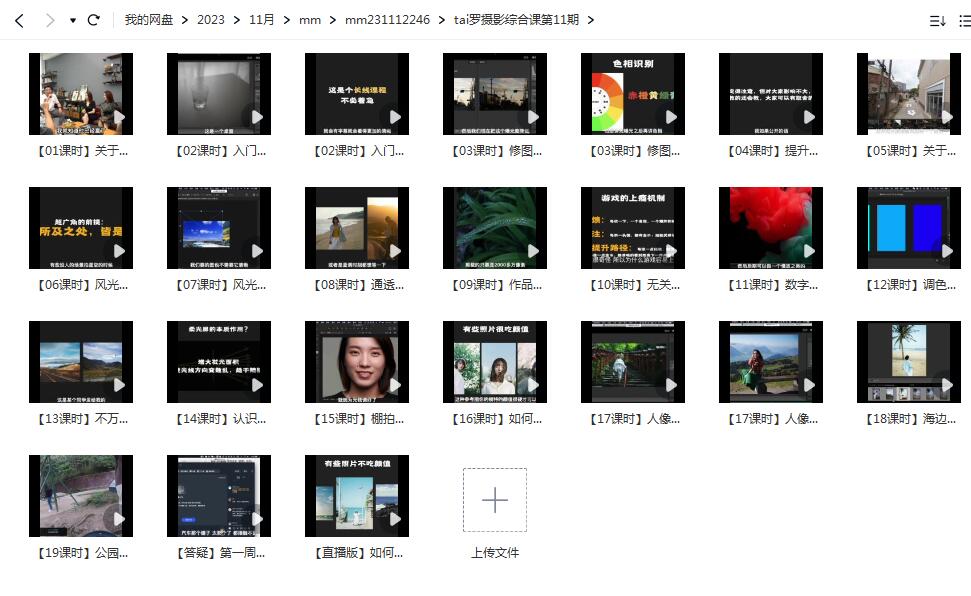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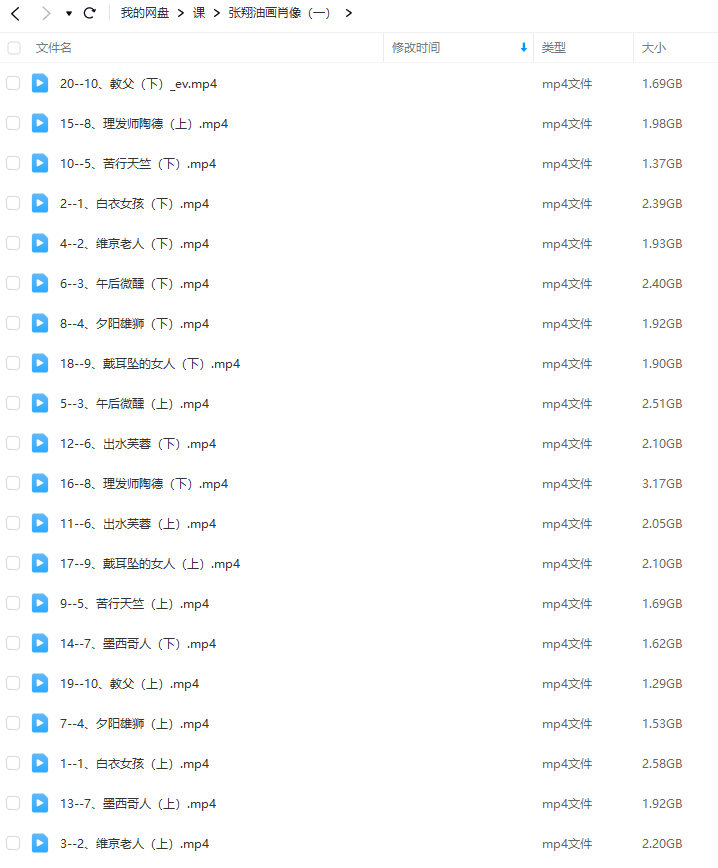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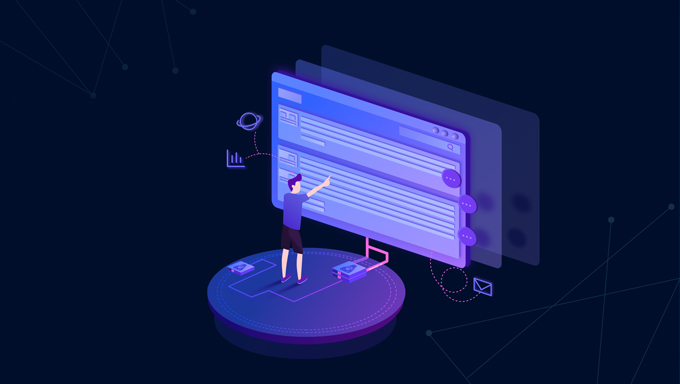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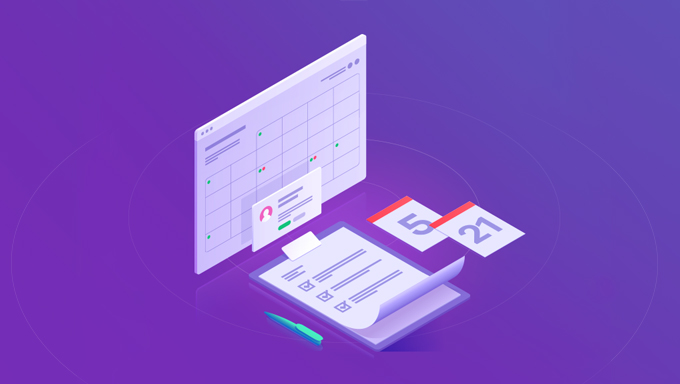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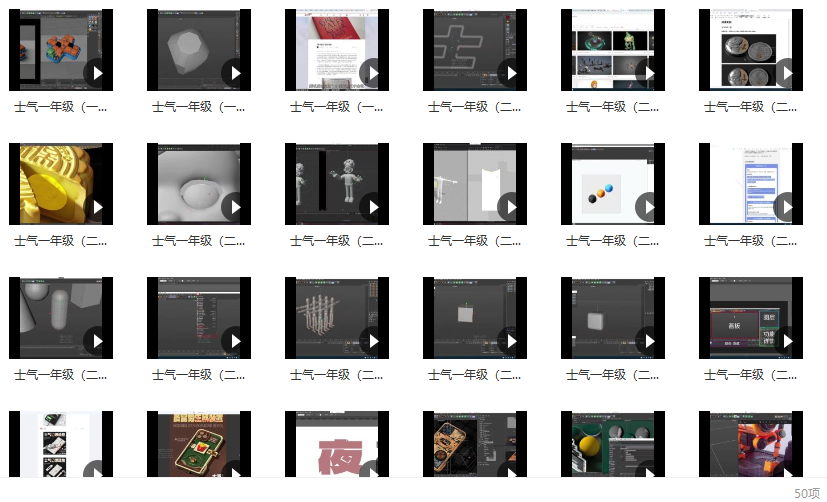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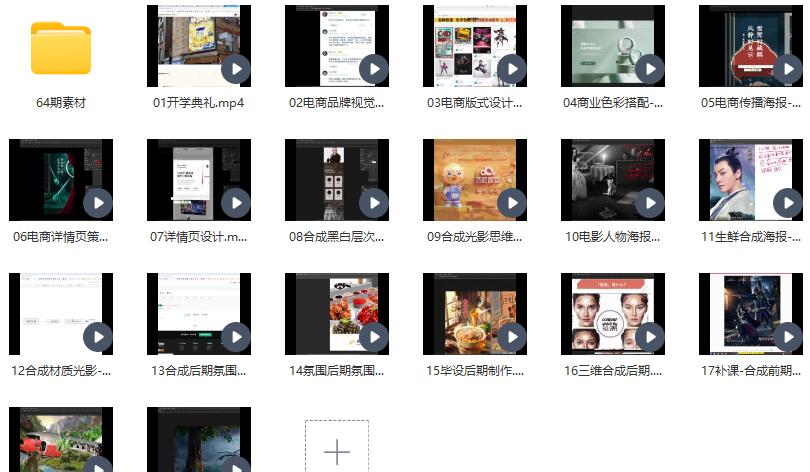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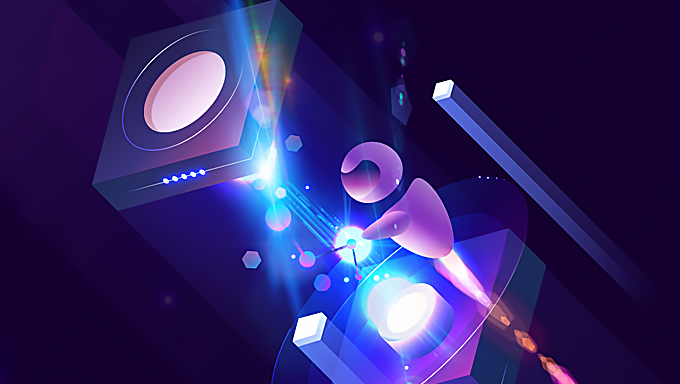



相关资源